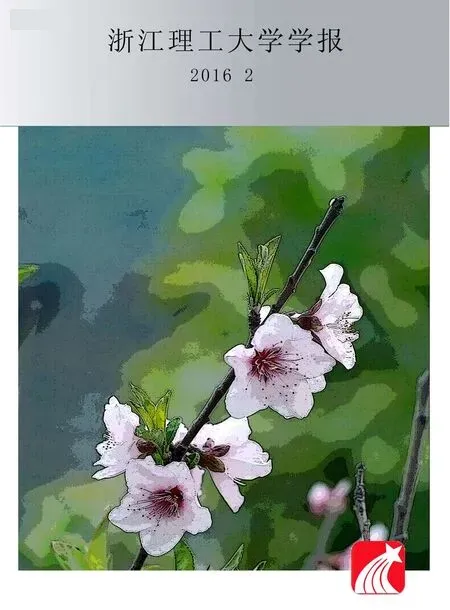组织传播视野下国际组织认同的构建
狄 丹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上海 200444)
组织传播视野下国际组织认同的构建
狄丹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以往有关国际组织的研究主要在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展开,侧重强调国际组织的影响和作用,而对组织自身运行中传播问题的论述则略显不足。国际组织传播无法回避其成员国来自多民族国家,成员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宗教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成员国间对彼此和组织是否存在认同,以及认同范畴的大小都影响着国际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文章以组织传播学的视角,对国际组织中认同问题进行分析,涉及认同构建的前变量的探讨、自结构构建与认同的关联以及外结构传播的选择等问题。文章认为对国际组织传播中“认同”的研究,不但有利于组织传播中组织认同问题的分析研究,也有利于我国融入全球化、集团化和组织化的对外交往,为我国参与国际交往和国际组织活动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组织传播;组织认同;国际组织传播;认同构建
组织传播学的研究最早开始于西方,其中以美国组织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厚,相关的学者包括:主张“传播提供组织一切活动”的罗杰斯[1],关注工业传播研究的瑞丁(W. Redding)[2],阐述传播过程中组织内、外结构、权力、象征性及历史影响的凯瑟琳·I·米勒(Katherine I. Miller)[3],提出组织传播是一个不断调节个人创意与体制约束之间矛盾过程的埃里克·M·艾森伯格(M. Eisenberg)和小H·L·古多尔(H·L· Goodall Jr.)[4],以政治学视角解读组织传播问题的丹尼斯·K·姆贝等。
多元化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丰富了组织传播这一交叉学科的理论,多角度阐述成为组织传播研究成果的主要特征。国内学界组织传播的研究脱胎于西方组织传播学。郑瑞城(台湾)1983年出版的《组织传播》中提及 “组际传播”;1988年戴元光、邵培仁等人合著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中明确提出的传播学的分支包括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内向传播;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象世界之谜》确认了组织传播涵盖了人际传播和自我传播;魏永征提出的组织传播最重要的特征是传播必须凭借组织自身的系统进行[5];中国组织传播学协会会长胡河宁的《组织传播学—— 结构与关系的象征性互动》[6]中对组织传播学学理性问题的多角度的论述;复旦大学谢静教授[7]强调了组织传播是动态过程,等等。一系列国内相关研究成果显示了我国组织传播学研究在经历了“西学东进”后,逐渐进入了尝试性地本土化实践阶段。
一、组织传播与认同
西方学界对组织传播研究路径的考察主要围绕“组织”与“传播”的关系而展开。学界对组织传播的实证考察涉及经济、医疗、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在吸取了组织学、管理学、语言学、法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后,组织传播更倾向于采用跨学科交叉分析的方法和理论。源自于20世纪50年代社会认同的组织认同的研究可以上溯至80年代。认同(identity)是对某事物区别于其他所有事物的认可,包括在其自身统一性中的所有内部变化和多样性。有学者将认同定义为某事物被视为保持相同或具有相同性。[8]国内学界对“组织认同”的翻译来自于“organizational identity”和“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两个英文词组,前者在台湾学界被译为“组织认定”,后者大陆被译为“组织同一性”“组织特征”“组织身份”以及“组织认同”。[9]由于研究视角和学科定位的差异使得学者们在对英文释义争论不休,对“组织认同”的界定也存在很大差异。
组织传播学研究早期的理论贡献者赫伯特·A·西蒙认为,认同是一个人在做决策时对被选方案的评价,如果是以这些方案给群体造成的后果为依据,我们就说那个人对那个特定群体具有了认同感。切尼(G·Cheney)则从组织现象和行为出发提出组织认同感与决策、工作态度、动机、工作绩效、目标成就、决策冲突、成员互动等众多因素相关。[10]在不同视角对组织认同的界定中,适用于本文探讨国际组织中认同的界定,笔者倾向于Ashforth和Mael提出的组织认同是一种对组织产生的归属感或共同感,是组织成员认为自己的特征与组织特征相一致的程度。[11]而组织认同侧重于认知结构的构建[12],构建认同的目标是激发组织内部成员在价值观、信念和目标上与组织协同一致。
组织是一个社会系统,是由多个子系统组成的有层次、有结构、有逻辑的体系,组织认同更是组织行为学和管理学领域的热门课题,而从传播学视角,尤其是组织传播的视域下,考察组织认同的研究却少有出现。组织传播视角下,组织认同的考究涉及组织成员与组织两个层面。国际组织传播以形成认同为目标,认同以传播为其在组织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范围内的延展为基础。特定组织内部的组织成员在同其他组织相比的基础上认为自己所在的组织具有独特的特征并与其保持一致性。[13]传播与认同同为动态过程,在组织的传播实践中两者互动促进。组织认同引起的组织内个体(成员)中传播方式的选择、文化和身份的认知,符号意义的展示、权利关系的构成等方面都是组织传播研究中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组织认同的构建和强化对组织的内部凝聚力、行为协调和集体决策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且直接影响组织传播的模式、方法和效果。
二、国际组织传播与认同
全球化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14]。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组织”的应用逐渐超出了经济和生产领域,跨国界、跨地域和跨文化的多样化国际性组织形态层出不穷。国际组织处于国际社会的大系统之内,通常指若干国家为特定目的,以条约建立的一种常设机构[15]。一般而言,国际组织分为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GOs)和政府间组织(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GOs)。狭义的国际组织仅指政府间国际组织。[16]政府间国际组织具有稳定性、权威性、专业性和自主性等显著特点。国际组织传播的研究离不开国际关系的现实语境,国际组织的认同更是如此。二战后,随着国际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跨国性的国家相互依赖构成了当今全球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17]国际组织中的认同必然需要重塑,相较于一般意义的组织认同,国际组织中的认同具有多元性、复杂性、社会性、可共存性、可塑性和有效性等属性。国际组织在成员构成、作用范围、决策行为等诸多方面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组织,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而传统国际关系的学说将民族主义、民族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却未曾将认同作为中心问题进行分析。作为重要的国际行为主体,国际组织在其运作机制、关系利益及传播方式的特殊性使得国际组织的有别于传统的组织传播活动,除了具有上述特征外还带有集体性决策、相对独立性、较强开放性等特征。
西蒙认为,组织指的是一个人类群体当中的信息传播与相互关系的复杂模式。[18]国际组织便是具有典型复杂模式的组织,在一些“软”机制约束的国际组织中,“协商机制”被作为国际组织协调的原则,而在一些“硬”机制约束的国际组织中,规章制度则成为组织行为的准则。国际组织中的成员来自不同文化、宗教、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的国家,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行为能力、认知程度的差异、传播实践行为能力的迥异,以及组织行为的相对独立。国际组织理论上不应受其他国际组织或个别国家的控制。组织成员的组织认同对组织具有潜在的积极功能作用。[19]正是由于组织认同的构建才能够促使成员产生的更多共识,保持组织内多种认同和谐共存的状态,这不仅有助于促进组织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助于提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
国际组织与包括国家、其他国际组织在内的国际环境之间互动往来,建立并发展组织内外的关系网络,构建属于其自身的组织形象和传递组织的特有文化。在组织内外互动往来将增强组织内成员国对所在组织的认知和对组织的归属感及认同感,协调组织内部与外部的交流中的矛盾冲突,为组织内成员国之间的交往合作和利益共享搭建平台,同时提升国际组织的国际影响力。由此,国际组织应争取成员国更多层面的认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此外,国际组织自身的结构发展与国际格局和全球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国际组织传播离不开国际关系的现实。依据国际组织的传播特征,其涉及组织自身结构传播、内部结构传播和外部结构传播三个主要传播层次,还涉及组织的层级结构、权利分配、关系构建、文化认同等传播学问题。正是由于国际组织高度的复杂性和差异性,突显了国际组织传播中的认同问题的重要地位。国际组织认同建构过程十分复杂,而构建过程也将有助于缩小成员国之间的差异、满足成员国个体诉求及缓解冲突,以及取得更加广泛领域的认同。
三、认同的构建
国际组织为各国达成有关合作提供了多边合作和多级外交的平台,各成员国通过在国际组织内进行信息传播、互动商榷及确定决议,再通过信息的交流使得相关决议在执行机制下付诸实施。随着国家之间互动日益频繁,民族国家通过国际组织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中展开频繁的国际合作。有学者曾提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主要认同是民族认同。[20]国际组织自身的特性致使国际组织的认同构建多元而复杂,笔者拟在这里简单地探讨国际组织传播中认同构建的普遍适用性问题。
(一)认同的变量
国际组织是依据组织内约定的原则和要求建立起来的,具有一定组织目标、宗旨,及组织运行规制等组织构建的必要条件。在经历了17、18世纪的酝酿、19世纪的制度探索与创新之后,现代国际组织得以在20世纪产生和发展起来。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频繁交往,促使国际性或区域性的常设机构得以建立,各国政府借助世界性或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实践着新型的国际性交往和合作方式。国际组织传播中认同构建的前因变量包括成员国自身、组织外部环境、组织目标与机制,此外还有国际组织在创立宗旨、决策执行、权能范围、权利义务等方面的影响因素。
国际组织传播中认同构建的前因变量决定着国际组织传播方式和方法的选择,作用于国际组织自身运行机制的有效性,与国际组织传播的效能成正相关关系。由于国际组织中多元文化的影响,各成员国对组织的认知和阐释存在着差异,组织成员对所在组织的认同以自身的感知为基础,而个体自身的感知则来自与组织价值观的相似性和共时性的共通之处的多寡。以成员国利益的共同进步与发展为国际组织发展的目标,必然获得个体成员国的更多认同,反之被大国或少数国家操控的国际组织只为满足个别国家的利益,必将只能迫使弱小国家在短时间内的顺从,而不能获得其本质上的认同,也必将导致该国际组织认同形成受阻。
国际组织具有多元文化并存的属性,文化是在成员国彼此间相互交流和借鉴过程中发展起来,现如今,跨文化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集,国际组织认同的构建与多元文化认同的建构密不可分。西沃特(Scholte)认为,多元文化体现在7各方面,即放松(relaxation)、承认(recognition)、尊重(respect)、互惠(rciprocity)、责任(responsibility)、节制(restraint)、抵制(resistance)。[21]国际组织传播绕不开多元文化的现实,认同的建构更是离不开对组织自身多元文化的解读。组织成员的多元文化随着组织化交往的增多和组织规范的加强,促使成员行为实践逐渐产生相似性,组织文化的包容性增加,从而促进了组织认同程度的深化和范畴扩大。此外,国际组织传播中认同建构前因变量还包括组织内集体认同和国家认同,成员国的行为方式决定于系统的组织原则,而以何种原则协调成员国与国际组织的利益关系,也将导致不同的认同建构方式及组织传播方式。正是由于国际组织内成员国行为的可预测性,才使得国际组织传播中控制认同构建的前因变量十分重要。
(二)自结构与认同
国际组织是当今国家间沟通交流的主要媒介,通过国际组织而展开的国际交往也成为每一个国家融入全球化的重要途径。各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情况以及在参与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已成为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22]组织的自结构包括组织机制和运行方式,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核心问题,成员国选择加入某一国际组织是在权衡国家权利和利益之后做出的决策,而考虑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利益,势必导致一国政府参与多个国际组织以获取自身最大的优势。
组织机制、组织规章制度可能对成员国造成“软约束”和“硬约束”。软约束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参与组织实践活动相对较少受到组织规制的限制,硬约束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则在诸多方面受到组织规制的约束。也有学者将前者称为开放型或半开放型国际组织,后者称为封闭型国际组织。欧盟(EU)、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属于“硬约束”类型的国际组织;而东盟(ASEAN)、亚太经合组织(APEC)利用规制其对组织成员的约束力相对较弱,属于“软约束”类型。“软约束”类型的国际组织中,成员国的行为实践及决议的执行主要依赖成员国自身的意识和觉悟,组织并没有相关机制和制度约束并保证决议的执行,由此也无法避免“软约束”型组织的效率相对较低。
随着国际组织多元化发展的深化,“软约束”类型的国际组织不断涌现,成为了当下国际组织发展的主要趋势。组织自身的结构关系决定了组织传播模式的选择,国际组织受其结构关系的影响,组织认同广度和深度也各有不同。一国政府选择加入某一国际组织是在权衡国家权利和利益之后做出的决策,而考虑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利益,势必导致一国政府参与多个国际组织以获取自身最大的优势。此外,由于国际社会交往的复杂性,一国政府对众多国际组织集多种认同于一身是可能的,即国际组织中的认同具有可共存性。反之,国家自身的稳定性和主观选择性也影响着对特定国际组织的认同存在的延续性。
(三)外结构与认同
在全球化程度逐渐加深的当下,一国政府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不能在本国框架下独立解决,例如,环境治理、反恐等在内全球治理性问题,与之相伴的是与他国之间的协作,已经成为解决共同问题的主要途径。国际组织(包括区域性国际组织)正在担负着解决国际性(区域性)问题的重要角色,作为独立的国际行为体,国际组织与组织外的国家、组织和个体人存在有交流和沟通的互动行为,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际组织更容易获得彼此的认同,并由此进一步促进组织间的交流合作。国际组织与包括国家、其他国际组织在内的国际环境之间互动往来,构建了特定国际组织与非成员国国家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网络的建立。
国际组织参与国际事务的处理,一方面促进了区域性和世界性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国际组织成员国相互之间的信任、了解和认同。而国际组织对国际性事件的有效处理,将有助于提高组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争取更广范围的认同,为国际组织的生存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空间。全球化使得传统国家和民族间以地域为中心的认同建构方式发生改变,国际组织在与国际环境的互动中树立了属于其自身的组织形象、传递了组织的文化以及组织的定位与身份,同时增进了国际组织内成员国对所在组织的信任和增加了对组织的归属感。反之亦然,如果国际组织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无法处理纠纷、协调矛盾将首先失去组织成员的信任、依赖和认同,并影响组织外部环境的认同构建。
四、结语
国际组织是世界秩序调整的产物,随着全球一体化和国际合作在各个领域的不断加强,国家边界出现了渗透性,以民族国家为主的集体认同方式不再适合全球化时代的现实。国际组织为实现各国共同利益、解决共同问题,提供交往互动交流的平台,将不同民族国家和组织联系在一起,通过国际间的合作与协商促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由此也必将带来多种途径和方式建构组织认同。国际组织认同的构建具有动态性、可变性、多元化和复杂化等特征。国际组织传播如何协调矛盾和加强合作,为组织内成员国之间的交往合作搭建平台,为在组织外部的交流互动中实现共同利益,是争取成员国认同和国际社会认同的关键所在。有学者就曾这样评价国际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国家和行为体在各种论坛展示自己的观点,并力图使自己关注的问题在国际组织汇总提出来,通过议程的扩大或缩小追求自身优势的最大化。
20世纪70年代,国外组织学的研究者就曾论及了组织理论应用于国际组织的适应性问题,可见将国际组织本身作为组织传播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重大。而国际组织自身的属性特征决定了传统的组织传播理论很难将其涵盖,国际组织中的认同建构亦是如此。基于上述论述,国际组织中的认同构建的具体内容涉及组织自我意象建构、共同体思维建构、组织及组织成员身份建构、组织多元文化的建构等多方面的内容。
国际社会关系的流动性和可变性决定了国际交往的不稳定性,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组织受到了来自成员国的不稳定性、国际环境的多变性、国际组织内权利关系的流动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国际组织中的认同不能自发产生的,是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互动中逐渐形成的。构建在国际关系现实语境下国际组织传播中的多层次认同,包括了组织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身份认同、目标认同、角色认同等多层次。国际组织认同构建只有承此脉络在对内和对外的传播实践中遵循共识大于冲突,尊重成员国多重认同于一身的事实,充分认识认同的可塑性和效力,构建“容纳和排斥”共存的认同体系,为国际组织传播的深入性研究提供更加崭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埃弗雷特·M·罗杰斯.组织传播[M].陈昭郎,译.台北:台湾编译馆,1983:10.
[2] 顾孝华.组织传播[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10.
[3] 凯瑟琳·米勒.组织传播[M].陈淑珠,译.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效公司,1998:20.
[4] 埃里克·M·艾森伯格,小H L.古多尔.组织传播:平衡创造性和约束[M].白春生,王秀丽,张璟,等,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传播社,2004:23.
[5] 魏永征.关于组织传播[J].新闻大学,1997(3):31-34.
[6] 胡河宁.组织传播学:结构与关系的象征性互动[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 谢静.经由传播而组织:一种动态的组织传播观念[J].新闻大学,2011(4):112-118,144.
[8] JAMES M B.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M].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98:504.
[9] 魏钧,陈中原,张勉.组织认同的基础理论、测量及相关变量[J].心理科学进展,2007,15(6):948-955.
[10] JOHNSON W L, JOHNSON A M, HEIMBERG F. A Primary and Second Order Component Analysis of the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Questionnaire [J]. Educational &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999, 59(1):159-170.
[11] 冯云霞,葛建华.组织文化的象征化过程研究:基于组织身份建构与认同的视角[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2(5):48-55.
[12] ASHFORTH B E, MAEL F.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the organiza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4(1): 20-39.
[13] 王彦斌.管理中的组织认同:理论建构及转型期中国国有企业的实证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2-64.
[14] 阿兰·伯努瓦.面向全球化[M]//王列,译.全球化与世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
[15] 梁西.国际组织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1-2.
[16] 刘金质,梁守德.国际政治大辞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31.
[17] HOLSTI K J.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95:9.
[18]赫伯特·A·西蒙.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M].杨铄, 韩春丽,徐立,译.北京:北京经济出版社,1998:9.
[19] ASHFORTH B E, MAEL F.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the organiza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4(1): 20-39.
[20] 杨筱.认同与国际关系[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
[21] SCHOLTE J A. Globalisation and collective identities[J]. Ident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6: 38-78.
[22] 王玲.世界各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比较研究[M].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11):47-54.
(责任编辑: 任中峰)
DOI:10.3969/j.issn.1673-3851.2016.02.009
收稿日期:2015-09-15
作者简介:狄丹(1981-),女,吉林长春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会展、传播、媒体、广告方面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 3851 (2016) 01- 0058- 06 引用页码: 020302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denty Under View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DIDan
(Schoo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Film,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For a long time, the researches abou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lways focus on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ci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and emphasize the influence and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hile the discussions on communciaiotn problem in the organization operation process are insuffici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communication cannot avoid huge differences of various member states in culture, politics, economy, religion and society. Identity among member states and the scope of identity influence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dentity and involves the discussion on variables before identity construction, relevance between self-structure construct and identity and external structure communication. The study on the ident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communication not just contributes to analyzing and investigating organization identity problem in organization communication,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external contact for China’s fusion in the world, and collectivization and organization. This paper offers reference for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ontact and activit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Key words: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organization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communicati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作为两用物项管制稀土出口的外贸制度探析
- 规范内容合法性的不同面向及其适用限度
——兼论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不同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