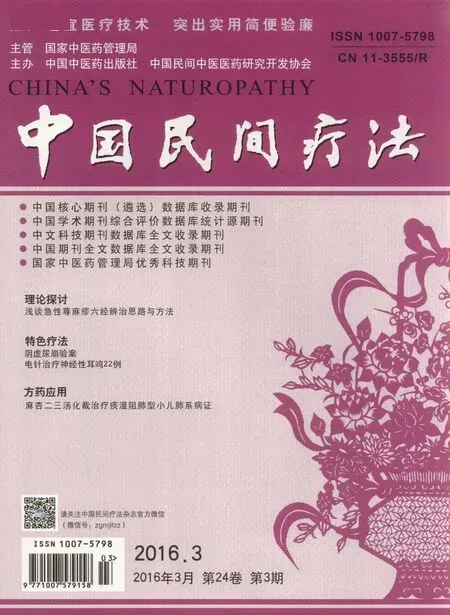浅谈急性荨麻疹六经辨治思路与方法
浅谈急性荨麻疹六经辨治思路与方法
黄超原1陈博南1通讯作者:李东海2
1.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广州510405
2.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关键词】急性荨麻疹;六经辨治;思路与方法
荨麻疹是由于皮肤、黏膜小血管扩张及渗透性增加而出现的一种局限性水肿反应,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病[1]。临床表现为皮肤出现局限性的组织水肿性风团,通常先伴有皮肤瘙痒的症状,随即出现轻度隆起的斑疹样风团、红斑或划痕等。中医学根据其表现症状和致病特点对其有不同的命名,如“隐疹”“风疹瘙疮”“游风”等。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描述“隐疹”曰:“人皮肤虚,为风邪所折,则起隐疹”“邪气客于皮肤,复逢风寒相折,则起风瘙隐疹”“风气相搏,隐疹,身体为痒”。“风疹瘙疮”首见于《千金要方》:“风邪客于肌肤,虚痒成风疹瘙疮。”“游风”则见于清代祁坤的《外科大成》:“游风者,为肌肤倏然焮赤肿痛痒感,游走无定,由风热壅滞,营卫不宣,则善行而数变矣。”从历代医家的记叙中可看出急性荨麻疹病机可归结为素体虚弱,卫外不固,营卫失和,风邪携寒、湿、热、燥入侵肌肤,肌肤受邪发之为疹。各家虽有不同论述,但本病皮疹来去急骤,与风性善行而数变的特点相同,故均强调风邪为患。
急性荨麻疹常见治疗方法
历代医家治疗急性荨麻疹多从祛风、养血、润燥、清热、除湿的角度入手。张志礼认为荨麻疹的治疗勿忘祛风,根据寒热不同,酌用清热或散寒之法,虚证宜用益气养血之法[2]。范永升治疗荨麻疹采用祛风、和营、清解、和胃四法。祛风法用于急性荨麻疹属风热证者,方用消风散加减;清解法多用于血热证,方用犀角地黄汤加减[2]。靖玉仲治疗荨麻疹以扶正固本、益气固表、祛风止痒为治法[3]。王玉玺认为荨麻疹急性期多属于表证、实证,治以祛风、清热、散寒、凉血、解毒为主[4]。然急性荨麻疹虽表现为局部皮肤的病变,但其根本病因在于机体阴阳失衡,全身机能紊乱,营卫气血不和,故治疗应该以调理全身症状的对因治疗为主,辅之以宣透祛风、养血润燥、清热祛湿等的对症治疗。笔者治疗荨麻疹以胡氏六经理论为指导,从患者整体状态入手,结合方证学说,患者全身症状得到改善,急性荨麻疹也随之痊愈。
四诊合参,先别阴阳
胡希恕的经方思维尤其重视八纲辨证,他认为《伤寒论》并非运用脏腑经络辨证,而是应用八纲辨证。而在表、里、虚、实、寒、热、阴、阳之中,阴阳为八纲之目,其余六者可谓是阴阳之延伸。清代江笔花在《笔花医镜·表里虚实寒热辨》中云:“凡人之病,不外乎阴阳。而阴阳之分,总不离乎表里、虚实、寒热六字尽之。夫里为阴,表为阳;虚为阴,实为阳;寒为阴,热为阳。良医之救人,不过能辨此阴阳而已;庸医之杀人,不过错认此阴阳而已。”[5]笔者认为急性荨麻疹虽然为一种表现在局部的皮肤病,但追本溯源其根本原因不能仅责之于肌肤的病变,更责之于机体整体的阴阳失衡。故治疗急性荨麻疹不能仅将目光局限在营卫气表和肺主皮毛上,治法局限在祛风清热、除湿止痒、养血润燥等,应从患者的整体出发,解决患者全身性的症状再兼顾局部突出的症状,荨麻疹也随之不攻自灭。从整体出发则要求做到四诊合参,先别阴阳。在望诊中,观察患者就诊时的精神状态、神情、行为以及面色等能初步分阴阳。若患者就诊时精神状态表现亢进或正常,此多属阳证,故诊断可优先考虑“三阳”证;若患者就诊时精神状态低下甚至淡漠,此多属阴证,故诊断时不可忽视“三阴”证,以少阴病提纲“脉微细,但欲寐”故而。患者神情若明显焦虑态,则可考虑少阳枢机不畅;若呆滞无神,则不可忘“三阴”证的可能。患者行为表现为多动,肢体语言丰富或正常,多考虑“三阳”证;若明显疲倦少动,提示可能合病“三阴”。在闻诊中,着重辨析患者陈述病情时的语气、语速等。语气高亢,语速较快者属阳;语气无力低微,语速迟慢者属阴。在问诊中,除了常规地运用“十问歌”和针对急性荨麻疹对应症进行问诊外,还可结合伤寒条文和方证学说进行问诊。方证学说最关键的切入点是“有是证,用是方”,全面掌握患者的症状,才有利于运用伤寒条文辨证施治。“切”脉则可以贯穿于前三步之中,切脉之后结合舌象,对患者整体属性做一总体的评估。
次审六经,尤重问诊
鉴于急性荨麻疹发病急骤,故多从“三阳病”入手思考。以新邪害人多从太阳经起,故首问有否发热恶寒之症。《伤寒论》第1条曰:“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有一分恶寒,便有一分表证,故患者可不发热,但恶寒较多见。之后再问患者有汗与否,若有汗则提示可能为腠理开泄,卫阳不固所致;若无汗出者,则卫阳受郁,汗出不畅,这类患者多伴有身体疼痛,以《伤寒论》第3条曰:“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结合体质而言,一般体质瘦小之人多有汗出,而身体健硕之人则无汗。另外,大汗淋漓者需要注意阳虚阳浮的可能,大汗出伴有高热而不恶寒者,需要考虑阳明热证的可能,以182条对阳明外证描述为:“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也”,以及196条:“阳明病,法多汗”。然后可问患者是否口干口苦,以探查其少阳经是否中邪,故而263条曰:“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随后再问欲饮与否,寒热往来,胸胁苦满等,以判断是否为小柴胡汤类证,96条:“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值得注意的是,太阳病与少阳病在急性荨麻疹尤为常见。最后问患者二便情况,若大便干硬,小便黄或不利,则追问有无腹部胀满不适感,考虑阳明实证,262条曰:“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冒不能卧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气汤”。
在问诊细节处理上也有考究。例如:由于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不少病人因长期不适而将一些异常症状当成常态而忽略,若仅简单询问患者“大便正常否”,部分病人的回答可能是正常,但当医生提示大便是否存在质地(硬、烂、先硬后烂等)情况后,患者则可能意识到自己大便的实际情况,同时还要询问肛门的灼热、下坠、疼痛、无力等感觉。对某一症状及与此相关的信息了解越详细,对后期的辨证论治越有利。
临床更常见的是二经或三经合病或并病,如发热恶寒、咽干口苦之太阳少阳合病或并病,发热恶寒,大便异常之太阳阳明合病或并病,寒热往来、心烦喜呕、大便不解之少阳阳明合病或并病等,宜将相应方药进行灵活组合。
再辨方证,有无皆求
经方大家黄煌[6]认为方证相应说强调方与证的对应性,临床上重视抓主证,有是证则用是药,无是证则去是药。《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吉益东洞在《方极》自序中云:“夫仲景之为方也有法,方证相对也。”清代伤寒学家柯韵伯在《伤寒来苏集》中言“桂枝汤为伤寒中风杂病解外之总方也。凡脉浮弱、汗自出而表不解者,咸得而主之也”,“头痛、发热、恶寒、恶风、鼻鸣干呕等病,但见一症即是,不必悉具,惟以脉弱自汗为主耳”。“辨方证”可与“别阴阳”和“审六经”相辅相成,后两者为前者的基础,前者为后两者的补充。冯世纶[7]认为,所谓辨证论治,重在辨八纲、六经,但由于影响人体患病的还有很多因素,则还需辨气血、瘀血、痰饮、水湿等,此则为辨方证。如患者全身大片风团,同时有发热恶寒、脉浮,诊为太阳病,但麻黄汤、桂枝汤、葛根汤等均治太阳病,故必须再询问有无汗出,有汗用桂枝汤,无汗用麻黄汤。如伴见便溏则用葛根汤;如发热多恶寒少,伴见口干、小便黄,可用桂枝二越婢一汤等。如果患者全身症状较少,医生仍需仔细寻找,从细微处着手,如情绪急躁,手足心灼热为阳热之象;舌淡水滑苔白,带下色白量多,为痰饮水湿之象;易汗出感冒为表虚卫外不固。黄煌提出的“黄连舌”“附子脉”“桂枝体质”“麻黄体质”等可参考。
讨论
笔者通过探讨六经辨证在急性荨麻疹治疗中的运用,认为通过先别阴阳,再审六经,后辨方证能有效快速地控制急性荨麻疹的病情。先别阴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言:“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笔者认为无论机体发生何种病理变化,基本不离阴阳气血失和的总病机。故先别阴阳,是治病求本的体现。再审六经,六经为仲景创立的一种辨证体系,其虽始创于伤寒,但非局限于伤寒。柯韵伯言:“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俞根初说:“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姜建国[8]认为六经辨证具有整体观、常变观、恒动观,联系性、系统性等特点,是《伤寒论》经久不衰的原因。最后辨方证,则是针对急性荨麻疹的具体局部表现进行对症施治的体现。若言阴阳六经皆属宏观治本,那方证可谓微观治标;若论阴阳六经均是抽象整体,那方证学说可是具象具体。
总而言之,先将人体视为一个整体来治疗为主,再将人体分为局部来治疗为辅,才是中医治疗疾病的核心思维。欲将整体与局部有机结合,则需要将六经辨证与方证学说相融合。纵观临床,笔者认为急性荨麻疹多属“三阳病”范畴,从六经辨证整体出发,故常用的经方有桂枝汤、麻黄汤、桂枝加葛根汤、葛根汤、小柴胡汤、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承气汤类等。若有两经或三经合病者,可用单方的合方或柴胡桂枝类方、大柴胡汤、麻杏石甘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等。
参考文献
[1]赵辨.临床皮肤病学[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613.
[2]王萍,张芃,韩冰,等.张志礼治疗荨麻疹经验[J].中国医药学报,2000,15(4):51-52.
[3]陈兵.靖玉仲治疗荨麻疹经验[J].山东中医杂志,2005,24(11):690-691.
[4]刘贵军,王玉玺.王玉玺教授治疗荨麻疹经验[J].中医药学报,2005,33(2):64.
[5]冯世纶.认识经方方证[J].上海中医药杂志,2013,47(1):27.
[6]黄煌.论方证相应说及其意义[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8,4(6):11-13.
[7]冯世纶.探讨方证对应之理[C].国际(中日韩)经方学术会议第二届全国经方论坛暨经方应用高级研修班论文集,2011.
[8]姜建国.论六经辨证与寒温统一[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24(1):11-15.
(收稿日期2015-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