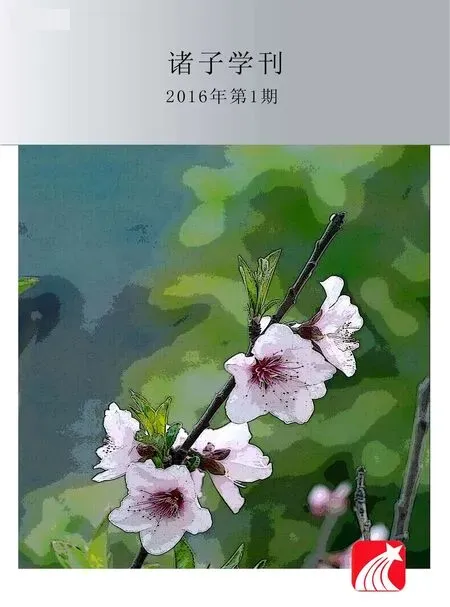論諸子學的範疇、智慧及現代條件下的轉化
劉韶軍
論諸子學的範疇、智慧及現代條件下的轉化
劉韶軍
諸子學從歷史發展到今天,已有脱胎换骨的根本變化,已經不能用傳統的子部之學來涵蓋之,因此需要從現代學術的角度重新界定諸子學的範疇。其目的是利用現代學術的理念與方法對傳統子部之學留存下來的豐富文獻資料進行全新的認識與闡釋,從中挖掘可為現在社會發展利用的有益智慧。在此基礎上,更要重視利用現代科技條件與手段來對歷史上傳承下來的子學進行轉化性加工、整理和研究。這應該是當代諸子學的重要任務之一。
關鍵詞 諸子學 子部 子部文獻 現代轉化
中圖分類號 B2
中國的諸子學來源於古代,發展於今天,自中國悠久的歷史過程和燦爛輝煌的文化土壤中形成、發展、傳承而來。它本身隨着時代的發展變化而不斷發展變化,這是今天思考諸子學現代轉型問題時應該承認的歷史事實。以往的發展變化,到了今天就需要更好地總結和前瞻性思考,使諸子學的現代轉型能够具有自覺性和科學性,滿足它自身的自然性適應與變化。這是諸子學面對現代轉型時所要考慮的又一重要問題。為此,需要立足於現代學術條件下重新思考諸子學的範疇,重新認識諸子學中的中國智慧,重新研究如何使之在現代轉型時能够做到自覺和科學,從而使現代中國得以從諸子學得到最大化的利用與效益。這是研究諸子學現代轉型時的根本點。
筆者認為,所謂諸子學這一概念或範疇,應該重新加以確認,不能局限於古代經、史、子、集分類體系對於子部和子學的劃定與認識。只有重新認定了諸子學的真正範疇,才能確認歷代傳承下來的學術資源可列入諸子學的研究範圍,然後才能在這個範圍内發掘諸子學的各種智慧,按照現代中國的需要加以自覺和科學的轉化,使之最有效地被現代中國從各個方面加以利用。這樣才可以説完成了現代研究諸子學的根本任務,才可以説現代研究諸子學的學者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一、 諸子學的範畴要重新認定
為什麽説對於諸子學的範疇要重新認定?因為諸子學這個概念本身是歷史的産物,它在過去受到古代經、史、子、集四部分類體系的影響,而被劃定了一個特定的範圍。到了現代,這個在古代社會條件下劃定的範圍已不能適應現代社會條件下研究諸子學的需要,不再合乎諸子學的真正意涵了。所以要根據現代的社會和學術的實際情況對諸子學的範疇重新認定。
在歷史上最早被稱為子的人,在今天看來,都是能創立一種獨到的思想學説的思想家式的學者,如孔子、老子、墨子等。具體的一名這樣的學者可以稱為某子,而諸子就必須是至少兩個以上的子的集合。古代學術界把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一大批思想家和學術家分成若干家派,其代表人物都稱為子,如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道家的老子、莊子,法家的韓非子、商子,墨家的墨子等。而對於一個時期内大量出現的子,則統稱為諸子,把他們視為同一類型的學者。在春秋戰國時期乃至漢代的史書與學術著作中,對這個時期出現的為數衆多的諸家之子,已有各種記載、論説和評價,後代學者就把這批諸子與他們的時代關聯起來,稱之為先秦諸子。這是諸子的最初形態與概念所指,反映了一個特定歷史時期内的諸子的情況。之後時代不斷發展進化,每個特定的時代都會不斷出現諸子式的學者及其學術著作。後來的學者也就按照他們各自的時代,而以不同的時代之名稱之為漢魏諸子、宋明諸子等。這種在不同時代出現的諸子,早已不是先秦諸子的概念所能包涵的,可知諸子的概念隨着時代的發展而有了不斷增添的新内容。如果僅限於先秦諸子的理解來看待諸子的概念,明顯是不合乎歷史事實的。據此可以説明,對於諸子概念的理解,應該具有時代性,使之包涵各個時代的諸子及其學術著作或思想學説。
古代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定型是比較晚的,如《漢書·藝文志》就與後來這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有相似處,那時還有一類稱為諸子略,但在諸子略之外又有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而兵書、術數、方技在後來的經、史、子、集四部體系中都已歸屬子部。《漢書·藝文志》共分七略,而屬於後世子部的就占了四略,由此也可看出當時的諸子學是何等地興盛,同時也説明漢代對於諸子的理解與後代不同,其範圍是比較小的,所包涵是比較少的。如果根據歷代正史所載的諸子或子部的内容來看,就可看出諸子在歷代的變化情況以及當時學術界對於諸子範疇的認定情況。從這個角度説,處於現代社會條件下的學術界對於諸子的認定,也應該與歷代一樣,拿出自己認定的範疇和分類體系。這樣才會使諸子的概念具有特定的時代性,才能反映出現代學術界對諸子及諸子學有了自己的符合時代現狀與學術科學性的認識。
至少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現代條件下的諸子與諸子學的認定不能固守歷史上的某一個特定的認識,而使諸子的認定不够完整與科學。但同時也要尊重歷史上的有關記載及相關資料,以此為基礎,根據現代學術觀念對這些舊的記載與資料加以新的認識與分析,從而確定現代學術條件下的諸子概念的範疇。這就是筆者所説的對於諸子和諸子學重新認定其範疇的意思所在。
基於這種認識,來看中國古代定型了經、史、子、集四部中的子部的範疇是什麽情況。就《四庫全書》中的子部而言,其分類如下: 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術數、藝術、譜録、雜家、類書、小説家、釋家、道家,共14類。如果按照《四庫全書》編纂時的概念,這樣的子部中的内容都應列入諸子的範疇之中。但是如果仔細分辨起來,就會産生不少問題,説明不能簡單地按照這種分類體系的子部來認定諸子的範疇。
上列14類中只有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道家是最早認定的諸子,釋家在漢代還未出現,但據它與道家並列的情況看,釋家也可以没有疑問地列入諸子範疇之中。
術數中下分數學、占候、占卜、命書相書、陰陽五行、相宅相墓等,《漢書·藝文志》的諸子略中有陰陽家,所以術數類中的陰陽五行,可以列入諸子的範疇。
雜家類下分雜學、雜纂、雜編、雜品、雜説、雜考等小類,其中雜考中的《白虎通義》應該列為儒家類,雜學中的《鬻子》《墨子》《慎子》《鶡冠子》《公孫龍子》《吕氏春秋》《淮南鴻烈》等都可列入諸子的範疇,但所屬的類别已與《漢書·藝文志》有所不同,如《漢志》有名家,名家中有《公孫龍子》,在《四庫全書》時就没有名家一類了,而把《公孫龍子》列入雜學之中。《墨子》《慎子》等也與此類似。説明後代的子部分類體系與漢代已有很大不同。
《漢書·藝文志》將天文、曆算、五行、蓍龜、雜占、形法等列入數術略中,這些在《四庫全書》的子部中仍然存在,但天文曆算已從數術中分了出來,單獨成類。
《漢書·藝文志》把醫經、經方、房中、神仙歸為一類,稱為方技,相關内容在《四庫全書》中獨立成醫家,但神仙一類則從醫家分離出去了。
以上這些類别都可列入諸子的範疇。但《四庫全書》的子部中還有不少内容是不能列入諸子範疇。如子部的類書,不能列入諸子的範疇。小説家之下又有雜事、異聞、瑣記三小類,也不能列入諸子的範疇。子部雜家類的雜纂、雜編、雜品、雜説、雜考、雜學等小類中也有不少内容不能列入諸子的範疇,如《元明事類鈔》《玉芝堂談薈》《説郛》《仕學規範》《古今説海》《鈍吟雜録》《雲煙過眼録》《韻石齋筆談》《硯山齋雜記》《王氏雜録》《文昌雜録》《仇池筆記》《師友談記》《冷齋夜話》《曲洧舊聞》《近事會元》《能改齋漫録》《雲谷雜記》《芥隱筆記》《經外雜鈔》《愛日齋叢鈔》《潛邱札記》《湛園札記》等,大多屬於筆記雜記一類,可以列入史部,卻不宜列入諸子的範疇。而《潛邱札記》《湛園札記》,《皇清經解》都已收入,可知也不宜列入諸子,可以列入經部。
《四庫全書》子部還有藝術和譜録兩類,藝術之下又分書畫、琴譜、篆刻、雜技,雜技之下有《棋經》《棋訣》《樂府雜録》等,譜録之下又分器物、飲饌、草木禽魚等,對這些内容也要根據具體情況加以分辨。
這説明《四庫全書》的子部不能一視同仁地劃入諸子之列,其中不少内容都應該仔細區分辨别,從諸子的範疇中剔除出去。但在《四庫全書》的經部、史部和集部中,卻有一些内容可以列入諸子的範疇。
如經部的《周易》類中有《易學象數論》《春秋占筮書》《易圖明辨》一類著作,從内容上看,已經不是對《周易》原書内容的闡釋與研究,而是借題發揮,作者由此闡發出一種與《周易》不同的新學説或思想,在内容和性質上與《周易參同契》《皇極經世書》《太極圖説》類似,因此被統稱為象數學,其中有不少思想性的内容,也有不少屬於術數性質的内容,所以是可以列入諸子範疇的。
經部《尚書》中有關於古代天文曆算的内容,不僅《堯典》中有這樣的内容,《尚書》的其他篇中都多有與古代天文曆算有關的内容,如王國維、陳久金關於《尚書》中所説的生霸、死霸的考證,就是純粹屬於古代天文曆算性質的内容,當然應該列入諸子範疇。《尚書·洪範》是一篇重要的古代政治學的作品,從諸子學的角度來看,其内容與諸子作品相同,所以像《洪範》篇這樣的經部著作中的内容也完全可以列入諸子範疇。與之類似的情況還有《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此二篇在宋代之所以被理學家重新提出來加以重點闡發,如《程氏經説》《融堂四書管見》《朱子五經語類》《四書章句集注》《四書或問》,都表明經部《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已成為宋明理學諸子所要研究和闡發的主要内容,這一歷史事實也充分證明它們完全可以列入諸子範疇。《尚書·洪範》與之相比,也完全有理由予以同等對待。
經部《詩經》中有不少關於植物、動物的專門研究,如《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一類的著作以及經部的《爾雅》中都有此類内容,具有這種内容的著作,完全可以與子部譜録類著作同等看待。《詩經》中還有不少關於天文的内容,也可列入諸子的範疇。
經部《周禮·考工記》,是關於古代各種建築與器物的專門製造的作品,《儀禮》中也有這種内容,如《儀禮釋宫》《宫室考》《釋宫增注》等。三《禮》中還有關於古代服飾的不少著作,如《内外服制通釋》《深衣考》。《禮記·月令》也有不少相關的著作,如《月令解》《月令明義》等。《禮記·夏小正》又與天文曆法相關,三《禮》總義類中的《三禮圖》《三禮圖集注》,這一類内容都是關於古代專門技術與製作工藝等的專門之學,也應列入諸子範疇。
經部《春秋》與三《傳》中有與天文曆算、占筮有關的内容,如《春秋長曆》《三正考》等,還有《春秋世族譜》一類的著作,也可列入諸子範疇。經部《春秋》類中還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明顯地更應放在諸子類中。
經部樂類有《樂書》《律吕新書》《瑟譜》《律吕成書》《鐘律通考》《樂律全書》《律吕正義》《琴旨》等,在内容上都與子部藝術類著作相關,也應列入諸子類中。
經部的《論語》《孟子》,直接就可以看作記載了子部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各種思想觀點和言論的著作,在最初的六經或五經體系中,二者並不屬於經部,後來才納入經部,所以二書完全應該視為諸子。而《周易》中的《繫辭》,也不是《周易》本身的内容,而是儒家學者對《周易》的闡釋,類似的内容在《禮記》中也有不少。這都應該列入諸子的範疇。
可知在四部所分的經部中有不少篇章或相關著作,都可視為諸子學的内容。在史部也不例外,如正史或類似正史的著作(如《通志》)中的天文志、天象志、五行志、靈征志、律曆志、樂志、釋老志、氏族略等,都可列入諸子的範疇。
史部還有時令類,其中有關於月令的著作,如《月令輯要》;史部政書類有考工之屬,其中的著作與内容與《考工記》類似,也都可以列入諸子範疇。
史部還有史評類,其中有些著作是思想家的作品,如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宋論》,這種著作中含有思想家反思歷史的重要思想與學説,如果王夫之可以列為諸子之一的話,那麽他的這兩部史評類著作當然不能劃到諸子學範疇之外。
就集部而言,其中的别集類收載了歷代學者的個人文集,在這些學者中有不少屬於歷代的諸子,因此他們的文集也應列入諸子的範疇。這樣的學者及其文集非常多,如賈誼、揚雄、張衡、嵇康、陶潛、劉勰、魏徵、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程頤、程顥、周敦頤、張載、邵雍、朱熹、陸象山、宋濂、劉基、王陽明、顧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為數衆多,難以一一列舉,但應該具有這種意識,即歷代思想家或衆多學者的作品雖然被傳統的四部分類法歸入了集部,但從諸子學角度來看,學者在進行研究時不應忘記這類學者的文集,也應當屬於諸子範疇。還有一些屬於合集的著作,如《弘明集》《廣弘明集》等也應這樣來看待,推而廣之,在《四庫全書》之外,如《道藏》《大藏經》中還有不少學者及其著作也應列入諸子範疇。民國以來編纂的《叢書集成》《新編叢書集成》等已對古代的文獻資料作了新的分類,這在今天思考諸子學的問題時,也有參考價值。
總之,對於諸子和諸子學,應該在現代學術體系背景下重新認定其範疇,分清歷史存留下來的諸多文獻與史料中的具體内容究竟哪些可以列入諸子範疇,哪些不可列入。這是一項繁重的工作,但必須在研究諸子學之前先行做好,然後才能順利地開展諸子學研究。
二、 全面整理諸子學説中的各種智慧
在重新認定了諸子包括哪些學者以及哪些相關著作之後,就要確定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即發掘研究其中的各種智慧,以便為現代中國的各項建設服務,使中國歷代思想家和學者的思想結晶能够古為今用,這也是現代學者進行學術研究時所要承擔的學術和思想的傳承的最大責任和歷史使命。
諸子類别繁多,從共性上講,凡是具有獨到思想或某種專門技藝的學者就可列為諸子,其著作中所包含的思想和專門之學的内容,就是諸子學所要研究的對象。
這樣的理解就使諸子的範疇比較大,所包含的學者與學術内容就比較多,因此其中所包含的中國古代學者的智慧就比較豐富。今天研究古代的諸子及其思想和學術成果結晶,要有一個重點,這就是研究、分析、理解、總結、轉化其中的思想與學術的智慧,而不要像漢代經師那樣,皓首窮經,只知繁瑣的考證與注釋,而不能站在思想與文化發展進步的高度,認識和總結其中最可寶貴、最具科學性的智慧。
從以上立場認識諸子及諸子學,就能看到諸子學具有極其豐富的内容。現代學者研究諸子,不能把它簡單化或單一化,而應該具備承認這種豐富性及複雜性的意識。對諸子學具備這種意識,就是承認中國歷史的悠久以及歷代學者思想與學説的博大精深與深沉豐厚,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證實中國歷史文化的光輝燦爛。同時也要意識到,這種複雜而豐厚的學説結晶之中的智慧對於今天的中國以及中國將來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不可因為它們已經成為過去而輕視和忽視。由此也可以證明今天重視研究諸子學具有極其重大的學術價值與文化價值,對於當今的中國來説,是一項不可替代的工作。還要意識到學術界在這方面的研究還非常不够,還有許多課題需要深入和專門的研究,為此要由衆多的學者來做大量的工作。從國家到地方的政府以及諸多部門以及整個學術界,都應該對此具有足够的認識。
一方面要認識到歷代諸子學者傳留下來的著作中並不是所有的話語和思想觀點以及相關技術方法都可以作為與現代中國的需求相適應的智慧來看待和使用的;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話語内容在表面看來不是什麽智慧,但運用現代各種學科知識與理論觀念加以深入闡釋後,卻能從中發現深睿的智慧。這兩種情況都需要現代學者運用現代的知識、理論、觀念以及方法、手段等對歷代諸子學者傳留下來的全部著作及其思想學説等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闡釋並且融會貫通,才能將其中符合現代社會學術標準的各種智慧總結出來。
諸子著作包含的智慧,從深和廣兩個角度來説,是極其豐富和深睿的,不是簡單的注釋或者介紹就能將其中的智慧展現出來的。
從諸子思想流派的角度看,有儒家、法家、墨家、道家、雜家、兵家、陰陽家等,從技術、技藝上看,涉及許多不同的學科知識與技術,如天文曆算、建築、音樂、製造、農業、醫藥、數學等,這裏面有許多不同的思想學説與技術方法,反映了不同學者對於各種社會與自然現象的深刻思考。在這種思考中,就有許多内容可以總結為中國人特有的智慧。對於這些思想智慧的内容,在現代學術條件下,應該給予全面而深入的分析,然後加以評定,而不僅僅是簡單定性。
如儒家、法家、墨家、道家、雜家關於社會政治問題的分析與認識,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與思想觀念,相互之間也存在着不少差異、分歧甚至是批判。對於這種情況不能簡單地説哪一家的思想學説是對的,哪一家的思想學説是錯的。在這樣的問題上,没有簡單的對錯,應該説都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且合理到什麽程度,也都是需要認真分析的。這就需要在現代學科的理論和觀念指導下加以重新研究。
還有一些不能簡單定性為哪一家的諸子的著作,則需要更精細的分别,不能籠統地或片面地指稱這一類諸子的著作中的學説和思想觀念是怎樣的。如《管子》一書,其内容就非常複雜,不能簡單地定為哪一家。
今天所看到的《管子》,本來並不是由一個學者完成的專著,而是多種資料整理後的合編,據《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記載,《筦子》經劉向整理後定為86篇,但在整理定稿之前,有《筦子書》389篇、《大中大夫卜圭書》27篇、《臣富參書》41篇、《射聲校尉立書》11篇、《太史書》96篇,把這幾種不同名稱的書對照之後,除去其中重複的内容共484篇,最後確定為86篇。可知是據幾種書整理合編而成的。在其後的流傳過程中也有不同的記載,據《史記·管晏列傳》“正義”,説《管子》18篇,與《漢書·藝文志》所説的86篇相差太多,這種記載也令人懷疑,不敢相信。到宋代《郡齋讀書志》就説86篇中已亡佚了10篇,即《謀失》《正言》《封禪》《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等,宋以後又亡佚《王言》一篇,後來這11篇在流傳的《管子》書中就只保留了目録而没有原本文字了,實存的僅有75篇。從以上情況看,《管子》可以列入諸子,但要説是諸子學派中的哪一家,就不是那麽簡單了。《四庫全書》把《管子》歸為子部法家,但近代以來不少學者研究《管子》,發現其中《心術》等4篇明顯屬於道家,而其他篇卻不能説也是道家的。就其書的實際内容看,有的篇目可屬於法家、道家、兵家、儒家、陰陽家、名家、農家,有的篇目内容則屬於理財,在今天屬於經濟,還有記事記言的内容,則屬於史家,可知一書内容涉及多種學派。
正因為如此,《管子》書中的思想内容就非常豐富,有不少時至今日仍然需要總結的獨到智慧,以下簡單列舉一些。如《牧民》篇説:“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這是説治國的人不能采取短視的政策,只求目前的利益而不顧長遠,也提示治國者凡事都要考慮長遠和周到,不要盲目決定某項政策或制度,更不要有欺民之意,這樣才能讓民無怨心而親其上。同篇又説:“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唯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這是説治國者不要單純追求具體的物質效益,而應從根本規律上掌握治國的關鍵,即所謂的有道,要把患禍消滅在無形之中,根本不讓患禍産生,而不是被動地等患禍出現之後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應對。從根本規律的層面掌握和控制形勢,這就是所謂的知時。只有有道才能知時,二者相輔相成,也是治國高明與否的分水嶺。後面説到的無私,也是一個重要條件,否則不能有道和知時,不能審時察用,這樣的人就不可以為官和為君。《管子》中此類政治智慧非常多,如《權修》篇説:“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貨財上流,可以理解為貨財都流到國家的上層手中了,會讓民覺得國家只知聚財,因而他們也要想盡辦法聚財,這就會使民變得無廉恥。如果國家上層與民衆都這樣無廉恥,就根本無法讓國家的民衆獲得安寧,更不能讓由民衆組成的士兵和軍隊為國拼死作戰。所以治國者應該是:“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也。”這是説如何教育國民,使他們有廉恥,除了國家不要只知由自己來聚財而使貨財上流外,更要注意從微小處開展國民廉恥教育,在這中間,士(男子)要無邪行,女要無淫事,即男女都不要做出傷風害俗的事來,這樣才能教訓成俗。所謂“成俗”非常重要,即要讓人們知廉恥而不做任何無廉恥的事,並讓這成為社會風氣,而不是只有個别人能做到這一點,並且還要由國家來表揚褒獎,那樣的話就稱不上成俗。治國的人都希望民衆都是正直的,知廉恥的,為此就要從制止微小的廉恥之事做起,對於微邪就要禁止,對於小廉就要修養,不要等到邪惡的事情成了風氣再來制止或批評,那樣就晚了,根本難以糾正。要從禁微邪、修小廉、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做起,這才是厲民之道和治國之本。這樣的問題不是哪一個時代特有的現象,而是在任何時期都會出現的問題,所以是有普遍性的,應該好好總結《管子》中此類智慧,用於今天的治國和社會管理。
在吏治方面,《管子》也有不少内容顯示出特有的智慧,可引為今天的借鑒,如《立政》篇説:“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以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與重禄;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禄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又説:“金玉貨財之説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説勝,則奸民在上位;請謁任舉之説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説勝,則巧佞者用。”從這些説法可以看出,對於官員的任用,對於治國來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不能掉以輕心。一個人德義有没有明顯的表現,得未得到證實,這是任用他為國家官員時必須考察的。為此需要一整套考察人們德義的辦法與制度,不能簡單地確認此人有德義或無德義。一個人有没有實際的功勞和能力,也要得到明確的證實,一個人對於民衆有没有信用,有没有過欺騙行為,也要明確考實。在德、功、能、信四個方面都没有確切證實之前,是不能任為大官、加以尊位、授與重禄的,否則就會造成良臣不進、勞臣不勸、材臣不用的局面,這對於國家治理是重大損失。另一方面,也要考察人們提出的主張,如果在治國方面主張以金玉貨財為先,主張觀樂玩好,讓官員任用上的請謁之風盛行,在官員的使用之中讓諂諛飾過成風,都會造成於治國不利的局面,如爵服下流、奸民在上位、繩墨不正、巧佞者用等。用這樣的官員隊伍來治理民衆,這個國家恐怕没有什麽希望,只會貪腐猖獗,民不聊生。
在社會風氣方面,管子也强調不要奢侈縱欲享受,如《重令》篇説:“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這與上面所説的不要讓“觀樂玩好之説勝”是一致的。
《重令》篇又説:“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這一説法可以作為外交方面的參考,對弱小施德,對强大樹威,軍事行動一定要讓天下服,只有這樣才能建立真正的威勢。
《法法》篇説:“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國家管理當中有時高層感到令不行,禁不止,這就要在法律制度以及執行方面找原因,制定了法律卻没有堅決執行,這就是法不法。法不法是一種客觀情況,而不法法則是一種主觀情況,二者都造成法律雖有而没有權威的局面,於是就會形成令不行禁不止的局面,而這是國家管理者的大忌。表面上看什麽法律都有,其實法律没有任何權威,等於虚設。如此,又怎樣治理國家呢?
《問》篇説:“事先大功,政自小始。”這是説治理國家首先要確定大的目標,即所謂事先大功,但確立了大的目標之後,卻要從具體的事務開始,即所謂政自小始。不能從小始,則大功根本不可能實現。
《小稱》篇説:“我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故先王畏民。”這裏以我與民相對而言,表明我是治理國家的人,他們必須懂得一個基本規則: 只有治國者管理者會有錯誤,而民衆是不會有過度的要求或意見的。民對治國者的觀察是治國者逃脱不了的,不要想象能瞞過民衆。總結這一規則,就是畏民,即害怕民衆的監視監督。治國者如果不具備這種思想,就會把問題推到民衆身上,而不檢查自己的錯誤,這樣治國,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所以説:“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罪身是對治國者而言的,遇事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才能得到民衆的信任,才能把國家治理好。
《任法》篇説:“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説,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任法就是相信法律,使用法律,任智就是只相信自己的小聰明小智謀,任數就是相信規律,按照規律來辦事,任説就是只相信自己的説教或説辭,希望憑藉口頭上的説辭來蒙混問題,推卸責任,任公就是一切出於公心,任私則與任公剛好相反,任大道是説按照事物的根本道理來辦事,與任數類似,但道比數更高,數可以説是符合道的具體規律,道是總和一切數的根本道理。任小物是説只就細小的事來認識問題,這樣就看不到大道是什麽,就會在根本上犯錯誤。能任法、任數、任公、任大道,這樣治國才是最正確的,不會産生錯誤,不會造成難局,不會引起麻煩和動盪,當然就是身佚而天下治。若天天忙於應對各種意想不到的麻煩動盪和難局,這樣的治國者只能説是比較低能、無能的。“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説,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這正好補充説明前面的道理,如果不如前述的那樣任法、任數、任公、任大道,民衆就會有相應的反應。反過來説,觀察民衆有無這些反應,也可以説明治國者是不是做到了任法、任數、任公、任大道。
《治國》篇説:“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富民這個道理比較容易想到,但能不能、是不是完全把國家的制度、政策與措施等按照富民的準則來制定和抉擇,則不那麽容易想到或做到了。有時候富民只是一種説辭,一種口號,而不能切實地讓民衆富裕起來,這就是治國者的最大失誤。前面所説的任法、任數、任公、任大道等,也要與這裏的富民結合起來,或者説要以是否富民為基準來衡量之,否則也會變成空洞的説辭,民衆也會看得非常清楚而採取符合他們利益的舉措來應對治國者。那樣的話,國家就會難治了。
《入國》篇説:“入國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絶。”這九條都應該與富民結合起來。富民不僅僅是讓民手中的錢多一點,而是讓他們在各方面都得到國家的關愛,得到應有的福利,各種困難都能得到國家的幫助而解決,使民衆的生活不至於走到困窮絶望的地步。
以上僅據《管子》一書中的有限資料説明了古代諸子傳留下來的著作中有豐富的思想智慧,值得現代中國參考借鑒。舉一反三,推而廣之,就會知道衆多的諸子及其著作中,還會有多少哲學、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教育、文化、科技、藝術、宗教等諸多方面的思想智慧,完全可以想象到在數量上是不可估量的,是極為豐富的,在深度上是非常睿智的。今天的“新子學”應該放寬眼界,拓廣視野,深化思維,認真挖掘,耐心整理,細心研究,對歷代諸子傳留下來的著作資料加以全面而完整的整理研究,通過現代化轉型,使之成為現代中國所需要的寶貴精神財富。
三、 總結整理諸子學的方法要科學、創新
中國歷代諸子學的豐富内容和各種智慧,在現代中國條件下,必須由研究者運用科學的觀念、方法、手段來進行全面而深入的總結、轉化後加以利用。所謂創新,是指一定要有科學性,使之符合客觀真實,而不是經不起驗證的結論與説法。所謂現代轉型,是指一定要以科學性為最高原則,在此基礎上的創新才有意義。否則單純只求創新,反而會引起混亂,造成謬誤。
在談到現代轉型時一定要認識到,歷代諸子學的内容,與現代的教育與學術研究之間存在着不小的隔閡: 一是雙方使用了古今不同的語言,這會影響今天的學者理解古代的諸子著作、話語及其所要表達的思想觀念;二是古代諸子論述問題的方式與現代學者不同,在現代學者看來,古代諸子的論述方式是分散的,甚至是散亂的,很多時候是隨感式的,没有系統,没有體系,没有專題,不分學科,没有上升到理論,没有徹底研究和論述清楚。這對於問題的徹底研究和系統廓清都是極為不利的。因此現代學者研究古代諸子,一定先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對於古代漢語,要徹底理解,並對古代學者喜歡採用的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的表述方式,要能透徹理解,然後加以細緻認真的思索分析,運用闡釋學的理念與方法從中詮釋出豐富的題中之義。其次是對古代諸子分散的、隨感的、不分學科的、未採取理論形式的、没有形成專題的、没有形成系統體系的種種論述中所隱涵的思想内容,要能根據和應用現代學術的各種學科的理論與方法等加以研究和詮釋。
此外,還應注意到,對於古代諸子學的研究,還要有更廣更高的視野,即諸子學的思想觀念與智慧,不是與國家、社會、個人的實踐相脱離或相隔絶的,而是緊密相關的。古代學者早已認識到諸子的思想學説與國家政治的緊密關係及内在關聯。如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説:“《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雖然諸子的思想主張有所不同而分為多家,但從根本上説,都是“務為治”的,即都是為了國家治理而進行思考和提出各種方案的,所以説是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這也是中國古代諸子的基本特點,與古希臘的思想家們有所不同,如亞里士多德就把自己的學術分為多科而不相混淆,這在中國古代諸子中是從來没有的情況。正因為如此,今天研究古代諸子也不能忽略這一特點,因為這本身就是歷史上的真實情況。
但關於國家治理的問題,按今天的學科分類體系來説,也不僅僅是政治學一門學科的事,也會牽涉到更多的學科,如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法學、軍事學、外交學、領導學等,甚至是地理學、海洋學、電腦與网絡、信息學以及更多的科技學科也是不能忽略的。這説明諸子本身的内容豐富,涉及學科衆多,從不同學科的角度出發,分别或合作地進行研究,也是一種必然。所以現代學者研究諸子學的時候,必須具有現代多學科意識,在此基礎上形成多學科交叉和融會貫通的研究平臺或群體,這是在現代學術條件下研究諸子學與以往任何時代都絶不相同之處,也是其優勢所在。如果真能在這方面形成理想的研究態勢,相信對於諸子學的研究必會産生史無前例的影響與效果,這對於諸子學的現代轉型也必將産生難以想象的重大影響。
以上所説的三個方面,是現代研究諸子學時不可偏廢的,應該作為整體而結合起來,這就需要從國家到各級政府再到學術界衆多學者的通力配合與自覺參與,不能再滿足於個體經營式的研究以及舊時那種注釋或單學科闡釋的方式。這對於國家及政府和學術界、學者來説,都是一個新的課題,是需要認真思考與通盤研究的。
具體説到諸子學的現代轉型,還有一點也需要注意,即要能够跳出古代諸子思考的命題範疇或範式,建立一套符合現代學科理念的研究範疇與範式,把有關問題整理成符合現代學科理念與命題的形式,不能仍舊用古代諸子所用的命題與論題。這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轉型工作。這一工作也是為了上述的各種整合所需要的基礎,同時也能使現代學者研究古代諸子的思想内容時形成共同的話語與概念,否則仍會是各學科的不同命題與論題以及相關概念,無法形成對話,無法作為整體而結合,也無法構成統一的研究平臺與系統。
在諸子學現代轉型過程中,還需要建立一套正確解讀古代諸子思想學説及其觀念的科學思維模型。這個問題的實質是要對古代諸子所提出和論述的各種學説見解按照科學思維的規律加以思考、分析和解釋,既不受古人思維模式的束縛,也不受現代學術中的某一家學派或理論的束縛。如古代諸子在反復討論人性問題時,提出了性善論、性惡論、性善惡混等不同的見解,分别反映了不同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思維與論證。到現代就有不少學者從多學科角度,根據不同學派的學説與理論,對這些關於人性問題的認識加以分析,予以一定的評價與定性。所謂科學思維,就是不能固守某一學派的認識來對它們進行評價和定性,不能做出簡單的肯定與否定,而應根據不同説法的具體内容進行科學分析,梳理其中合理與不合理的成分,由此形成關於人性的科學認識。諸子學中還有許多問題的見解不同,各有各的論證與分析,如何對這些複雜而不同的學説以及論證加以科學的分析,是諸子學現代轉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之一。建立一套科學思維模式,目的是避免對古代諸子的思想學説和見解做出簡單的定性和評價,而是應當全面清理其中的見解、主張、論證,把其中真正的智慧整理論定,才能提供給現代中國各方面人士作為有益而正確的參考。
最後一個問題是,如何整合龐大衆多的歷代諸子著作及其文獻中的複雜内容與資料?這也是現代轉型問題中的一環,不可忽視。所謂現代轉型,這一命題中包含一個意義,即能够使古代諸子學的思想與學術成果為現代中國所利用。從反推的方法來講,為達到這一目的,需要提供對於古代諸子學各種思想學術成果的具有科學性的研究成果;而形成這樣的成果,需要研究者在掌握現代學科理論與知識方法的同時,對古代諸子的相關文獻資料全面掌握而没有遺漏,這是任何科學研究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之一;而要完整掌握相關文獻資料,根據現代的技術條件與手段,應該利用資料庫技術與方法把歷代諸子文獻資料電子化,使之成為可以通過各種角度檢索出來的電子化資料,這樣就可大大節省研究者翻查海量文獻資料的時間,使他們可以集中精力分析研究這些文獻資料中的思想和學術内容。
現代電腦和网絡技術已經提出了大數據(big data)的觀念,科學界已經提出了大數據時代或大數據智慧時代的觀念。大數據即巨量資料,指所涉及的資料量規模巨大到無法通過目前的軟體工具在合理時間内進行擷取、管理、處理、並整理成為幫助經營者或研究者達到其他目的的信息。因此大數據具有四V特點: 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樣)、Value(價值)。研究大數據的專家已經發現,通過大數據方法提供的全新的信息處理模式,能够為使用者提供更强的加工能力和關於特定目標的決策力、洞察發現力,從而形成多樣化的信息成果。因此人們相信在大數據時代,誰能具備更好地掌控資料的力量,誰就能看到更多的真相,從而做出最明智的決策,從而對已有的關於世界的認識提升到全新的層次。
這樣的理念在諸子學現代轉型中也具有現實價值。諸子學研究所要面對的資料是巨量的,但在研究中又需要從巨量的資料中實現高速的檢索與擷取,收集到必要的且是複雜多樣性的全部資料,由此通過研究分析形成重要的研究新成果,實現新的價值。所以大數據的方法就是幫助諸子學現代式研究迅速、完整掌握必要的複雜資料信息,大數據方法應該成為學術研究者手中的必要工具之一。在諸子學的現代轉型之中,掌握這種方法與工具將有巨大意義。
如果按照大數據的觀念來對歷代諸子的文獻資料加以整合、整理,就要把分散的文本中的字句、話語及相關的豐富複雜的信息内容進行加工,把巨量的歷代諸子的原始資料加工為可以通過現代電腦网絡處理的資料,讓研究諸子學的學者或政府機構等各類使用者根據特定需要迅速檢索出所需的全部原始資料,而且這時檢索出來的資料在保持其原始形態的同時,也因為已經做了資料化的加工而具有了更多的學術信息。它們已經不再是原始的分散的無系統狀態,而是已被加工成具有一定系統性的資料信息。這就會為研究者或利用者提供更為方便和有用的信息,幫助他們在分析時形成更有科學性的結論與認識。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這本身是一項龐大的工程,不是哪一個人或單位就能勝任的,應該由國家統籌規劃和部署,從經費、組織、人員、管理等各方面加以整合來從事這項工作。這樣可以節省人力、物力等各種資源,避免分散低效重複和遺漏,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工作和研究的目的性,最大程度上符合國家利益,這也是諸子學現代轉型中的重要問題,是保證現代轉型得以成功的條件之一。
總之,關於諸子學的現代轉型問題,是一個涉及廣泛的重大問題,需要各學科學者以及國家與各級政府共同關心,協同思考,緊密合作,不能認為只是某些學者的事情而置之不顧,這種意識對於諸子學的研究及其現代轉型是不利的。這一點筆者也想借本文提出,請專家學者思考。
[作者簡介]劉韶軍(1954— ),男,山東掖縣人。現為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教授,著作有《太玄集注》《日本現代老子研究》《儒家學習思想研究》《楚地精魂——楚國哲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