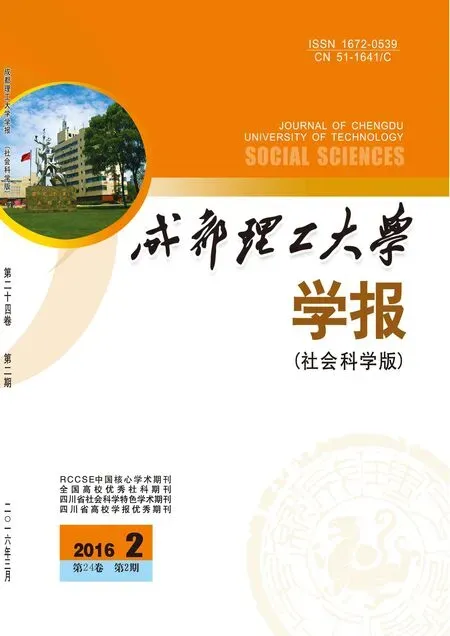波兰人民共和国三次政治危机的原因与评析
张牧洲
(首都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 北京 100048)

波兰人民共和国三次政治危机的原因与评析
张牧洲
(首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北京100048)
摘要:波兰人民共和国(1952年-1989年)在其存在的47年间于1956年、1970年和1980年-1981年发生过三次政治危机。每次危机发生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者都会更换,但这并不能阻止社会主义波兰最终走向剧变。这三次政治危机产生的共同原因,即国内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国际因素的共同作用。从更深层次来讲,二战后波兰在苏联的影响下而走上不适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使危机的产生成为历史的必然。
关键词:波兰人民共和国;政治危机;波兰统一工人党;东欧社会主义
二战波兰沦陷期间,波兰国内的波兰工人党及其他党派和境外的流亡政府同时存在且均拥有武装力量。苏波军队解放波兰后,错综复杂的波兰国内政治形势很大程度上被苏联以及其他国际势力所左右。后来波兰统一工人党(Polska Zjednoczona Partia Robotnicza)(1)领导下的“统一工人党代表工人阶级,农民党代表农民,民主党代表知识分子”[1]的三党联合执政格局形成,波兰人民共和国(Polska Rzeczpospolita Ludowa)(2)成立并成为了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此后,波兰局势并不稳定,政治危机呈周期性出现并对整个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最终波兰成为了苏东剧变中第一个改旗易帜的国家。
一、波兰人民共和国三次政治危机的基本情况
简单来讲,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历史可以分为贝鲁特时期、哥穆尔卡时期、盖莱克时期和雅鲁泽尔斯基时期这四个阶段,本文所研究的三次危机正是划分出上述不同阶段的重要历史节点。
(一)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Poznański Czerwiec)和党的二届八中全会
在1948年八九月间的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上,奉行有别于苏联经验的“波兰道路”社会主义的第一书记哥穆尔卡遭受到“右倾民族主义”的错误指责,随即被贝鲁特取而代之。此后,波兰开始模仿斯大林模式,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强调公有制,在意识形态上主张阶级斗争尖锐化等。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波兰党内和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紧接着,波兰共产党被恢复名誉,贝鲁特在莫斯科逝世,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解散,东欧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开始逐步传到波兰。1956年6月28日,由于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等诉求没能得到满足,波兹南斯大林机车厂的工人走上街头以游行的形式表示抗议。随着参加游行的人数越来越多,人们的不理智情绪被煽动起来,群众与警察在双方均有武器的情况下爆发了流血冲突,当局调动军队才平息了事态。此次不幸事件被称为“黑色星期四”。
1956年7月,党的二届七中全会在社会矛盾尖锐且党内两派分歧严重的背景下召开,做出了恢复哥穆尔卡等人党籍的决定。10月,二届八中全会召开的当天,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代表团在未与波兰方面沟通的情况下飞抵华沙,并“表达了他们对即将到来的统一工人党内人事变动的担忧并敦促波兰进一步加强同苏联的经济、政治、军事联系”[2]。同时,苏军有向华沙方向开动军事的迹象,这都使波兰局势骤然紧张。但万幸的是,经苏联权衡与双方会谈后,更大规模的冲突并未发生,此次危机以波苏两党达成协议、哥穆尔卡当选为第一书记而告终。
(二)1970年的“十二月事件”
哥穆尔卡当政时,波兰历经了三个“五年计划”。此间他逐渐向贝鲁特时期的发展模式靠拢,在国民经济上采取“重-轻-农”的安排顺序。从国际关系角度看,波兰与苏联关系密切,甚至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中参与了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1964年,34名作家和学者公开反对限制言论自由。两年后,科拉科夫斯基对哥穆尔卡执政的过去十年进行了批评”[3]。受到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鼓舞,“波兰的杜布切克(3)”成为了全社会的期望。1968年初,波兰的大学生参与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是为“三月事件”。此次事件虽然规模不大,但可以看出波兰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对时局的普遍不满。
计划经济下的波兰价格形成机制为政府定价。1970年圣诞节前夕,波兰部长会议决定提高食品和日用品的零售价格,这招致了群众的强烈不满。于是格但斯克的工人率先开始了罢工和游行。当时波兰统一工人党正在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和平示威迅速演变成为骚乱并波及到格丁尼亚和什切青等城市。当党政领导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事态已经超出了他们认为可以用常规手段控制的范畴,于是哥穆尔卡下令调动军队介入。使用强制力以镇压骚乱的军警与示威者发生冲突,从而再次酿成了不幸流血事件。事态平息后,哥穆尔卡抱病辞职,盖莱克开始担任第一书记,波兰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三)1980年到1981年间的“团结工会”危机
盖莱克执政的前一阶段即“四五”时期,波兰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的成绩,呈现出繁荣景象。但第五个五年计划开始后,各项指标全面回落,波兰经济陷入了困境。1976年6月政府宣布提价后,各地再次发生罢工,这迫使提价决定被收回,同时总理雅罗谢维奇辞职。此次工人运动持续时间较短,但可以被看作是波兰第三次也是规模、影响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机的预演。1978年,波兰籍的前克拉科夫主教当选为罗马教皇,即保罗二世,这使波兰全社会对天主教的态度更加狂热。
由于一段时期以来糟糕的经济形势加之政府再次宣布提价,“据保卫工人委员会的统计,1980年前7个月,波兰共发生了121次罢工,甚至在莫斯科奥运会期间,卢布林的工人封锁了莫斯科到华沙的铁路线”[4]。在1980年8月份时,罢工已经从分散走向了联合并发展为全国性的罢工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各罢工委员会达成了基本满足其包括政治层面要求在内的协议。当然这样协议的达成必然在官方认定的政治限度之内,例如副总理雅盖尔斯基在与瓦文萨(4)签订完协议后的演讲中强调:“新工会在意识形态的方向上是明确的——他们支持宪法所规定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地位并接受我们的盟友”[5]。按照协议,东欧地区第一个独立的自治工会——团结工会在1980年11月成为了合法组织。自此,波兰政坛出现了一股将矛头直指现行制度,与执政党对立的政治力量。团结工会自成立后“招募了包括不少全职人员在内的多达20万的活动者”[6],积极充当政治反对派的角色。危机的持续使生产停滞、社会动荡,而且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执政地位受到了严峻挑战,因此在1981年底,波兰当局开始实行军事管制以稳定局势。第三次危机虽然结束,但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军管后,西方国家不仅对波兰实施制裁而且加紧了和平演变的步伐,团结工会则转入地下继续活动,同时波兰的经济状况并未好转。终于在1989年,波兰统一工人党将“政治多元化”付诸实践并在大选中失利,波兰就此剧变。
二、波兰人民共和国三次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
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三次政治危机的导火索都是短期经济问题,而且每次危机的爆发都有个性因素。但从整体和根本上讲,危机的产生是当时国内国际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波兰在战后不顾其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发展状况,急于按苏联模式踏上社会主义道路,使危机的爆发成为了必然。
(一)波兰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冒进的发展方式
波兰的国民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且在二战中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时期,波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民经济发展有两个显著特点——“重-轻-农”的顺序和追求高速度,其最终造成的就是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困境而且人民生活水平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提高。三次政治危机前期的抗议活动都是由工资或物价等因素引起的,而危机产生的实质原因是宏观上波兰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弊病。作为传统的农业国,截至到1960年,波兰仍有“47%的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苏联为39%,东德为17%)”[7]。波兰也曾做过农业集体化的尝试,但哥穆尔卡上台后根据集体化效果不甚理想的实际情况,决定“实施将小农作为农业生产和乡村生活结构转型的主要推动力的农业政策”[8]。不过遗憾的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导致农业领域的投资不足,这制约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因此,不仅农民的收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1956年,农民月均工资为852兹罗提,而同期体力劳动者的整体月均工资为1144兹罗提”[9],而且农产品的供应难以满足居民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战后,波兰开始大规模工业化进程。“1953年,波兰的积累率高达38%,同时政府将国民收入的22.6%用于投资,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短时间内人民的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8]139。同时,在工业领域急于求成必然导致工人工作量增加且工作环境恶化,如果工资不变,工人的劳动报酬实际上减少了,这也是造成1956年危机的原因之一。哥穆尔卡执政时,波兰的经济体制比较僵化,60年代末,“波兰的食品需求收入弹性仍较大”[10],“从1959年到1968年,波兰人均个人消费与1958年相比合计仅增长了24.3%”[11],这都说明了哥穆尔卡时期波兰的消费水平偏低而且提高缓慢。
盖莱克上台后,波兰经济迎来了一段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1971年到1975年间,波兰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为9.8%。但成绩的取得很大程度上是在“当时波兰增量资本产出率很高”[10]611的情况下偏向重工业领域高投资的结果。这种失衡冒进的发展方式浪费严重、效率低下,而且超过了波兰当时国民经济的整体承受能力,所以是难以为继的。投资之外,随着1970年波兰同西德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波兰同西方的经贸往来大幅增加(“1970年波兰进出口总额为71亿美元,1980年为361亿美元”[12]),这的确对波兰经济的增长起到了拉动作用。不过当“1975年,油价波动和西方市场经久的衰退开始影响到波兰时,盖莱克为保持经济增长继续借贷”[13],此举导致了波兰的经济危机。从1979年开始,波兰的GNP已经开始负增长,至1980年,波兰的净外债已高达235亿美元[13]461。“1980年9月中旬,86%的波兰人认为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差的”[14],民意证明了盖莱克不切实际的发展战略的失败。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70年代,波兰的经济发展确实比以往更多地惠及到了人民。与1970年的数据相比,1975年波兰人均小时工资提高了42%,而且市场上物价比较稳定,这使波兰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量大幅增加,生活水平也有显著的改善。如“1965年,波兰年人均肉类消费量为49千克,1980年为74千克;相应地,马铃薯年人均消费量从1965年的215千克下降到1980年的158千克”[12]161。不过此时波兰人的消费层次并没有迈上一个新台阶。“1973年,一台23英寸的彩色电视售价为25000兹罗提,当时一户家庭的全年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取值在55000到60000兹罗提之间”[15],这样的售价对于工薪阶层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更重要的是,由于波兰在经济发展中一直没能兼顾到国民经济中的各个部门使其协同进步,农业和轻工业的产品供应并不能跟上消费需求增加的步伐,鉴于此,决策者只得暂时“通过调整计划和实际供给来平抑过量的需求”[16]。可以说在社会主义波兰时期,人们的消费欲望由于受到了从能力到供给两方面的压制而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满足。此外,“从1971到1976年,波兰政府支出的食品补贴从220亿兹罗提增加到了1000亿兹罗提,这样的数目将近占国民收入的8%”[11]268,沉重的财政负担使政府不得不在经济困难时进行价格调整,这从短期来看是符合市场规律的正常行为。但长期的政府定价使价格变动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很大,再加上人们对于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和个人生活水平的不满,由涨价引发的危机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波兰僵化的政治体制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
统一工人党成为唯一执政党后,波兰的国家权力愈发地集中在一党手中。“政府官员中波兰统一工人党员的比例在1955年为53%,这一数字在1982年已经上升到了85%”[17]。这样一来,波兰也出现了类似苏联的党政不分甚至以党代政的现象。权力的行使在程序上限制减少,其结果的正当合理性也必然会打折扣。人民共和国时期,波兰统一工人党最高权力的移交没有一次是通过正常的制度化安排完成的。非任期制使国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掌握最高权力的个人的能力和决策。不论是贝鲁特、哥穆尔卡还是盖莱克,他们在国家发展出现问题时都寄希望于通过局部调整来加以解决,即固执地认为自己的政策从根本上讲是正确的。虽然统一工人党有中央政治局这样的集体领导机构,但在党的最高领导人因不受制度约束而可能长期掌握权力的情况下,其集体领导的作用会十分有限,反而会形成一个执意坚持现行政策的政治团体并阻碍改革的推进。此外,统一工人党内垂直不流动的现象也比较突出,广大普通党员的政治上升通道被堵塞。总的来讲,不论是从党内还是党外,不论是从决策层还是实践层,波兰的错误发展方向都不能被及时纠偏。党和国家的权力过多地集中在上层,这样在政策制定上民意难以有效传达而在政策落实上基层又缺乏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的自主权,而且人民对缺乏民主和权力垄断等政治上的不满会因为经济局势的恶化迅速放大,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首先“要求与波兰社会的其他三个支柱——国家官僚、共产党和教会分享权力”[18],最终导致了危机的产生。
二战末期波苏军队解放了波兰全境,因此以波兰工人党为多数派的临时政府相较于流亡政府更具掌握全国政权的优势,而且苏联也更有能力对波兰的未来选择发挥作用,何况苏联本身就有地缘优势。在伦敦流亡政府和国内反对派一直存在的情况下,虽然波兰建国的过程中经过了全民公投和选举等程序,但波兰的社会主义选择从某种意义来说是拥有更强军事实力的一方做出的,而没有特别广泛、牢固的民意基础。“波兰在文化上属于西方并拥有民主政治的传统”[19]。贵族共和国时期,波兰曾实行过自由选王制,“二战前的波兰具有政治多元化的特点——例如在1928年至少有28个党派参与了竞选”[20]。人民共和国时期波兰统一工人党高层垄断了国家权力,必然招致社会各阶层包括党内的不满。更为重要的是,波兰一直是天主教国家,其天主教徒比例在95%[21]以上,而且波兰统一工人党也同意其党员拥有宗教信仰,这与马列主义无神论的哲学观点形成了严重对立,大幅削弱了社会主义政权的价值认同基础。贝鲁特时期,在党内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雅各布·伯曼曾说:“教会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反动思想的哲学基础来源于此,并且它还持续不断地将这种思想传递给群众”[20]1261。20世纪70年代末,波兰籍克拉科夫主教当选为罗马教皇并于不久之后访问波兰,即保罗二世,此时恰逢波兰经济陷入困境,时任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预言:“波兰籍的教皇将像霍梅尼在伊朗那样,调动起同胞们对宗教的热情”[22]。天主教使人们团结在波兰的文化传统和相对一致、有别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周围,无形中对历次政治危机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从1956年开始哥穆尔卡有选择地搁置了一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因为他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来确保政治领域的改革在推行时不会使社会主义的根基动摇”[23]。波兰的社会主义基础不论从文化价值还是政治认同、国民经济来说都比较薄弱,首先这就为危机的产生埋下了隐患;日后,党为了保证红旗不倒,当然还有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只能小步、缓慢甚至流于形式地改正现实中出现的错误,使改革的进程滞后于问题的积累,最终国家积重难返,导致了三次政治危机的出现。
(三)外部环境对波兰国内政治的制约和影响
苏联一直对波兰人民共和国政治形势发挥影响。其一是苏联政局变化对波兰产生作用。贝鲁特时期,波兰不光在经济上效仿了斯大林模式,在政治上也采取了缺乏民主法治的高度集权式的组织管理形式,比如“两个层次的文艺审查机制——即当局不仅在出版演出环节确保文艺作品遵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且在流通领域限制非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文艺作品传播”[24],诸如此类的做法引起了党内外的广泛不满。有学者认为:“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是令波兰共产主义复活的唯一机会”[25],事实的确是这样。虽然赫鲁晓夫并不希望一个独立自主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出现,但他的“秘密报告”将斯大林的错误昭示天下,这客观上使波兰党内斗争的天平迅速倒向了走“波兰道路”的哥穆尔卡一边。这样一来,在贝鲁特亡故、工人罢工之后,哥穆尔卡再次走向台前并与苏共和波兰党内保守势力产生矛盾最终引发了一次政治危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其二是波苏关系。“1946年红军撤离时,苏方不仅保留了指挥部和几个师的兵力,还将号称拥有双重国籍的约15000名退伍军人安放到波兰军队中”[17]96。此外,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还于1949年出任了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波兰国防部长。诸如此类的事情表面上是两国同盟的体现,但由于两国在历史上存在过节,现实中苏联模式的实践也不很成功,因此波兰社会上下对战后形成的以苏联为主导的波苏双边关系并不认同,而且希望波兰在东欧能保持独立地位。尽管如此,处于冷战前沿阵地的波兰一直存在于华约框架内,这必然引起全社会对波兰执政当局的严重不满。可以说在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反苏的民族情绪一直在社会上蔓延,三次危机的爆发与此不无关系。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双重考虑,冷战时期,苏联一直保持着在波兰的存在,当然波兰在国家安全和经济上也确实对苏联有依赖。而且“西方越是尝试用经济、科技、军事优势来换取苏联的让步,越会增加苏共领导人的不安全感,因此西方并不能阻止苏联对东欧的干涉”[26]。虽然波苏关系未像苏南、中苏一样曾经决裂,苏联也未曾像干涉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直接插手波兰内政,但毋庸置疑的是直至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之前,苏联对波兰改革的制约作用还是比较强烈的。与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波兰的命运可以说是和苏联捆绑在一起的。
除苏联外,另一个在冷战时期对波兰政局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马歇尔计划东扩失败后,美国并没有放弃通过经济手段来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努力。当然在两极格局业已形成的情况下,大规模的援助建设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努力更多地潜移默化地寓于双边经贸往来中。盖莱克上台后吸取了前任的教训,着手迅速提高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水平,但这依靠波兰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1971年-1975年,波兰年均进口增幅为15.5%,其中自西方进口年均增幅达27%”[27],可见盖莱克时期波兰大规模的外贸中,西方所占比重在逐渐增加。1970年,随着波兰和德国边界问题的解决,波兰同西方的关系有了显著的改善,这为波兰通过与西方进行经贸往来,依靠发达国家力量发展本国经济提供了政治可能。波兰距离西欧市场近而且自然资源、劳动力都比较丰富,所以“当局尝试引进西方的资本和技术发展外向型工业”[28]。由此,波兰经济虽然仍在计划体制和社会主义分工体系内,但是更多地与西方产生了联系。西方国家的“滞胀”危机发生后,波兰的出口受阻,在缺乏硬通货以偿还贷款的同时国内经济也因前段时间的超速发展和国际经济形势而陷入了困境。但此时盖莱克仍固执地坚持他的高速发展战略,给了西方利用借贷从而从一定程度上控制波兰的机会。20世纪70年代后期,波兰经济难有起色,其所欠外债越来越多,对西方的依赖逐渐增强。西方发达国家与波兰的经贸往来,首先,使其不再完全依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框架,并试图渐进地将它纳入到市场经济体系中来,以经济转轨推动政治变革;其次,西方的贷款、援助等都附加有政治条件,当波兰经济出现困境而又对西方依存度越来越高时,波兰不得不做出政治让步以换取经济支持,避免短期内国内更大的动荡;第三,经贸往来中的人员流动、文化交流等使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更便利地输入到波兰,这使波兰人民看到自身生活水平与西方的差距,加剧了人们对于波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主义的不满。总之,冷战时位于前沿阵地,属于西欧文化圈同时又归附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自然是两大集团争夺的热点地区,美苏都对波兰人民共和国的三次政治危机的产生起了不小的作用。
三、对波兰人民共和国三次政治危机的评析
从根本上来讲,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三次政治危机是波兰战后在苏联影响下错误地走上了与本国国情不相符合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在日后未能进行有效改革造成的。这三次危机并不是孤立的。首先,它们可以被看作是波兰剧变的预演。从波兹南事件开始,波兰每一次政治危机都将最终导致剧变的种种国家弊病暴露无遗。随着各种矛盾越来越激化,每次危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最终在1989年内外因素都具备的条件下,波兰发生了剧变。其次,这三次危机之间呈现出周期性规律,即危机发生在每位长期执政的第一书记任内末期。一位领导人一贯的、得不到适时改变的政策是危机产生的原因,危机也正是导致该领导人下台的原因。第三,这三次危机的过程几乎如出一辙,都是从工人罢工到广泛的群众游行,从单纯要求改善经济条件到提出深层次的政治诉求。在这三次危机中,前两次都发生了流血冲突。究其原因,信息传达滞后、对群体性事件意识薄弱使当局没能在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事态扩大,面对群众诉求的官僚主义态度激起了群众强烈不满,波兰党政部门难辞其咎,这也是给我国的一个深刻教训;但另一方面,游行队伍中有不理智者(或确实是别有用心者)煽动群众,采取了纵火、冲击机关大楼等极端行为,大大超出了行使公民权利的合法、合理范畴。在这种情况下抛开意识形态不谈,当局完全从维护社会治安的角度采取一定的武力是正当的。因此,将前两次危机的流血冲突简单概括为政府血腥镇压或是国内外反动派制造动乱都是片面且有悖于事实的。
另外,“有别于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来自西方顾问的建议,团结工会从不通过任何形式的暴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29]。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中就已经出现了“打倒布尔什维克、米科瓦伊奇克(5)万岁”[30]等政治口号,但直到“团结工会”危机时,波兰统一工人党才“展现出了政权更大的灵活性,即迅速做出让步的同时准备与反对者达成妥协”[31]。事实的确如此,比如“文化部宣布于1969年12月30日施行的第120号指令失效,文化管制的力度有所减轻,克拉科夫的党报甚至介绍了一些诸如伦敦流亡政府出版的《当前波兰政治历史》此类的禁书”[32]。“团结工会”运动席卷波兰,调动起来社会各阶层,甚至“有学生占领了罗兹大学,要求赋予高等学校在学术和内部组织上更大的独立性”[33]。从影响上看,团结工会大大超出了工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范畴,使波兰统一工人党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党在国家发展已经陷入困境的情况下选择了尽快与团结工会达成协议以维持现状来确保其执政地位,虽然历史已经证明此举是无济于事的。
肇始于波兰的苏东剧变标志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终结,它的发展过程中有太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从宏观上看,如何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怎样使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国家经济腾飞的速度相一致,如何在保证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推进政治民主化;从微观上看,怎样及时、正当地处理群体性事件等都是极具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波兰人民共和国的三次政治危机已经成为了历史,其应该能在上述问题中给发展中国家以经验和教训,使它们不再重蹈覆辙。
注释:
(1)波兰统一工人党,即为波兰的共产党,是执政党。1938年,波共被共产国际错误地解散。1942年,波兰工人党成立。1948年底,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组成该党。
(2)波兰人民共和国:1944年成立时称波兰共和国,1952年宪法通过后改称此名。1989年波兰剧变后仍称波兰共和国。杜布切克: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在1968年推动了国内的改革运动,尝试走一条异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为布拉格之春。后来他的改革遭到华约集团的武装干涉而被迫终止。
(4)瓦文萨:原为格但斯克造船厂电工,1970年“十二月事件”时崭露头角。时任格但斯克-戈丁尼亚-索波特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后为团结工会领导人,曾获1983年诺贝尔和平奖。剧变后任波兰总统。
(5)米科瓦伊奇克:曾任波兰伦敦流亡政府总理,1947年大选失利后赴美国,反对“人民波兰”。
参考文献:
[1]Pedro Ramet.Poland’s Other Parties[J].The World Today, 1981,37(9):332.
[2]Mark Kramer.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1956 Crises in Hungary and Poland: Reassessments and New Findings[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98,33(2):169.
[3]Adam Bromke.Beyond the Gomulka Era[J]. Foreign Affairs, 1971,49(3):481.
[4]Philip Windsor.Can Poland Strike a Balance?[J]. The World Today, 1980,36(10):392.
[5]Jadwiga Staniszkis.The Evolution of Forms of Working-Class Protest In Poland: Soci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Gdansk-Szczecin Case, August 1980[J]. Soviet Studies, 1981,33(2):217.
[6]Jerzy J. Wiatr.Mobilization of Non-Participants during the Political Crisis in Poland, 1980-1981[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4,5(3):237.
[7]Ole Nørgaard, Steven L. Sampson.Poland’s Crisis and East European Socialism[J]. Theory and Society, 1984,13,(6):778.
[8]Wladyslaw Bienkowski.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Poland Since October 1956[J].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8,34(2):140.
[9]Lidia Beskid and Jan Solecki.Real Wages in Poland during 1956-1967[J].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1969,7(3):33.
[10]Bogdan Mieczkowski.Recent Discussion on Consumption Planning in Poland[J]. Soviet Studies, 1971,22(4):611.
[11]Bogdan Mieczkowski.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in Consumption and Politics in Poland[J].Soviet Studies, 1978,30(2):264.
[12]Cezary Kuklo, Juliuszukasiewicz i Cecylia Leszczyńska. Historia Polski w Liczbach[M].Warszawa: Gwny Urz?d Satystyczny, 2014:433-434.
[13]Kazimierz Poznanski. Economic Adjustment and Political Forces: Poland since 1970[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6,40(2):465.
[14]Alex Pravda. Poland 1980: From’Premature Consumerism’ to Labour Solidarity[J]. Soviet Studies, 1982,34(2):172.
[15]J. Hart Walters. Marketing in Poland in the 1970s: Significant Progress[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75,39(4):47.
[16]Richard Portes, Richard E. Quandt, David Winter and Stephen Yeo.Macroeconomic Planning and Disequilibrium: Estimates for Poland, 1955-1980[J].Econometrica, 1987,55(1):36.
[17]David A. Andelman. Contempt and Crisis in Poland[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82, 6(3):102.
[18]Johan Galtung.Poland, August-September 1980. Is a Socialist Revolution under State Capitalism Possible[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80,17(4):281.
[19]Kristi S, Evans. The Argument of Images: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in Solidarity Underground Postage, 1981-87[J]. American Ethnologist, 1992, 19(4):750.
[20]Tony Kemp-Welch. Dethroning Stalin: Poland 1956 and Its Legacy[J], Europe-Asia Studies, 2006, 58(8):1262.
[22]Matthew J. Ouimet.National Interest and the Question of Soviet Intervention in Poland, 1980-1981: Interpreting the Collapse of the’Brezhnev Doctrine[J].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2000, 78(4):712.
[23]Andrzej Werblan.Wladyslaw Gomulka and the Dilemma of Polish Communism[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8, 9(2):154.
[24]Oskar Stanislaw Czarnik.Control of Literary Communication in the 1945-1956 Period in Poland[J]. Libraries & Culture, 2001, 36(1):104.
[25]Tony Kemp-Welch. Khrushchev’s ‘Secret Speech' and Polish Politics: The Spring of 1956[J]. Europe-Asia Studies, 1996,48(2):183.
[26]Jonathan Steele. How the West Does Not Serve Poland[J].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82, 4(4):300.
[27]Peter S. H. Tang. Experiments in Communism: Pol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J].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1983, 26(4):322.
[28]Michael Mandelbaum. Poland between East and West[J]. Society, 1988, 15(4):11.
[31]Wojciech Lamentowicz. Adaptation through Political Crises in Post-War Poland[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89,19(2):123.
[32]Alexander Remmer. A Note on Post-Publication Censorship in Poland 1980-1987[J]. Soviet Studies, 1989, 41(3):416.
[33]Jack M. Bloom. The Solidarity Revolution in Poland, 1980-1981[J]. The Oral History Review, 2006,33(1):47.
编辑:鲁彦琪
The Causes and Comments to the Poland’s Three
Political Crises Dur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Period
ZHANG Muzhou
(School of Politic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048,China)
Abstract:In 1956, 1970 and 1980-1981, there were three political crises brok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Poland. After each crisis, the leader of the Polish United Workers’ Party was replaced, but it could not stop the country from the revolution in the end. These three periodic crises have the same reasons: the state’s rigi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international factors’ effect. Analyzing in deeper, under the Soviet Union’s effect and regardless the country’s objective situation, Poland set up the socialism after the World War II. It made the happening of the crises inevitable.
Key words:People’s Republic of Poland; Political Crisis; Polish United Worker’s Party; Socialism in Eastern Europe
中图分类号:K5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2-0089-07
作者简介:张牧洲(1996-),男,北京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国际政治。
收稿日期:2015-08-15
DOI:10.3969/j.issn.1672-0539.2016.0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