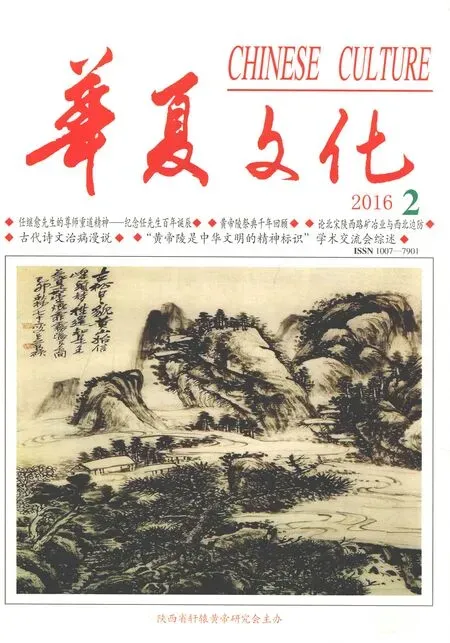论二程对张载《西铭》的接受
□ 姜 辉
论二程对张载《西铭》的接受
□ 姜 辉
张载是宋明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其思想体系的完备和周密,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并不多见。他在讲学期间,于书房东西二牖各铭一文,东一则曰《砭愚》,西一则曰《订顽》,后经程颐提议,更名为《东铭》和《西铭》。此“二铭”被置于张载著作《正蒙》的末篇《乾称》的首尾,成为此篇的一部分。《西铭》言辞简要,意蕴广大,全文仅仅二百五十三字,却作为张载儒学思想的总纲,化育出整部《正蒙》,常常被视为独立篇章加以研习、探讨,对于宋以降新儒学的发展影响颇大。
北宋时期,张载关学的影响较二程领衔的洛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由于历史原因,张载后学并未能将关学一脉发扬光大,北宋之后,纯正的张载之学就已然没落,时至明清时期,绝大多数头戴“关学”帽子的关中学者,实则以朱子为宗。《宋元儒学案序录》曰:“关学之盛,不下洛学,而再传何其寥寥也?亦由完颜之乱,儒术并为之中绝乎?《伊洛渊源录》略于关学,三吕之与苏氏,以其曾及程门而进之,余皆亡矣。”此中蓝田吕氏兄弟、苏昞在张载亡后,由关入洛,尚有一定建树,其余关学学生影响均有限。而即便是吕大防、吕大临,著作、资料也是散佚严重,据袁本《郡斋读书志》附志卷下集部语录类著录《二十先生西铭解义》,二吕各自撰有“西铭解”,但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称吕大临著有《西铭集解》一卷,但未言及吕大防之《西铭解》,可见大防之书于元初已佚。而此后亦无人再论吕大临之《西铭集解》,疑此书佚于元代。应该客观地说,本当为张载学术正宗的关学弟子对《西铭》的研学,对于整个《西铭》接受史来讲,并未产生足够的影响,而《西铭》在宋明理学中的地位,首先是由二程确立的。
二程对《西铭》极为推崇,多次论及《西铭》。《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上)》有黄百家案语曰:“程子曰:‘《订顽》之言,极纯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又曰:‘《订顽》立心,便可达天德。’”此为程颐对《西铭》的评价。程颢说:“《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又说:“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还说:“《西铭》,某得此意,只是须得子厚如此笔力,他人无缘做得。《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语。……若《西铭》,则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说道,元未到《西铭》意思。据子厚之文,醇然无出此文也。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下)》)二程将《西铭》推向至高,认为孟子之后,秦汉而唐宋,无出其右者。古人常好厚古薄今,在此却是个例外,二程不仅将出于同一时代的《西铭》和孟子相提并论,而且程颢还明确指出唐代韩愈的《原道》“元未到《西铭》意思”。二程甚至要求自己的学生入门先研读《西铭》,以至于朱熹说:“程门专以《西铭》开示学者。”二程如此推崇《西铭》,但并不是全面接受了张载,小程子曾就张载《正蒙》提出过不同意见,说:“横渠立言,诚有过者,乃在《正蒙》。”(《二程集·答杨时论〈西铭〉书》)唯就《西铭》一篇,二程是毫无保留地接受和认可。其原因在于,二程的学识积累如同一垛薪柴,而《西铭》如同一根燃烧的蜡烛,正好借来点燃了自家“理一分殊”的大火。
根据《西铭》提出“理一分殊”的概念,始于杨时和程颐讨论《西铭》的书信。先后师从大程子、小程子二位先生的杨时,在书信中就《西铭》与墨子“兼爱”之比较求教于程颐,说:“《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而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则后世有圣贤者出,推本而论之,未免归罪于横渠也。某窃意此书盖西人共守而谨行之者也。愿得一言推明其用与之并行。庶乎学者体用兼明,而不至于流荡也。”(《龟山集·寄伊川先生》)杨时表面上在说《西铭》之旨与墨子“兼爱”的关系,实则直指《西铭》体用不相及的问题。在回答学生疑问书信中,程颐全面否定了杨时对《西铭》的质疑,于破立之间道明了张载和墨子之间的差异,认为《西铭》的伟大就如同孟子一样,是前无古人的:“《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二者亦前圣所未发,岂墨氏之比哉?”程颐继而比较了《西铭》和墨子的“兼爱”思想的差异:“《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所谓“爱无差等”就是“无分”,这是要求人们无论远近亲疏一律毫无区别地对待,这会导致“无义”。而“无分”的对立面也不见得可行,“无分”的对面就是“分殊”,“分殊”过分地强调差异性,会导致个人主义思想的蔓延,也就是“私胜”,这是“失仁”。若要既非无义,也不失仁,只有在分殊之前加上一个前提,就是“理一”,从而即可推己及人。同时,程颐认为杨时对《西铭》“言体不及用”的评价更是偏颇,“且谓言体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为用也,反谓不及,不亦异乎?”强调《西铭》思想本来就具有实用性,绝非体大而无用。杨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师说,“横渠著《西铭》,先生(此指杨时)疑其近于兼爱,与伊川辩论往复,闻‘理一分殊’之说,始豁然无疑,由是浸淫经书,推广师说。”(《宋元学案·龟山学案》)
综上可以见出,北宋时期,《西铭》并未引起关学学者的足够重视,张载弟子苏昞在整理、出版张载遗作《正蒙》时,并未将《西铭》篇独立成章,而只是置之于《乾称》篇首,作为此篇的一部分而已,这就相当于关闭了张载关学正宗对《西铭》解释的大门,而将话语权交给了二程。
《西铭》在两宋学界影响巨大的原因,首先在于二程的推广。在当时,不惟杨时,但凡洛学子弟都必认真研读《西铭》,朱熹说“程门专以《西铭》开示学者”,程颐评价学生游酢“读《西铭》,已能不逆于心。言语外立得个意思,便能道中庸矣。”而程颐晚年弟子,后来开创和靖学派的尹焞“因苏昞见伊川,自后半年,亦得《大学》、《西铭》看。”没有二程的极力推广,《西铭》不可能被广泛了解和接受。
经由程颐与杨时通过书信对《西铭》进行的探讨,“理一分殊”的命题就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西铭》的接受就集中在对“理一分殊”问题的讨论上。由杨时引发的讨论,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虽然《宋元学案·龟山学案》称杨时后来认同了程颐的观念,但实际上,杨时对于《西铭》的理解与程颐还是存在一定差别的,他说:“前书所论,谓《西铭》之书……所谓明理一也。然其弊无亲亲之杀,非明者默识于言意之表,乌知所谓理一而分殊哉?……某昔者窃意《西铭》之书有平施之方,无称物之义,故曰言体而不及用,盖指仁义为说也。”这样的讨论也没有随着南渡而结束,恰恰相反,朱熹延续并发展了对《西铭》以及“理一分殊”的研究讨论,使《西铭》之论成为闽学的关键学术问题之一。
(作者:陕西中医药大学人文管理学院,邮编712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