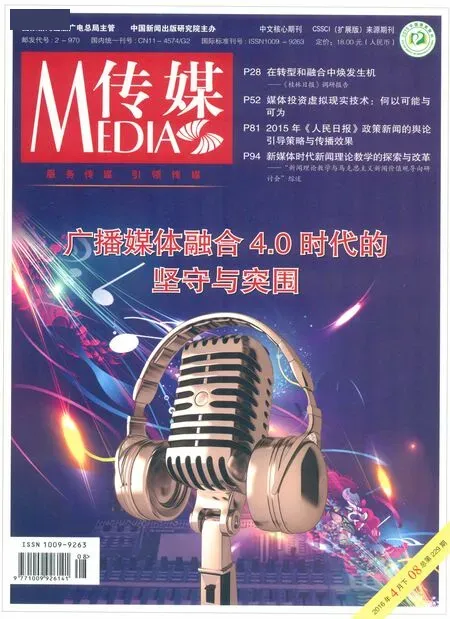电影《捉妖记》对中国传统艺术的承袭与创新
文/席 威
电影《捉妖记》对中国传统艺术的承袭与创新
文/席 威
由许诚毅执导,白百何、井柏然主演的《捉妖记》以新颖的故事情节,传奇的故事发展脉络,精准定位内地消费市场,取得了电影票房上的良好成绩。从构思到拍摄,《捉妖记》历经5年的时间,其故事原型来源于中国志怪故事《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情节,并加入《山海经》中的传统元素。从电影对中国传统志怪小说创作的承袭上来看,无论是影片的选材、主旨,还是人物塑造等都有传统文化的影子。这也是这部电影之所以让观众倍感亲切和熟悉的重要原因。但是,影片制作者并不满足于仅仅承袭传统文化元素,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融入了大量的现代元素,使影片演绎得新颖独到,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比如,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妖魔鬼怪势必是邪恶的象征,被无数文学作品塑造成反面形象,俨然成为类型化的艺术形象。为了取得良好的故事效果,许诚毅与编剧袁锦麟突破这种思维定势,采取与众不同的风格来包装电影,本着一种综合开放、兼容并包的态度,汲取一切观众喜爱的元素,并兼顾了各个观影年龄段,融搞笑、温情、奇幻、古装等为一体,最终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毫不夸张地说,《捉妖记》在承袭中国传统艺术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创新和改造,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是传统与现代、温情与搞笑、正义与勇敢、承袭与创新的典范之作。
对中国传统艺术元素的承袭
《捉妖记》的情节设计来自中国古典文化观念。在遥远的古代社会,受制于恶劣环境的影响,人对自然的认识及解释都远未达到科学的水平,人只有通过对自身生活空间的认知以及伦理来类比不能够解释的自然社会现象。当时的农业发展受制于自然环境,因此理所当然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敬畏使人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
电影《捉妖记》对妖怪的塑造恰恰反映了中国古人对自身生活环境的解释。妖界大乱,新妖王要铲除老妖王的余党,老妖后带着腹中的胎儿逃命途中遇到除妖天师霍小岚(白百何饰)和永宁村保长宋天荫(井柏然饰),机缘巧合下,宋天荫“孕育”出了小妖王“胡巴”,在一路的遭遇中,人与妖身上的复杂性被不断表露出来。有凶恶杀戮的妖,也有忠贞护主的妖;有斩妖除魔维护人间和平的人,也有猥琐势利、唯利是图的人。人妖共存是否可能?影片通过几个主要人物心理状态的改变与次要人物真实身份的揭露告诉了我们答案。霍小岚作为天师,除妖是她的职责所在,在天师的固有概念中,“妖”是威胁人类和平的存在,要予以消灭。而在宋天荫“生”出了胡巴后,霍小岚决心要将胡巴卖掉,在与胡巴一路相处的过程中,霍小岚对这个会卖萌、会体贴人的小妖王逐渐产生了感情,天师身份的霍小岚对胡巴的态度转变是影片中主要的情感线索之一。而作为这一条情感主线的辅佐,天师罗刚(姜武饰)和小妖的相处从开始时的水火不容,到最后小妖救下了罗刚,罗刚成为“又一个叛变的天师”,在为影片提供了丰富笑料的同时,也丰富了影片的情感表达。
《捉妖记》在叙事方法上有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借鉴。除故事取材于中国古代传统小说外,影片在叙事手法上也借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方式。中国人长期受到历史文化的熏陶,形成对中国文化的固定认知,正是对传统文化的自我认同,才使观众能够对《捉妖记》产生思想观念上的强烈共鸣,可以说,正是这种文化观念的契合才将观众与影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此分析可知,《捉妖记》体现了如下几种传统叙事手法。
首先,影片彰显的是一种世外桃源式的理想。传统农耕社会中,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是农民对安逸生活的一种向往,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影片所塑造的场景开始于“永宁村”,单从这一名词上就能体会到居民对自己安稳生活的向往,而电影所呈现的画面更是洋溢着田园气息,处处清晰可见的是祥和安乐。在中国古代,中国文人希望过着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人与人和谐共处。其实,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一直都存在着相关的心理认知,为了与这种心理形成文化契合,电影将美好的永宁村画面展现给观众,同时也演绎着美好生活被破坏的一面,正是这种剧烈的反差形成了强大的叙事张力,而这也是电影想要彰显的效果。
其次,中国传统志怪小说善于描写妖魔鬼怪的奇异形象,在这些怪异形象中赋予了中国古人充满奇幻色彩的想象。鬼怪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这种产物与现实生活既具有时间距离又存在着空间距离,现代人对其的理解存在于好奇心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染,中国电影文化偏向于从古典的志怪小说中借鉴相关的内容。《捉妖记》借鉴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也将现代文化的流行元素融入影片中,使其在契合历史传统的文化心理的同时,也满足了现代人的审美习惯。
最后,寄托美好愿望的大团圆式的结局也是对中国传统小说的承袭。在中国人的历史情结中,圆满的故事是大众一致的心理期待,同时,大众对具有喜剧性情节的电影也非常钟爱,所以电影制作方可根据观众的喜爱来把握电影发展的走向。《捉妖记》立足中国文化背景,始终考虑到观众的心理接受能力,在文化上认同正义的观念,善恶皆有果,也将观众内心所渴望的正义表现出来,从而赢得良好的市场回报。
形象塑造与表现手法的创新
《捉妖记》是一部充满新意与诚意的电影。炫丽的特效中结合多种艺术形式,集中表达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的主题,其嵌入对社会发展的思考,引人深思。相较于同时期上映的电影,《捉妖记》在人物形象塑造和电影情节两方面的突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影片的创新之处也是其获得成功的重要卖点和看点。
以胡巴为代表的人物形象的创新。小妖胡巴承担起了这部影片中的大部分“萌点”与“泪点”。胡巴作为影片的主要形象与线索,他的遭遇推动着影片情节的发展,也维系着影片情感的发酵。胡巴的形象,结合了西方奇幻色彩与中国本土审美观念,“中西结合”的胡巴在众多虚拟人物中独树一帜,受到了人们的喜爱。灵动的大眼睛,生气、撒娇、内疚时会表现出不同的情态,尽管观众听不懂“妖语”,却仍然能够领会到小妖的情感动态。除胡巴之外,影片中几个戏份较重的妖也各具特色,并具有鲜明的形象特点。忠贞护主的一男一女两妖:竹高和胖莹幻化成人形时由曾志伟、吴君如扮演,而他们的原型却是男妖高挑,女妖丰腴,在视觉上颠覆的同时也达到了很好的喜剧效果。这对妖怪情侣在出场时就给人带来一种亲和感,导演也赋予了他们很多人性化的特色,无论是在被四钱天师捉住还是在逃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搞怪、搞笑行为,都不禁让人捧腹。
同时,众多以动植物为原型的妖的形象是影片不得不提的独特之处,胡巴更是以其极像萝卜的造型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小萝卜”。这种代入是不可避免的,而导演也似乎有意在这种代入下传达一种理念。现实世界中没有妖,但人类绝不是天地中唯一的生物体,万千动植物与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和谐共处”的最终结局,也是一种情感诉求。在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葛千户(钟汉良饰)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对妖界进行屠杀,将各种妖怪做成美味佳肴供人享用,这种场面无疑是在映射现实社会中的不良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为了满足对野生动物的新鲜口感,在利益的推动下,一大批珍稀野生动物被掠杀。影片有意地通过一些台词来呼吁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为自然界的生物创造一定的生存空间,通过实现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最终创造出一片和谐的自然环境,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电影情节表现手段的创新。电影作为艺术表现形式的一种,为表达主题有着不同的表达手段,不同的表达手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捉妖记》采用现实与虚拟、真人与动画相结合的形式,让观众耳目一新的同时,也突出了幕后班底强大的制作能力。绚丽的歌舞表演融入电影的表达中产生了惊人的感官效果,歌舞强大的情感表现力能更好地营造氛围,触动人心,从而表现影片主题。如罗刚抓住小妖竹高和胖莹,夜晚在篝火旁休息的那一段歌舞表演,不仅歌唱内容贴近“和谐相处”的主题,引人思考,更营造了人妖之间相处的和谐氛围。在这个情节中,歌舞所制造出来的氛围是传统的电影表达方式无法渲染出来的,正是这种创新之处才将《捉妖记》的艺术效果推向顶端。
以情感线索为链条的叙事方式也是电影表现手段的创新之处。小妖胡巴的转变作为独立的一条叙事线索,主要依托情感要素推衍。胡巴是妖,妖天性嗜血,宋天荫心疼胡巴让他吸自己的血,但也没有放弃教育胡巴成为“良妖”。妖不吸血,才能为人妖和谐相处创造前提。而胡巴作为影片中的“萌点”,导演依然在其身上安排了情感线索,在关键时刻,胡巴想起了“不能吸血”的教导,竭力抑制自己吸血的天性,体现了妖身上向善的一面。妖可以感化,而情感的表达是相通的。当小妖回归大自然的那一刻,不舍的不仅仅是霍小岚与宋天荫,还有共同见证了其成长过程的观众,影片与观众产生了良好的情感共鸣,增强了影片的抒情性与感染力。
结语
人们通过对《捉妖记》中超越现实空间的想象来体验导演为我们营造的玄幻世界。妖界的展现既是对人的生存现状的表达,也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由此衍生出现代人如何看待人类的生存空间之外的其他世界等主题。而在影片中人与妖有敌对,也有和解,结局中人妖的和谐相处,引发了人类对其他物种的包容性,以及对人性的拷问等深层次话题的探讨。“理论派”观影者可以找到影片中深层次的价值内涵,而单纯“图个乐呵”的观影人士也能在《捉妖记》中收获众多笑点。从主题上看,《捉妖记》老少皆宜,各种年龄段的人群所推崇的价值观念都有一定的体现。从电影制作创新上来看,小妖王胡巴的细节设计、特效的使用都使得电影角色更加深入人心。总而言之,影片《捉妖记》在承袭传统艺术元素的同时又有所创新,是近年来玄幻电影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作者单位 洛阳师范学院艺术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