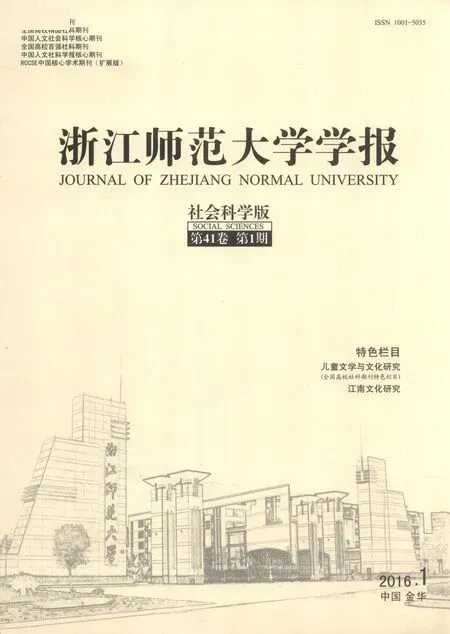“白马湖作家群”国文教学的历史影像和现实启迪*
潘涌,郭雅莲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白马湖作家群”国文教学的历史影像和现实启迪*
潘涌,郭雅莲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摘要:“五四”以后,以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叶圣陶等为代表的文人汇聚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从事教学和写作活动。他们以文会友、教学相长、切磋互补,创造出一种超越尘世、清新脱俗的纯粹的教育境界即“春晖境界”。“白马湖作家群”以卓越的文学才华、高洁的人格风范以及诚挚朴素、超然物外的教学风格在民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清晰的历史影像,并为今天全面深化基础教育改革时期探索语文教师专业化发展路径、深远培育新国民的母语文化软实力提供了有益的现实启迪。
关键词:“白马湖作家群”;春晖境界;现实启迪
“五四”以后,一批创作颇丰、活力洋溢的文坛高手,曾经汇聚到浙江上虞的白马湖畔,展开国文教学和白话文创作等一系列佳话盛传、影响深远的文教活动。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实绩已经获得高度定评,并以“白马湖作家群”这种充满诗意的美誉而定格在现代文学史的幽邃深处。但是,他们斑驳灿烂的教育实践,迄今尚未得到中国当代教育界的深度回眸和专业聚焦。
“白马湖作家群”以高尚的人格风范、卓越的语言艺术、清新而质朴的教学实践,创造了现代教育史上迄今令人憧憬不已的“春晖境界”;而且,他们以“作家”这种独特身份所从事的国文教学活动,留下了新鲜活泼、感人至深、意韵无穷的历史影像。这对于探讨并解决热议已久却无共识的语文教师专业化发展问题、深入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走向可期远景,皆具有深刻的启示价值。
一、“白马湖作家群”的文学特色与人格风范
(一)“白马湖作家群”的文学特色
20世纪20年代初,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叶圣陶、朱光潜等一批知名作家,还包括经亨颐、俞平伯、李叔同、匡互生等重要外围人物汇聚在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为白马湖注入了涟漪荡漾的清新活力。置身世外的他们,在白马湖畔一边教学、一边写作,互相切磋、真诚相待,创作了大量以素朴真淳、底蕴淡雅、口耳相传、历久弥新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在我国现代散文史上留下了熠熠生辉的一页。“卓立清风有主张,朗天化雨后时旸。湖滨春意不须色,惟为出墙竞短长”,[1]春晖中学校长经亨颐这首韵味绵远、音律铿锵的咏竹诗,就是对他们极其生动的概括,不仅活化出了他们卓越的人格、崇高的信仰,更突显了其师法自然、一派天然的艺术化语用品格。
“白马湖作家群”成员之间亲密交往、关系深厚,或同乡、或师生、或同窗、或同事。透过这层关系,我们可以深入挖掘到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血脉和艺术渊源。首先,除少数人外,他们基本上都是弥散着江南诗意气息的江浙人,文化地域上属于历史上的吴越一带,形成了归属“江南文化”的性情才子群落。其次,他们守护着“五四”以后新时代、新国民共同的人文主义理想,注重“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态度,强调以“爱”为核心的人性人情之熏陶,实践摒弃世俗、超越功利的纯粹人格之感化,标举起理想化的“新村教育”之信念。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他们以各具特色的文学创作而彪炳现代文学史史册,同时为刚刚独立设科、适值草创的现代国文国语教育,作出了筚路蓝缕、手胼足胝的拓荒之探,且为二十一世纪当代语文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提供了生动有益的启示。
朱自清的散文呈现出精工洗练、清新典雅的语言特色。如《春晖的一月》《绿》等散文名篇,渗透出馨香温润、颇耐回味的鲜活灵性,萦绕着一缕缕春天般的美妙诗意。在《欧游杂记》《伦敦杂记》这些文章中,朱自清着重将口语化的语言运用其中,力图从平实的口语中提取更加有效的富有表达力的语言。他朴实凝练的语言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彰显出生活中真实的语言之美。如《威尼斯》这篇游记中关于世界著名“水城”的特征描述,语言真实生动、自然亲切,被视为现代白话文创作的精美典范之一。
夏丏尊的散文风格平实质朴、真挚自然。春晖中学校刊《春晖》上发表的《读书与冥想》《文学的力量》等作品,足已表现出这种独特的文风。他“以闲适为格调”“以从容不迫的达观态度”来对待散文创作,使人读其文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另外,在语文教育上,夏丏尊先生提出学习国文的目的在于让学生学会用文字来表达,如果只是着眼于文本的表达内容而不关注文本的表现形式,其结果是徒劳甚至有害的。
而谈到丰子恺的作品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他如诗如画的浓郁艺术色彩。丰子恺是“白马湖作家群”中散文创作历史最长、作品数量最多的一位,其不俗成就和身后影响足堪与公认名家的朱自清媲美。从1922年到1974年,在几十年的创作中形成了他那种既悲悯又洒脱、虽只是一杯清茶米酒却极具人间情味的散文风格。[2]202
纵观“白马湖作家群”的文学作品,它们或是清丽精工,或是稳健妥帖,或是亲切温婉,风格各异。而在涉及教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明显具有似曾相识的共同之处。首先,在主题上,“白马湖作家群”的文章多取材于现实教育生活,如《文心》这本书就是夏丐尊和叶圣陶两位先生运用他们多年从事中学国文教师的经验专门为中学生而作的。其次,在题材上,“白马湖作家群”的文学创作在题材上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阐述作家自己的教育理念,如朱自清的《教育的信仰》等;一类是写给中学生阅读的文字,如朱自清的《欧游杂记》、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谈美》等;还有一类是对现代教育体制的批判性反思,如丰子恺的《伯豪之死》。简言之,“白马湖作家群”具有不事张扬、态度温和的高尚人格,时刻关注教学改良、呵护学生成长,坚守以“立人”为唯一目标的教育信念。
(二)“白马湖作家群”卓越的人格风范
“白马湖作家群”成员有着相近的文化气质和卓越的人格风范:淳朴、恬淡、超然。“先器识而后文艺”的儒家文化传统深深濡染着白马湖畔的这群作家,他们时刻奉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讲求作文之前先做人,追求“人”“文”和谐相称。他们崇尚君子的“讷于言而敏于行”,讨厌圆滑世故而追求质朴真实、率性自然,喜怒哀乐都出于本心、发乎性情,以至于质朴得有些“木讷”,率真得像个“大孩子”。朱自清说“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3]李健吾也用“没有架子,人老实,却又极其诚恳,他写得最坏的东西也永远不会违背他的良心,他永远表里如一”[4]来形容朱自清。匡互生是“不爱多说话,但常常微笑;那微笑是自然的,温暖的”。[5]至于丰子恺更“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俗的孩子”。[6]夏丏尊拥有一种“人间情怀”,他看见世间一切不真、不善、不美的事,都要叹息忧愁。朋友病了,他要皱眉替他担忧;学校里的学生放假出去玩耍,他也要再三叮嘱不要打骂和吃酒,被学生称为“妈妈的教育”。简言之,这批作家教师表面上不喜侃侃说教,内心深处却充满了教育的责任感,行动上更是表现出实践家特有的精神风貌。他们在日常教学生活中所渗透出来的对朋友和学生的牵挂意识和忧患感,正是其古道热肠、淳朴心灵的鲜明体现。
这批生活在白马湖畔的国文教师,仿佛世外桃源的谦谦君子。为人忠厚、为教真诚、为文率性,不染世俗的一点腌臜或庸俗,以一颗纯粹的童心而静静释放出教育的人文和诗性之光。这为“民国情结”浓重的当代学界,留下了一抹清晰可见的亮丽色彩。
二、“白马湖作家群”的教学特色
“五四”运动发生不久,“白马湖作家群”完全是在民国自由主义文化氛围中从事现代意义上的国文教育,其教学呈现出自主宽松、生动活泼、个性灿烂的特色。他们没有应试教育的拘泥心态,没有标准教材的同质化教学内容,没有刻板化禁锢的程式化教法,从而创造了“卓立清风有主张”的本色化和个性化的教育“春晖境界”。
(一)“白马湖作家群”的“范文”教学特色
在“白马湖作家群”中,夏丏尊、朱自清和叶圣陶等都担任过春晖中学的教师。其教学活动的基本内容,既包括常规意义上的授受语言文学知识,更有特色的则是将自身的语言艺术结晶即诗文亲切地转化为学生们欣赏的美妙对象,进一步引导他们怡养通过现代汉语来传情达意的优秀表达力。
这样,作家特有的“范文”意识如同一根红色主线贯穿在课堂内外的日常教学。在没有统一教材的情况下,他们自发并精心地为学生编辑教材、写下水文。更常见的是,这批兼任作家角色的教师,毫无对既有作品的崇拜情结,总是以作家的审美眼光融入对他人作品的严格审读之中,作出诸如语法、语词、标点等方面的适当修改。
1.传播新作文观
新文学的“新”不仅包括“白话文”这种语言之新,还包括以“求真求实”为核心的观念之新。1920年初,“新的国语”还在创作变化中,无论是新文学写作还是现代语文知识的概括都处在探索阶段。这时,“白马湖作家群”自觉从自身独特角色出发,不仅在国文教学中讲究现代文体意识、标点符号以及表达个性,通过对新作文观的传播将新文学观的基本精神弘扬到了课堂。丰子恺在悼念夏丏尊的《悼丏师》中回忆:我们做惯了“太王留别父老书”“黄花主人致无肠公子书”之类的文题后,他突然叫我们做一篇“自述”,而且说:“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在丰子恺的文章中,夏先生就是用课堂来实施胡适关于新文学的“八不”主张,将其进行生动的阐述:作文“不准讲空话”,而是要“言之有物”;写父亲客死他乡不说“匍匐奔丧”,而要“去烂调套语”;赞君子隐遁,不说“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而要“不作无病之呻吟”“不讲对仗”“不摹仿古人”;在学生关于用典知识的讨论中,也明确呈现“不用典”等要求。[2]122要求弘扬上述新作文观并落实到学生的日常习作中去,无疑是以“立言来立人”这种现代教育意识的伟大觉醒,是现代语文教育历史性进步的深刻象征。
2.为教学而写作
在“白马湖作家群”中,教师的身份常常使他们的写作活动拥有一个假想的读者群,即“中学生朋友”,由此,他们的写作有相当一部分具有明显的“范文”意识,因而特别注意文章的遣词造句。这使其文章呈现出了精工绵密的特色,堪为中学生朋友的“范文”;另外,由于教学的需要,或为了补充教学的不足,他们还专门为中学生朋友编写了许多课外读物。[2]130
夏丏尊与叶圣陶为学生合著了广有影响的语文知识读本《文心》。书中的故事取材自日常现实生活,又反过来施教于国文的课堂学习,贴近学生的经验世界,感情淳朴深挚,道理平易晓畅,颇能为阅历有限、修养尚浅的中学生所接受和喜爱。除此以外,这两位著名现代语文教育家合撰了诸如《国文百八课》《文章讲话》《阅读与写作》等至今依然为语文教育界所欣赏的教学书。朱自清常常直接为学生写作供教学所需要的作品,如以《欧游杂记》《威尼斯》等为学生作游记的写作范例。至于丰子恺、朱光潜,同样也为学生编著通俗教育读物,深得学生喜爱,如《艺术概论》《艺术教育ABC》《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白马湖作家群”在这一时期为学生所创作的读本,数量众多、质量优胜,其积极影响更是有口皆碑。他们将自身精湛的语言艺术变为学子欣赏的对象,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具体、生动和亲切的语用示范,在教学中充满了真实感、体验感与和谐感,进而很自然地促进了学生语言表达力的自觉养成。
(二)“白马湖作家群”的“立人”教学理念
“白马湖作家群”一边进行文学创作,一边从事着春晖中学的教育教学工作,他们以切实的努力创造着名扬四方、以“立人”为理念的“春晖境界”。20世纪20年代初,整个民国新教育体系还处在初级阶段,虽然说新的教育思想已经产生并迅速传播开来,但脱胎于封建主义的现代新教育毕竟遗留着一些显见的消极弊症,特别是“非人本化”的规训和教条仍然盛行。但是,“白马湖作家群”的教师们始终怀抱着一个共同的理想,即坚持“立人”理念指导下的感化教育,提倡“德智体美群劳”六育并重的教育价值观,追求“挚诚、挚爱、人格感化”的“爱的教育”,采用“多彩活泼的教学手段”[7]等,从而在现代教育史上创造了着墨不浓、意蕴饱满、感人至深的“春晖境界”。
夏丏尊在对教师观的论述中提出“教师要用人格感化学生”。首先,教师要有真才实学,真情投入。其次,教师应该有教无类,同情幼者和弱者。在《学斋随想录》中,夏丏尊写到:“优等生受教师之奖励,勤勉益力。劣等生受教师之呵责,志气愈消。天下不平之事孰甚于斯?”[8]278体现出夏丏尊先生同情弱者的一面。最后,夏先生认为“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在《教育的背景》中写到“人格恰如一种魔力,从人格发出来的行动,自然使人受着强大的感化,同时一句话,因说话者的人格不同,效力亦往往不同,这就是有人格的背景与否的分别”。[8]278-279从中可以看出夏丏尊先生提倡以诚相待、身教胜于言传的新观念。夏先生的观点在白马湖教师群中颇有代表性。他们都有强大的人格感召力,均以一种平等和谐的沟通方式来熏陶学生的身心,春风细雨般地润泽其蓬勃旺盛的生命成长。朱自清在《教育的信仰》中指出“教育者要有信仰”。第一,教师自己要有“培养”的自觉意识,有一颗高尚、诚挚、忠实而无限温情的教育之心。所谓“培养”方法则是位居自觉意识之下的。第二,教师要将“为人”与“治学”有机融合起来。唯有严于律己的教师,才能“以己立身”来实现“示人立身”,最后抵达“不言之教,无声之诲”的新境界。[9]177-184
那所名闻遐迩的春晖中学,就这样通过这批信念卓越的名师之教学而彰显出一种令后人憧憬的“春晖境界”。“白马湖作家群”的教师们,形成了儒雅亲和、自在洒脱的教学风格,创造了一段朴素超然、纯真淡泊的教育佳话,矗立了祛除功利、净化污染、标举信仰的现代新教育范例。他们或是在清风朗月下对酒交谈,或是闲庭信步于白马湖畔而深沉思考,或是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向学生传达一种人道主义的心灵关怀,无不是在朴素自然、不事张扬地创造着独具神韵的“春晖境界”——亲和的人文关怀、高洁的人格风范及特色化的教育之道。
Interdecadal change in relations of convective activities in tropical Northwest Pacific and Southeast India Ocean
三、“白马湖作家群”的现实启迪
在第八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语文教师如何走专业化发展道路,成为各界共同关注的突出问题。“白马湖作家群”所创造的春晖境界深刻启示我们,优秀的语文教师同时应该成为高超的语用艺术家,走作家化发展道路是优秀语文教师应该秉持的逻辑的价值选择。语文教师不仅仅是卓越文本的接受者和欣赏者,更应是学生最亲近的语用艺术的创造者和示范者——躺着,是一本合拢的教科书;站着,是一本打开的教科书。
(一)语文教师应该成为语用艺术的活的教科书
“白马湖作家群”在从事教学活动的同时,能够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和学习情况,自己编写适合学生的教材和读本,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教学。其诗化的语言表达、亲切和谐的以身示范,收到了直接的积极效应。当代语文教师应全面提升语用能力,同时要优化作为外在语言表达力的内部支撑——思想力。这是春晖境界的核心价值之一:以己立言,促人立言。
第一,语文教师要提高自身语言的艺术表达力。语文阅读课的基本内容就是对语言艺术精品的鉴赏和审美,如果语文教师自身缺乏“独立创作”的语用艺术,不但难以引领学生走入对课本语用艺术精品所呈现的审美世界,更难以让学生积淀语用艺术精华并且转化为自己积极的、输出性的强劲表达力——而就语文教育的最高目标而言,无疑应是养成学生基于阅读、理解和鉴赏之上的优质表达力。因此,语文教师必须像“白马湖作家群”那样,首先要具备“创造”语言美的能力,然后才可能引导学生学会“品味”语言美,即让学生鉴赏语用品质、领略意境韵味、感悟文外之旨,并从长年累月的积淀中完成从“输入”到“输出”这样的重要转换,最后使学生走向独立表达、创新语用的艺术大化境界。教师自身拥有不同凡响、高人一筹的艺术表达力,本质上就是获得了一种可持续增值前景的重要教学资本。
第二,语文教师要深度优化内在的思想力。语言,作为人内在思想和情感的对外显现,从来就是其自身存在价值的鲜明象征。富有品质的优秀表达,必然是深刻精彩之思想的有力表征。“白马湖作家群”将自身真挚深邃、洞察世事的心灵之光,或隐或显地折射在自己的文字丛中、谈吐之间;他们用幽邃精致、撼动人心的语言艺术,再现了自己丰富深厚、独一无二的精神世界,辐射出或清丽或深刻或高洁的思想魅力,直接感染着学生们的精神世界,启迪着年轻心灵吸纳智慧而自由成长。当代语文教师,由于长期束缚在指令性应试教育的禁锢中,难免缺失独立思想、自我判断的精神力量,诸如著名特级教师吴非(王栋生)“我美丽,我思想”这般的卓越人物,着实寡乎。而如果没有内在强大的思想力,自然缺失输出性的旺健表达力,更难以促进学生积极成长为善于思辨、长于表达的“语言人”。就此而言,当前语文教师自觉养成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和新观念,自觉优化自己的精神境界,是破解其职业发展的“瓶颈制约”、积蓄“教育软实力”的一项紧迫使命。
语文教师不仅是学生日常语用的示范,也是其人生与发展的现实榜样。语文教师的高尚人格理想,往往非常隐蔽地渗透在课堂内外、显现于举手投足之间,构成了一门日常必修而不自觉的“潜隐课程”。如果说语文教师课堂上的教学表达与和谐对话,确实是学生直观化的必须修炼的“显性课程”,那么,纯洁高迈的人格理想之熏陶,就是耳濡目染、时时动心的“潜隐课程”。
“白马湖作家群”诚挚地信奉:作文之前先做人,追求“人”“文”一致的人格理想。他们在教育教学中更要求学生将“求学”和“做人”并重发展,就像人的两足,“跛脚教育”难以行万里远途。身处白马湖畔的简陋校舍,心系学生一生的所作所为,他们不仅关注学生的智育,也关注学生的艺术才能,更注重学生品行的长远发展。丰子恺就曾画过漫画《教育手段》和《毕业生产出》,以此来批判封建教育对学生个性的磨灭和身心的残害。他批评传统旧教育如同园丁的所谓劳作,使学生在标准化的切割下丧失参差错落的生态和个性特色;批评教育的工具理性致使课程流水线上的毕业生就如被一个模具批量制作的产品一般。白马湖畔的这批怀抱教育理想的国文教师,始终以青年的人格养成为目的,并且以“人师”的要求来修炼自身健全的人格、高尚的情操、坚定的信念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夏丏尊说“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教师人格示范的积极影响是最具有深切的感召力的。朱自清也强调:“教育者须对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对于他的上帝一样;教育者须有健全的人格,尤须有深广的爱;教育者须能牺牲自己,任劳任怨。”[9]184除此以外,“白马湖作家群”的教师们,还能做到不满足于人格观念的倡导,更注意在实践中熏陶学生,即是在“润物细无声”的感化中体现“人格理想”的潜隐课程特点。
当代语文教师应该从“白马湖作家群”身上得到深刻的启发和强烈的激励,将“做人”与“作文”深度融通、将“身教”与“言教”紧密结合。从本真意义上说,母语就是母乳,学生从课本中习得母语文化的精华而逐渐成长为身正、行笃、心诚、言美的现代新国民,而作为母语教师就是促进学生精神发育的“伟大母亲”。由是言之,“春晖境界”的核心价值之二就是:以己立身,促人立身。
(三)语文教师应该成为特色化教学的探索者和改革者
回顾民国时期,“白马湖作家群”的国文教师们都能在“立人”的教育理念下,积极进行各种大胆的教学探索。他们既是现代国文教育的先行者,也是实践创新的大胆探索者。
第一,打破统一公共教材的束缚。朱自清、叶圣陶等敢于突破课内教材的限定,甚至将新文学作品和自己的创作直接引入课堂,拓展了学生的阅读视野。当前语文课程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深广地拓展阅读范围,将“课内”与“课外”融会贯通。没有海阔天空般的大阅读,就没有心怀天下的大胸襟、大抱负,就没有视接霄壤的大眼界、大气度。由此而言,语文教师致力于教材突破和阅读视野的拓展,就是让学生的心灵获得自由洒脱的“放养”。
第二,为学生尝试“下水文”,以身示范。这是“白马湖作家群”的一大特色。在长期应试教育的禁锢下,语文教师被反对文艺性写作直至主动拒绝文艺性写作,已经成为教育界的一大咄咄怪事——他们仅仅拼凑泡沫化的所谓论文,而善于进行文艺性创作却被视为“不务正业”。其实,教师自身热爱写作,甚至同题写作,对于吸引学生、培育兴趣、激发才能,具有“课堂教学”所不可替代的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教育行政部门要从制度层面开通绿色通道:语文教师不但应该能写当下流行的教研论文,更应该擅长文艺作品的审美创作——这应当成为全面深化教育改革背景下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一大发展新趋势。
第三,鼓励学生参加社团活动。“白马湖作家群”的教师们弘扬“五四”运动的精神,开放校园、组织社团,在封闭的社会体系中形成了活泼的校园文化氛围,对青年学生产生了“催化成长”的积极作用。今天,新课程深入推进,营造多元开放的社团文化已经上升为教育界的共识。尤其是办好文学社、演讲社、故事会、经典诵读,更是理所当然地纳入了语文教师的“教学范畴”——这就是正在蓬勃兴盛的“活动课程”。“春晖境界”启发今天的语文教师们:突破传统的课堂,努力成为这些“活动课程”的设计者、组织者和主持人,这正是深化课程改革背景下语文教师的一种新使命。
总之,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叶圣陶等一批在“五四”精神激励下成长起来的新文学作家,在温情梦乡、世外桃源的白马湖畔创造了一段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教育童话,穿越斑驳黯黄的时光隧道,至今依然飘散出历史的浓郁馨香。其中积淀着很多足勘细细咀嚼的现代国文教育的珍贵经验,经过梳理完全可以成为改革时代语文教师们持续增值的一笔精神财富。这段在美丽江南、白马湖畔所诞生的教育童话,正可以概括为令今人恒久审读、细细回味的一副美妙对联:江南诗意荟萃白马湖畔,纯粹师魂创造春晖境界。
参考文献:
[1]经亨颐.经亨颐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379.
[2]陈星,朱晓江.从湖畔到海上: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及流变[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
[3]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155.
[4]李健吾.怀王统照/ /我与开明[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 121.
[5]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4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316.
[6]丰子恺.丰子恺散文全集:下[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108.
[7]陈星.白马湖作家群的教育、教学理念[J].杭州:浙江社会科学,1997( 1) : 96-100.
[8]程稀.夏丏尊与现代语文教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9]朱自清.朱自清语文教学经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张丽珍)
The Historical Image of Chinese Teaching of the“Baima Lake Writer Group”and Its Implications
PAN Yong,GUO Yalian
(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China)
Abstract:Since the May 4thMovement,some scholars like Zhu Ziqing,Xia Mianzun,Feng Zikai and Ye Shengtao,worked in Chunhui secondary school by the lakeside of Baima Lake in Shangyu city,Zhejiang province.They taught and wrote there,and befriended each other,sharing similar interests in literature; they learned from each other in teaching and they were free from things of the world,showing a pure teaching ideal,which was since referred to as“Chunhui Ideal”.The writer group left a clear image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over the Republic of China,with their excellent literary talent,noble personality and sincere and simple teaching styles.They also provided a way for Chines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may have further implications for the strenthening of native culture as soft power.
Key words:Baima Lake Writer Group; Chunhui Ideal; implications
基金项目: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项目“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强国战略研究”( 2013GH026)
作者简介:潘涌( 1959-),男,浙江嘉兴人,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
*收稿日期:2015-10-22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 2016) 01-01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