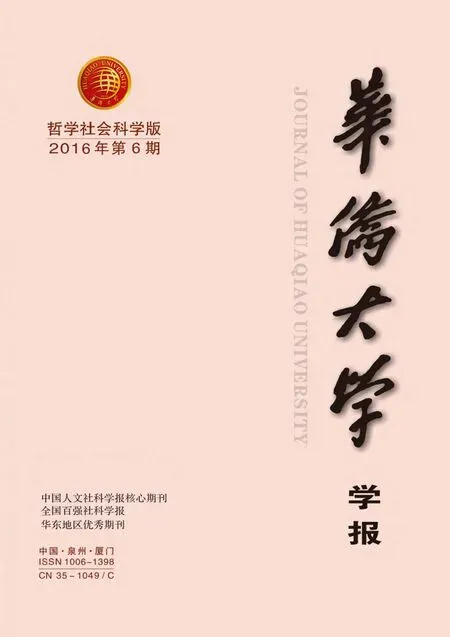华族离散与身份认同
——马新及印华女性小说的例析
○马峰 朱崇科
华人流动性极强,其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族裔散居(diaspora)指某个种族出于外界力量或自我选择而分散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情况(用通俗的话讲即是移民现象)*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前言。。中国人初离故土成为第一代移民,其身份具有双重性。海外华人从居住国再迁移,于是便有了三重身份。多次跨界就形成多重身份,而移民永远具有流动性、多元性与不确定性。移民是一种旅行文化,在居住中旅行,在旅行中居住,它本身包含着“连续与断裂、本质与变迁、同质与差异之间的历史性对话”。*Clifford James,“Travelling Cultures”,in Cultural studies,edited by L.Grossberg, C. Nelson and P.A. Treichler,New York:Routledge,1992,p.108.廖建裕以“根”来概括中华移民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及族群认同,将其分为归根、生根、失根与无根,在全球化年代,“浮萍无根”则变成了今天的华族新移民共有的概念。*廖建裕:《现当代的中华移民及其后裔:归根、生根、失根与无根》,吉隆坡: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八届国际会议主题演讲,2013年8月17日下午2:00-3:00。霍尔(Stuart Hall)也认为,文化身份认同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总是混杂的(hybrid)。*Stuart Hall,“The formation of a Diasporic Intellectual: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by Kuan-Hsing Chen”,in 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5,p.504.根性及混杂性都具有多元性,其实是相同概念的变体,都可言喻归属感的不断变化。
在日常言语里,认同(identification)的概念牵涉到描述(describing)、命名(naming)及分类(classifying)的过程。*Chris Barker,The SAG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Studies,London,Thousand Oaks & 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04,p.92.从类别来说,认同可以包括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文化认同等多方面。海外华人的认同以地域性来看,可分为“在地认同”与“故国认同”。早期的华人大多属于故国认同,包括认同中国国籍、中华文化等。当前的华人多是在地认同,以政治上认同当地政府为主,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仍倾向于“文化故国”。文化故国,可称之为“想象的故国”,是一种精神的家园,喻指对本身民族文化的依恋而形成的归属感,主要指精神层面,而不是政治层面的故国。对海外华人而言,文化故国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是政治层面的中国认同。对海外移民群体而言,认同与离异都是主体的人对客体文化的反应,即对主流文化的应对策略。认同应该是自由平等的主观抉择,如果主流文化过分强势,以强制同化的方式去达到文化认同,那么必然产生离异。即使弱势文化迫于形势而屈从,也只能得到貌合神离的效果,结局导致两败俱伤,也就不利于文化的发展。
一 离散与认同
华人移民的离散经验影响其身份认同,根据移民的先后可以分为三个批次,每个批次都具有不同的阶段特征。第一批华人,也就是第一代移民,有着浓重的侨民意识及落叶归根情怀, 只把移居地当作暂时的停留,大都具有衣锦还乡与光宗耀祖的念头。作为离乡背井的海外开拓者,他们既有对家乡亲人的眷恋,也有在当地安居奋斗的创业心。他们是远离故国乡土的离散群体,其认同倾向于中国,但对当地已渐渐产生留恋与感情。爱薇的《回首乡关》便体现了第一代移民对故国的回望情绪,这也是整代人的集体乡愁。
想到中国家乡走走的念头不是没有,这是从前到南洋来的先辈们,心中隐伏着的共同愿望,杜竹标当然也不能例外。尤其是那些在那里还有亲人的,这份感情更是浓烈,纵然是远隔千山万水,也割舍不了。*爱薇:《爱薇文集·中篇小说》,蕉赖:方正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海外华人进入另一个文化空间,经历着文化断裂的焦虑与苦恼,特别是一旦与异邦异族的文化碰撞时,便擦出光亮,“乡愁”因之而转化为文化归属的大命题。*杨匡汉:《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61页。第二批华人,在海外土生土长的华裔群体,他们已落地生根。虽有一些“文化中国”的想象,但认同已定位于所在国,其“故乡”已指向本土所在地。“对于那些生在东南亚、长在东南亚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人而言,所在国理所当然的就是他们的祖国,是他们所依恋、所思念的故土与故乡。浓稠的本土情结,构成东南亚华人新的集体性记忆。”*王列耀等:《趋异与共生:东南亚华文文学新镜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2页。由于长期的本土滋养及隔代距离,他们对祖籍地已略感陌生。黄叶时的《锦绣山庄》表现东马小镇的华人家庭,虽然长辈们依旧保留华人传统习俗,但是年轻辈并不了解与中国的关系。“唐山,这名字,是留着泥土味,在上一代的记忆中是缅怀的,对水香来说又是陌生和渺茫。”*黄叶时:《露从今夜白》,古晋:砂朥越华文作家协会,1992年,第71页。第三批华人,多指第三代及其后裔,他们是新世代华人。面临世界全球化趋势,其认同观念趋于不稳定状态。这种不稳定性可指“地球村式”认同,此观念在所在国的政治变革及种族分歧时便会不可阻挡,也就是再移民潮流。这批新世代的华人再移民趋于精英化,留学生占有一定比重,他们往往学成定居当地。此外,还有技术移民及投资移民,多属高学历的专业人士及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群体。
在东南亚地区,华族的离散与认同又有其特殊性。随着时代历史的演进,东南亚各国逐渐走向独立建国。同时,中国的新国籍法颁布,不再承认双重国籍。再者,冷战时代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东南亚各国与新中国的政治外交关系相对紧张而微妙。黄枝连讲到,某些东南亚国家在冷战时代所推行的反共、反华、排华政策,迫使华族人士在“同化”和“归化”中选择出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迫害,加上文化教育权利的剥夺,在于造成那么一种困境,迫使弱势民族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处于一种破产状态,产生虚无主义和投降主义。*黄枝连:《东南亚华族社会发展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1992年,第313页。就马新及印尼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独立建国,这可以视为华族认同的重要分水岭。独立前,在当地的第一批华人涵括性最广,可以包括从早期移民史至建国之前的数代人。第二批华人,指土生土长的一代,主要包括横跨独立前后的华裔。第三批华人,指独立后出生的华裔,他们经历着国家制度的新变革,华人权益受到当地政策调整的冲击及制衡。马来西亚、新加坡与印尼,由于国家实施不同的民族政策及华文教育政策,因此华族的离散与认同也有很大差异。目前,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大多归化入籍当地,长期的生活让华人选择扎根当地,这是“落叶归根”的故土情怀到“落地生根”的在地意识转变,慢慢形成对所在国的政治认同,这是一种自然发展的大势所趋。*沈玲:《中国经验:海外华文诗歌文化表征》,《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19—125页。
具体到东南亚的女性境遇及女性写作,她们所呈现的离散与认同又带有些许性别色彩。在不同的地区、时代、语境下,女性主义或女性写作的形态不一。东西方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能拘泥于被想象和被表述的话语,当然对西方理论不可一律照搬。东方人生活的世界虽与西方不同,然而却有着完备的组织结构,有其民族的、文化的和认识论的独特特征和内在一致的原则。*[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49—50页。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体现其东方色彩,并不是激进奔放的狂飙突进,而是跋涉迂回的含蓄省思。中国妇女从未有过自己独立的行动纲领和生存宗旨,因此现代女性写作不可能像西方女权或女性主义文学那样,以全面更新的思维和自我界定,进行文化话语的渗透,并赋予其鲜明的性别政治意义。*李少群:《追寻与创建:现代女性文学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引言。东南亚华文文学源于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其女性文学也不可避免的受到此潮流影响。虽然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同属东方文化圈,其文化也有较多相似性,但是椰风蕉雨的风土民情又赋予其独特的南洋色彩。由此而言,东南亚华文女性文学同中国文学、西方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本土性的张扬又让其迥异于二者。迈克·克朗(Mike Crang)从人文地理学角度阐述“有关地区的写作”,他提到文学作品的描述涵盖了对地区生活经历的分析,“这些充满想像的描述使地理学者认识到了一个地方独特的风情,一个地区特有的‘精神’。这样的地理描述不注重位置是否准确,也不是细节的罗列。”*[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页。所谓“地区精神”,一是对当地华人日常生活的描写,以朴实无华的笔法细致再现生活的逼真原貌;二是以本土为故事发展的背景,展现当地社会生态的独特性。女作家从多方位去观照本土,以真情实感抒发对本土的国民、政治、历史的多重沉思与关怀。或从人性及文化角度观照华人女性及社群,传达出超越性别与族群的生命豁达情怀。这种本土情怀,掺杂着自省与批评,表现为在地的沉思,更深层意旨则是对华人生存窘境的反思。东南亚的华人女性,不同于西方女性,不同于东方其他地区的女性,也不同于当地其他族群的女性。她们的思想变化更为微妙,其本源来自祖籍地中国的传统伦理,同时又受到世界潮流与当地习俗的影响。就族群境遇而言,除新加坡之外,华族都属于弱势族群。就性别而言,相对于男性的强势,她们又处于性别劣势。因此,东南亚华人女性大都身处双重弱势地位,具有多重边缘性。她们表现离散与认同的主题,但书写策略更具柔性细腻的特点。
二 马来西亚:压制与抗拒下的认同
在国家公共领域,马华文学被定位为马来西亚的族群文学,它并未被纳入国家文学范畴。伊斯迈·胡辛(Ismail Hussein)在1971年9月号的《文学》曾撰文专论“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其概念重点是:只有以马来西亚马来文写作的作品可以接受成为国家文学。其他土著语系文学(譬如伊班、马拉瑙、比沙雅、慕禄、柯拉必、加央、肯雅、普南等等)可视为地方文学(sastera daerah)。而以中文、淡米尔文以及其他族群语文书写的作品可视为马来西亚文学(kesusasteraan Malaysia/Malaysian literature),但是基于这些作品的读者只限于某些群体,则我们不把它视为国家文学。无论如何,地方文学和族群文学(sastera sukuan)对国家文学的贡献明显地是非常重大的。*庄华兴编著译:《国家文学:宰制与回应》,吉隆坡:雪隆兴安会馆、大将出版社联合出版,2006年,第35页。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有关国家文学的讨论仍在继续,不过以马来文学作为唯一的国家文学的定位依旧是不可撼动的。当然,华人并不赞同马来学者的论调,他们积极争取马华文学所应有的国家地位。林慕直言,否定“马华文学”是“国家文学”的组成部分,则意味着否定马来西亚是多元种族、多种文化的国家,无形中也自我贬低了多姿多彩的“国家文学”崇高的国际地位。*林慕:《迷失与醒觉》,吉隆坡:东方企业有限公司,1997年,第270页。未来,马华文学是否被接受为国家文学,这与国家的政治及族群策略有莫大关系。国家文学自五十年代开始讨论至今,在马来学界和国家机器的建构下,已经成了“国家文学=马来文学”方程式,导致非马来人文学无法进入国家文学。*张玉珊:《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论述及其问题研究》,元智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11页。不过,以马华作协为代表的马华文学团体并未放弃向当局表达其合理诉求。马华文学理应是国家文学的一环,作协应当是国家文学资产的重要支柱之一,希望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所做的努力,能得到国阵政府的认同。*马华作协即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78年7月29日在语文出版局礼堂举行了成立大会,当时称为“马来西亚华文写作人协会”,首届主席为原上草。参见《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简报(2010-至今)》,《马华文学》(网络版月刊)2011年7月创刊号,第40—46页。不管马华文学在将来是否能成为国家文学的一部分,它在世界华语文学体系中已具有较大的潜力与影响力。
马华文学以西马为中心,东马作家的创作与研究都相对边缘。沈庆旺是“书写婆罗洲”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他提到“在政、经、文化等方面,东马砂沙两州被‘边缘化’是我们长期以来深觉不平的感受。在文学方面,由于文艺作者的互动与交流,近年来的情况有所改善。”*沈庆旺:《雨林文学的回想:1970-2003年砂华文学初探》,《新世纪学刊》2005年第5期,第74页。东马由砂拉越(Sarawak)和沙巴(Sabah)两州构成,其中砂拉越华文作家的创作比较活跃,他们将婆罗洲情怀融入文学作品,出现了一批颇具特色的书写本土的作家。当前,砂华文学史研究专著有黄妃的《反殖时期的砂华文学》和田农的《砂华文学史初稿》,其探讨主要集中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此后的研究还有待开拓。砂华文学有其独特性,特殊的历史因由、地理环境都影响着当地华文文学的发展演变。“砂华文学,乃是砂罗越华文文学的简称。一般而言,砂华文学是属于马华文学的一部分。但在1963年砂罗越加入大马以前,不但砂华文学的定义和现在有所不同,即使当砂罗越成为大马一个州属,砂罗越的华文文学仍有其独特的一面。”*田农:《砂华文学史初稿》,诗巫:砂罗越华族文化协会,1995年,第1页。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此前的砂拉越独立于马来亚之外,其华文文学也具有相应的独立性。陈大为在《婆罗洲“场所精神”之建构(1974-2004)》中指出,早期砂华文学的作家如郑子瑜、洪钟、赵子谦、魏萌、吴岸等,这个创作谱系确实是独立的,完全不受西马文坛生态或权力架构的影响。*潘碧华主编:《马华文学的现代阐释》,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2009年,第106页。以砂拉越为代表的东马华文文学,其独特性源于文化的相对独立,即在关怀、审视当地而产生的本土性。同西马相比,其政治生态、族群关系有较自由的宽松环境,又秉承浩瀚雨林的原始与淳朴,因此,其本土关怀的纯度更为明显。东马女作家中,煜煜、融融、英仪、鞠药如等的小说都带有强烈的本土气息。
在马来西亚,华族是第二大族群,然而却未能在国家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中占有相应比重的发言权。自建国以来,马来人是执政者,是国家的主导,国家政策也偏向于马来族群。执政党长期由巫统(UMNO,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占据,而巫统属于马来人(Orang Melayu)和土著(Bumiputera),自1946年5月11日成立后其历届主席都极力维护马来人的权益。马哈迪(Tun Dr. Mahatir Muhammad)曾说,巫统是马来人的权力,现在也是其他土著的权力。*Tun Dr.Mahatir Muhammad,Amanat Presiden:Demi Agama,Bangsa dan Negara (1981-2003),disusun dan diselenggara oleh Abdul Rahman Abdul Aziz dan Mustapa Kassim,Kuala Lumpur:Berita Publishing Sdn Bhd,2009,p.320.尤其是新经济政策(Dasar Ekonomi Baru)实施后,马来人在教育、技能、管理、商业、工业等多领域都受益,其生活水准和收入得到提升,马来人的中产阶级已经成功扩大。2005年7月19日,巫统大会以“民族大跃进(Lonjakan Perkasa Bangsa)”为议题召开,有一项“马来人议程”讲到“新经济政策给马来人新气息”。主席训词所提供的数据更能证明马来人所分享到的巨大经济利益,而土著群体也一并受益:“在新经济政策初期,从非马来人的收入来看,马来人只占有每一令吉的44分。1990年新经济政策后期,马来人已经成功拉近了差距,收入为每一令吉占57分,增加幅度为30%。土著的股权从开始的2%提升到2000年的19%。”*Tun Abdullah Ahmad Badawi,Amanat Presiden:Demi Agama,Bangsa dan Negara (2004-2009),disusun dan diselenggara oleh Abdul Rahman Abdul Aziz dan Mustapa Kassim,Kuala Lumpur:Berita Publishing Sdn Bhd,2009,p.43.许文荣在谈到官方意识形态霸权时认为,马来执政精英把马来文以及马来文化视为建构一个马来化“民族-国家”的两个法宝。*许文荣:《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巴生:漫延书房,2009年,第43页。马来人是土著族群,华族被视为外来者。赛·胡先·阿里(Syed Husin Ali)也指出,马来人在日常政治演说中,时常称非马来人为外来民族(bangsa asing)或外来人(orang asing)。*Syed Husin Ali, The Malays:Their Problems and Future,Kuala Lumpur:The Other Press,2008,p.8.马来中心意识不断树立,华族受到排挤,华文教育面临挑战,这些都挑动着华族国民的敏感神经。由此,移民问题就成为当代马来西亚华族的严峻课题。曾沛关注华人族群,并结合马来西亚现状探讨社会问题。她的《阿公七十岁》以阿公之口吐露对华族移民的忧心,三代人的不同经历也影响其家国认同观念。他是第二代华人,对从中国南移到马来亚的拓荒先贤充满敬意。身为马来西亚的国民,他有淳朴而真诚的本土情怀。
我们是道道地地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的国民。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拓荒及努力耕耘,以橡胶的乳汁换取生活费;采锡米、种油棕维持生计。所以,我们对这块国土有很浓厚不能移的乡情。我们爱这块土地,我们从未想过要离开这里;我们对国家的效忠是不容受到质疑的!*曾沛:《行车岁月》,吉隆坡:创历出版社,1988年,第245页。
阿公的话语更像是爱国宣言,他是历史的见证者,曾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也为华族权益而奋斗。然而,当国家的种族敏感课题不断被挑起,大学学额实行配额制,华裔子弟受到排挤,于是不少华人渐渐心生不满与怨恨。关于马来人享有的教育特权,马哈迪讲到,奖学金不是种族不平等的证明,它们是打破“非马来人”在教育领域优势地位的方式。*Mahathir bin Mohamad,The Malay Dilemma,Singapore:Donald Moore for Asia Pacific Press,1970,p.76.这种教育权益的分配不均,对马来学生的特权照顾,对华族学生是极大地打击。在尴尬处境下,主人公的儿孙纷纷移民英国。对此,他痛心于华族青年的消极逃避,也为国家的人才流失而惋惜。他有爱国家、爱民族的责任心,渴望对华裔地位及母语教育的不懈争取。然而,他无力挽回儿孙的去意,温馨的回忆更显落寞与苦涩。当然,华族青年并不是一味的崇洋媚外,《抉择》与《眷眷爱心》表露新老两代华人对本土的信心,他们不离不弃的坚守本职;思妮是一位尽职的导游,男友移民他国迟迟不归,但她依旧笑对游客,动情地讲述本地景致,传达着对家园的热爱;父亲在锡矿土崩中意外身亡,他为家园付出而无怨无悔,雯妮继承了父母的的依依乡情,她不打算随哥哥移居美国,而是渴望成为本地画家或教师。温玉华的《迷惘的年代》则直接表现留学生的国家意识,虽然他回国后并不如意,最后还带着国憾家愁飞返美国,但归国窘状并未打消他对母国马来西亚的眷恋。面对以国家机器为后盾的马来特权,华族无力打破不公平的现状,“离去”不代表全然的消极逃避,“留下”则需要顽强的斗志与非凡的忍耐力。针对马哈迪的言论,叶林生以“华人的困境”作为回应,“我一直认为,如果有一个种族可以理解‘马来人的困境’,它将会是我们华人。”*Ye Lin-Sheng,The Chinese Dilemma,Kingsford,New South Wales:East West Publishing Pty Ltd,2003,p.197.华人的去留都充满无奈,这也暗含对马来执政者政策偏失的不满。
1963年,东马的沙巴、砂拉越正式归入马来西亚联邦。在布洛克家族统治时期,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并不隶属于英殖民政府。因此,同西马相比,东马的华族虽同样处于弱势地位,但其认同却有较大差异。弱势团体也提倡多元文化下的自我认同,借此强调族裔认同的差异,以及不同文化位置和地方所形成的独特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廖炳惠:《关键词200》,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第137—138页。华族在砂拉越是第二大族群,华人对砂拉越的开拓、发展有重大贡献。二战时期的砂拉越华人,大多具有较浓厚的“效忠中国”意识。英殖民政府接手砂州后,当地华人渐渐在反殖斗争中培养起“效忠砂拉越”的思想。随后的万隆会议对华人国籍的界定及马来西亚联邦的提出,让砂拉越本土情怀愈加强烈。在布洛克家族、日治、英殖民时期,华人积极参与反帝反殖的斗争,为争取砂拉越的独立自由而不懈斗争。其实,美里华人同古晋、诗巫等地的华人一样,都涌现出一批敢于斗争的积极分子,他们在砂拉越的政治发展史上留下重要印迹。砂拉越州美里的文史研究者蔡宗祥讲到,美里省人民的政治斗争史,是政治思想的嬗递。时局迭更,华人从侨居,在商言商,从效忠中国转变效忠砂拉越,联同各民族抗御不合理统治,继之为反殖反大马的斗争。*蔡宗祥:《美里省左翼运动史事》,美里:美里笔会,2011年,第45页。煜煜的《血债冤情》以1995年8月15日为时间切入点,以高辛强的见闻为主线,追述日本南侵时期在砂拉越的暴行。
五十年虽是一段悠久的日子,但那些毒打、灌水、奸杀、活埋、枪毙等残酷的景象,又岂是一根烟所能焚灭。瞪着袅绕上升扩散的烟雾,这些景象又晃如电影般映现眼前。迷迷蒙蒙间,他沿着时光隧道回返五十年前的旧居华人村。*煜煜:《轻舟已过》,美里:美里笔会,1998年,第61页。
曾经的岁月慢慢铺展开来,并穿插叙述“砂州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巴都林当集中营、美里大山背村民、诗巫拉让江游击队”等一系列事件,展现砂州华人的悲惨遭遇及抗争精神。作品除了对砂州的纪实性描写,还表现了主人公的侨民意识。他对故国有浓浓的情谊,称中国为“祖国”。他强烈谴责日本的南京大屠杀暴行,还大力筹备侨胞回国抗日。《轻舟已过》展现五、六十年代一批青年人在砂拉越的反殖反大马斗争,他们曾有崇高的理想、澎湃的激情。故事将爱情与战争交织,表现青年人爱情与理想的冲突,以及对斗争的坚守、迷茫、反思、醒悟。中学时期,他们就受到砂共组织影响,开始参加砂拉越先进青年协会,积极宣传反英殖的思想。1963年后,他们转入“反大马”的游击战争。在斗争中,有的被捕入狱,随后投诚;有的偷渡出国,去香港攻读大学。30多年后,他们从香港、美国、新加坡、吉隆坡、美里等地重返古晋,砂拉越河畔的欢聚勾起辛酸的回忆。当前,包括华族在内的砂拉越各族群依然保有砂州本土意识,不过“反大马”已成历史,在国籍上已普遍认同马来西亚。
三 新加坡:跨界流动下的认同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此前,新加坡的华文文学被统归于马华文学。此后,新华文学开始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关于新华文学的定义,黄孟文、周维介、王润华等都曾下过界定。胡月宝则如此概括,“新华文学指的是在新加坡、由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以白话文创作,并在感情、题材、认同感上与新加坡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华文作品。”*胡月宝:《新华女性小说研究》,新加坡:新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第4页。新华文学相较于马华与印华文学,其独特之处在于获得国家文学的认可。在新加坡,凡是由四种官方语言文字:英文、马来文、华文、淡米尔文写成的文学,都是新加坡文学。*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稿》,新加坡:BPL(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2页。王润华指出,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华文文学一直被纳入国家文学,它远比东南亚地区其他华文文学来得幸运,其地位与价值完全被接受和肯定。*王润华、白豪士主编:《东南亚华文文学》,新加坡:新加坡歌德学院、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1989年,第2页。虽然新华文学位居国家文学之列,然而却无法扭转因国家语文政策而导致的华文文学弱化。方桂香以写作人兼出版人的角度调查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整体经营,她发现本地华文从业者有悲观基调,语文政策的改变,已造成一代人华文水平低落的现实,新一代学生的华文水平每况愈下,是造成新华文学作者断层和读者下降的主因。*方桂香:《因为你就在我的视野里:新加坡华文语境中的本土关注》,新加坡:创意图工作室,2004年,第29页。这种悲观情绪多发自于老一辈华校生,尤其是南大毕业生对华文教育的殇悼。当前,华文教育又获得一定的重视,来自中国大陆及港澳台的新移民不断加入到创作队伍,新华文学也有回春的迹象。
新加坡是移民都市,政府推行吸纳人才的开放政策。李光耀讲到,“外国移民的到来将推动我们的经济,同时提高我们的国家地位。”*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新加坡: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联邦出版社,1993年,第507页。随着新加坡对外来人才/精英(尤其是中港台)持续不断的大力引入,新华文学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新移民文学”思潮。这里的“新移民文学”并非只是经由作家的新加坡身份来制定,而是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即由文学产生的场域——新加坡这个文学生产的特定时空来决定。毋庸讳言,凡是在新加坡文学场域内发生的新移民文学事件、现象、思潮等等都属于“新移民文学”,尽管执笔者可能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朱崇科:《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年,第267—268页。黄孟文则认为,外国人才在文学这一方面,没有什么可观的建树。移居新加坡的人大多数首先要寻求温饱,无法兼顾文学。*黄孟文:《黄孟文选集》,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2年,第379页。不过,当新移民生活渐趋稳定后,有些在精神追求方面便会转向文学。在众多外国移民中,来自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新移民文学创作不容忽视,他们以留学、劳务、投资等多种方式移居新加坡,在习惯当地生活后进而申请成为永久居民或加入国籍。关于中国留学生群体,新加坡创意图出版社曾策划出版“到新加坡求学的中国奖学金得主的故事”。对此,方桂香指出,“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毕业后还选择在新加坡扎根,和我们一起在新加坡这片国土上耕耘明天。”*方桂香主编:《人生历程从此不一样:到新加坡念书的中国奖学金得主的故事》,新加坡:创意图出版社,2006年,序二。同时,由留学生教育附带而来的“陪读妈妈”,也有不少人从事写作,这些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其中,有位中国母亲更是撰写了一本“陪子留学实录”。她说,“孩子留学不仅影响孩子的一生,同时也会影响到家长和整个家庭。……在新加坡,带着年龄尚小的孩子读书的中国妈妈不算少数,至少这个群体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石清桐:《陪读新加坡:一位中国母亲陪子留学实录》,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1年,前言。中国新移民群体以最为擅长的华文进行创作,他们是新移民华文文学的主体力量。从台湾移居新加坡的写作者较少,镐娇是其中一位。她的长篇小说《天若有情》讲述的是台湾老兵与中胜号军舰的故事,可以说是国共战争时期的一段真实史料。从中国大陆移居新加坡的女作家数量较多,王文献、巧巧、张惠雯、唐晓岚等都较为突出。其中,肖晓雨的长篇小说《歌场暗战》表现中国大陆女孩江晓枫到新加坡做歌手的生涯。新移民作家书写新移民的经历,其感受相比本土作家更为真切,也形成一种独特的写作风貌。假以时日,随着新移民写作者的不断涌现,新移民华文文学将成为新华文学的一大板块。
新加坡是华族为主导的国家,有别于马来西亚华族的少数民族地位。虽然如此,新加坡依然有大量华人移居他国,其中华校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究其根源则在于政府对华文教育及华文人才的漠视。新加坡是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度,其自身的人才外流也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林秋霞的《缺月》探讨新加坡的移民现象。林安安曾在哈佛大学念法律,后回新加坡任外交部公务人员。大哥安平是南洋大学的理学士,到美国念医科,随后定居洛杉矶并任职于加州医院。安平的心声道出华校生的伤楚,也倾诉着身份认同的悲慨。
我爱国家,可是国家爱我吗?在老家同在美国又有什么不同;我们是华人,可是我们不讲华语;年年推广讲华语运动,可是受高深华文教育的高官却宁可用不流利的英语来同选民沟通;唯一的华文民办大学被关闭了,……是一个华族凝聚力的国家却本末倒置,等到人们个个心灰意冷了才力挽狂澜,还来得及吗?*林秋霞:《宠物》,新加坡:锡山文艺中心,1992年,第21页。
在新加坡无用武之地,在美国又饱受二等公民的歧视,美籍华人的身份令人深感不平。纵然华校生曾面临困境,但他们对新加坡依旧有浓浓的眷恋。“缺月”潜含隐喻与象征,母子两地相隔是家庭的无法团圆,本土人才外流是国家政策的缺失。最终,跨海越洋的视频交流是对过去的正视,象征着理解与信任的回归,正如一抹亮丽的阳光,让人满怀期冀。除了高级人才,普通华人的国家意识也值得关注。尤琴的《游离份子》表现偏离时代轨迹的小人物,他是融不进社会主流的华校生,因不懂英文而屡遭打击。当曾经工作20多年的店铺被征用,他在失业的沮丧与愤慨中独自到乌敏岛求生。
你远离了新加坡岛,在离岛上第一次认真地投入地观看国庆庆典……这是我的土地,这是我的国家……你闭上了眼睛。在七个月前,你憎恨周遭的一切,现在你却平心静气地观赏与分享人们的欢愉。*尤琴:《游离份子》,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1992年,第28页。
虽然无法贴近社会,人生也有诸般的不如意,但主人公并未放弃对新加坡的热爱,这种困境中的效忠意识十分难能可贵。
李如玉生于马来西亚,后入籍并定居于新加坡。她的离散经历促成其双重身份,她所探讨的移民问题也牵涉马新两地。马新华人的西方移民之路,随遇而安与故土纠结并存,表现寻根与回归的困境。《无根的云》表现移民想归而不得,以“云”象征移民的漂泊不定。林伟平是有博士学位的高级工程师,在国外已成家立业,却无法抗拒身处异地的孤独与寂寞。
他实在有点厌倦当今在国外的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做什么都得看那些蓝眼白皮的脸色,而人家也老当他们是第×等级的,真受不了!因是之故,他很想回去看看,能在家乡找到一份合适自己的工作最好;要不然嘛,就干脆抛弃那“高级知识分子”的包袱,回乡下去替老父接管那一片“树胶山”,做个纯朴的乡下人亦是不错的。*李如玉:《无根的云》,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他有强烈的思乡病,并给孩子取名“念祖、念华”。妻子慕西,人如其名,她倾慕西方的“文明生活”,一心一意当外国人。他为寻找归属感而回马新找工作,希望将所学用于自己的乡土,不料却四处碰壁,只能再度流浪异国他乡,充满怀才不遇的落寞。《捐肾的人》表现移民的不归路,剑雄长期定居加拿大,回国反而感到不习惯。《抉择》则面临归与不归的矛盾考验,表现移民的文化心态,夫妻间的隔阂也是文化追求的冲突。陈亚南出自西马的乡下家庭,曾留学台湾并移居美国,他渴望重返故地。妻子则心系美国,有极强的崇洋心态,她讨厌新加坡的拥挤与嘈杂,不喜欢西马乡下的落后与土气。当美国公司分派他到新加坡工作,终于得偿所愿,而妻子却离他而去。他选择了东方落根,代表着东方文化气息的本土情怀;妻子选择在西方扎根,象征对西方文化与生活的迷恋。《移民》以华人为关注点,侯南生的父亲从唐山经历“走土匪”而避难于马来亚,他自己为扩大视野而赴新加坡与英格兰求学。最终,他归化为新加坡公民,但心中却纠缠着故土情结与流浪之感,有种归程渺茫的恍惚与迷失。父子两代人都有移民经历,父亲是为“求生”来到马来亚,儿子则为了“求知”而再迁至新加坡。同样,他妻子来自中马的望族之家,其兄弟姐妹则散居在马来西亚、美洲、澳洲、英格兰与新加坡。这两个马来西亚家庭贫富有别,代表华人的不同阶层,其共同点则是后代的离散性。
四 印尼:强制同化下的认同
印华文学的发展曾历尽艰辛,它的兴衰与历史变革、国家政策息息相关。印尼华人移民为数众多,具有悠久的历史,从临时侨居到永久定居,他们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印尼独立后,政府以限制打击华侨经济为主,对华侨社团、新闻报社、文化教育则相对宽容,于是出现大量亲台湾、亲大陆阵营的社团、学校、报纸。由于华文报刊及华侨教育的发展,印华文学开始兴盛,出现雅加达无名社、椰华青年习作社、棉兰印华文学社、万隆椰岛文艺社、翡翠文化基金会等文学组织,涌现许多华文作者,发表出版了一批文学作品。
同华侨教育一样,20世纪50年代的华文文学也是面向祖国、面向华侨社会。多数作品讴歌中国文化,怀念故土,反映中国的各方面情况。描写华侨社会的作品,多数以契约华工的苦难、荷兰殖民者和日本法西斯的残酷、学校生活、华侨家庭、青年的婚姻恋爱等为主题。60年代以后逐渐面向印尼,描写华印民族同甘共苦、深厚友谊、印尼习俗等的作品越来越多。*黄昆章:《印尼华侨华人史(1950至2004年)》,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30页。
此后,与华侨相关的文化教育等全面走向衰落,1966年印尼政府关闭所有华侨学校、查封华文报刊,华文文学几近荒芜。
六十年代起,印尼政府陆续对华人实行一系列的强制同化策略。1966年9月,当时全国性唯一的印尼文、华文掺半的《印度尼西亚日报》开始出版,该报在印尼政府情报部门辅导下设立,曾设有《青春园地》《椰风》《星期天》《周末版》及《文艺园地》等文艺性副刊。*严唯真:《翡翠带上》,香港:获益出版,1997年,第11—13页。此外,犁青在《艰苦成长中的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一文中也谈到《印度尼西亚日报》的设立因由,即“当局为了照顾国内尚有为数众多阅读印尼文书报的华人的需要。”*犁青:《印度尼西亚的笑声和泪影》,香港:汇信出版社,2004年,第141页。在困难时期,《印度尼西亚日报》成为印华写作者的文学殿堂,它以缝隙之地为印华文学播下火种。当局的管控,时局的敏感,这些政治考量限制着作品导向,其副刊难免产生逃避政治现实的“风花雪月”倾向。同时,这种政治高压也激发出作家潜在的社会参与意识。印华作家对该报感情颇深,充分利用这有限的本土华文空间,能在副刊发表文章也激励他们坚持创作。印华文学在五六十年代有过短暂繁荣,随后便进入创作的“冷冻期”,七八十年代渐趋沉寂。从九十年代起,印尼的文化环境逐渐开放,印华作家开始不断接触世界华文文坛。此间,印华文友克服困难进行写作,印华文学的著作陆续在海外问世,大多在香港、新加坡出版。
1998年政权更迭后,印尼进入改革时期,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渐趋民主。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苏西洛四位总统在任职期间都厉行改革,开始解除一些对华人有歧视性的政策,华人的文化习俗、新闻报刊、社团、教育开始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印尼经历了广泛的积极改革,包括政策转变、建立新的国家机构和采用众多的新条例;然而关涉到华族,其进展依然不确定,其改变是有限的和肤浅的。*Tim Lindsey.“Reconstituting the Ethnic Chinese in Post-Soeharto Indonesia:Law,Racial Discrimination,and Reform”.In Chinese Indonesians:Remembering,Distorting,Forgetting,edited by Tim Lindsey and Helen Pausacker,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5,p.41.印尼华文文学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华侨华人自立的生存环境,更离不开印尼的客观环境,在一定条件下印尼的政治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庄钟庆:《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410页。1998年12月22日,印华文友与文化界其他人士共同成立“努山打拉之光基金会(Yayasan Budaya Harapan Nusantara)”,并成立隶属此基金会的“印华作家协会”。*关于印华作协的成立始末,在1999年2月的《印华文友》创刊号上,“印华文学五十年来大事记”有详细记录。印华作协是印华文学复苏的重要标志,它是印华文坛最大的文学团体,在组织文学活动、作家交流、创作比赛、出版书籍等方面都发挥着突出作用。2000年,华文报从独家增设了七家,华文杂志更是纷纷面世。当时的七家华文报分别为《和平日报》《商报》《新生日报》《印度尼西亚广告日报》《龙阳日报》《新纪元》《千岛日报》,华文杂志有《印尼与东协》《绿岛》《群岛》《千岛》《印华文友》《呼声》《望远》《拓荒》《印华之声》。*谢梦涵:《开放后的印华文坛和华文报刊一瞥》,《马华文艺》2002年6月,第137页。目前,印尼主要的华文报纸有《国际日报》《印尼星洲日报》《印度尼西亚商报》《千岛日报》《印华日报》《印广日报》《好报》《讯报》等,大量文学副刊也相继设立,这有助于印华文学的复兴与发展。截至2016年,印华作协和《国际日报》已联合主办五届征文比赛,见证了印尼改革开放后华文文学的复苏历程,既活跃了印华文学的创作,也有助于发现培养文坛新秀。
随着华文教育与华文文学的复苏,新时期的印华文学迎来了发展契机。1996年至1998年是印华文学的井喷期,写作者们长期压抑的热情被点燃,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让华文文学走上复兴之路。印华写作者在短短三年间出版了大量文学作品,据东瑞在《流金季节》统计有31部;该时期作品多在新加坡、香港出版;写作者的复出与作品的涌现预示了黎明的降临,不仅在印尼国内引起了震动,在国际上也宣告了印华文学的归来。1998年至今,跨世纪的印华文学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汉语教学开始萌芽发展,各种中文报纸、文学杂志、文学社团不断涌现,这为作家们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十几年的历程,印华文学在不断摸索创新,出版著作一百多部。不过,在文坛繁荣的背后也有隐忧。莎萍提到,印华文学的水平与亚细安各国华文文学相比,仍有很大的距离。目前在文坛上活跃的写作者平均年龄都在60岁以上,最叫我们惶恐的是后继无人。“1998年华文解禁后,在形势逼迫下,禁锢年代的年青华文写作者,被拉去做编辑、翻译、记者、教师等,在华教与华文文学上出现了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断层现象。卅多年的禁锢,导致现在20至50岁的华人,大多数是‘华文盲’。”*莎萍:《印华文学的两个现象》,《泰华文学》2010年10月第55期,第134—137页。印尼当前自由开放的环境促使该地的华文女作家群崛起。印华女作家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男性与女性、主流文化与本民族地域文化的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多重书写推动了印华女性文学的多元发展,但也可看出印华女作家在多元文化发展的社会中面临着多重文化的边缘身份。*张淑云:《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印华女性文学》,《新世纪学刊》2011年第11期,第29页。印尼华人女性具有多重的边缘身份,尤以“双重边缘”最为明显。所谓双重边缘身份,一是作为华人而处于印尼主流社会的边缘,另一是作为女性而身处传统男权文化的边缘。这种边缘身份深刻影响其创作思想,杨怡对印尼华文女作家予以关注,并概括其创作的共同特点:从日常生活入手,表现生活,反映社会,以及对爱情和生命的探讨。*杨怡:《从新华文坛论及印华文学》,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3年,第134页。慕·阿敏认为,作为反映现实生活、促进族群融洽团结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文学工作者应有时代使命感,印华写作者应立足本土,描写具有本土气息的作品。*立锋主编:《印华诗文选》,香港:新绿图书社,1999年,第11页。在印华女作家中,小说写作者以曾三清、袁霓、碧玲、茜茜丽亚、夏之云、晓彤、雯飞、张颖、何淑慧等为代表。她们虽是印华女性的精英,但在社会上仍属弱势群体。她们饱经磨难也铸炼出其坚强的品格,敢于发出内心的诉求,以小说去展现华人的艰辛奋斗与苦难遭际。印尼华人女作家大都有着悲天悯人的心肠,她们的目光并不局限于个人的感情世界里,而是以更广阔的眼光去看待社会上的人和事。*王列耀、颜敏:《困者之舞: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四十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36页。她们细腻描摹印尼华人生态,不乏真实、感人之处。
马新华人的认同具有自然过渡的特征,而印尼华人面临的则是国家的强制同化。自50年代起,印尼政府着手处理外裔问题。针对华侨设置种种规章,加强对华侨的监督与管理,征收外侨税及限制外侨职业,限制中国人入境、移民,限制华侨的居留、旅行等。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签订,华侨面临国籍的抉择,入籍印尼成为主要趋势。印尼的国籍政策可分为被动制和主动制两种类型。*黄昆章:《印尼华侨华人史(1950至2004年)》,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页。1946年至1954年为主动制时期,由于独立战争及战后复兴等因素,印尼政府鼓励华侨选择印尼籍。随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1954年至1966年为被动制时期,印尼政府制定各种规章排斥华侨加入印尼籍。随着双重国籍的解决,印尼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民族同化政策。谈及印尼“少数民族”问题的核心,有论者将同化归纳为:“外裔加入和被吸收到统一的印度尼西亚民族的躯体之中,以致具有自己特点的集团再也不复存在了。”*周南京、陈文献等编译:《印尼华人同化问题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1996年,第133页。这种观点便是对同化政策的有力印证。新秩序时期,当局实施“强制”同化政策。印尼政府长期推行的同化政策已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华裔青年大多不谙华语,已经被同化并全面认同印尼社会。不过,这种强制同化是反人道的,带有歧视、排外性质,种族文化灭绝的举措更不可取,也违反了民族自然融合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印华女作家也关注华人的身份认同。晓彤的《金伯》表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认同观。金伯在椰城的市场经营小金店,他十多岁就随叔父下南洋谋生。他在印尼待了五十多年,但难以释怀对故乡的怀念,最终选择回唐山老家去“落叶归根”。金伯代表老一辈华人移民的故土情结,他六十多岁仍孑然一身,始终无法融入印尼本土,他全身心地认同中国。“我”虽理解金伯的选择,但却有不同的体验。
我生于斯,长于斯,也可能死于斯。我热爱我居住的地方,也习惯了我现有的环境,当然我明白我祖上的来源,可是我出世在这南岛,这儿是我的家。所以无论如何,我就不能像金伯那样对遥远故土的情深,万般的感触与乡愁。*晓彤:《哑弦》,雅加达:印尼与东协月刊社,1996年,第67页。
随着时代发展,“金伯”们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我”们悄然而至成为主体。“我”所代表的则是年轻华裔,具有“落地生根”的本土情怀,身份认同也转向本土国民。90年代以来,这种认同趋势更为突出。印尼华人不同方言区之间交往都是用印尼语,尤其是土生华人多不会华语,因而本民族意识渐渐让位于“新国家意识”,他们逐渐成为一个地道的当地少数民族。*陈鹏:《东南亚各国民族与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151页。云昌耀也提到,1998年苏哈托政府下台,终结了新秩序时期的同化政策与意识形态,并且开启了印尼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复苏的新空间。*云昌耀:《当代印尼华人的认同:文化、政略与媒体》,邱炫元等译,台北:群学出版,2012年,第15页。当前,印尼华裔已不存在政治认同的疑虑,他们早已“落地生根”成为印尼公民。
反面来说,印尼的政治环境也会催生逆向效应。廖建裕对印尼华人族群进行细致考察并强调,苏哈托对印尼华人采取同化政策,以“土著”为“国族”的模式,视华族文化为外来文化,不能成为所谓的印尼文化的组成部分。1966年10月发布的改名换姓法令是冲淡华人身份认同最重要的措施。*廖建裕:《现阶段的印尼华人族群》,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2年,第123页。印尼的强制同化及排华事件造成逆反效应,而霸权政治也带来负面影响,外在强势政治举措、族群冲突更加激发起华人内在的民族文化的“本能自卫”。印尼华人在社会中处于尴尬的地位,华人对印尼的国家认同并没有换来政府的信任,国家的政治理念让华人产生无所归依的疏离感。因此,华人的民族文化认同则远远强于国家认同,必然产生一种“族”大于“国”、“精神家园”大于“在地国度”的文化现象。
结 语
马新两国女作家笔下的“移民题材”,主要聚焦于华族的离散与认同,也反映出国家的移民及人才外流问题。当然,移民问题并不限于华人族群,而是共通于各国各民族,这是不可扭转的世界多元化潮流。马新的华族移民,就祖籍地中国而言,他们是再移民,有者甚至是多次移民。不断的离散让其认同带有多元性,唯一不变是其华族身份,就如“美籍新加坡华人或英籍马来西亚华人”之称。马新的华族再移民群体,他们的认同倾向于“双重家国”,“家”指故土家园的马新,“国”指移居入籍的国家;其文化认同则更趋多元,除了“家、国”文化,可能又带有文化中国色彩。三国的华族都曾为当地的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当今,华族的国家认同已毫无争议的归属当地。因此,如何更好的发挥华族才智?如何防止人才流失?这应当引起各国政府的足够重视。同时,族群关系的好坏也影响着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华族及其他族群都应摒弃各自的民族优越感,应以平等、和谐的心态去共谋发展。马来西亚与印尼都曾推行“保强削弱”的民族政策,一再忽视少数族群的正当权益,这不利于各民族的健康发展。理想的族群关系应是彼此的融合,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及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具有一定的示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