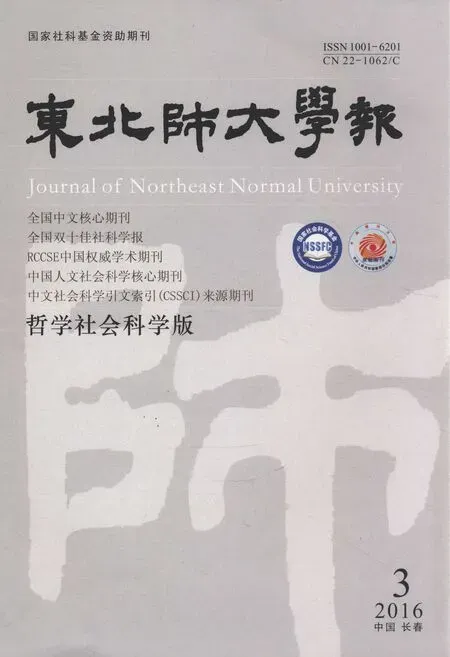错失与错置:《洛丽塔》中的流亡意识与道德存在探究
吴中东,宫玉波
(1.国际关系学院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91;2.北京交通大学 语言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44)
错失与错置:《洛丽塔》中的流亡意识与道德存在探究
吴中东1,宫玉波2
(1.国际关系学院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91;2.北京交通大学 语言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44)
[摘要]纳博科夫作品中的流亡意识表现在他对时间的感悟。作品中对于语辞的驾轻就熟的幻化表达将时间进行了“艺术再造”,并由此来寻求心灵慰藉。与此同时,传统的道德观念在《洛丽塔》中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在他的作品中,文学传承的思想消失了,代替它的是小说的真实与审美,由此展现了纳博科夫作品中跨越道德界限的艺术观。本文将从道德判断和流亡意识两方面为切入点来分析纳博科夫在时间阈限中的艺术创作。
[关键词]流亡意识;道德判断
一、引言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20世纪杰出的小说家和文体家。他出生于圣彼得堡,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纳博科夫随全家流亡德国。他有着法国和俄罗斯文学的丰厚底蕴,在蝴蝶标本制作的旅程中,开始了如同蝶翼般绮丽多变的创作历程。1955年9月15日,《洛丽塔》出版,同时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这部作品首先是一部反映美国现代生活的小说,描绘了爱与死的轮回与纠葛,因恐惧爱情的消逝而陷入的道德沉沦,珍藏于记忆中的那份爱情实则是对已逝青春的赞叹与惋惜。因此,整部作品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价值和意义的错失和错置。
与其说纳博科夫是一位语言天才,不如说是因为流亡生活和异国文化给予了他成为语辞世界里王者的机缘。在研读他的作品时,如果只是从单一方面谈论其作品的文化属性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就大大贬低了其作品的价值。他的创作发端于现代俄罗斯文学,同时又与现代美国文学交汇。更为巧合的是,彼时彼刻,正是文学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时期。就此而言,《洛丽塔》是纳博科夫凭借自己对语言的准确把握,依托于长久以来对人类生存桎梏的思索,所揭示的人心本质的某种纠缠与抗争。
二、现实与反现实——洛丽塔的自我救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洛丽塔似乎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亨伯特对初恋的幻想及其衍生出来的,因为无法离开洛丽塔而产生的执念。要依靠幻想来存在于现实一定也是纳博科夫本人的存在困惑。游走于现实与虚幻之间,作者把故国深情寄予他乡,寄予一生痴迷的标本采集,寄予时空交错中,恍惚瞥见的那个同样孤独的背影,她有着14岁初见时的那一抹明媚的笑,有着阳光照耀下如同蝶翼一样令人神往的美好。于是,作者将这种追逐的信仰赋予亨伯特,让他替自己去体验手指触碰阳光,驱散孤寂阴霾的生命体验,至于结局如何,或许作者自己也不清楚。每一位伟大的作家,都是文学殿堂里的忠诚卫士,在他们的作品中,文学性高于现实,内心体验高于道德说教,语辞造诣高于情感泛滥。追寻,一如奥德修斯的旅程,本来没有最终结局,灵魂已然上路,就不问归途。于是,纳博科夫创造了亨伯特,也毁灭了亨伯特;亨伯特幻化了洛丽塔,也束缚了洛丽塔。然而,真实与悖论相辅相成,洛丽塔并不属于任何人,她可以因爱而生,也可以因爱毁灭,纵然有着向往自由的决心,却少了追求真正自由的理性。洛丽塔的存在就像一口深井,一口无法填满的悲伤之井,而亨伯特只能以幻想为这口井盖上盖子。
品读《洛丽塔》,更像是做着一个又一个字谜游戏。那些富于意味和象征的语词奠定了全文的基调,预设了结局的发展。因而让读者不断地产生好奇,想要竭力寻找蛛丝马迹印证自己的设想,描绘自己眼中的洛丽塔。小说描写的是牢狱般的生活,洛丽塔被亨伯特的欲望所束缚,要挣脱这枷锁,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自由,一如空气,如影随形,却可触而不可得。虽然洛丽塔最终选择了逃离,但还是没能逃脱死亡。在小说结尾,洛丽塔逝去的生命阐释了宿命般的轮回。20年前的同一天,一位同样历经磨难的不知名的妇人在肮脏的床榻上产下一个注定孤苦一生的女婴,听到孩子的第一声啼哭便撒手人寰,那便是洛丽塔的母亲。故事回到开头,却永远无法为结局画上一个圆满的句点。对于存在的悖论而言,这是困顿的人类永远追不到的幻梦,是孤寂的灵魂永远到不了的天堂。环形的叙事结构,是作者的良苦用心,像是织就蝴蝶羽翼那样的精密、准确、生动,又让人捉摸不透。读者不禁反问:难道在字里行间,作者早已予以“永生”一个不同寻常的注解?只等着结局的大幕拉开,让读者幡然领悟:故事之中,生活之中,命运之中那无法挣脱的宿命般的梦魇。
纳博科夫并未受到动荡的苏联政治文化的影响,所以他很好地保留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化艺术。正是他不拘一格的写作手法,使他的作品跨越了文化的边界。因此,只有在多元文化视角下进行研究,才能反观文学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不断演变的大环境。此时,再次进入到纳博科夫的文学世界,仿佛在重读一本已知剧情的小说,内容是熟悉的,而情感是全新的。
将现实虚拟化,将空间时间化,正是作者一贯处理作品的态度。而在研读其文学作品时就会发现,纳博科夫以其惯用的颠覆性审美观念来阐释文学世界中的诸多经典。作为一个有情怀的作家,他往往能够转换视角,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字世界。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对于生命中那些破碎的、消逝的,以及未知的种种,作者都能创造一个空间让它们被安放、被召唤、被预测。那些隐秘与困扰的人性纠葛,实际上是伴随边缘化文学而自然生成的文字质感。作者将“个人情怀”与“公众意识”做了明显的区分。在感受性与思辨性的分界点,在能够审视文化与文学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当下,作者不遗余力地用语言勾连起了断裂的情节。从人物到故事,从故事到人物,在循环往复的主题中,衍生出了“洛丽塔”这一幻化的形象,又或者,在作者看来,幻化即是真实。那些跳跃的故事情节,不被公众接受的道德评判,在亨伯特执着而又癫狂的追寻中,渐渐被读者所容忍,直到把对于洛丽塔的同情迁移到命运本身的不公上,让亨伯特出人意料地逃脱了道德训诫。那么,这样的情感归因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洛丽塔的出现,以及作者对她的描述,平衡了作品中感官经验与道德意识之间的悖论。洛丽塔就是所谓的“边缘文化”的产物,在探寻她之所以成为“她”的道路上,关于情感和道德的迷思不分国界,无关信仰。或许洛丽塔只是读者万千阅读体验中的过客,但她无疑会成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那个流逝于时间的孤独背影,那个迷失于亨伯特想象空间的小精灵。洛丽塔的世界是空寂的,在养母夏洛特的凝视下空洞的生长,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没有关于生母的一切消息,甚至不知道母亲的名字。因此只有将自己放逐在生活的边缘地带,远离行色匆匆的人群,才能无所畏惧的走向未来的不可预知。她想要的只是便利店的一瓶可乐,只是在陌生旅馆里放好的一条崭新的、鲜红的裙子[1]302-324。她甚至不去过问关于养母的一切,却在夏洛特死后悻悻地看着窗外,没有震惊、没有哀伤,没有恐惧。这一切只是因为,她与生俱来的对于恐惧的熟悉,对于冷漠的亲切。她爱亨伯特吗?她内心的答案或许是:什么是爱?爱又从何而来?那么,她爱自己吗?这个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即便生命如同草芥,她也想奋力地活下去,不管跟谁,不管在哪里,只是活着,只要活着,盲目也好,清醒也罢,如同最后她与马戏团演员的私奔,虽然最终逃离了亨伯特的控制,但归途在哪里,她也是一片茫然。当她因为难产而握紧了气味难闻到令人窒息的肮脏床单时,她不会料到,许多年前的同一天,自己也降生在类似的床榻之上,更不会料到,无缘见到彼此的母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由命运的悲剧将彼此连接在一起。洛丽塔其实从未有过救赎,有的只是懵懂的挣扎,在宿命般的轮回之内,她自以为是的骄傲让读者震撼,进而怜悯,之后是无限的悲叹。然而穿越悲剧的泥沼,她对生命与存在的追寻,也让人心生敬佩。
三、道德与反道德——亨伯特的命运悬置
洛丽塔对于纳博科夫而言是一个等待被人发现的灯塔,在迷航之际能唤起生存勇气的幻梦[2]105-111。然而,幻梦终究不可依附。于是对于纳博科夫来说,流离失所、不被认同,就如同灯塔已经熄灭,许久不曾照亮大海。幸而有妻子维拉相伴左右,在精神世界及文学创作中给予坚定的支持,纳博科夫才得以在边缘身份和信仰的迷茫中一往无前的寻找“自己”,寻找语辞世界中王者的冠冕。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有着不为人知的纠结、困顿与挣扎。同时也有着为人所知的阴郁、诡秘与自大。这样的怯弱与强大,卑微与悲情,以二元对立的深刻描摹了一个时代的呐喊,一个流亡作家群体的心声。
纳博科夫笔下的亨伯特被现实也被自己禁锢在道德的牢笼里,并用这牢笼囚禁了他心中的挚爱,在道德与不道德之间试探、追问、拷打着自己的灵魂。然而,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时间之狱”困住了亨伯特,他幻化了洛丽塔的形象,希望洛丽塔像仙女一样青春永驻,生动迷人,这样他可以永远拥有内在觉知中幻化出的“洛丽塔”。这个“洛丽塔”便是永不会失去的,某一个特定时间段的代表。
逻辑与道德从来都是根植于人心而见诸世事的。由于道德,才有了善恶,因而催生出秩序。那么小说家就要有更为广阔的视角,善于洞察世间万象的相对性质。我们当然可以指责纳博科夫的逻辑跳跃,他对道德沦丧的不屑一顾使他敢于从自身的某种精神渴望衍生出精神图腾,并让它以小说的形式实际存在[3]32-40。另一方面,我们同样可以把这看成是他对自己信仰的表述。如果我们承认人的存在只是偶然,我们追求的一切精神价值也只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那么我们的对于生存价值抑或道德的追溯就只能是自我崇拜。
踏入纳博科夫的语辞世界,实则来到了一个符号的世界,徜徉于此的人们会不自觉地对作者精心创造出的韵律、象征、文字产生敬意。对作者借由语言控制思想的决心而深深叹服。即便纳博科夫在创作中的时空观念、人物设定、行为动机和道德评判令人心生疑问,但古今中外的东西方学者们毫无例外的对其作品给予了中肯且相似的评价,笔者可将其归纳为:边缘文化特质中成人的童话,另类的传统。这是用一个人物来代表一个群体的传奇,用一种情感来追问一种普遍无意识的内心体验。或许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错过的是时间,错过的是情感慰藉,但只要追寻不变,向往生命力的灵魂永远不会暗淡。
错失与错置,时间与空间,理性与感性相互交织成赞颂生命悲情的华美乐章。有人说,“借我三生烟火,换你一世迷离”。亨伯特曾经重温那些灰暗与阳光交织的日子,那些被洛丽塔填满的日子,在属于他的那些岁月里,从屋子的门窗直对着草坪的方向,传来了喧闹的欢笑声,那里面有一个是属于洛丽塔的,也是属于他的。就像是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用心品味的玛德莱娜小点心,融化在对爱人的美好向往中,然而,又具体向往些什么呢?自由不可得,又或许不能得。爱情不可得,又或许不存在。卑微的忏悔与欣喜若狂之后的辗转难眠才是属于一个纠结的灵魂的最终归属。在储存于幸福感和童年记忆的洛丽塔身上,唤醒的是亨伯特的爱情,是纳博科夫对故乡的执着。只不过这种执着被艺术化的再现为卑微而狂妄的不伦之恋。在创作的过程中,道德已死,同时,接受这部作品的过程是一份拆解语辞迷思的惊喜,但在人物本身的情感连接中,读者不能妄图去得到任何回应,有的只是作品本身赋予的贪婪地汲取和沉默接受。这样的小说似乎只能远远观赏,如同欣赏一件艺术品。原因是,纳博科夫热衷于储存过去,他兀自拟定了属于人物的精神图腾,不等读者回应就将其带入到他的世界中。他的雄心壮志是足不出户就把世界牢牢掌握于手中,这就酿成了叙述者亨伯特的人生悲剧。禁锢、游离、逃避、回归……感性体验与理性智识之间的鸿沟,道德界定的悬置,无不证实作品中随处可见的被边缘文化赋形的痕迹。死亡的魅惑笼罩在每个人物身上,勾勒出了受限于“时间之狱”的生命线条。如同齿轮般精确的命运轮转,往往会误导读者犯一个基本的错误,那便是将时间与空间混淆,将时空的串联看成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其实不然,时空的表里具有两面性,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只有作者的情感直观才是语辞迷宫的出口。
四、通俗与非通俗——“流亡意识”的隐形禁锢
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中写道,“初看之下如此无边无际的时间,是一个监狱。”漂泊无依,已成定局,唯有祛除妄念,体会人生百味,才能超越时间,入定内心,有着对自我的清醒觉知。在此意义上,小说中的道德质疑就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表现力与人伦规约上的相互角力,而是关于易逝人物的最完美,也最真实的描述,以及人物形象受时间和痛苦所制约的复杂性。他在小说中诗情洋溢、激扬文字、臧否古今,使整个文本从里到外都焕发着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巨大魅力。它从某一方面影射出了纳博科夫在时间之狱中的反复摸索与探寻。
小说家永远有着一颗不安定的灵魂,他游走于文化的边界,观察着异质文化的内核,并试图融入它,成为它。但最终,即使身体安顿了,精神还是需要漫游的,永远在寻找的路上,不会停歇。这时候,存在就向我们展现了它可怕的虚无本相。
对于读者而言,我们与作品面对面的交流,早已深藏在与人面对面交流的意义与惯例中,无论是作者还是他笔下的人物,都是作品在表达它独有的艺术理念,也是作者的自由道德立场的体现。就如同你盯着蝴蝶色彩斑斓的翅膀时,有人就会觉得纷繁复杂到让人迷惑不解。或许作者要用一个惊世骇俗的文本告诉我们,生命的本质虽痛苦,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法不祈望自由。这自由体现在时间向度中的绝对性和永恒性。或许在主人公的痛苦追寻中才能让读者体会到:想要到达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彼岸,必先有欲望。亨伯特通过洛丽塔取得的暂时性的精神避难所是谎言与自欺,在谎言的迷宫里,洛丽塔则扮演着伪装与掩饰的角色。而在逃入奎尔蒂的“避难所”之后,她无疑用更为不堪的方式诠释着自己的存在,对于洛丽塔而言,或是固执的滑向欲望的深渊,幻想碎裂并终于衰老的边界——灵魂的死亡;或是用流水一样的生命韧性对抗现实——美丽容颜的消逝。纳博科夫用诗意的话语来描写青春已逝的残酷与死亡的决绝,表达自己对于美好的思考,表现人的种种存在。他用现实的公正来拷问主人公堕入命运漩涡的内心,回味生命的短暂和迷离。作者在创作初期,在《洛丽塔》诞生之前,就曾写过一部风格类似的俄语小说《魔法师》,这部作品在后来得以出版,于1991年问世。它的主要情节几乎与《洛丽塔》如出一辙。或许在作者的记忆深处,并不是“无根”,而是“寻根”。《说吧,记忆》中描述了作者在创作这两部作品时的内心状态,真实到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敬佩,精彩到让人对于这两部惊世骇俗的晦涩作品产生了瞬间的理解。当《洛丽塔》以自传回忆录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时,从主人公的视角记述一切,这种手法极为新颖,既是读者获取信息的唯一来源,然而,又是一个不可靠的来源。故事的字里行间充满了黑色幽默,荒诞情节和机智的嘲讽。
尼采曾说,“要真正的体验生命,你必须站在生命之上。”隐喻,构成了纳博科夫作品的基础要素,只要抓住它,就能随作者遨游于象征的宫殿。可以说《洛丽塔》的确是作家敢于凭借一己之力撼动现实的“微暗的火”。在纳博科夫的时代,作家用一小块一小块劫后余生的碎片,努力构筑起一个早已死去的年代。对“彼在”文化和“彼时”文化错位的怀念。纳博科夫的语言具有仪式般的力量,他的时间和空间区别于那些在其之前和随之而来的主体状态,他使人物的生命获得真正的道德维度,从而扩展了读者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畅想。乔治·艾略特在185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无论画家、诗人,还是小说家,他们的最大贡献在于扩大了我们的同情范围。但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描绘的人类生活画面甚至能让我们突然发现那些除去他们自身以外的琐碎细小和自私。而这些可能也是道德情感的原始材料[11]51-79。
当我们回归文本,初遇洛丽塔,初识亨伯特,就如同小说的主人公在一家便利店不经意间相遇:夏末未至的八月里,仅仅遇到一个洛丽塔,对于亨伯特来说,每个早晨就再也不一样了,每个当下也再也不同于以往,因而孤独便能被内心阴暗角落里照射进来的阳光拭去。
五、结束语
纳博科夫用俄、英等多种语言创作,唯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俄罗斯文化传统特质,以及命运赐予的流亡意识,都凝练成文学殿堂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用纳博科夫自己的话说,《洛丽塔》是他自己和英语语言的爱情故事,书中荒诞的现实对立更进一步加剧了人物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这是作者自己对文字和艺术的感悟和体验。
在这部作品中,有迷失在时间之狱里的固执,有追逐在欲望空间中的迷惘,也有隐匿在道德边缘的质疑与追问。纳博科夫之所以倾心于描述道德沦陷和疯狂,是为了说明,时间不可停留,欲望永无止境。即使“活着”也无法逃脱死亡的阴霾,因为苦难更能彰显命运的力量。人在强大命运面前是脆弱的,除了在夹缝中求生存,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之外别无他法。时空变幻、命运沉浮、道德危机所施与个体存在的发展形态在这部作品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位对人性和命运的终极意义有执着追求的小说家,纳博科夫在文学殿堂中的地位不可小觑,并随着时间的不断沉淀,成为影响后世文学的重要声音。
[参 考 文 献]
[1] Nabokov,Vladimir. Bowers Fredson Ed.Lectures on literature [M].New York:Mariner Books,1969.
[2] 黄铁池.玻璃彩球中的蝶线——纳博科夫及其《洛丽塔》解读 [J].外国文学评论,2002(2).
[3] 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 [M].孟湄,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
[4] 马泰·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 Eliot,G.Essays of George Eliot 2,270[J].Firstprinted in Westminster Review,1856.
[责任编辑:张树武]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3.027
[主持人语] 著名科学史家萨顿曾说过:“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换言之,西方文明肇始于希腊文明,希腊文明又是在埃及文明和两河文明的深刻影响下得以诞生的。而在目前,随着“一带一路”研究的不断深入,作为其中节点之一的埃及历史与现状遂成为学者们的研究重点,近期举行的中埃文化交流活动更是把对埃及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由此,对古代埃及文明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更有现实意义。基于此,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王国时期古代埃及经济文献整理研究》(13BSS008)为研究平台,《东北师大学报》组织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和厦门大学的五位学者分别就古代埃及的经济制度、精神世界以及古代埃及的对外关系等古代埃及文明研究中的几个重要论题进行了探讨。古代埃及人留给我们的最为直观的遗产便是五千年来屹立不倒的金字塔和恢弘壮观的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然而它们的建造需要组织缜密、运转良好的经济体系的支撑。提及古代埃及的经济体系,一个无法规避的问题就是古代埃及人的经济观念。古代埃及人确乎经济观念淡薄,但这与古代埃及存在着活跃的贸易活动并不相悖。古代埃及人的这种极具特点的经济观念和经济活动与他们的精神世界有着密切关联,他们对来世的渴望以及对神祇的笃信是他们建造金字塔等大规模坟墓和神庙的精神支撑。无论经济制度还是精神世界都是古代埃及人的自我完善,然而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不是孤立进行的,都需要与外部世界进行交往,互通有无。纵观古代埃及文明三千年的发展历程,埃及与其周边国家或地区如努比亚、利比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两河流域等均发生了密切的交往,而其与希腊的交往则为它最终完全融入东地中海世界埋下了伏笔。
Lostness and Misplacement:A Study of Alienation and Moral Existence in “Lolita”
WU Zhong-dong1,GONG Yu-bo2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100091, China;2.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The sense of alienation embodies Nabokov’s understanding of time.His fiction displays the writer’s magic of word-and-image play that entertains a dazzling delight for readers as well as the artistic rebuild of time for his works.Through this unique writing-style,Nabokov seeks his inner consolation.Meanwhile,the traditional moral value is also challenged in the novel Lolita.The literary inheritance is brilliantly replaced by its affirmation of the abiding beauty and truth inherent in the novel.Therefore,Nabokov expresses his belief in art by isolating from morality.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analyze Nabokov’s writing sty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ienation and moral judgment.
Key words:Alienation;Moral Judgment
[收稿日期]2015-11-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WW028)。
[作者简介]吴中东(1961-),男,江苏常州人,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外语系副教授;宫玉波(1967-),男,吉林白城人,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6)03-0153-05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3.026
——《洛丽塔》的成长小说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