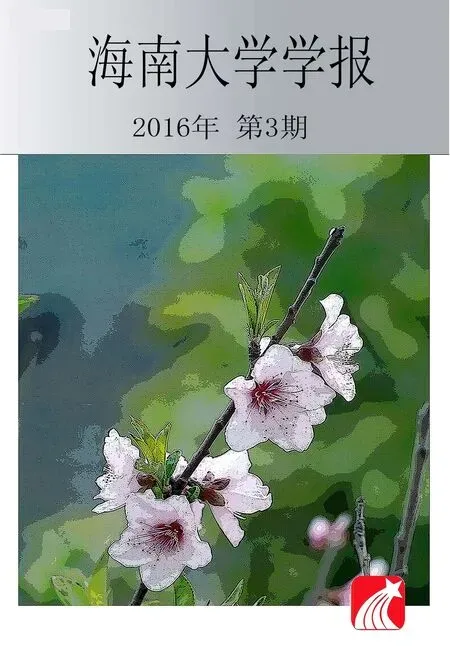《离骚正义》与望溪“义法”
许 光
(南京大学 中文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离骚正义》与望溪“义法”
许光
(南京大学 中文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离骚正义》是《离骚》学史上一部魅力彰著的不可或缺之作,其魅力建构与方苞“义法”相互关涉。以“人臣之义”为要义的思想表达与望溪对“义”的持守以及其对当时社会的思考和态度相辅相成。而其注重从文章体例和结构推寻大义, 强调“明于体要”诠解方式则呈现出与望溪之“法”相一致的文学审美旨趣。
[关键词]《离骚正义》;方苞;“人臣之义”;“义法”
“桐城三祖”之一方望溪古文成就卓著,享誉一代文坛。然而,除却文章学,望溪还曾注解过文学经典《离骚》。或许是文名太盛的缘故,方氏《离骚正义》在《离骚》学史中几乎湮没无闻,鲜有现代学者关注。实际上,自《离骚正义》问世以来就从不缺少赞誉,如梅曾亮父亲梅冲就认为:“本朝《楚辞》研究总杂重复,不暇至铨,只有方苞《离骚正义》、张德纯《楚辞节解》为能得其大意。”[1]其后,对《楚辞》和屈原研究颇深的清代学者陈本礼对《离骚正义》颇为看重,其于名著《屈辞精义·离骚》中所引注解一以《离骚正义》为鹄的*王夫之《楚辞通释》、戴震《屈原赋注》以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为清代《楚辞》学研究的代表著作,然陈氏在《屈辞精义·离骚》诠解中于此并未摘取,专以《离骚正义》疏解为鹄的。。近世《楚辞》研究学者姜亮夫先生亦给予《离骚正义》较高评价:“既异于明以来以时文义例说《骚》之弊;亦少桐城批点之恶气。望溪学有根柢,非泛泛以文章为宗主之桐城他家可比。”[2]然而,于明清浩繁的《离骚》注解中不失颖异的《离骚正义》何以既能“得其大意”,又能少时文义例和桐城批点之弊,亦或说此书的魅力何以构成,望溪《离骚》学素养来源何处,这些都有待解决。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离骚正义》与望溪“义法”关系的梳理,力图寻索构成此书魅力的思想渊源与文学传统。
一、“承祧与创见”:方望溪《离骚》观拟测
中国士人向来注重学术传承,开启学风的先辈们所创立的学术方法和特色在后人承接中不断与时代相互作用,交融而前行,方望溪《离骚》学素养形成自然也不例外。自祖父方帜任官芜湖教谕,方氏家族就已经开始了学术相承累积的进程,方帜顺治年间曾以明经贡廷考试第一,由于善作诗文,被推为江上十子之首。父亲方仲叔以隐逸与诗歌享誉当时,时常与曹寅、杜浚、钱澄之*钱澄之(1612—1693)安徽桐城人,原名秉镫,字饮光。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有《藏山阁存稿》数十卷,另有《田间诗学》、《庄屈合诂》(包括《庄诂》、《屈诂》)等。《屈诂》在《楚辞》研究史上是一部具有较高地位的著作。《四库总目提要》云:“盖澄之丁明末造,发愤着书,以《离骚》寓其幽忧,而以庄子寓其解脱。不欲明言,讬于翼经焉耳。”(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139页。)等诗文家相互唱和,传为一时佳话,方望溪自小就是在这样一个深具骚人旨趣的家庭环境氛围中成长的。在《廌青山人诗序》中,望溪回忆先辈对自己的影响:“苞童时,侍先君子,与钱饮光、杜于皇诸先生以诗相唱和,慕其铿锵,欲窃效焉。”[3]102《田间先生墓表》亦云:“自是先生游吴、越,必唯舟江干,招余兄弟晤语,连夕乃去。”[3]337虽然“晤语”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望溪对诗性的推崇以及钱澄之等人对望溪《诗》、《骚》方面影响,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其回忆感知一二。当然,除却对望溪耳提面命的教导,《离骚正义》具体注解也可以寻索到钱澄之等人的影响,如对《离骚》“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一句,钱澄之曰:“理与媒皆为导言者也。弱则不能力争,拙则不能善道,是为导言之不固”[4]。望溪的解诂与其高度一致:“不得于父而求信于子,则理已弱;以直道事人,则媒甚拙。恐虽有为之导言者,而亦不能固也。”[5]17a再如,对“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一节阐释,游国恩先生认为:“方苞之说殆出钱澄之所谓日暮图穷者”[6],主张此解脱化于钱澄之。值得注意的是,望溪对“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一节的解释与前贤王逸、洪兴祖等人差异显著,独与钱氏的应合应该不仅仅是巧合吧。
此外,望溪与李光地、何焯等颇具《离骚》学素养文人的交游*何焯《义门读书记》对箫统《文选》所选《楚辞》作品考证精密,对全章、全句之义皆有发明,大致宗于程朱而断以己意,旨在“发先哲之精义,究未显之微言”,黄季刚称赞曰:“清代为《文选》者,简要精核,未有超于何氏。”(参见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8页。),对其《离骚》审美趣味的建构以及诠解范式的形成也不无影响。顾就李光地而言,其曾著有《离骚经注》一书,《四库全书总目》评曰:“所著皆推寻文意,以疏通其旨,亦颇简要”[7]。而望溪《离骚正义》引用唯一处它注就是来自李光地《离骚经注》:“清溪李氏曰:‘不近称熊绎而原溯高阳,大夫不得祖诸侯之义。’”[5]1a可见其对望溪影响之深。
当然,就现存文献而言,除却《离骚正义》,望溪并没有直接关涉《离骚》的评述,然而人们或许可以通过其对《楚辞》的评议略微窥探其对《离骚》态度与认知。望溪重视《楚辞》“比兴”,他说:“诗人虽未尝先以比、兴分章,而及其既成,则或出于比,或出于兴,不可比而同至,复而不厌,则本文固然,《楚辞》及汉、魏诗人犹师用之”[3]660,认同《楚辞》“比兴之义”师法《诗经》。在《书朱注〈楚辞〉后》,望溪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有关《楚辞》的理解:
朱子定《楚辞》,删《七谏》、《九怀》、《九叹》、《九思》,以为类无疾而呻吟者,卓矣!而极诋《反骚》,则于其词指若未详也。吊屈子之文,无若《反骚》之工者,其隐痛幽愤,微独东方、刘、王不及也,视贾、严犹若过焉……戚属至,则将咎其平时起居之无节,作事之失中,所谓垂涕泣而道之也。雄之斯文,亦若是而已矣。知《七谏》、《九怀》、《九叹》、《九思》之虽正而不悲,则知雄之言虽反而实痛也。[3]116
王逸《楚辞章句》是在刘向辑录《楚辞》基础上另入其《九思》并作注解。洪兴祖则只就王逸所录注释作部分补充修正。从现有传世文本来看, 刘、王在选篇上还是有原则的:他们全录屈原的作品,对屈原以下辞赋家仅选录那些悼屈、拟屈的作品,其它概不收录。朱熹《楚辞集注》虽以王逸《章句》和洪兴祖《楚辞补注》为蓝本, 但除全录屈赋外,在选篇上还存在不同。他认为:“《七谏》、《九怀》、《九叹》、《九思》虽为骚体, 然其词气平缓, 意不深切, 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8]168,于是删去不取,于王逸所收汉人之作只存《惜誓》、《哀时命》、《招隐士》,另收贾谊《吊屈原》、《鹏赋》并附录杨雄的《反离骚》,但极力呵责之。《楚辞集注》对《反离骚》态度和选录原则清晰展示朱子对屈赋思想和艺术传统的认知,朱子曰:“王逸《楚辞》篇次本出刘向,自原之后作者继起,而宋玉、贾生、相如、杨雄为之冠。然较其实,则宋、马辞有馀而理不足,雄乃专为偷生苟免之计,既与原异趣矣。其文又以摹拟掇拾之故,斧凿呈露,脉理断续,其视宋、马犹不逮也。独贾大傅以卓然命世英杰之才,俯就骚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时诸人所及”[8]200。朱子以理学家的标准对扬雄《反离骚》在思想内容上采取呵责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偏见,当然,这也与朱子“屈原之忠,忠而过者;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的态度一脉相承。
望溪对扬雄的为人及其作品辩护就在于他能深体扬雄和屈原之悲愤,“戚属至,则将咎其平时起居之无节,作事之失中,所谓垂涕泣而道之也”。这与朱子“屈原之原罪”是有原则性的区别。在上述引文中,望溪对朱子删定《七谏》、《九怀》、《九叹》、《九思》给予肯定,而对其诋毁扬雄《反骚》之文却并不认同。他认为《楚辞》中其它吊屈子之文之所以“无若《反骚》之工者”就在于《反离骚》深寓“隐痛幽愤”之情。望溪的评价标准与自己的经历和认知密切相关,即“托兴以喻己志”,用比兴探寻屈原“忠爱之思”。经历了“《南山集》案”的方望溪对扬雄“屈从王莽”的忧思悲愤感同身受,他赞赏扬雄的《反离骚》工于文,其实是在深层次上寄寓了自己的情感。诚然,望溪此论是在指涉《楚辞》的其它篇目,但《离骚》毕竟是《楚辞》的重要组成部分,望溪罹难经历的折射以及对“隐痛幽愤”的显扬很难抽离于《离骚》的诠解中。正因为如此,望溪的《离骚》诠解旨趣很容易与明末清初钱澄之等先贤“以《离骚》寓其忧”处于同一维度上。同时,望溪对《楚辞》的评骘也间接表明了他对屈原的“忠孝”是持赞赏的态度,而对于朱子“屈原之忠,忠而过者;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观点,望溪似乎并不以为然。
二、“人臣之义”:《离骚正义》思想建构与望溪之“义”
《离骚正义》极力寻索深隐《离骚》之“义”。正文起首“帝高阳之苗裔兮,字余曰灵均”一节诠解已为全书立下张本,望溪曰:“首推所自出,见同姓亲臣,义当与国同命也;次及生辰,见人之于天,以道受命也;次及名字,见先人以德命成忠,乃所以成孝也。清溪李氏曰:‘不近称熊绎而原溯高阳,大夫不得祖诸侯之义’”[5]1a。从此节幽约隐微的叙述中寻索出屈原所隐匿之“人臣之义”、“忠孝之义”、“诸侯之义”,而望溪所坚持的“忠孝是人的天命”则又为《离骚正义》全书核心精义所在。
望溪强调“人臣之义”,并将《离骚》中宓妃诸女等繁杂人物与人臣相关联,如“下女,乃喻亲臣、重臣能为己解于君者”、“佚女,盖以喻王之亲昵未在位而为王所信,或故旧之臣已去位而为王所重者”[5]15b,这些阐释俱将众女释为朝堂臣子。在阐释“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绁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一节时,望溪将男女诠为君臣,并将其上升到伦理纲常的高度:
古人以男女喻君臣之义,盖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以佐阳而成终一也。有男而无女则家不成,有君而无臣则国不立,故原以众女喻谗邪,以蛾眉自喻,此义也……高丘无女喻楚国之无臣也,意谓群邪塞路,我复远逝则楚国为无臣矣,故忽反顾而为之流涕也。[5]14a-14b
他从成“终一”的目的上认为“有男而无女则家不成,有君而无臣则国不立”,对“人臣之义”的理论价值自有认识,对其践履极为重视,认为君臣应各守其道,不应僭越无理。对“保厥美以骄傲兮”一节,他认为“怙其势宠”是人臣无德表现,而“恃其色美”则是人臣无礼表现。望溪认为为官秉持廉洁之道和德行操守为“人臣之义”所应有,解释“朝饮木兰之坠露”四句时云:“此自喻居官之清洁也。以贪官喻众之污,故以饮露餐英喻己之洁,情姱练要,则修名可立,虽庸颔无伤也”[5]4b。望溪主张“擘木根以结蓝”四句比喻“当官守道审固而不可摇夺”,而“擘”、“贯”、“矫”、“索”等动词连用“皆坚持固揽之义,《九章》所谓重仁袭义也”,在解释“謇吾法夫前修”四句时又云:“当官而洁清守道,所以法前修也。治前修自不得同世俗之所服,非世俗之所服自不合于今人”[5]5a。以上这些阐释,方氏反复申明做官要坚持清廉的品质,反对贪婪;要坚守仁义的信念,不要动摇;要抱定守死善道的决心,不要与世俗混同、随波逐流,这些解释未必尽合屈子本心,却折射出方氏对于《离骚》大义的诠释和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王逸、王夫之等学人已于《离骚》阐释中建构起“屈原、君王、贤臣”的论述体系,但从立论依据到文本细节都存在不可弥合矛盾,而望溪以“人臣之义”为核心诠解体系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种不一致*“‘求女’之义,王逸解为求贤臣,朱熹解为求贤君,两者都有一批跟从之学者,方苞此处解为“亲臣重臣能为己解于君者”,实即以后胡文英所言之通君侧之人,此为有创见之解释。方氏如此解后,其下求女之各方面解来亦通达有理。”(参见潘啸龙,毛庆主编:《楚辞著作提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诚然,论证望溪诠解体系的特色和价值并不是本文重点所在,笔者所关注的是这种以“人臣之义”为核心诠释体系思想基础,实际上,它与望溪重名节、尚理学思想渊薮相辅相成。
望溪年少时即与明末遗老交往甚多:“仆少所交游,多楚越遗民”[3]174。楚越遗民多为由明入清的士大夫群体,易代之际,他们坚守气节,隐姓埋名,不肯出仕,并在当时享有极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流风所及,这些“至诚恻怛,忠孝节义”的君子[9]自然也是年轻的方望溪和同时代人所敬仰的对象。无论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时代巨子,还是方以智、钱澄之、方文、黄冈二杜( 杜浚、杜齐) 等复社名流,明亡后都尽守“人臣之义”而拒绝与满清朝廷合作,表现出很高的民族气节。望溪与这些前贤或前贤弟子基本都有交往,或主动拜谒,或心向往之,这其中,他们高洁的立节制行自然会影响望溪对君臣大义的认知。《再与刘拙修》一文中,望溪对背弃君父的变节行为大加鞭挞:
汉代儒者所得于经甚浅,而行身皆有法度,遭变抵节,百折而其志必伸。魏晋以后,工文章垂声于世者众矣;然叩其私行不若臧获之庸谨者,少遇变故,背君父而弃名节,若唾溺然。[3]175
从望溪对汉末士人行身法度表彰中,可以看出他对忠义的尊崇。另外,望溪还于《光禄卿吕公慕志铭》、《断截红尘图》、《书杨维斗先生传后》等追念前贤文章中盛推先辈忠于君王人品气节,这都说明方苞对忠孝气节推重。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同宗同源的关系,明末遗老的气节持守与宋儒理学的要义在一定程度上亦是相切合的。顺、康时期,随着政治逐渐稳定,清统治者开始大力提倡义理之学,以图恢复和弘扬程朱理学思想体系,稳固满族政权统治,于是程朱理学重新占据历史舞台,宋儒论学核心特质即奉持纲纪伦常士大夫精神,明守君臣节义行为操守也随之得到最高统治者认可,由于这种理学思想提倡体现的是帝王意志和国家行为,所以在当时和后世均具有极大的影响,广大文人士大夫莫不顺风承旨,由此开启清初尊奉忠孝气节新风尚。与朝廷尊奉理学一致,望溪自二十四岁入京之后即确立“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10]的人生信条,君臣大义自然熟稔于心。因此,就“人臣之义”而言,望溪是一以贯之并始终奉行,这正是望溪诠解《离骚》思想基础。
当然,除却思想信仰的修持,以“人臣之义”为中心诠解体系还具有较强现实针对性,与望溪所经历文字狱浩劫以及晚年任职朝堂时步履蹒跚政治场域相关联*关于《离骚正义》的创作年代,至今无确切时间,清代学者苏惇元《望溪年谱》曰:“所著《离骚正义》,不知其撰着年月。”姜亮夫先生《楚辞书目五种》和饶宗颐先生《楚辞书录》亦无记载,但《离骚正义》第一页正文引用了李光地《离骚经九歌解义》,此书最早刻本为康熙五十七年,因此望溪《离骚正义》应作于康熙五十七年之后。。“《南山集》案”后,涉案友人几乎被斩杀殆尽,而望溪却得到名臣李光地营救并最终被康熙帝赦免,心有余悸真实心态以及感激圣朝的应合心理客观上对《离骚正义》“人臣之义”书写起到助推作用。《离骚正义》中“人臣之义”的诉说在一定程度上既是方望溪经历人生变故后对朝廷的一种态度,亦是其身处高位的自觉思考,它所呈现忠孝面貌与“《南山集》案”中的僭越不忠似乎有所不同。
三、“明于体要”:《离骚正义》意脉贯通与望溪之“法”
《离骚正义》之所以在《离骚》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固然可以归因于该书在诠释角度和内容上具有新颖亮点,但同时也与其行文体例相关,而这种体例形成无疑与望溪“义法”关系密切。清初统治者承用“清”、“真”、“雅正”这些传统审美性概念,并使之凝结为一个固定概念,以此作为科场衡文标准。由于统治者积极宣扬,朝臣和士子们积极响应,“清真雅正”审美概念很快由时文领域延伸至诗歌、古文、辞赋等文体领域,望溪“义法”正是这种审美风尚典型代表[11]。关于“义法”内涵,望溪释曰:“古人叙事,或顺或逆、或前或后,皆义不得不然”[12]。既然“义”与“法”彼此混融,不可强分,那么从结构方面探寻深隐之“义”自然顺理成章,无可厚非。
《离骚正义》注重从屈骚结构和文脉贯通的角度疏通文义,各节注解在宣屈原之幽怨、阐《离骚》之文脉时皆以“义法”为准绳,常常切中肯綮,令人会心,如“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一节,方氏云:
欲君之弃秽,故下言三后之用众芳,欲导君以先路,故陈尧舜之尊道,桀纣之囧步,邪径之幽险。忧皇舆之倾拜,而奔走先后,以及前王之踵武,皆所谓导以先路也。[5]2a
另如“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一节: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孰有称予之美于嗣君者乎?前云世溷浊而不分,好蔽美而嫉妒,道其已然也;此则虑其将然,而其后卒如所料。故矢死于怀王之时,而终致命于顷襄王之世也。[5]17a-17b
望溪申述文义时强调前后文义串联,上述二例中“欲……故……”以及“前……后……”句式结构是“义法”呈现典型范式。再如,对于“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望溪曰:“四句总结上文”[5]17b。至于“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县之遗则”,望溪曰:“自首至此,皆正言己意,以后则言之不足而长言之,长言之不足而嗟叹之也”[5]5a-5b;对“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望溪曰:“盖拟度及此,而非实有其事也。若曰吾欲使鸩为媒,则必告余以不好矣。鸩之佻巧又不可信,无人可以自通,故下承以欲自适而不可也”[5]16a;另如“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一节,望溪曰:“上言欲少留灵琐,虽被竦而犹得至于君所,故欲少留也。至是则闲阖不开,思见君而不再得矣”[5]13b。上述文例皆是从结构和行文体例方面对屈骚文义进行疏通阐释,明白而直接。由于望溪注重从内在“法”推寻隐藏“义”,并着意阐释结构前后贯通一致,故其诠解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征实可信和圆通畅达之特质,并使得《离骚》某些原本含混不清、次序难明问题引刃而解。
另外,不落科举义例和桐城评点繁琐窠臼亦是《离骚正义》特色之一,而这与“雅洁”审美艺术标准密切相关。关于“雅”内涵,望溪概之曰:“唐臣韩愈有言:‘文无难易,惟其是耳’;李翱又云:‘创者造言,各不相师’,而其归则一,即愈所谓是也。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即翱所谓造言也。’”[3]581要求文章合于自然,文从字顺、纯净古雅,理得要旨。关于“洁”,望溪曰:“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辞不杂,其气体为最洁耳”[3]55,认为“明于体要”是“洁”最高境界,“体要”*“体要”一语出自于《尚书·毕命》,其曰:“趣完具而已之谓体,众体所会之谓要”,《集说》引夏氏馔曰:“体则具于理而无不足,要则简而不至于余,谓辞理足而简约也。”又引王氏樵曰:“趣谓辞之旨趣,趣不完具则未能达意,而理未明,趣完具而不已则为枝辞衍说,皆不可谓之体。”《序志》篇:“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由此可见,“体要”就是在辞理表达完整的基础上崇尚简约。见(南朝·梁)刘勰著,詹瑛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就是要“所载之辞不杂”,行文简要而精核。“雅洁”是“义法”在文章体式和语言上体现及必然要求,《离骚正义》于此获益良多。
《离骚》之所以让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学者皓首穷究,除却经典深刻性之外,兴寄繁复,晦涩难懂也是重要缘由之一。自朱熹解读《楚辞》以来,注家益多,对于林林总总不能明屈子之心注疏,明代学者王世贞就已大声疾呼:“所以总杂重复,兴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恻怛深至,不暇致铨,亦故乱其绪”[13]。由于《离骚》一文中隐喻应接不暇,种类繁多,如果各以寄托,容易隔离文义,出现前后语意不一致甚至矛盾情况,然《离骚正义》却于“所载之事不杂”方面独具匠心。虽然屈骚端绪繁多,但望溪比兴对象指涉较为统一,统以君臣为中心,并自始至终一以贯之,较为清晰地阐明《离骚》幽微隐约之忧心。《离骚正义》由“众女”想到“谗邪”,由“求下女”想到“求亲臣重臣”,由“保厥美”想到“以色言之,为怙其势宠之人”,由“瑶台之佚女”、“宓妃”想到“王之亲睚或故旧之臣”,至于“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方氏则释曰:“少康喻君之嗣子也。帝阍既不可呌,左右莫肯为言;欲远逝以自疏,而又无可讬足。故欲浮游逍遥,以有待于嗣君。嗣君未与邪佞相合,或尚能亲忠直,如少康未有室家之时,庶或留有虞之二姚也”[5]16b-17a。望溪用“贯一”作为拯乱之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因比兴寄托繁复而割裂文义以及文辞芜累现象,使得前后文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离骚正义》不仅结构上明于体要,而且语言上也着意于雅洁自然。尽管《离骚正义》也存在个别近俗伤繁诠解,但那些简明雅洁, 文通义顺的阐释才是方望溪着笔最多的,也是《离骚正义》最大特色之一。方氏在阐释文义的同时,十分注意文章“雅洁”,故阐释大义常能通顺明了,易懂易诵。如“阽余身之危死兮”以下四句,望溪释曰:“秉义服善而不求苟合于世,吾之初心也。以是而阽于危死,何悔之有。枘喻己之操,凿喻君之度也。不量君之度而惟正己之操,持方枘以内圆凿,前修因以是殖醢矣。既法前修,焉能辞世患哉?”[5]11a简洁畅达,让人一目了然。再如“屈心而抑志兮”以下四句,释之曰:“内则屈己之心志,外则忍人之尤诟,而终不悔者,良以伏清白以死直,乃前圣之所厚也。前言亦余心之所善,虽九死犹未悔,问之己心而以为安也;此则质诸前圣而无所疑,其所以处死者,盖审矣”[5]7b,将“伏清白以死直”与前“九死未悔”联系起来,叙述自然晓畅,易于理解。
总之,《离骚正义》以“人臣之义”为核心要义的思想表达与望溪对“义”的持守以及其对当时社会思考和态度相辅相成,虽然未必尽合屈子本意,但所言却自成体系。而《离骚正义》注重从文章体例和结构推寻大义, 推崇“明于体要”诠解方式则又与望溪之“法”相互钩连。由于《离骚正义》从内在“法”推寻隐藏“义”,故其阐释征实可信;由于《离骚正义》明于体要,故其阐释能摆落繁琐窠臼而直达屈子的艺术之心。
[参考文献]
[1] 梅冲.楚辞经解:卷首[M].刻本.1815(清嘉庆二十年).
[2] 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M].北京:中华书局,1961:130.
[3] 方苞.方苞集[M]. 刘季高,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 钱澄之.屈诂[M].刻本.1864(清同治三年).
[5] 方苞.离骚正义 [M].嫏嬛阁刻本.1898(清光绪二十四年).
[6] 游国恩.离骚纂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480.
[7]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270.
[8] 朱熹.楚辞集注[M]. 蒋立甫,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9] 钱穆.中国思想史论丛[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2.
[10] 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四[M]. 刻本.1894(清光绪二十年).
[11] 参见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M].北京:三联书店,2007:265-275.
[12] 方苞.左传义法[M]. 王兆符,传述.台北:广文书局,1977:9.
[13] 王世贞.艺苑卮言:增补卷一[M]. 樵云书舍刻本.1589(明万历十七年).
[责任编辑:林漫宙]
[收稿日期]2015-11-26
[作者简介] 许光(1987-) ,男,安徽滁州人,南京大学中文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散文史及清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16)03-0069-06
LiSaoZhengYiand Wangxi’s “Principles of Writing with Concrete Things and Logic”
XU Gua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Li Sao Zheng Yi is an indispensable works with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Li Sao, whose construction of charm relates to the “principles of writing” proposed by Fang Pao. The expression of thought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officials” as the core exists effectively with Wangxi’s insistence of the “Yi”, namely writing with concrete things, as well as his thought and attitudes towards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In the meantime, his stress on the inference of key principles from the style and structure of the article, along with his emphasis on the interpretive way of “explicitness out of the outline”, displays the aesthetic purport of literature identical to Wangxi’s “Fa”, namely writing with logic.
Key words:Li Sao Zheng Yi; Fang Pao; “principle of the official”; “principle of writing with concrete things and lo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