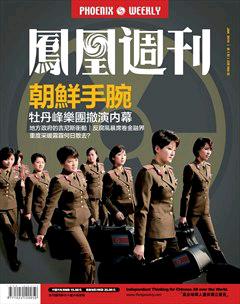迈向治理型法治
王锡锌
身处我们今天所在的时空,法治并不陌生。无论是在媒体头条,还是官方公文,或知识界的对话以及大众的呐喊中,法治都是当之无愧的关键词。不过,稍加观察不难发现,在“依法治X”的形式之外,依然存在法治的形式与内核的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已经说了什么,而是需要做些什么;不是要不要搞法治,而是要搞什么样的法治。
大陆的传统法治是一种“管理型法治”或者说“管理型法制”,特征主要表现为行政机关单方面对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事务的管理和控制成为法的内核。“依法而治”或“以法而治”,主要都是围绕行政管理及控制这一根本目标的外在形式。相应地,这种行政法治以管理者为中心,以便利管理者单方面管控为目标。“管理型法”在形式上往往就表现为“XX管理法”,比如《土地管理法》《自然资源管理法》《户籍管理条例》《城市养犬管理办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等等;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法律规则及其构成的体系,在功能上主要是实现对社会中人和事的单方面管理和控制。
无论称其为“法制”或“法治”,其核心在于“以法而治”,而非“通过法律的共同治理”——这就导致了管理型法治与现代政府治理之间的内在紧张。现代政府治理的基本要求是:面向公共问题,通过政府、市场、社会、个人等利益主体的合作,寻求并实现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这里必须注意,市场、社会及个人是解决问题的主体,而不是问题本身。作为管理和规制者的政府当然是面对问题的主要主体,但并非唯一主体。“管理型法治”的最大问题,就是在一些情况下将提出问题的人当作了问题本身。这种法治模式在实践中已经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比如在此起彼伏的PX事件以及其他形式的“中国式邻避困境”、群体性事件处理等领域,虽然我们也试图以“法治方式”来应对,但由于管理型法治内在的缺陷,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合作治理型法治的展开
正因此,如同中国的经济一样,国家的行政法治建设也需要一次升级转型,即由过去以政府管控为核心功能的“管理型法治”形态向“合作治理型法治”转型升级。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要旨的“合作治理型法治”,应该成为法治新常态。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法治新常态正在不断展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四中全会又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改革部署。就其内部逻辑看,四中全会所提出的法治,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法治应该成为推进现代国家治理的路径,而不是强化过往单向度管理模式的手段。这一共识应该成为法治新常态建设的根本逻辑。
在政府法治改革的实践层面,由管理型法治向合作治理型法治的变迁在几个重要方面已经初步展开。
第一是政府职能优化的改革。“依法行政”往往强调政府依法进行管理,但依法管理的前提问题是政府是否需要干预和管理。政府职能的合理界定是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如果在职能上政府不应该管,即便依法去管,也会与现代政府治理的目标南辕北辙。现代政府的治理需要在合理界定政府、市场、社会、个人的基础上,通过多元主体的合作,共同解决问题。近几年来,政府转变职能的改革有了进一步推进,主要表现为行政许可制度和非许可审批制度改革,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等一系列“清单式管理”。这一领域的改革旨在反思过去管理型体制当中“无限责任公司”式的政府模式,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使政府职能真正体现“放”与“管”的结合,从而激活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活力。这一过程是政府职能“瘦身”的过程,也是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充权”的过程。政府职能的优化是推进多元合作治理的前提,是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结构现代化的基础。
第二是合作治理程序框架的改革。政府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合作共治,不仅需要主体的充权,而且需要改造行政法治的程序和技术。公共问题的解决,如环境治理、邻避困境等等,涉及到政府、市场、社会、个人等多元主体利益,因此需要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才能获得解决方案。作为合作治理的法治框架,应当引入“参与式治理”,超越过往“管控型”模式的弊端。在过去一段时间,政府法治改革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表现为在重大行政决策、行政立法、环境治理、食品治理、基层治理等等领域开始重视并尝试参与程序的改进。比如,2015年初实施的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一个重要的改进就是将公众参与作为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机制。同时,在环境保护等领域已经尝试的公益诉讼、包括公益行政诉讼,将为社会中的利益相关者、社会组织提供一个参与公共问题治理的重要程序平台。
第三是行政管理体制和技术改革。从治理的要求看,法治改革的实体目标是推进公共治理的结构体系优化。在这一过程中,行政管理体制的改进既包括结构性改进,也包括技术性改进。结构性改进主要是指不同主体间关系的改进。包括纵向和横向府际关系,以及政府、专家、大众、个人之间的关系重构。比如,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治理当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县、乡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如何实现管理体制所追求的“统一性”与现实治理所面对问题的多样性之间的平衡,是体制改革的核心。管理体制改革还必然涉及到政府、专家、大众、个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行政立法、政府规制、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如何在议程设定、话语、决策等环节充实专家、大众、个人的知情、表达、参与、监督等权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也是当前行政法治改革的关键。
第四是透明度改革。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治理,需要主体间的信任、有效的利益表达、理性的协商妥协和共识构造,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及时、充分的信息公开。透明度既是公共治理的要求,也是当今政府法治的核心。自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信息公开的实践已经并不断重塑行政法治的地形图。特别是在财政体制改革、行政立法、行政决策、审批制度改革、市场秩序维护、环境污染治理、突发事件应对、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冲突管理等领域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信息公开实践所带来的治理和法治红利,已成为合作治理型法治建设的主要增量来源。
第五是责任机制的改革。行政法治领域责任机制的改革目标在实体上要求权责对应、权责统一;在形式上则要求法律责任的法律化。就前一个方面而言,无论是在行政决策领域和立法、执法领域,还是行政裁决领域,都开始不断强调权责法定、权责相应;并通过决策的终身问责、行政执法责任制等机制来落实责任。在责任机制的改进领域,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案件登记制、受案范围扩展、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司法审查广度强度等方面的改革,行政权力责任的制度化、程序化、外部化追责机制进一步发展。在责任机制的形式方面,责任追究的政治化虽依然是一个突出问题,比如信访指标考核,问责机制的过度内部化、政治化,但这方面的改革共识正在强化,相应的改革措施也正在部署之中
政府法治建设的新思维
行政法治新常态的建设,需要我们超越工具型法治和管理型法治的陷阱,将法治的新衣与现代治理的内核结合起来,将参与、透明、责任等治理的关键要素融入法治体系当中。
在将来,面向治理的行政法治改革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的统一。
第一是法治与改革的统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实际上为法治改革提出了根本方向,那就是变法必须符合变革的需求。法治改革不应无的放矢,为法治而法治,而应当面对改革的现实需求。比如互联网+带来的新兴产业,必然带来利益的调整,这既是改革问题,也是法律问题。改革需要通过法律来实现,但首先需要有重构利益格局的勇气,否则就会出现以保障法治为名而拒绝改革或者使改革成为重申既得利益格局的法律游戏。法治应保障改革的速度,防止改革进程久拖不决,错失改革时机;法治应保障改革的力度,防止选择性改革,防止改革雷声大雨点小;法治应保障改革的温度,平衡制度转型过程中新旧利益格局的衔接过渡,避免“零和博弈”。
第二是法治与治理的关系。政府法治的未来发展必须以推进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为目标,穿越观念、利益、现实的重重迷雾,不忘初心。在这个意义上,今天行政法治改革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政府自身改革的问题,特别是政府职能改革、许可审批制度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基层治理,特别是县乡治理的“本地化”改革。
最后,需要处理好法治与政治的关系。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治理中,需要考虑宏观统一性与微观多样性的平衡。治理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底层创新。顶层设计主要考虑制度基本的统一性,底层创新主要回应地方面对的多样化问题。应当注意到,宏观和微观治理的混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地方治理创新的活力。就改革推动力而言,中国的治理改革和法治改革因为传统的路径依赖,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这当然有其背景和优势,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动员、自我变革的推动力,往往面临在时间维度上递减的困境。因此,改革的进一步推进,需要新的动力来源。这个新的动力源就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也就是通过市场、社会、公众等市场和社会力量的组织化和有效参与,推动治理转型和法治新常态的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