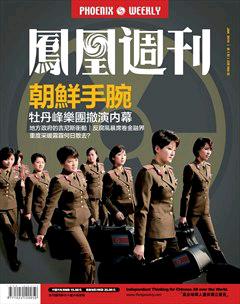《慈善法》:内地开门立法典范
杨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事业促进法》(下称《慈善法》)十年长跑,一朝提速。2005年,民政部正式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提出起草《慈善法》的立法建议。2009年,民政部将《慈善法》草案上报国务院。此后,慈善法的立法进程一度搁置,总是“排不上队”。
2014年2月24日,《慈善法》的立法进程迎来转机,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召开慈善事业立法领导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列出立法时间表和路线图。2015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慈善法》草案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尽管目前的《慈善法》草案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讨论,不得不说,如今的《慈善法》吸纳了不少民间意见,与我们当时的悲观预计相比,已是天差地别。
此次立法过程中,民间发挥了超出以往的热情。2014年以来,来自不同民间机构的《慈善法》建议稿共七个版本,在这一年针对慈善立法的民间研讨会也有十余场。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也在短短一年时间内,积极吸收民间意见,立法效率很高。可以说,《慈善法》是内地开门立法的典范。
慈善组织外延扩大
2014年,在各方争议下久拖不立的《慈善法》突然走上快车道。而此次全国人大开门立法,吸收民间智慧,也是慈善立法最终能在2014年得以迅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过去的立法是先经由行政部门拟定草案,再提交国务院法制办,然后经人大审议,步骤冗长。此次《慈善法》由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导立法,仅用一年的时间即提请审议,效率提高了很多。未来的立法,政府行政部门都不要参与比较好,因为即使行政部门对相关的行业较为了解,但其在立法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考虑自身利益。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在立法伊始对慈善领域了解有限,但能在起草阶段秉持虚心和开放态度。另一方面,出于对与自己息息相关法律的关心,民间也积极提供意见,与立法部门保持良性沟通。目前的这个草案版本,是吸收了民间智慧的结果,尽管仍有很多问题,但已经超出预期。
此次《慈善法》实际上让慈善组织没有了“主管部门”,只存在民政部这个“监督部门”。民政部的职责就是慈善组织的登记和监管。对于民政部来说,这不是“削权”而是“统权”。
过去,成立慈善组织既需要找到业务主管部门,也需要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实行双重管理体制。而如今慈善法推行的是“大慈善”理念,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事业的发展,都可以被定义为慈善,只需依法在民政部申请登记即可。依照慈善法草案规定,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
尽管未来民政部能否良好地执行,是一个待考的问题,但以法律而言,成为“慈善组织”的标准宽泛了,慈善的大门打开了。
此次草案中专门列出“慈善信托”一章,使企业不仅能以捐赠的方式,还能以信托的方式为慈善事业积累资金。比如有理财公司将客户投资利息的一部分聚合起来为农民做公益性的小额贷款,这样的行为活化了慈善的形式,也即将获得法律的认可。
草案还有一个重大的立法亮点:“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的非营利组织即使没有登记,也可以开展力所能及的慈善活动,但应当遵守本法相关规定,并依法享受相关权益。”
这实际上是一条开放性的条款,让很多愿意做慈善的人找到了法律支持。据我们的估算,目前中国登记的慈善组织为60万左右,而没有登记的非营利组织约在2000万以上。在中国有很多企业、社区都有一些没有登记的组织,大家为了一个慈善目的聚在一起,做完事情就散掉。这些组织其实真的无需登记,却也真的柔化了我们的社会。
相对而言,这也是一条表述模糊的法条。类如“宗教”这类在立法期间就因过于敏感而无法明确在列的慈善组织类别,最终也可以援引这一法条进行一些慈善活动。但关于中国的慈善组织如何到境外开展慈善活动,以及境外的慈善组织在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草案中没有体现。
慈善活动需分层定义
草案针对公募权的开放引发争议。根据草案规定,依法登记满两年、运作规范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原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证书。这实际上是开放了公募权。在过去只有公募基金会享有向不特定公众进行公开募捐的资格,而现在,非公募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形式,只要满足相关的条件,也可以申请公开募款的资格。
但草案同时规定“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采取公开募捐方式开展公开募捐”,这一条款引发很多不同意见,很多人认为,个人通过互联网筹集资金,是无法被限制的,也不应被限制。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争议,是因为草案没有对慈善活动进行分层定义——区分组织和个人。慈善立法的目的就是要鼓励大家都来行善,无论是帮助自己熟悉的人,还是为不特定的公众服务,都是需要在法律政策上给予鼓励的。比如,为一个白血病患儿捐款,或者为专门帮助白血病儿童的慈善组织捐款,两者虽然都叫做慈善活动,但对二者的规制又应有所区别。
《慈善法》的规制对象应该是组织,包括未登记注册的组织,而非个人。对于针对不特定公众的募捐,要给予他们“公募权”,而不具备公募资格的组织和个人,只要不是采取“公开募捐”设定的几种方法(如设置募捐箱、义演、筹办慈善晚会等),就应允许其存在。
对慈善活动进行分层定义的意义是,让每一个慈善活动的主体在法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我们要倡导的,是更广博概念的慈善活动,要让慈善行为辐射到更多非特定的大多数人。
应进一步明确政府与慈善的界限
2014年以前,我对《慈善法》一直持悲观态度。对于“慈善到底是什么”、“慈善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慈善与市场的关系”这样的基本问题,我们都没有厘清,何谈立法呢?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激发了全民慈善的热潮,被称为中国的慈善元年。这一年至今是中国建国以来社会捐赠总额最高的一年——1070亿元,几乎是人人捐款。但在实际上慈善究竟应该如何运作,老百姓搞不清楚,政府更搞不清楚,只是将慈善视为政府功能的补充——将慈善捐款划归为自身的财政规划,把民间慈善的资金装进政府的“钱袋子”。
到2010年玉树地震时,情况更加严重,民政部会同五部委发布《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其中规定,慈善组织募集的善款需要汇缴拨付到青海省政府、青海省红十字会、青海省慈善总会的专用账户中,由青海省方面统筹安排使用。这从理念、做法到组织方式上,都是没有划清政府与慈善边界的表现。
在可从慈善募捐获利的前提下,政府怎会有立法限定自身与慈善界限的动因呢?这样做的确可以在早期为政府带来不少效益,但显然不利于慈善事业的长远发展。
此次慈善立法在这方面有明显进步。草案所称“开展募捐活动,不得摊派或者变相摊派,不得妨碍公共秩序、企业生产及人民生活”的监督主体,应该是指政府部门。“向单位或者个人摊派或者变相摊派”将受到民政部门的警告,并停止募捐活动。
谁有向单位摊派的权力呢?只有政府。有了表意,却在法条上的表述比较模糊。未来,如果还有政府部门将慈善捐赠划入政府财政,我们是可以援引这一条法律进行反对的。这或许是立法者的一种智慧。
但我仍希望立法中进一步明确政府与慈善的界限。慈善是独立的、民间的,不应隶属于任何政府机构。对于民间来说,法无禁止就可行;对于政府来说,法无规定不可禁。政府要厘清自己的职责,不要越位。推动慈善组织在社会的平台上公平竞争、重组、整合,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这一点仍是我对《慈善法》未来实施最担心的地方。目前有很多慈善基金会实际就是地方政府自己成立的,如何规制仍然是个问题。法条已立,监管摊派募款的民政部能否坚定地执行,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