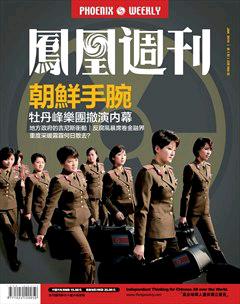导演徐皓峰:用电影还原真实的武林
刘荣
三年时间,导演徐皓峰誉满江湖。这一天,在北京电影学院,一个小时后是《师父》电影座谈会,他一边飞快地给新书《坐看重围》签名,一边竖起耳朵听我提问,已顾不得吃饭。
“白发怎么又多了?”我问,上次见面是《一代宗师》上映后,徐皓峰华发初生,彼时,他说满打满算,只剩20年黄金时间搞创作,要分秒必争。今日,他顺势幽了一默,“白发说明血热,我还是少年。”说着把茶杯往我面前客气地一让,手势干净利落,像练家子。
人:文武徐皓峰
徐皓峰习武。坊间传说,某次饭局后,他和一个习武的朋友抢着埋单,双方都下意识地把手探到对方腋下。又传,一山东哥们儿找他认同门师兄弟,他伸手就摸那人小腿,练没练过形意门功夫,要先验小腿肌肉。更有神乎其神的,说他气功护体,五层楼跳下,没事。对这些传说,他神秘一笑,不置可否。
他的武脉,靠文脉来接。他曾闭门八年写作,前后出过十本书,都在武术、武德、武林和武行上用力,包括《大日坛城》《道士下山》《武士会》和电影《师父》的短篇原著,皆为故事好看,人物饱满,儒、释、道兼收。他还参办过一本杂志,最后一期的主题叫《最后的妖精》。于是作家圈子里的格非嘀咕说,“这人怎么什么都懂?”
十年前,他刚出版《逝去的武林》,武术界笑话他,你当真练过吗?后来,他给王家卫《一代宗师》当武术指导,打得连大武指袁和平都叫好,还连拍三部武行电影《箭士柳白猿》《倭寇的踪迹》《师父》。也许是成败论英雄,后来,江湖认他了。形意门收徒弟,师父们先拿他写的《逝去的武林》当见面礼。
2015年12月10日,我在电影院看完《师父》最后一个镜头,听见身后的一对情侣说,听说打戏都是导演干的,他威武,长得像“魔鬼肌肉男”。我看了看眼前的徐皓峰,他实在与想象相去甚远——发福,圆鼻头,皮肤滑润,眼睛笑成一条缝,过于慈祥——他是好友眼中宠辱不惊的南极仙翁、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心目中的大神。
徐皓峰懂电影,乃电影学院导演系科班出身。毕业8年后,老师请他重归母校,教授大课《试听语言》。他写的一本武术电影影评《刀与星辰》也颇受好评。身份种种,作家、导演、武术指导都是他,但每次上课,还得老老实实应学生的一声呼唤“徐皓峰老师”。至于那帮被大师徐克、胡金铨们熏陶得无比挑剔的学生,搜集了他上课的百条金句,发上网络,引为美谈。

道:刀背藏儒道
八年前的正月,我首次采访徐皓峰,他带来了一本书《逝去的武林》。
书里带出了一个清末民国初年的武林,这基于他为《武魂》杂志数年如一日的采写整理。这个武林里,囊括了京津冀一带有史可考的传人们,包括八卦掌、形意门、太极等诸多门派,他们有规矩,有传承,有故事。其中,他的二姥爷李仲轩就是这部口述史的活见证。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徐皓峰惊动了白岩松、崔永元等传媒大咖。这事儿的直接影响是,徐皓峰生生把已成模式十几年的港台武侠电影,逼成了“想象中的武侠”,而他自己另辟了一条“硬派武术”电影之路。
交谈中,徐皓峰好用手势。他在我面前比划出一个阴阳太极鱼般的“圆弧”,好似一切矛盾都是合理存在的,天然圆融。“武林人有了,那什么是武道?”他笑眯眯地看着你,笑容里没有侵犯性。这个潜心钻研传统冷兵器,能让刀、枪、箭成为自己电影焦点的男人,告诉你——武道的核心是“止戈为武”。
溯源到大院子弟徐皓峰的少年生涯。生于1973年的他,初习武艺是在15岁,“当时,老北京世风开始变痞。”那时候,李连杰的《少林寺》已经有了,《上海滩》的引入带来了黑帮情结。记忆里,一代年轻人的青春期荷尔蒙无处释放,于是学校里分帮结派,打群架。徐皓峰也被人唤过“大哥大”。对此,他另有看法,“文革武斗,把世情变得粗鄙无礼”,他眼中的小马哥,却是个盗亦有道、受过文明洗礼的绅士。徐皓峰喜欢老北京文化“有理有面儿”,于是,移情到海派黑帮身上,觉得那是“儒”的精神。
所以,他不混江湖,跟着二姥爷李仲轩学武术。李仲轩也是个奇人,得了形意拳大师唐维禄、尚云祥的真传。34岁突然从武林退隐,晚年在西单一家电器商场看门。
李仲轩的隐,是“道”的精神。徐皓峰少年时代与另一位道教宗师胡海牙的接触,同样影响至大。毕业十年,徐皓峰也迷茫落魄过。人事磨炼,他修出了坐看“山河大地,万古星辰”的一颗闲心。他在《刀与星辰》中写到,“道家比儒家高明,儒家谈善恶,道家谈自然”。还索性出版了一本《道士下山》,露出说教的职业病,“道心原本宽广,可容万物”、“不择手段非豪杰,不改初衷真英雄”。
道心宽广,故东西文化也可相容。徐皓峰津津乐道一个太极拳传人的故事——一个71岁的中俄混血儿!真东西为何教了洋人?他自问自答,儒家也是这个道理,“有教无类。”
在电影《一代宗师》里,他用叶问的大半生,问了武人一个问题:“为什么越执着,越会为人所夺?”他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咏春的交手口诀,更是人事规律。
庄子要“齐物”,说的是道家的天人合一。而儒家求进取,也似武人的一生,被他放进了刀的意象里。刀背之下,可藏武人之身。他反复思考自己关起门来读过的金庸与梁羽生、庄子与孔孟。于是在《一代宗师》里,东北漫天大雪,宫家大弟子马三正要反出师门,宫老爷子出来替徐皓峰说话,武道与儒、道有什么关联呢?“刀有鞘,不是为了杀,是为了藏。”
术:武行电影课
《一代宗师》上映后,徐皓峰已趋不惑之年,武行电影三部曲正在陆续酝酿出品中。
大得声名,影响了他多少?“他是个有七分,只说三分的人。”他的朋友、编剧史航,在微信语音里给我留言说,徐皓峰并未改变初衷。
徐皓峰愿意说出来的“三分”,指的是中国武术电影的当下去留和推陈出新,到了箭在弦上的关头。
从《逝去的武林》开始,回望近代武术的源流,武术从生活走向戏曲,再走向书籍和电影,一百年已经过去。鼎盛多年的武侠电影正在衰落和转型期,作为一种商业类型片,在整体上已走向末路。港式的“飞天”和“炫技”手法已经无法满足越来越挑剔的受众,更在制作手段上远远输给好莱坞。
相比前两部小成本电影《箭士柳白猿》和《倭寇的踪迹》,《师父》是徐皓峰为武术电影“说话”的一次实践。它遵照了商业片制作模式,104分钟时长,有情感段落,有武术场面,廖凡、宋佳、蒋雯丽、金士杰,演员阵容颇为可观。
死守自己的“三分”,徐皓峰就有了风格。“我是用真实的武打,在电影里还原真实的武林和武行。”他在电影《师父》和电影笔记《坐看重围》里,变回了那个“徐皓峰老师”。
不论对方是影帝还是武替,他一拳一脚亲身传授,而且要求演员真打,连淑女蒋雯丽都在《师父》里动了手。此前,张震拍《一代宗师》,武术特训一年,成了半个高手。而廖凡在徐皓峰特训下,用两个月就出现了武者气象。“你可以打咏春了。”徐皓峰通知他。
史航读过徐皓峰所有的出版物后,评价他那没说出口的“七分”,“他想让你们看到,传统中国人是怎么做人的。武行人的分寸感在哪儿。”这做人的分寸感,包括规矩,对武道尊严,都来自徐皓峰对武林与武行的理解。
徐皓峰的小说和电影往往是对位关系。比如电影《一代宗师》和小说《武士道》。王家卫用三年时间遍访民间武林人士,发现了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清朝灭亡后的1912年,北方的武林人士企图建立中国武士道,统一北方武林,企图成为社会名流,以改变社会的性质,核心机构就叫中华武士会。于是,徐皓峰在《一代宗师》的剧本里说了个故事,中华武士会的第三代人何去何从?他们和南方的叶问有交集,叶问也延续了中华武士道的精神。而小说《武士会》是电影的前传,写的是中华武士会的第一代人。
后来,徐皓峰又用三部武行电影想要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行业有尊严,人以自己的职业为荣。要表现真正中国人的境界,职业必须成为载体。而所谓武行,必须以城市为基础,不同于民间的游侠和匪帮,是有固定职业生活的人,比如武馆、镖局。《一代宗师》中的大师群像,《师父》中的武行底层生态,都脱离不了这个真实的行业载体。
“我会写出具体行业的人际关系和运作规则。”他写武行和武林,小到规矩,大到阶层的命运,都在社会大环境里。他看到了近代一百年的战乱,如何促成又消解了武行这一阶层。“他们企图改变国民性,可惜只传了三代。”
徐皓峰在电影里还想上另一课——传统文化的去留。“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都在否定传统文化,中医被人瞧不起,武术是中国人保留传统的最后底线。”他在《一代宗师》里,用“天地、众生、自我”标注了武人和武术的三个境界。即使在探究人性复杂面的《师父》一片里,也给武德留了个余地。对规矩死不撒手的天津武行人士,最终想起了自己的武道和“士”风,放走了陈识,咏春拳最终得以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