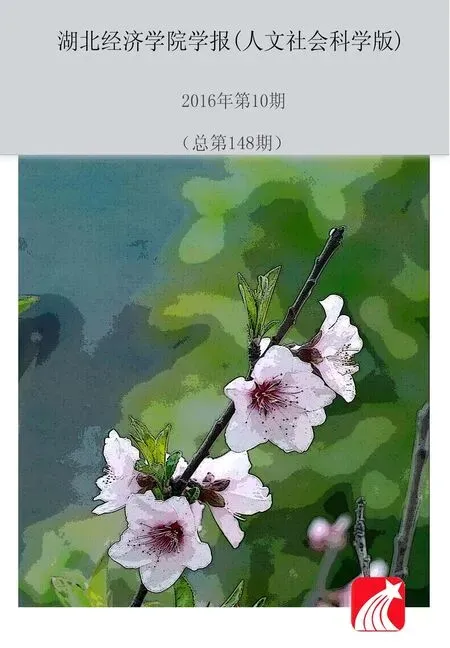论农村法治建设中的政府作为
曹益平
(中共益阳市委党校,湖南益阳413000)
论农村法治建设中的政府作为
曹益平
(中共益阳市委党校,湖南益阳413000)
以民主为核心内涵、以法治为基本方式的农村基层治理,既需要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和村级组织的自治功能得到全面发挥,更需要有一个能把握农村法治发展方向、裁断治理行为合法与否的权威机构来主导。作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的代表,基层政府是农村法治建设当然的主导者。其主导农村法治建设应以转变职能为前提,以规范基层执法为核心。
农村;法治建设;政府;作为
农村法治建设以涉农制度的法律化、基层执法的规范化、农村司法的权威化、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和农民权益保障的合法化为核心内容,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在农村社会的具体实践,也是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以民主为核心内涵、以法治为基本方式的农村基层治理,既需要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和村级组织的自治功能得到全面发挥,更需要有一个能把握农村法治发展方向、裁断治理行为合法与否的权威机构来主导。作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的代表,乡镇党委政府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动员能力,其特定的政治地位和掌握的国家权力使其成为农村法治建设最具有合法性基础和权威性势力的主导者。目前的乡镇行政工作中,经济的发展和上级政府交办的政治任务的完成是重心,对基层法治建设的推进被搁置,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主导作用推进农村法治建设成为亟需探讨的问题。
一、基层政府是农村法治建设的主导者
一般理性认为,农村法治建设似乎不存在主导方向的问题。然而,在现代农村社会,特别是农村偏远地区,农民群众不可能有很高的法律认知水平,他们对“法律”内涵和外延的把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笔者接触到的普通农民中,能区分法律与政策差异的并不多,能完整地界定法律内涵和特征的更少。
在笔者走访的一个中部欠发达地区的相对开放的农村,由于政府推动下土地流转加速、规模扩大,农民基于土地的各种利益诉求涌现,促使他们更多地了解法律的知识和方法,即便如此,他们对法律的认知仍然匮乏。据该镇政法书记讲述,农民在维权过程中,似乎懂得了很多法律,但是他们对法律的认识却很模糊,对关乎自身利益的个别法律条文,他们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可是他们自认为的“法律”依据却包括了法律、政策、文件、权威报纸文章、专家观点甚至网络言论。除此之外,农民对法律的认知还有较大的片面性,他们熟知对自己有利的条文,却不了解同一法律文本中对其权利给予限制的其它条文。由于对法律的内涵和外延把握不准,农民可能错误地将违背法律的行为视为合法维权,将非法的利益视为合法权利,基层干部很难严格依法处理矛盾纠纷。
正因如此,农村法治建设需要主导者,需要有权威的释法者。这个释法者最理想的应该是农村法庭的法官,他们却由于跨乡镇设置,农民很少接触,不具有群众基础。而公安派出所尽管每个乡镇都有,其干警却专注于办案,对《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对熟悉,对民法、土地流转法、侵权责任法、劳动法等其它法律接触较少,受自身法律水平局限,亦不适合释法。只有乡镇综治人员(包括司法所干部),与农民群众联系密切且一般都有一定的法律基础,熟知农村法律需求,有丰富的用法律解决矛盾纠纷的实践经验,堪当“释法者”。他们的释法能让农民群众逐渐了解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了解法律与政策的区别,了解其他观点、言论的不可适用性。由此,以乡镇综治人员为主体的一部分乡镇干部,在农村基层治理实践中能代表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建设的基本方向。
二、转变职能是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建设的前提
转变政府职能,让基层政府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主导属于隐形政绩的法治建设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基层政府在每个时期的职能定位和主要工作,决定了其在农村治理中的作用。“人民公社”体制下,国家权力深入“大队”,农村秩序稳定。“乡政村治”体制下,国家政权回撤到乡(镇)政府,村级实行民主“自治”,乡镇成为最基层的国家权力。“后税费时代”来临,地方政府职能发生转变,不再是单向从农村汲取资源,而是让国家各种资源回流到农村,实现城市对农村的支持,管制型政府开始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服务型政府理念支配下的乡镇,不再忙碌于催收“皇粮国税”,而是致力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发放惠农补贴,职能转变似乎已经到位,实则还有更多的职能不曾体现,有更多的农民需求未曾满足,推进农村社会的法治化治理,培育农民民主自治的能力,追求农村社会的“善治”,即是其中之一。
乡镇政府在整个国家政权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其重要性,也决定了其职能转变任务的艰巨性。县以上政府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进或者纯粹的上行下效,除涉及政府冗余人员安置外,更多的是各种机制和办事规则的执行。乡镇政府在国家权力体系结构中位于底层,直接联系农民,是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中间环节,任何孤立或单项的改革都很难取得实际性的成效。必须从农村社会治理的层面,进行至少包括市级(地级)、县级、乡(镇)级的机构改革,使乡镇一级政府彻底完成由“搜刮”体制向“服务”体制的过渡。要结合各地农村的实际情况,通过改革试点和实践创新,针对改革的制约因素和出现的问题、难点制定相应的措施。实践中,乡镇政府的机构改革应以实现乡镇政府职能由管制向服务转变为基本目标,合理设置乡镇内部各事业站所,明确站所职能和工作人员主要职责,完善运转机制。要按照因事设岗的原则,结合各个乡镇工作的实际情况,合理配置人员,做到既不弱化公共服务职能,又不增加行政成本,全面履行好政府职能。
戴维·奥斯本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指出:“(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治理和实行治理的政府。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这是一个治理的政府。”[1]基层政府职能的确定,要遵循“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原则,在“小政府,大社会”理念的指导下,凡是通过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凡是各类主体和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政府都应放手,除此之外的市场监管其它公共服务,政府则应积极作为。随着国家综合国力增强,农业税得以免征,乡镇职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钱”、要“粮”、要“命”的历史已经终结,相反,各项惠农政策不断推出,政府服务提上日程。积极推进乡镇职能转变应积极关注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基层政府的决策职能,乡镇政府应积极主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落实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进程,扎实推进国家农业农村政策在每一个村落的实施;二是基层政府的协调职能,农村基层是各种矛盾的集聚地,村落与国家、与社会、与市场的各种冲突以及村落内部的各种利益冲突都在农村社会的场域显现,基层政府应通过指导制定村落发展规划、优化经济发展目标、提高国家惠农资金利用效率等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三是基层政府的服务职能,政府的基本责任是营造“可预期的”公平正义的农村发展环境,政府的职能更多的是指导而非管制,更多的是服务而非控制,应在提供基础设施服务的基础上着手推进农村法治化治理的“软”服务;四是基层政府的管理职能,基层政府代表国家政权所行使的一系列职能不可能没有管理,其要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无疑需要有必要的法律和行政管理手段,比如市场监管,即需要政府由基本的法律手段和方式,对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应给予严惩,比如社会治安,对诸如寻衅滋事等违法行为的惩处也需要法律的方式。总体而言,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并非放弃管理,而是要寓管理于服务,在服务中追寻“善治”。
目前转变基层政府职能的核心内容有两项。一方面,严格规范县与乡镇之间的关系。应依法界定县(包括各职能部门)与乡(镇)两级政府的职权职责,逐步改变乡镇工作的被动执行状况,减轻乡镇的工作负担,使乡镇工作有更多的自主空间,真正做到权责一致。凡属上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该承担的职能,如无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得通过委托方式随意转移给基层政府,基层政府只应承担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职能;上级政府及其部门的工作确需基层政府配合、协助的,应明确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通过合法的途径赋予相应的办事权限,严厉禁止领导干部口头委托和赋权。另一方面,改革上级政府及部门对乡镇工作的考核机制。“官大一级”的传统观念使基层政府的工作时常面临否定性评价甚至被“一票否决”。对乡镇工作的绩效考核要改革“多头考核”的做法,原则上只能由一个部门组织综合实施。
三、规范执法是政府推动农村法治建设的核心
基层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有法律运行机制的不完善,有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更有执法者的基本素质的因素。通过严格公正文明的执法诠释法的精神和价值,让基层政府充当法治表率,是全面推进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现代行政法治要求乡镇干部要树立三个方面的理念。首先,乡镇干部要跳出权法之争,树立“法律至上”的权法观。在一个遵循法治的社会中,法的权威时不容置疑的。法本身是设定权力的一种载体,又是权力得以恰当运用的依据和保证,但是,当法之权威与领导者或者执法者不依法而为的行为相冲突时,要强调法的权威性。其次,乡镇干部要树立行政必须依法的理念。在政策、文件满天飞的农村基层,农民对法律缺乏基本的认知,往往将政策与法律混为一谈,将文件的效力视同法律,个别乡镇领导为实现所谓的农村“治理”,滥发文件,愚弄群众,甚至曲解法律和上级文件,使政府威信扫地。要推进农村的法治化治理必须强调政府的依法,必须让政府权力纳入法律规制的范畴。最后,乡镇干部要树立合理行政的理念。法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具有强制性的权威,更需要广大群众接受其公平、公正的基本理念。一些乡镇干部习惯于将亲情、熟人列为执法考虑的因素,相同事件不同处理,不同违法同等处罚,人为地以远近亲疏衡量处罚的严厉与宽松,尽管就单个案件而言可能没有超出法律授权的幅度和范围,但在多个执法行为的比较中,明显不合理。应通过严格执法程序和制定自由裁量权基准实现行政的合理性。
在乡镇政府行政决策和行政执法过程中要突出“程序正当”的原则。控制裁量性权力的方式就是建立程序性机制。[2]不仅仅是在农村,在整个我国的法律传统中,对实体公正的过度关注和对程序公正的相对忽视都是根深蒂固的。在乡镇政府行政决策和行政执法过程中,首先应考虑程序性问题。比如行政决策,没有民意的调查和公众的参与不能称之为“治理”,没有集体决策和合法性审查不能称之为“合法”。比如行政执法,没有履行相应的执法程序和告知义务,即使结果为民众所认可,亦不能称之为“合法”。应努力破除行政主体决策和执法过程中重结果轻过程的传统,赋予民众更多的程序性权力,让群众参与到政府行政中来。
[1][美]戴维·奥斯本.改革政府[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2]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