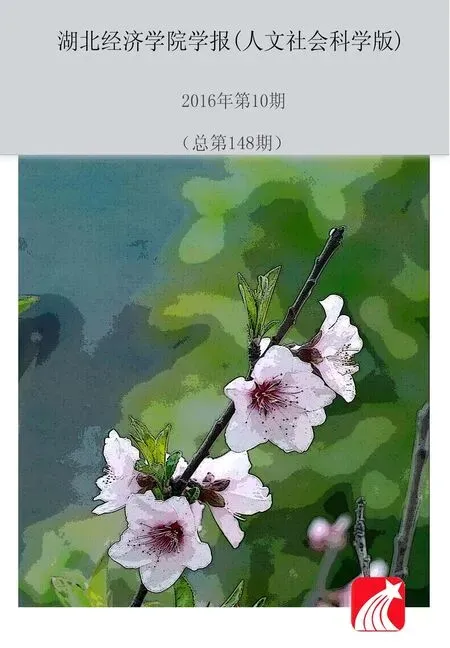《红字》中“刑台”的象征寓意与叙事功能
陈蓓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湖南长沙410205)
《红字》中“刑台”的象征寓意与叙事功能
陈蓓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湖南长沙410205)
《红字》是美国黑色浪漫主义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象征手法的运用是这部小说的特色之一。小说中的“刑台”不仅象征着“惩罚”与“审判”,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叙事功能。它所导引的叙事曲线与弗莱的U型结构模式高度契合,体现了牧师丁梅斯代尔“负罪而隐瞒-知罪而忏悔-获得救赎”的救赎之路;不仅如此,霍桑还借对刑台的描述,表达了他对当时北美殖民地政教合一的清教统治所持的批评态度,揭露了当时清教统治的严酷和违反人性。
《红字》;刑台;象征意义;U型结构
《红字》是美国十九世纪黑色浪漫主义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它讲述了发生在年轻美丽的女子海丝特·白兰与教士阿瑟·丁梅斯代尔之间的爱情悲剧。和霍桑的大多数作品一样,《红字》以清教统治下的北美殖民地为背景,以罪孽和邪恶作为故事的主题。象征手法的运用是这部小说的特色之一,在这部传世之作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比比皆是,比如女主人公佩戴的红字、狱门前盛开的野玫瑰、森林里的黑男人和精灵般的小珠儿。
霍桑在象征手法的运用上可谓独具匠心,其作品中的人与物往往具有多重象征寓意。以狱门边争妍竞放的野玫瑰为例,作者这样写道:“这丛野玫瑰由于某种奇妙的机缘,历尽劫难,而永葆生机。[1]”的确,在整部作品中,野玫瑰不仅寓意着美丽热情、饱经忧患而坚韧不拔的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也象征着人性倍受压抑的清教时代新英格兰漆黑土地上绽放的爱情之花和道德之花。然而,比之野玫瑰,小说中刑台的象征寓意来得更加丰富、更为深刻,更能够反映霍桑的宗教观。
一
与作为小说篇名的“红字”一样,“刑台”贯穿故事的始终。不一样的是,“红字”无处不在,而“刑台”则主要出现在小说的“市场”、“相认”、“牧师夜游”和“红字的显露”四个章节中,并有着与整个故事发展格局相吻合的象征意义。
刑台位于市场的西端,几乎就竖立在波士顿最早的教堂的屋檐下,像是教堂的附属建筑物。关于这个建筑物的作用,作者这样写道:“事实上,这个刑台是整个惩罚机器的一部分……这个用木与铁制造的刑具充分体现了要让人蒙辱示众的思想。依我看来,没有别的暴行比它更违背我们常人的人性;不管一个人犯了什么过失,没有别的暴行比不准罪人因羞愧而隐藏自己的脸孔更为险恶凶残的了,因为这恰好是实行这一惩罚的本质。”同样,在“相认”一章中,当新来乍到的齐灵渥斯向当地人询问海丝特示众受辱的原因时,当地人回答道:“你终于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地方,有罪必惩,犯罪者得当着法官和老百姓的面受到惩罚。”因此,刑台首先寓意着“惩罚(punishment)”,[2]对触犯了当时的法律和教规戒律的罪犯所实施的惩罚。海丝特·白兰因其所犯的罪孽被罚胸珮象征耻辱的红字站在刑台上示众受辱。而与她同伙的罪人丁梅斯代尔却由于海丝特的沉默而免受惩罚,得以保全洁白的名声与崇高的地位。
在“牧师夜游”一章中,在夜色的掩护下,牧师邀请海丝特母女和他一起站在七年前海丝特受惩罚的刑台上。但当小珠儿追问什么时候他们三个人才能在白天站在一起时,牧师回答:“最后审判日。到了那一天,你妈妈,你,还有我都将站在审判席前。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光天化日之下是看不到我们站在一起的!”可见,刑台的另一重象征意义是“审判(judgment)”,[2]是清教道德或上帝在场的体现。由于海丝特的沉默,丁梅斯代尔避免了世俗的惩罚,却注定要接受上帝的审判。终于,在“红字的显露”中,在逃离殖民地开始新生活的展望被齐灵渥斯断送后,牧师选择在完成了上帝选择日的布道、达到人生最光辉最荣耀阶段的那一刻,在光天化日下和海丝特母女一起站在了刑台上。承担起他一直逃避的耻辱,接受上帝对一个罪人的审判。
二
作为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场景,刑台聚焦了故事的主要人物,海丝特、丁梅斯代尔和小珠儿,导引了“市场-牧师夜游-红字的显露”的叙事结构。刑台所建构的这一故事格局与《圣经》的U型叙事结构恰好吻合,尤其是主人公之一丁梅斯代尔“负罪而隐瞒-知罪而忏悔-获得救赎”的过程正好体现出与《圣经》U型叙事曲线的契合。
加拿大神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3]用一种U形模式对《圣经》的叙事结构做出了高度概括:“我们可以把整部圣经看成一部神圣喜剧,它被包含在这样一个U形故事结构中:在《创世纪》之初,人类失去了生命之树和生命之水;到《启示录》结尾处重新获得了它们。首尾之间是以色列的故事。”弗莱进而从这种U形结构分析了整部《圣经》的叙事结构都是遵循着乐园-犯罪-受难-忏悔-得救这一模式。这种U形结构形成了一种原型结构模式。
主人公之一丁梅斯代尔的救赎过程体现了与弗莱原型结构模式的高度契合。丁梅斯代尔是世人眼中的圣徒,一表人才、有着极高的天赋和学术造诣,年纪轻轻就已经蜚声教坛。然而,正如生活在伊甸园中的亚当,年轻的牧师和海丝特偷吃了禁果,犯下了“原罪”。海丝特含辛茹苦,通过自己的无私奉献把胸前罪孽的象征变成了德行的标志,而牧师则经历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救赎之路。在罪行披露后,丁梅斯代尔不仅没有和海丝特一起站在刑台上接受应得的惩罚,还要隐藏一颗罪恶之心,虚伪地规劝海丝特悔过自新、坦白招供。但是,这种“负罪而隐瞒”的状态却不能使牧师得到片刻的安宁。他天性热爱真理,厌恶谎言,深知自己的罪孽与伪善,灵魂备受煎熬。他不断自省、彻夜祈祷,把斋戒当成自我惩罚,甚至鞭打自己来忏悔隐瞒的罪孽。在夜游中,他拉着海丝特母女的手一起站在了那象征惩罚的刑台上。只不过这一“知罪而忏悔”的举动仍然有着夜幕的掩护。终于,在与海丝特母女一同逃离殖民地开始新生活的梦想破灭后,在“选择日”的光天化日下,牧师拉着这对母女的手再次站上刑台,接受了世俗与上帝的审判,获得了精神的救赎。
三
除了赋予刑台“惩罚与审判”的象征寓意外,霍桑还借这一建筑物表达了他对当时清教统治的看法。
在文中,霍桑把殖民地的清教统治比作一部“惩罚机器”,而海丝特受到的站在刑台上示众的裁决则“带着这个丑恶的惩罚机器的最邪恶的特点”。为了表达对海丝特的同情,作者不无讽刺地指出怀抱婴儿站在刑台上的她令人自然地想起那怀抱为世人赎罪的婴孩的圣母。而且,除示众受辱外,海丝特还必须终身佩戴那象征耻辱的红字。在作者看来,这对于一个妇女来说,“比之烙在该隐额头上的印记还要难以忍受”。这些评论都反映出作者对当时北美殖民地政教合一的清教统治所持的批评态度,揭露了当时清教统治的严酷和违反人性。
霍桑对殖民地清教统治的批评态度和他的家族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于1804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的一个清教家族。塞勒姆镇是当时的一个重要港口,清教势力在当地占据统治地位。清教徒们在马萨诸塞州获得了宗教的自由,却不能够容忍异己。当时的法律极为严苛。霍桑的先祖威廉·霍桑,马萨诸塞殖民议会的首任议长,就因迫害贵格会教徒而闻名。而约翰·霍桑,威廉的儿子,则是当时声名狼藉的塞勒姆驱巫案的法官之一,因判处女巫死刑而被世人称为“绞刑法官”。霍桑对祖先的行为怀有深深地负罪感,虽然并无确凿的证据说明霍桑Hothorne在自己的姓氏中加入字母W是为了有异于不光彩的先祖,但这种负罪感却在他的作品中有着真实地体现。霍桑的第二部长篇《七个尖角阁的老宅》就取材于他的家族史,小说中的品钦家族因先祖所犯的罪恶而受到诅咒。
在象征主义大师霍桑的笔下,黝黑颓败供犯人示众的刑台,成为了“惩罚”与“审判”的代名词,成为了清教道德或上帝在场的体现;刑台所导引的叙事曲线与弗莱的U型结构模式高度契合,体现了牧师丁梅斯代尔“负罪而隐瞒-知罪而忏悔-获得救赎”的救赎之路;不仅如此,霍桑还借对刑台的描述,表达了他对当时北美殖民地政教合一的清教统治所持的批评态度,揭露了当时清教统治的残酷和违反人性。在整部作品中,刑台所具备的象征意义与发挥的叙事功能比之“红字”毫不逊色。
[1]纳撒尼尔·霍桑.红字[M].姚乃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
[2]Hawthorne,Nathaniel.The Scarlet Letter[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8.
[3]诺思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郝振益,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