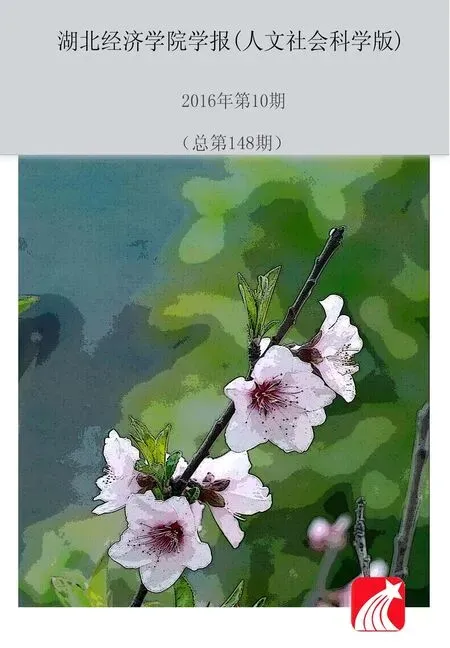叶广芩动物小说的叙事技巧分析
李名奇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湖北黄石435003)
叶广芩动物小说的叙事技巧分析
李名奇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湖北黄石435003)
叶广芩的动物小说运用多种叙事艺术手段,从而使小说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作家本人的创作个性和审美趣味,像背景的烘托,古诗词的引入,古代传说的有机改造,还有,新闻笔法与小说笔法的结合,从而使整个小说在结构上散而不乱、杂而有序,产生了逼真的艺术效果。
叶广芩;动物小说;叙事技巧
在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诗歌散文侧重于感情的抒发,“小说无疑侧重于叙事,是一门叙事的艺术。”[1](P165)作为一个擅长讲故事的小说家,叶广芩的叙事手法十分特殊。就她的动物小说而言,她广泛地吸取其他小说作家的叙事经验,在注重小说趣味性和曲折性的同时,运用了多种叙事艺术手段,从而使小说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作家本人的创作个性和审美趣味,像背景的烘托,古诗词的引入,古代传说的有机改造,还有,新闻笔法与小说笔法的结合,从而使整个小说在结构上散而不乱、杂而有序,既克服了传统游历小说结构松散、缺乏中心情节的弊端,又有助于产生逼真的艺术效果。
一、精彩的背景烘托
通过对叶广芩作品的阅读,大蟒河、殷家坪、老君岭、营盘梁、厚畛子、射熊馆、五柞宫、上林苑、终南镇……这些秦岭深处真实的名字,我们已经不再陌生,秦岭是一块充满灵性的土地,它的灵性,不仅在它她居于我国内陆西部山区的独特地理位置与地形地貌,它的自然山水,更在于她的土地上自古以来生活着众多可爱的动物,而那些动物也把秦岭这样一个美好的所在当做了幸福的家园,对秦岭神奇美丽的自然风光的泼墨式描写,不仅展示了动物在秦岭地区的大山和森林里的生存背景和动物原本可以拥有的自在的生命形态,从而烘托出这种和谐在遭受人类破坏之后更引人深思的悲哀,使主题得到了升华。
烘托本是绘画术语,金圣叹说:“欲画月也,月不可画,因而画云,画云者意不在云也,意固在于月也”。《山鬼木客》开头的一段描写是整篇小说的精彩篇章,作家采用烘云托月的方法,为陈华寻找野人进入秦岭深山与动物为伍作了层层铺垫,典型地体现了小说中人物描写的烘托艺术,不妨看看:
下了近半个月连阴雨,老君岭溪水涨满,山石膨胀,在无休无止的雨水中,山林松软得似要崩塌一般,植物像鱼缸里的水草,从里到外都让水浸透了,整座大山笼罩在一片迷茫的水汽之中。鸟不鸣,兽无影,林子里显得出奇的静,动物都缩在树叶下,缩在树洞里,缩在岩缝中,艰难地躲避着这场秋雨……周围是浓重的草腥气,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山,野绿野绿的,没有其他颜色。
这便是寻找野人而孤身进入深林考察的陈华和众多动物的生存环境,秦岭深山里独特的地域风光、一草一木组成了独特的地域乐章,也间接地烘托了陈华和各种动物在森林中亲密相处的和谐场景。而在这原始的林莽中间,还有着“漫山遍野的松华竹”、“密得解不开的灌木丛”、从天而降的大雪落在山尖的针叶林上,变作了“美不胜收的树挂”交织成了独特而美丽的森林景观。类似这样的描写在《熊猫碎货》、《老虎大福》以及《黑鱼千岁》等作品中比比皆是,既生动地描绘了老虎、熊猫、黑鱼等野生动物的独特环境,也显现了独特的秦岭风光,烘托了主人公们生活交往的独特情调,给人一种奇异与新鲜的感受。
二、历史传说的合理铺垫
叶广芩在动物小说的创作中,恰当地引入了古代的一些历史传说,使得历史传说为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展开和作品主题思想的深入做了合理的铺垫,可谓古今交汇,相得益彰,小说作品也有了更加厚重的文化意蕴,显示出卓著不凡的风姿。
叶广芩为了更为直接地接触动物,她选择了周至县的老县城村作为她的生活基地,周至自西汉就有建制,农耕文明高度发达,汉唐时代为京畿之地,文字典籍、文物遗址很多,老子在楼观台讲述五千言《道德经》,白居易、李商隐历任周至县尉,这里诞生过不朽的诗歌《长恨歌》,据云杨贵妃便是由周至通过傥骆道逃亡南方,奔向日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特定地域,作家免不了耳濡目染中会把对该地域文化的体验、感受和领悟潜存心中,当她创作作品时,她的主体意识就自然落脚于特定地域文化的根基上,把特定地域的文化结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信仰习惯、价值观念等灌注其中并恰切地展示出来。《黑鱼千岁》正式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黑鱼千岁》开头描写了秦岭北麓低峦环抱的地界风云大作,雷电交加的场景,震撼大地,很有气势,作家笔锋一转,通过当地人的心理引出了汉武帝当年狩猎的传说,同时,作家也作了有机的改造,使得古代传说和当时的雷雨、当下的人民心理联结在了一起,看看下面的一段描写:“两千多年了,这位皇帝常常回来,尤其在这夏秋之交的时候,他喜欢到他生前钟爱的猎场和他最后离开人寰的启程之地来巡视,无论世界怎样地变迁……无时不在向后人宣告他的存在一样”。叶广芩把黑鱼的故事与汉武帝狩猎联系起来,置于评法批儒的时代背景,使历史和今天互动,便有了新的内涵。
叶广芩对古代传说的有机改造,并非引入一些古代人物的传闻轶事来取悦读者,作家始终秉承严肃的创作态度,围绕着作品的主题来展开,使得小说情节丰满而不枝蔓,文化意蕴深厚而不显得繁琐。对古代传说的创造性吸收运用,无疑也加重了作品的文化意蕴。她主要择取了古代传说中大肆狩猎、摧残动物的事件,如汉武帝当年的狩猎,数十万人“罗千乘于林莽,列万骑于山隅”,将豺狼虎豹赶至山口捉住,运往博熊馆圈养在硕大围网中,“责胡人徒手与野兽相搏”,“武帝高坐博熊馆上,以观其乐”,博熊馆周围的黄土地承载过多少血腥与杀戮。
作家把大鱼的故事与汉武帝狩猎联系起来,置于评法批儒的时代背景,使得历史和今天互动,便有了新的内涵。显然,作家是要通过古代传说,把当年汉武帝那君临天下不可一世的风采张扬了出来,而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在小说中所渗透的对传统文化的负载以及反思现代生态伦理的缺失而闪耀着永恒的光芒,让读者感悟动物自古以来就遭受屠杀的悲剧命运,这正好与下文中儒捕杀两条黑鱼的故事情节相呼应,儒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正是“评法批儒”运动的时候,于是儒的名字便带上了很强的时代特色,有趣的是,儒的出生地正是汉武帝狩猎,观看胡人俘虏搏击野兽的搏熊馆村,儒的名字又蒙上了历史色彩,儒的性格很犟,没有什么特长,但是,儒对猎取野生动物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要成为这方面的精英,他猎取了第一条黑鱼,但是他不吃鱼,只是要以此炫耀自己,让别人赞扬他捉鱼时的英勇,他名字的背后似乎是作家有意地让读者联想到中国儒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统治下的中国人格中的某种性情。《长虫二颤》中,也有类似古代传说的铺垫,即汉武帝用箭射伤大蟒,呵斥青衣童子,获取童子所捣之金疮奇药,后来刘秀兵败奔走秦岭再次遇见大蟒,盛怒之下赐死大蟒,遭王莽篡位报应的传说。使得传说中的奇药与秦岭的珍贵草药连在了一起,与秦岭的蛇连在了一起,古代帝王猎杀动物的传说与现代人的老佘之流无情捕蛇交相辉映,这种辉映越契合,作品的文化蕴涵越显得厚重沉实。
三、新闻、报告笔法的运用
叶广芩的动物小说行文朴实流畅,但她的小说不古板,所以,阅读她的动物小说,不会觉得枯燥,可读性很强,不过,她对这种效果的把握是很不容易的。她的动物小说之所以具有较好的可读性和生动性,是因为她打破常规,有所突破,在继承小说文体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创新,她有意将新闻、报告等纪实文体的笔法带进小说创作中,而且合情合理,对故事情节的展开起到了很强的帮助作用和补充作用。不妨看看《山鬼木客》,作品一开始就将读者带入了一个新闻事件:
2001年7月19日,某市法院判决了一起离婚案件,四十三岁女性杨青雅因丈夫陈华于1997年7月12日离家出走,四年来杳无音信,已按失踪处理,根据婚姻法规定,杨青雅与陈华自动解除婚姻关系。
接下来,围绕着这一事件,展开了故事的矛盾冲突,故事主人公陈华正式登台亮相,他只身前往秦岭森林深处,与动物为伍,从而使得动物也跟这一新闻事件扯上了或近或远的关系。从作家的主观意图说,叶广芩开篇就融合新闻的要素,目的就是运用新闻笔法来交代小说主人公陈华消失的悲剧结局,显然,她在此并不是平铺直叙地记述这一结果,而是用新闻笔法来转载法院一桩案件的判决书,既生动活泼,又典雅大方,这不仅是叶广芩写作思想上的创新,在写作实践上她也尝试了新的创作思路。同样,在这部作品的结尾,作者使用了“科研报告”这一叙事手法。文章以附录的形式叙述如下:
半个月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收到了一份从天花镇寄来的包裹,是一个近似人类的颅骨,附带着一份简要报告。内容如下:
农民李春桃,1902年生,女性,天花山核桃坪人。1930年3月在田间劳动,被一直立行走的不明动物掠上山,两个后自行逃回。回来后怀孕,于当年12月产下一子,取名王双财。据当地人回忆,王双财从生下起便生棕色短毛,足大臂长,面目似猿……前额低窄,眉脊向前方隆起,脑量不大,是正常人的三分之二……枕骨大孔较一般人小,枕部平展,枕骨粗窿不明显,与我国晚期化石智人相接近,显示了脑髓不发达的特质。
从以上粗略情况看,核桃坪王双财颅骨与类人猿接近……请进一步研究验证。
笔者认为,叶广芩在文章末尾处特意地运用报告笔法,使作品更生动了一些、更活泼了一些、可读性更强了一些,让读者不知不觉进入到了故事的现场。在内容上,除了照应文章题目“山鬼木客”以外,还照应了贯穿整篇文章故事展开的线索,为陈华寻找野人,走进深山与动物为伍却被人群追逐跳下山崖这一心酸的结局作了补充,这是对小说艺术手法的一种大胆拓展和创新。
叶广芩对新闻、报告等纪实文体笔法的运用,不仅使她的小说面貌产生新的变化,内容有趣,为读者所喜闻乐见,也使得她的小说具有了较多的鲜活性,有冲击力,有震撼力,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笔法产生的效果是其他笔法所无法取得的。
总之,叶广芩在动物小说叙事策略方面的把控和运用通常都有新的拓展,她在小说情节的叙述中,巧妙融合传统手法和当代叙事策略,这确立了她在小说叙事方面属于个人的形式感,“一个好作家的功绩也在于提供永恒意义的形式感。”[1](P145)叶广芩在动物小说叙事技巧方面的努力,使她走上了这“提供永恒意义的形式感”的康庄大道。
[1]吴道毅.南方民族作家文学创作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2]苏童.想到什么说什么,纸上的美女[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