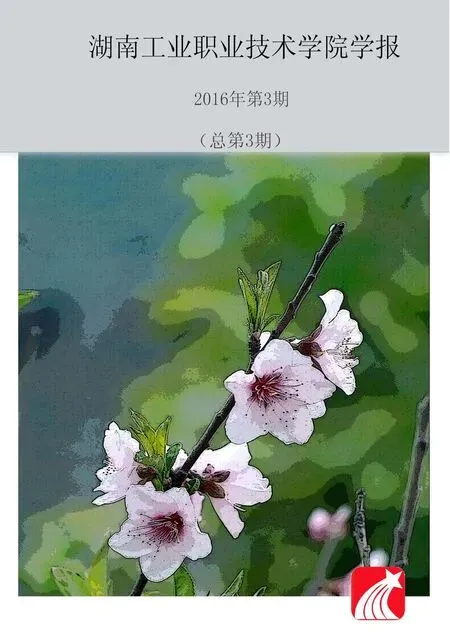从文学伦理学角度解读《流沙》中海尔嘉悲剧的原因
吴 琳,程立黎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41081)
从文学伦理学角度解读《流沙》中海尔嘉悲剧的原因
吴 琳,程立黎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41081)
[摘要]《流沙》描述了一位黑白混血儿女性海尔嘉因追寻幸福而不断变换生存空间但最后却以悲剧结局的故事。本文通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追溯海尔嘉在伦理意识觉醒之后,在主客观条件相互作用下做出的伦理选择,并分析影响她做出伦理选择的因素。她通过不断转换自己的生存空间来与现实的伦理环境抗争并获取伦理认同,但由于失序的伦理环境和自身条件的限制,海尔嘉迷失了自我做出了错误的伦理选择,致使她灵和肉都陷入了流沙之中。这是种族矛盾尖锐的时代环境下黑白混血儿不可逃避的悲哀与无奈。海尔嘉的悲剧值得深思,更给现实中的人们以教诲。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海尔嘉;伦理意识;伦理身份;伦理选择
《流沙》是美国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内勒·拉森的作品。拉森的这一作品自1929年出版以来就受到众多批评家和读者的兴趣,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外学者沃尔顿和凯瑟琳·谢泊德·海登都认为这是一部关于女主人公内心生活与内心斗争的小说,而南森·哈金斯和克劳迪娅则联系种族主义与女性主义谈了海尔嘉作为一个黑白混血儿在当下社会内心和现实的生存现状。也有从主人公的性格方面着手进行文本分析的。国内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以《流沙》为对象,探索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黑人女性的身份认同以及种族意识上,也有对《流沙》主人公形象和写作手法的研究。近年来,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繁荣,一些硕士论文对《流沙》的研究渐渐多起来。有把它和音乐、历史联系起来,分析当下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特征的,有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角度分析非裔美国女性的身份认同的。这些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从女性主义、种族主义、社会阶级和社会文化的角度切入来分析《流沙》,对国内的认识和理解哈莱姆文艺复兴及内勒·拉森及其作品有很大的帮助。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切入也有值得探索的价值,故本文试从伦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文本,探索海尔嘉伦理身份的变化与其伦理追求之间日的相关性,用文学伦理学批评原理分析其作出错误的伦理选择导致悲剧的原因。
在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在白人世界和黑人世界之间主张种族隔离和反隔离的对峙气氛空前紧张。种族隔离政策对内勒·拉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内勒·拉森作为一名黑白混血的女性作家,1929年创作的《流沙》中塑造的黑白混血女性形象是新黑人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她的创作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双重压迫下展开,故拉森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使得作品的带有了浓厚的自传色彩。《流沙》讲述了女主人公海尔嘉离开黑人聚居区纳克索斯,去白人世界寻找幸福。她辗转于芝加哥、纽约、哥本哈根这几个地方,但她最终都没能过上理想的幸福生活。最后,她来到黑人牧区,皈依宗教,把自己的一切托付给上帝。她嫁给黑人牧师,为人妻母,沦为男人泄欲的工具和繁衍后代的机器,海尔嘉的悲惨结局值得我们深思。本文试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探寻海尔嘉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下所作出的伦理选择,以及在新伦理身份下她的现实与历史处境,追寻她辗转于几个城市之间伦理意识的觉醒与迷失的过程,接着本文分析了影响她做出伦理选择一步一步走向悲剧的人物。最后本文着力探索了《流沙》给我们的伦理教诲和现实意义。
一、伦理身份的转变
《流沙》讲述的是主人公海尔嘉伦理追求的故事。随着海尔嘉伦理选择的不同,她的伦理身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把海尔嘉的漫游看成是一条伦理链,她每一次的伦理选择则可以看成一个伦理结,她在伦理觉醒后做出的伦理选择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因素。各种主客观条件的相互作用促使她做出了伦理选择,而伦理选择后伦理身份的变化则是她伦理追求的结果。海尔嘉每一次伦理身份的变化就是一个伦理结的形成,伦理身份的转变也推动这个伦理链条向前发展。在美国当下的种族伦理体系下,海尔嘉的伦理选择导致的悲剧不仅是她个人梦想的破灭,也是美国整个中产阶级黑人女性群体无法逃避的悲哀与无奈。
海尔嘉的形象不同于以往被塑造成“黑保姆”和“荒淫无度的荡妇”的黑人女性形象,她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单身黑人女性,她的伦理意识从蒙昧的状态中觉醒,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新黑人”的典型人物。但当下的伦理现实却和海尔嘉的觉醒的伦理意识有一定的差距。在一次白人牧师的演讲中,白人牧师夸奖纳克索斯这种臣服于白人统治下的状态很好,言外之意是要黑人不要反抗这种被压迫的状态,这让海尔嘉却觉得学校“这个巨大的团体,不再是学校了,它长成了一个大机器,现在展示在一个黑色的地带,表彰白人的慷慨以及驳斥黑人的无能。”[1]这样的伦理秩序让她感到恶心。对于伦理意识觉醒了的海尔嘉而言,这里的伦理环境和教育制度深深压抑了黑人的独立性和人性中的美。于是她离开这里去了她的出生地芝加哥。在芝加哥她找不到工作,她带着被驱逐的悲哀跟随白人妇女罗斯夫人去了纽约,在纽约、哥本哈根继而又回到纽约后,她都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她每到一个城市都满怀希望,但无一不是带着逃离的心态离开了所有的城市。对美国的黑人来说,逃离似乎是他们的宿命,这是历史遗留问题,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罪恶的黑奴贸易把黑人从非洲带到了美洲,而在美国,随着经济大萧条时代的到来,南方的黑人为了生活随着移民大潮来到北方。美洲人看不起非洲人,在美国如纳克索斯大学一样,白人处处统治着黑人。文学伦理学认为:客观的伦理环境或历史环境是理解、阐释和评价文学的基础,文学的现实价值就是历史价值的新发现。[3]文本中的历史伦理条件是黑人不被白人世界所容纳。而客观的伦理现实是随着黑人生活质量的改善、文化程度的提高,黑人的整体素质已经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但是社会伦理现实和大部分人的伦理意识还停留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而对于部分受过新思潮影响有教养的黑人如海尔嘉等伦理意识觉醒的年轻人来说,他们需要跨越的是伦理意识觉醒和伦理环境未改变之间的鸿沟。故作为一名单身的黑人女性,她逃离每一个城市都是由于想要融入白人世界触犯当时黑人不被白人世界接纳的伦理禁忌的结果。
以单身黑人女性为伦理身份的海尔嘉在五个城市间的漫游后,还是没有在现实的伦理环境中找到幸福。重回哈莱姆黑人聚居地,海尔嘉心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想逃离黑人世界变成为接纳,“她发现周围有着几百甚至上千的黑眼睛、棕皮肤的人们。那是她的种族。”[1]她感到很兴奋,因为她在这个伦理环境下,她好像找到了归属感。但她从欧洲回来之后,觉得“她的生命分配给了两块土地。在欧洲享受着身体的自由,在美国享受着灵魂的释放。”此刻的她灵和肉是分离的,她想努力使自己灵肉合一。在一次酒会上,安德森想要吻她,“一种隐藏良久、半明不白的渴望涌上心头,还夹杂着突然出现的一个梦。海尔嘉用自己的手臂向上环住他的脖子。”[1]所以此时不知道是安德森吻了海尔嘉还是海尔嘉吻了安德森,但很清楚的一点是,海尔嘉在哪短短的几秒钟内,欲望得到了释放。明显,此刻的海尔嘉对这个吻寄予了太大的希望,也赋予了它太多的意义,她的理智和感官都把这个吻当做释放爱情和欲望的出口,但安德森却礼貌又冷酷地拒绝了她。在经历几个城市的漫游之后,海尔嘉身心俱疲,她的理性意志处于崩溃边缘,在一个下雨天无意中走进一间教堂,她看到了许多的人在唱歌和哭泣,那么多痛苦的灵魂在主的安抚下得到安宁。她也跟着大家毫不压抑地大哭了一场,好像所有的痛苦都得到了释放,她肩负的理想以及黑人身份给她带来的困扰都被万能的上帝一手揽过了。她感觉“一切都变得真实起来。她奇迹般地变得冷静了。生活似乎还在延展,甚至变得简单了。”[1]此刻的海尔嘉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目的是通过伦理的解释去发现文学客观存在的伦理价值,寻找文学作品描写的生活事实的真相。[3]海尔嘉想融入白人世界压抑了自己的本能和欲望,但触犯白人禁忌的她失败了,继融入白人世界失败后,她又失去了误以为得到的爱情。海尔嘉一路追寻都没有结果,此刻有一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神来拯救她,处于崩溃边缘的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它。海尔嘉以为选择上帝就能得到幸福,但成为基督徒的她依旧没有找到精神的皈依。因为事实上她信仰的上帝是白人的上帝,白人的上帝是以白人伦理观来约束黑人,带有狭隘性和欺骗性,海尔嘉固然得不到幸福。
从教堂回来,牧师送海尔嘉回家,海尔嘉的心绪飘然不定,在这个能言善辩的牧师半真半假的话中,海尔嘉内心经过激烈的斗争,成为基督徒的海尔嘉最后嫁给了这个牧师。和海尔嘉在婚姻上有关系的人有三位,一位是有过婚约的万勒,一位是向她求过婚的画家奥尔森,一位就是她的丈夫格林。海尔嘉和万勒有婚约是因为作为一名没有社会背景没有家庭没有亲人的黑人女性,她想要利用万勒来充实自己的社会背景,但她最终离开了。画家向她求婚,她拒绝了,因为她清楚地知道,画家是把她当做一个充满异域情调具有野性气质的女郎来消费,这不是她想要的,更加不愿意触犯当时的伦理禁忌,去跟一个白人结婚。最后她和黑人牧师走进婚姻的殿堂,为人妻母,但也没有如愿的得到幸福。她选择和黑人牧师结婚,符合当时的伦理现实。但她并没有因为伦理选择后伦理身份和伦理地位的改变而使自己的伦理困境得到解除。一方面,在性欲的解放上,她选择婚姻这个合法的途径,最后获得一个合理的社会地位来释放自己的性欲,但却步入了一个更为悲惨的命运,沦为了男人泄欲的工具和繁殖后代的机器,让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彻底的陷入了更深的泥沼中。但如果不选择婚姻这条道路,她要么违背伦理禁忌释放自己的性欲,要么就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性欲。这是不合理的伦理环境加诸于黑人女性身上的伦理束缚。
在文学批评中,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3]海尔嘉伦理身份经过单身黑人女性、基督徒和妻子这三个伦理身份的变化,她做出的每一个选择,不仅是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些选择是哈莱姆时期大多数受过教育的黑人女性困境的写照。她们受过教育,伦理意识觉醒了,想进入高贵的白人世界,但于当下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伦理现实而言是不可能的,更加不敢触犯禁忌去和白人结婚,在信仰发生危机的时候,选择看似万能的上帝,再和黑人结婚,在当下的伦理秩序来看,以合理的途径来释放自己的本能和欲望,一步一步走上悲剧的结局。其实,拉森是借海尔嘉悲惨处境来引起公众的注意,黑人文化已经发展起来了,而当下伦理现实和黑白种族之间的伦理禁忌限制了他们,由于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局限,这些在夹缝中生存的黑白混血儿结局却很悲惨。拉森在此发出呐喊,呼吁大家关注被边缘化的新黑人女性。
二、影响海尔嘉伦理选择的男性
早期研究表明,海尔嘉是一个缺乏的人。她缺乏社会背景,缺乏健全的政治意识,缺乏一个清晰可行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是缺席的。由佛洛依德的“厄勒克特拉情结”可知,在海尔嘉在自己成长的这条伦理链上,影响她做出伦理选择从而成为伦理结的主要人物有三个男性。分别是纳克索斯大学的校长安德森、哥本哈根的画家奥德森和她的黑人牧师丈夫格林。
安德森可以说在海尔嘉成长道路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海尔嘉理性意志和非理性意志的交锋中,他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第一次对他的影响是在海尔嘉准备离开纳克索斯去他办公室辞职的时候,校长安德森极力说服她留下来,而海尔嘉也被安德森的一席话所感动,“那种想要为他人服务的冲动再一次涌上心头,不过现下不是为她的人民服务,而是为眼下这个那么诚恳地谈论着他的工作,他的计划和他的希望的人服务”[1]她想重新成为学校的一部分,为自己要离开感到后悔,甚至决定“不仅会留下来待到今年六月,明年还会回来”[1]。而安德森继续夸海尔嘉是一位有尊严和教养的淑女,使在芝加哥贫民窟出生的海尔嘉觉得受到了侮辱,[6]以为安德森讽刺她没有尊严没有教养,她非常愤怒,因为伦理意识刚刚觉醒的海尔嘉内心十分脆弱,她决定离开并不是因为她没有校长说的那种奉献精神,而是在谈话中她感到校长扭曲了她的人格。海尔嘉第二次回到纽约和安德森在一次酒会上重逢时,安德森吻了自我意识在膨胀中的海尔嘉,海尔嘉因为那一吻而深陷爱情中,但安德森却说自己当时被激情所主宰,并非出于理性。处在每个阶段的海尔嘉自我意识非常的强烈,伦理意识上也非常敏感,她觉得自己是黑人,但同样有高贵的思想和淑女的品行,并不是因为自己身上的白人的血统而使自己高贵。所以他在纳克索斯大学没有给她介绍信的情况下还是离开了这里。而在她觉得自己获得了安德森的爱情继而幻灭之后,她内心的一份坚守已然崩溃。这不仅是白人世界对自己的拒绝,更是在人格上否定她,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所以后来她转变了之前的态度,做了一个重大的选择。
在哥本哈根,影响她做出回国的决定的非画家奥尔森莫属了。在哥本哈根的上流茶会上,海尔嘉被当做一个稀有的孔雀来吸引大家的眼光,画家也是其中被吸引的一个。原本去丹麦寻找幸福的海尔嘉被光怪陆离的现实所吸引,伦理意识也渐渐迷失。画家以挑剔的眼光审视海尔嘉,因为异域风情和姣好的面容,画家被海尔嘉迷住了,所以画家向她求婚,她感受到了画家仅仅把她当做一个特别的性感的黑人女郎来对待。在芝加哥,因为她只是一个黑人女性,不是上流社会的女郎,所以她被一些男性当做妓女来对待,此时她身处上流社会,一样被当做商品来消费,和那些马戏团耍杂技的黑人一样,并没有受到尊重,如果跟画家结婚,她永远都只可能被当做一个装饰品来呈现在世人的面前[7]。画家也很坦诚地说:“你有非洲女人令人兴奋冲动的本性,除此之外,我的小可爱,恐怕你有一个妓女的灵魂。你把你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我当然高兴那个人是我。实事上,那个人就是我。”[1]虽然海尔嘉暂时迷失了健康的伦理观念,但她深知自己嫁给画家奥尔森不会幸福,所以很坚决地拒绝了画家的求婚。因为拒绝了画家的求婚,姨父责怪海尔嘉说如果在有成百上千的黑白混血儿的美国,海尔嘉就不那么珍贵了。说到底,还是因为她特殊的黑皮肤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荣耀才这样劝说海尔嘉的,因为不能很好地和姨母家相处了,所以在接到安妮的结婚请柬时,她离开了丹麦。
在海尔嘉成长的伦理链中最重要的一个伦理结就是黑人牧师的出现给她带来的影响。因为她的出现,海尔嘉的伦理身份有了质的改变。出于对自尊的要求和对满足性冲动的要求,她想作一名真正的黑人女性来实现自己对幸福的期盼。在这个节点上遇到黑人牧师,让海尔嘉误以为这就是她自我救赎的途径。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黑人和白人通婚还是要算是伦理禁忌,不被黑白两个世界所接受。和她有过婚约的万勒、向她求过婚的画家奥尔森、误以为给自己爱情的安德森都是社会的上层阶级,而此时的黑人代表广大的贫苦黑人民众,是下层阶级的代表,从当下的伦理现实来看,海尔嘉觉得和黑人牧师结婚自己会过上自己一直追寻的幸福的生活。早在白人画家向她求婚的时候,她就坚定地说自己不会和白人结婚,因为海尔嘉从内心深处不想违背伦理禁忌。况且从自身努力之后仍旧不被白人社会接受的现实情况来看,她也不想自己的后代过和自己一样的生活。种族和地域在时间和空间上束缚着她。曾经在身体和地域之间的关系与社会隶属关系中,她为了融入白人世界做过努力和妥协,最终回到了黑人的土地上,在她这条伦理发展链条上黑人牧师出现得刚刚好。如《圣经》中说的那样,来自泥土又归于泥土一样,最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伦理环境中。但是她遇到的黑人牧师,传递的却是白人信奉的教义。因此她归顺的上帝是白人的上帝,说服她成为一名基督徒的牧师也具有欺骗性。可以说黑人牧师是在海尔嘉极度悲伤的时候趁虚而入。由于海尔嘉性格软弱好妥协的一面,每当她觉得很苦的时候,黑人牧师就拿上帝来压她,所以,她的理性意志在被黑人牧师一天天传递教义的过程中消磨殆尽。
在现实伦理环境中,海尔嘉通过处理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来调适自己,使自己和这个伦理现实保持一致,让自己生活在可被接受的伦理秩序中,但她遇到的影响她做出伦理选择的人都没有给她带来积极的影响。聂珍钊教授指出:“一旦人身上失去了人性因子,自由意志没有了引导和约束,就会造成灵肉背离。肉体一旦失去灵魂,就会失去人的本质,只留下没有灵魂的人的空壳。”[2]海尔嘉身上的人性因子没有很好地受到理性意志的指导、约束和控制,使其兽性因子违背了当下的伦理环境。海尔嘉本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因为错误的伦理选择而导致的悲剧结局令人唏嘘。
三、伦理启示及现实意义
《流沙》深刻的描绘了美国20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间黑人社会和黑人社会的伦理禁忌,以黑人女性海尔嘉为代表,中产阶级的黑人女性的自由本能和原始欲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是在作家对人的自由本能和原始欲望的揭示中,我们看到了自由本能和原始欲望对于人的命运的影响。”[3]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的任务就是描写这种伦理秩序的变化及其变化所引发的道德问题和导致的结果,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3]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在现实中,我们还需要在主观和客观上做出努力。主观上,我们应该克服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克服性格上的缺陷,培养坚定的性格。客观上,应该把“人人平等”落到实处,完善教育制度、法律制度等等。
主观上,海尔嘉在性格上有很重大的缺陷,她没有坚定的自我,在很多事情上犹豫不决,容易被别人影响。“她承认自己是黑人,但不容许别人轻视她;她致力于诱惑别人,但不敢让自己陷入一段浪漫的感情中;她反对别人将她当做妓女来消费,有没法完全做一名淑女。”在跟校长辞职的时候,她打定主意要离开了,却因为校长的一席话有所动摇;在丹麦姨妈家的时候,她明明对衣服的材质、剪裁和颜色有独到的品味,但为了迎合姨妈她妥协了。在遇到黑人牧师时,她明明知道自己不爱黑人牧师,但在他的奉承下半推半就地答应了黑人牧师的求婚。除了海尔嘉之外。
同时,黑人内部也有很多对白人加诸于自身的伦理的墨守。除了需要改变个人性格上的缺陷之外,客观上的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也需要改进。传统的道德规范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南方的黑人,他们融进血液里的“黑人没有白人高贵”的道德观促使海尔嘉对明亮的色泽如黄色、绿色、红色的喜爱,并认为是个性和美丽的象征,就昭示着她对个性和美丽的需求。她讨厌黑人中“这些人一面高喊着种族、种族意识、种族骄傲,又一面压抑着它最美好的昭示,例如对那色彩的喜爱,对那爵士舞曲的喜爱,对那纯洁的、发自内心的笑声的喜爱。和谐,朝气,朴素,所有这些所谓的精神之美的构成要素他们都要将其毁灭。”[1]海尔嘉作为一名受过教育有良好修养的黑人女性,不仅处于白人世界的边缘,也处于黑人世界的边缘。就像骆洪教授说到的边缘人的困境:一方面,种族歧视使得他们难以为主流文化所接受,而且在白人控制的社会里还到处受排斥;另一方面,他们又对黑人社区里许多僵化、教条的思想、习俗产生不满。黑人的生活本来就受到了许多限制,而黑人社区又为黑人设立了许多禁区,一旦超越,将被视为对种族的背叛。甚至与白人正常的交往也会受到黑人同胞的非议。[4]努力的海尔嘉始终还是不幸的,她所在的任何一个地方,她都是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她是那个伦理环境中的他者。不仅在白人世界中她得不到尊重,在黑人世界里,她同样不受欢迎。在白人族群中,她要遵守白人的伦理道德,但白人却不会承认她是自己种族的一部分。在黑人族群中,她始终也是不被接受的。海尔嘉和牧师结婚后,想尽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里贫穷落后的面貌,自告奋勇地帮助他们改善居住环境、卫生条件等等,但“她们互相之间讨论着,‘那个傲慢自负的、爱瞎管事的北方佬’,‘可怜的牧师’,在她们看来,‘跟年轻姑娘克莱门泰因·理查兹过的话,会生活得更好。’”[2]她努力的奉献自己可以奉献的爱心,但并没有被这里的人接受,这里的人把她看做一个“爱管闲事的北方佬”。她始终没有融入自己所处的环境。
《流沙》这部作品给了时代一个信号,那就是中产阶级受过教育的新一代黑人妇女已经觉醒了,她们和同时代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一样,有抱负有追求,也为自己的理想生活在奋斗着。虽然,她们有的最终都没有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但黑人妇女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拉森的作品已经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了经验和教诲。海尔嘉努力追寻的过程,其实也反映了觉醒了的美国黑人努力想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强烈愿望。因为非裔美国人毕竟也是美国人,在美国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有着对美国的文化认同。就如休斯在《大海》中写道:“我只是一个美国黑人。虽然我爱非洲的外表,非洲的节奏,但我不是非洲人,我是芝加哥人,堪萨斯人,百老汇人,哈莱姆人。”这里有黑人饱受白人的欺凌和辛酸,也有渴望得到认同的期望。但现实却是在《流沙》的开篇中,拉森引用休斯的诗歌:
我的老爸死在漂亮的大房子,
我的老妈死于低矮的棚屋,
我不知道我将在何处了却此生,
因为我既不是白人亦不是黑人。[1]
在现实的伦理环境中,黑白混血儿面对的却是进退两难的窘境。海尔嘉最后对自己伦理身份的选择,有自己主观上的判断失误,但造成这种结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却是当时失序的伦理环境。故拉森的《流沙》即使在当今社会,也能带给我们很多启迪,指引人类完善自己的伦理秩序,促进人类的进步。
[参考文献]
[1]Nella·larsen,quicksand.[M].NewYork:university of michigan,1928.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和斯芬克斯因子[J].外国文学研究,2010(1).
[3]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 2010(1).
[4]骆洪.身份建构中的双重话语—谈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创作思想和作品主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4).
[5]胡敏捷.浅析莱拉·拉森《流沙》中性政治的表现及应对[D].华中科技大学,2011.
[6]赵秋玲.浅析《流沙》中的反讽艺术[J].文学与传播,2014(7).
[7]Catherine·Rottenberg,BeggingtoDiffer:NellaLarsen’s “Quicksand”and Anzia Yezierska’s“Arrogant Beggar”[J].St. Louis University:African American Review,2007.1.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004(2016)03-0051-05
[收稿日期]2016-2-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3&ZD128);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的伦理探索(项目编号:14YBA393);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青年教师发展基金项目二十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的伦理学批评研究(项目编号:14WYQN0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5M57217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琳(1973-),女,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西方文论和欧美文学研究。程立黎(1991-),女,湖南邵阳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文学。
Interpret the Reasons Leading to Helga’s Tragedy in Quicks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Ethical Literary
WU Lin CHENG Li-ni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
[Abstract]Quicksand described a mulatto woman named Helga Crane who continuously changes her living space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yet her life ended as a tragedy,this paper,through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reviewed the ethical choices made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elements after Helga’s awakening in ethical consciousness,and analyze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ed her making these ethical choices.Helga struggled with the realistic ethical environment and achieved ethical agreement by constantly changing her living space.however,due to her own restrictions and being a misorder ethical environment,Helga was lost in ethics and made wrong ethical choices to the point that both spirit and flesh were mired in quicksand.That sorriness and holplessness are what mulattos cannot escape from when racial conflict was at it’s climax.Helga tragedy worth our pondering and it gives lessons to people in real life.Content of abstract.
[Key words]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Helga Crane;ethical consciousness;ethical identity;ethical choice
——为单簧管、小提琴、钢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