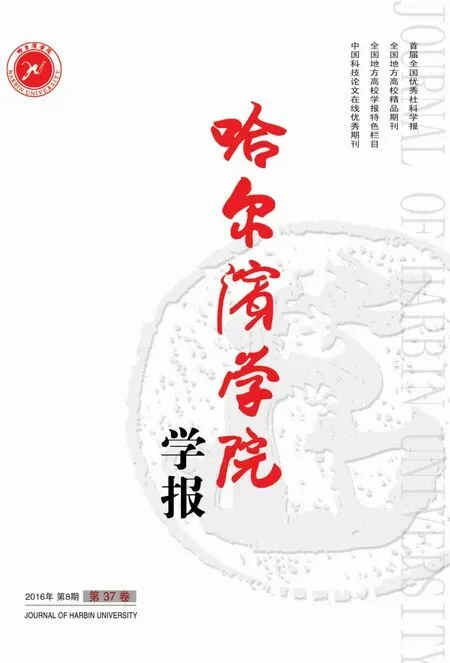论法家人性观对中国古代刑法的影响
华志强
(安徽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59)
论法家人性观对中国古代刑法的影响
华志强
(安徽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230059)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法家认为,人人都有的好利恶害本性是不可以教化改变的,因此统治者只有采取强制措施遏制人的欲望,使民众不敢犯罪。人性恶论是法家重刑思想的逻辑起点。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制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对中华法系成文法典的刑法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自战国以降各朝代不仅重视成文法的制订和公布,而且形成了我国古代法律刑法制度发达的局面,这也成了中华法系的一大特色。
[关键词]法家;人性恶;中国古代法
对人性善恶的讨论一直是中西方学者长期以来争执不休的话题。西方学者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人自身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而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人性争论的核心在于人性的本质是善良还是邪恶。西方的哲学话题在此姑且搁置,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有关人性善恶的观点可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派。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认为人性善,是故可以通过教化使民从善远恶,实现国家大治;而认为人性恶的思想家则有以荀子为代表的部分儒家学者和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家。而且两者在人性是否可以得到教化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荀子虽对人性持否定态度,但他同时又认为人性可以经过适当的教育而重新完善,这就是他提倡的“化性起伪”说;法家则在提出性本恶的理论后,却并不相信人性“可化”,认为对于恶的人性,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以恶攻恶,施以重刑,严刑重罚以警示他人不再犯罪,以此达到所谓“以刑去刑”的目的。
一、法家的“性本恶”思想
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是以主张“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强制作用而著称的学派。法家的代表人物大多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春秋时期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李斯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法家的思想以抽象的人性为依据,并且把法律特别是刑法的作用夸大到可以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
法家认为,人人都有好利恶害的本性。管仲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1]商鞅也说:“人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2](P81)商鞅从人性恶的角度论述法治的必要性,他认为法治是基于人性特点而可能采取的最好的治国手段。他认为“好利恶害”是人的天然本性。“人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矣。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2](P81)商鞅认为,好利恶害的本性人皆有之,这种人性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而且是不可以改变的,因此治理国家就不能依靠儒家的仁义道德、教化德治,而只能依靠法治。商鞅说:“行刑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致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消。”[2](P98)
慎到也认识到人性在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他在《因循》篇中说:“因人者,因人之性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是故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入难。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则上下区取用焉。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得而用矣,次之谓因。”[3]人人有“自为”之心,不过这在慎到看来却恰恰是国君“使之为我”的可资利用之处,施以厚禄而后委以重任,则可以驱驰,使其“与入难”,为国君效力。但这种以利益为引导的对人性的利用毕竟是有限的,因为人性恶的结果更多的是会危及到社会的正常秩序,甚至一国政治的治乱。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在《备内》篇对人性恶的论述可谓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4](P180)不仅普通人是这样,父母子女之间也是如此,韩非子在《六反》篇云:“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其长利也。”[4](P611)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尚且如此,君臣、君民更是这样,无不是以“利”为核心。人性的本质就是逐利避害,所以韩非子在《二柄》篇对于人性之恶主张赏刑并用,即其所谓:“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杀戮为之刑,庆赏之谓德。”[4](P54)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统治者就是利用刑罚和赏赐这两个工具,他进而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法,比如信赏必罚、赏罚有度、赏罚合乎刑名、厚赏重罚等。韩非子用“赏”的方式因势利导,在社会生活中“定纷止争”,不过他更注重“刑罚”,尤其是重刑的作用,认为制定法律“禁奸止邪”就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法家的逻辑由此显而易见了,因为天生欲望,人总会在“欲”支配下作出各种损人利已的行为,犯罪活动也就层出不穷。而且人性的恶是人的本性使然,不可改变。为此,以礼治仁义的道德教化除“化性起伪”是徒劳无益的。只有采取强制手段遏制人的“欲望”,使民众因惧于严刑而不敢为非作歹,犯罪才会减少乃至消失。这种思想虽然带有很大的偏执性,但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发展史上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法家是第一次从人性论的角度对犯罪的发生进行深层次理论阐释,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关于犯罪预防的学说,丰富了古代的犯罪学理论,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法家人性恶论对中华法系刑事法律制度的影响
在法家之前,古代刑法理论几乎处于空白阶段,刑法的主要功能基本停滞在对外征服、对内镇压的国家职能方面。刑法在统治者手中成为“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威慑性暴力工具,甚至任意诛伐的借口。这样只会带来法律的恐怖色彩,很难起到预防犯罪发生的作用。法家人性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古代较早地从哲学思辩的角度分析了犯罪之所以发生的个体心理原因。在此基础上,法家有针对性地公布成文法和提出以刑法去刑的主张,希望以此达到预防犯罪乃至最终消灭犯罪的理想境界。成文法的公布,在客观上使民众知晓一国的法律规定成为可能,而其中的重刑措施又往往使民众生畏惧之心而不敢冒然触犯法律,这在理论上的确可以产生一定的预防犯罪的效果。
法家这种“以恶去恶”的思想通过法律儒家化的途径成为中华法系传统公法文化的一大特点。汉代硕儒董仲舒在继承了儒家“性善论”衣钵的同时也吸收了法家学派“性恶论”的主张,进而对人性采取了折中的“性三品”说,他在《实性》篇中指出,下等的“斗筲之性”,即使经过教育也难以转化为善,所以对“斗筲之性”的小人就只有以刑治之,以惩其恶,即其所谓“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5]由此可见,制定法律的目的就是用来防止小人的恶欲的。这真可谓法家思想的汉代翻版。
晋代刘颂也以“以刑去刑”的观点进劝统治者恢复肉刑,他说,古代通过刑罚以达到消除犯罪的目的,是故使用肉刑,而现在废除肉刑后,则不足以防止犯罪,因此,应“亡者刖足,无所用复亡。盗者截手,无所用复盗。淫者割其势,理亦如之”。否则,“不刑,则罪无所禁;不制,则群恶横肆。为法若此,近不尽善也。”[6]虽然晋武帝最终未采纳刘颂恢复肉刑的主张,但这与历代统治者中“以刑去刑”的观念是一致的。
宋代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将这一思想表述地更为直白:“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7]对于“群饮”“变衣服”这类小错也要严刑重罚,以期天下之治。
在法家“以刑去刑”思想的引导下,中国古代刑法法律制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首先是成文刑法典的公布,使刑与罪相结合起来,其意义不仅在于为刑法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还为法的普及进行了初步尝试,对法的预防犯罪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可能。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鼎”,将法律铸在鼎上,公布于众,这是中国古代第一次公布成文法,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荀寅铸铁鼎。公元前5世纪,李悝在魏国制订出中国传统社会第一部系统的“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刑法典——《法经》。从秦汉至明清,各个封建王朝也都把制订成文刑法典当作政治治理的根基,纷纷制订出一大批优秀的刑法典,其中尤以唐朝的《唐律疏议》为经典,集中代表了中华法系的精髓。其次,法家在制定成文法的过程中还将刑罚的适用主体扩大到统治者中的旧贵族和官僚阶层,“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4](P42)从而打破了古老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8]的传统。不论什么人犯罪,一律严惩,绝不宽宥赦免,这是法家“刑无等级”思想的体现。再次,为了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法家将刑罚的手段广泛推行到国家及社会活动中的各个方面,商鞅“刑弃灰于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法家“以刑去刑”的思想必然带来的法律刑罚化的结果,这一结果在诸侯各国大行其道,尤其在秦国得到彻底的实践。李悝所作《法经》经商鞅改法为律在秦国得以全面地推行,及至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立即着手进行大规模的立法。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虽在内容上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主要内容仍以刑法为主,与犯罪有关。尽管秦朝以刑罚为威的政策为后世所诟病,但历代的统治无不继承其重刑衣钵。在官方史书中关于法律的记载也仅仅只有“刑法志”,这无疑给中华法系传统法文化打上了深深的公法化烙印。同时,这种重刑思想也对中华法系成文法典的刑法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总之,法家思想家从人性恶的角度出发对刑罚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给予了充分的理论阐发,并改造和创新了中国古代法制文明,使以刑法化为主要特征的法律制度系统化,并以成文法的形式在战国及以后朝代制定和公布,形成了中华法系独特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以刑罚化手段解决民事纠纷的鲜明特征。
[参考文献]
[1]滕新才,荣挺进.管子今译[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4.
[2]石磊.商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许富宏.慎子集校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李亚东.韩非子今译[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4.
[5]张世亮,钟肇鸣,周桂钿.春秋繁露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历代刑法志[Z].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
[7]梁启超.王安石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8]潜苗金.礼记译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张庆
[文章编号]1004—5856(2016)08—0036—03
[收稿日期]2015-11-27
[作者简介]华志强(1972-),男,安徽潜山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法律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D90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6.08.009
The Influence of Legalist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on Ancient China’s Penal Code
HUA Zhi-qiang
(Anhui Institute Economics & Management,Hefei 230051,China)
Abstract:The legalists,in the period of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believe that it is human nature that people love the good things and hate the bad ones so the ruler should constrain people’s desire. The idea that human nature is evil is the logical start of legalists’ practice heavy penalty. With the effect of this opinion,the penal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had developed rapidly. Since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all dynasties had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legislation and contributed to the rich achievement of law making practice in China.
Key words:the legalists;human nature is evil;the law in ancient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