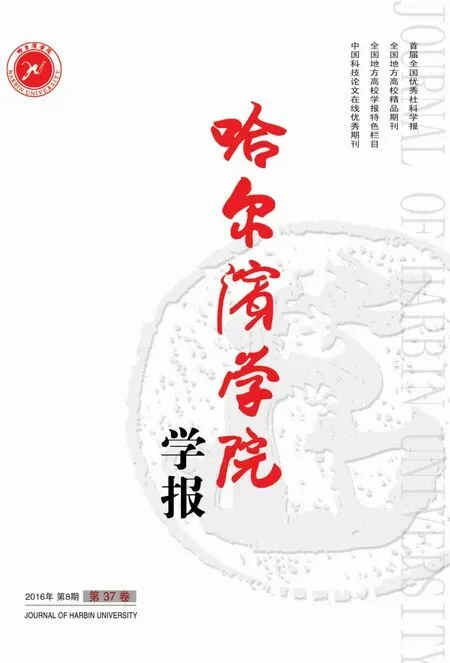历史背景下的个人书写
——论“江南三部曲”的经典性
彭园园
(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000)
历史背景下的个人书写
——论“江南三部曲”的经典性
彭园园
(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230000)
[摘要]“江南三部曲”是格非以现实题材建构的个人书写,在大时代背景下维持故事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展现文字背后的真实意图。建构当代文学经典是时代的要求,文章从写作的意图入手,整理文本内外空间与故事之间复杂的关系,探究如何超越历史维度建构文学结构,论证“江南三部曲”的经典性特征。
[关键词]“江南三部曲”;虚构;写实;历史;经典
新世纪以来,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一直是学界热衷探讨的重要课题,这一课题涉及到对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的重新考量和估算,同时也影响着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1949年以后的文学史,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被生产出来的具有丰富意识形态的内涵的概念。”[1]意识形态被认为与当代文学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必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影响着文学经典的建构,但不能起到决定作用,更不可能成为操控的力量。文学是真实与虚构的统一,作家在真实的基础上构建起自己作品中的世界,文学经典的虚构空间是作家审美想象和历史真实的完美融合,历史为艺术提供背景和素材,作品由此对历史产生新的思考和认知。在文学内部和外部两个空间维度里,历史都深刻影响着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审视,有时甚至导致作品的审美价值淹没在读者对真实历史的认知中,历史为建构文学世界创造条件,同时以其历时性的特点解构文学世界的可靠性,文学经典以文学结构历史,它在历史的框架中维持着自己的步调。
“江南三部曲”是作家格非历时十余年创作出版的系列长篇小说,全书三部《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该书于2011年定稿发表,2015年8月荣获第九届矛盾文学奖,这一荣誉将作品又拉回到公众的视野,引起新一轮的讨论和解读,格非在先锋文学时期以迷宫式的叙事手法闻名于世,并一直是以写中短篇小说见长,此次系列长篇是他在延续以往风格的基础上对自我的突破,“江南三部曲”分别以辛亥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当下的现代化社会为背景书写,三部分各自成书又相互连结,格非用不同于以往的精巧的叙述技巧消解历史,而是在历史的维度上建构小说的世界,它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以自己一贯的风格直指人的精神世界的变迁。
一
一部文学作品自诞生起,它就脱离了作者所能控制的范畴,成为文学消费的对象,读者在阅读中不断发掘文本解读的可能性,此时作者的意图往往在读者的多重解读中被遮蔽忽略,而文本解读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影响着消费者对作品意义本身的判断,因此隐匿于文本之中的作者的意图,是挖掘作品内涵的重要立足点,文本是明晰和含混的统一,还原作者的意图,要从确定性着手发掘文本更多地不确定性。“江南三部曲”自问世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世界的再现,书中的花家舍被认为是乌托邦理想的寄托,评论者大多将目光集中在乌托邦理想的破碎上,而忽略乌托邦理想构造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者格非在一次作家访谈中曾说道:“三部小说的主线都是爱情,爱情故事处于前台,是我首先考虑的,其他目标附着其上。”[2]就是说,爱情是文本构建的首要内容,在这之外的思想行为的塑造是为了服务于情感线索,在宏观的历史图式中人与人的情感关系是作者的首要考虑。
《人面桃花》中秀米是乌托邦理想的实践者,她与张季元之间的爱情是她的行动元,秀米原本是个懵懂无知的少女,在父亲陆侃走失后,她开始好奇普济之外的广袤的世界,从梅城来的亲戚张季元无疑打破了她原本狭小的生存空间,张季元的神秘莫测不自觉地引起了秀米巨大的关注,但在张季元死后她才看清彼此之间的情愫,这时张季元遗留的日记成了秀米的精神寄托,日记展开了张季元全部的精神世界,也使得秀米和张季元在精神理想上实现深入地沟通,她将张季元的理想当作是自己的理想,未完成的爱情遗憾由日记传达出的人生理想去弥补。秀米后来试图在普济建立起一个如花家舍般的世界,她的乌托邦理想实质脱胎于张季元的革命理想,无论是成立地方自治会还是后来的兴建学堂,秀米始终没有考虑普济的实际情况,她的理想是张季元的理想的延续,缺乏自我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人面桃花》中的乌托邦理想必然以失败为告终,秀米的乌托邦理想是她与张季元间的爱情的产物,没有现实的根基,建构在张季元的革命理想之上。
《山河入梦》里谭功达和姚佩佩之间的爱情线在小说中显而易见,谭功达是秀米的儿子,他身上同样承载着几近疯狂的乌托邦理想,这种执迷在文章之初就显露无疑,贯穿谭功达人物性格发展的整个过程,乌托邦理想的架构为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提供了可能,理想型人格是两人爱情的连接点。谭功达和姚佩佩都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谭功达始终将自己陷在改革的幻想中,最终导致自己孤立无援的境地,姚佩佩坚定地做着“落后分子”,凄惨的身世和寄人篱下的生存处境使她看清现实的虚幻,他们的目光超脱眼前的世俗,执著于理想的世界,一个试图建立起理想的世界,另一个试图逃离现实世界,不谋而合的理想是两个人心灵契合的表象。谭功达的花家舍生活和姚佩佩的逃亡生涯的复线叙述相互交织,使两人的爱情从之前的理想遮蔽中显露出来,爱情与乌托邦理想相互照应,由表及里地呈显人的精神世界的消亡。
《春尽江南》的叙事以谭端午的家庭为单位,谭端午和庞家玉之间的婚姻岌岌可危,两人迥异的性格和人生认知消解了爱情,爱情的表象破损不堪,精神维度却重构了爱情的内核。谭端午在这个和平的年代里信奉着“无用”的理论,他用君子不器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庞家玉全然是世俗世界里的人,她尽力维护着自己的生活,内心却又有着朝圣的渴望,她对西藏的执著是试图用此方式填补精神世界的空缺,而谭端午的存在恰恰缓解了她对精神世界空缺的恐慌。在一个乌托邦理想消亡的年代里,谭端午和庞家玉看似相悖的人生态度下是两人以互补的方式相互依靠、依存的状态使破碎的外壳内仍保存爱情的内核。
三段爱情故事隐没在作者创造的广阔纵深的文本中,爱情的主线间接或直接地指涉文本的精神内核,没有一成不变的人物形象,作者的创作意图,会随着人物性格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偏离初衷,这种偏离丰富了文本的内涵,作者意图的更改是偏离的主观因素,所架构时空的影响则是导致偏离的不可控因素。
二
文学打破现实世界并在文本中打造一个拥有自身逻辑的世界,但这个世界依然不能脱离现实世界的影响,虚构的元素总是不自觉指涉现实时空中的事物,真实世界影响文学内部时空的建构,文本中的时空被建构并影响着故事线索的发展,文学空间呈现和谐统一的局面。文学真实是对于时代的解构与重构,服务于主线的发展,并不自觉地影响文本的走向。
《人面桃花》中的故事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分子以图存救亡为己任,试图用革命的方式挽救衰败的国家,混乱的社会局面人的理想随时有夭折的可能,革命党人张季元借养病之名来到普济,行革命之实,在这过程中他暗中倾慕少女秀米,并使他对革命的信念产生了动摇,他的革命事业以自己的猝死告终。动荡年代革命的失败是常态,是历史的真实面貌,但作者却留下了一本日记,为张季元和秀米无疾而终的爱情故事开启新的旅程,虚拟的空间——花家舍犹如理想的化身召唤着秀米为失落的爱情奋斗,它如桃源般存在于这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花家舍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人企图建立的理想社会,“桑竹美池,涉步成趣;黄发垂髫,怡然自乐;……舟摇轻飏,风飘吹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洵然有尧舜之风。就连家家户户所晒到的阳光都一样多,……桃李争艳之时,连蜜蜂都会迷了路。”[3]花家舍是理想的现实载体,作者以逼真的描写虚构出它,让它确切地存在文本空间里引领秀米的追逐。
《山河入梦》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花家舍似乎依然和谐美丽,人心却已不如昨,顺应时代的要求,花家舍也进入了建设时期,集体劳动下的大生产是时代的主题,作者在花家舍这一虚拟的空间呈现现实,理想状态的现实世界必然以非真实的方式呈现,花家舍是五六十年代理想状态的化身,“花家舍的社员并不是被动地去应付上级指派给他们的任务,而是依照花家舍未来可能的样子来忘我地工作。这样一来,每个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培养出一种奇妙而伟大的直觉,这种直觉会引导他们去完成各自的使命。事实上,既不会造成误工,也不会窝工。”[4]极端的背后充满隐患,集权控制下人的自由变成麻木的机械化,谭功达建造梅城时不切实际的理想在花家舍全部实现了,最大化地实现物质追求实质上是以牺牲精神世界为前提的,社会的发展趋势注定了谭功达与姚佩佩的爱情是时代的牺牲品,他们的爱情须以理想世界为前提,不可能在现实的世界里存活。
《春尽江南》中的花家舍像极了现实世界的一角,它不再是理想社会,是现实可能存在的荒淫腐败的销金窟,“我们其实不是在生活。连一分钟也没有。我们是在忙于准备生活而成天提心吊胆。”[5]庞家玉的一句话总结了现代人的生活困境,这或许正符合时代现状,一个理想缺失的时代,一个精神迷茫的时代,人的理想由虚幻到化为乌有,由存在到消失,理想桃源化为纸醉金迷的纵欲之地。男主人公谭端午的身份是诗人,充满浪漫和理想的身份特点并未在他的行为中显现,缺乏诗意的时代不需要诗人,谭端午的诗人国度退缩到只有自己,他用“无用”的理论守护狭小的空间,他与庞家玉的爱情在精神匮乏的时代背景中飘摇不定,他们的婚姻失败,他们的爱情看似已经消亡,作者残酷地展现了个体在大时代中面临精神匮乏的困境,又以爱情为荒诞的世界填补一丝温情。
三个时代以其真实影响着故事的发展演进,作者以虚幻解构时代的真实,花家舍是虚构的时空,又是与时代吻合的时空,它是现实的极端化呈现,是作者为了呈现小说的精神向度的虚构世界;它是真实的虚构化呈现,是作者为了推进小说的情节发展的艺术加工。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志,以政治、经济、文化等为表征,读者阅读文本时通过标志判断时代,作者通过构建相似的社会展示故事的背景。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是时代的代名词,而是超越时代的个人书写,时代的标志在作者的叙事伦理中转变为个人的审美符号。
三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是对存在的探索,是虚构的艺术,是对现实的失真处理,虚化历史维度以突显个人生存本相,去蔽公共话语范式以探索个体生存体验,客观再现社会或历史事实不是小说的义务,那些单纯记录史实或研究现实的小说,“都是一些大众化的小说,通过小说语言表现一种非小说的知识”。[6]而小说背负着“违背道德与背离理性的沉重包袱”。[7]《西方正典》中也提出“能成为经典的必定是社会关系复杂斗争中的幸存者,但这些社会关系无关乎阶级斗争”,[8]文学的审美与认知标准不应沦为政治和道德价值的卫道士,“江南三部曲”中的三个时代是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时代,太过强烈的时代印记时常让读者忽略文本的思想高度,转而使小说沦为历史的代名词,“江南三部曲”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它成功的规避了历史背景,南帆谈到阅读“江南三部曲”带来一个特殊经验——疏离感的不断出现,[9]这种疏离感是作者文学话语解构和重构真实历史的结果,是作者叙事策略的成功。
三部曲以人在时间维度的变化结构故事,故事的一个个环节被拆开,叙事视点总是呈现不断变化的状态,三部曲有格非先锋时期的影子,以谜面的叙事建立起文学的结构,使历史的痕迹隐退在对存在的探索之间。三部曲里小说始终呈现给读者的仅仅是一些人、一些事,以及人与人、物或事之间的关系,作者没有着力于大环境的描写,而是建造出一个人存在的空间维度,在一个个小空间中人的悲欢离合成了读者的视线焦点,降低了时代背景对读者阅读的影响力。为了虚化历史背景,作者故意隐藏了个人与时代重叠的时间点,秀米在回普济闹革命前东渡日本的情节被作者一笔略过,姚佩佩因何原因家破人亡而寄人篱下?谭功达的能力与县长的地位并不匹配,他因何功绩能居于高位?谭端午和庞家玉的婚姻结合突如其来文本中却没有任何解释。这些与时代紧密联系的时间点上的故事环节在作者的叙事中成为无关紧要的点缀,鲜明的时代特征褪色为小说文学框架的观念符号,历史背景始终处于次要地位。
“江南三部曲”中的时代跨越百年,三代人的命运随历史浮沉,却始终保持某些共通点。他们激烈地投身历史的洪流,却都被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抛弃出来,他们企图实现乌托邦理想,却都被时代逼迫到无路可走。主人公始终与历史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无论是秀米、谭功达、姚佩佩还是谭端午、庞家玉,他们似乎总与时代格格不入,有的人改造生活有的人屈于生活,以不同的态度生存却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构建了一个异于现实的世界。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以不同的形态在文本里交相辉映,作者细致而耐心地描绘着主人公的理想,花家舍呈现出虚拟的社会形态即是主人公理想的具象化,或者说是带有时代标志的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作者以写实的手法架构虚拟时空,使虚拟空间与真实世界真假难辨,使读者忽略真实历史的模样,进入到作者建构的文学空间。小说的文学结构与历史框架相生相成,历史化作宏观的背景支撑故事线索的发展,故事的线索不屈从于历史的走向,作者的个人书写以文学的结构按图索骥,指向小说意义世界的生成。
文学结构由现实层面、原型层面和审美层面组成,审美层面是现实层面和原型层面的指向和归宿,它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最高层面,主导着文学作品的意义生成,审美层面是原型层面的升华,是现实层面的转化,是最终被读者所感知的审美价值。文学结构的三个层面经作者的匠心独运呈示在文本的叙事框架中,“江南三部曲”是一部成功的作品,是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作品,小说显露出的审美张力肯定了它的审美价值,它超越历史的范畴建构起独特的审美世界。
四
“假如我们读经典是为了形成社会的、政治的或个人的道德价值,那我坚信大家都会变成自私和压制的怪物。”[8]服膺于意识形态的阅读不能算作是阅读,同理,服膺于历史的文本不能算作是经典,经典拥有审美的力量且不服务于任何功利目的。格非曾说过:“小说能推动社会进步吗?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小。这个社会不会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当然你还可以去揭露真相、维护公正,但是我已经认识得很清楚,这个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所能承担的东西,相当程度上出现了一种很无奈的状况。”[10]作家总有一种忧患意识,一种自觉承担的使命感,这正是格非在三部曲小说里所呈现的道德关怀和价值承担,这种呈现虽然不能称之为经典的范式,却为建构文学经典范式提供了审美选择。
[参考文献]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2).
[2]格非谈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江南三部曲”:因为乌托邦梦想,我们的现实不会变得非常可怕[EB/OL].http://www.yicai.com/news/2015/08/4670451.html.[3]格非.人面桃花[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4]格非.山河入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5]格非.春尽江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
[6]米兰·昆德拉.董强.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7]李凤亮.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8]〔美〕哈罗德·布鲁斯.江宁康.西方正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9]格非.《江南三部曲》:确有可能成为一部伟大的小说——格非《江南三部曲》学术研讨会发言纪要[Z].作家,2012.
[10]格非.小说就是对遗忘的一种反抗[N].新京报,2005-04-14.
责任编辑:张庆
[文章编号]1004—5856(2016)08—0060—04
[收稿日期]2015-10-19
[作者简介]彭园园(1994-),女,安徽舒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6.08.015
A Personal Story Under the History Background——The Classic Character of “Jiangnan Trilogy”
PENG Yuan-yuan
(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00,China)
Abstract:The “Jiangnan trilogy” is Ge Fei’s personal story constructed with realistic theme. The gener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makes the story independent and creative and presents the writer’s real intention. To construct modern literary classic works is the requirement of time.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 between in-and-out spaces and also the relation between stories are analyzed to explore how to construct a literary structure beyond history dimension. The classic characters are examined.
Key words:“Jiangnan trilogy”;fiction;realistic;history;class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