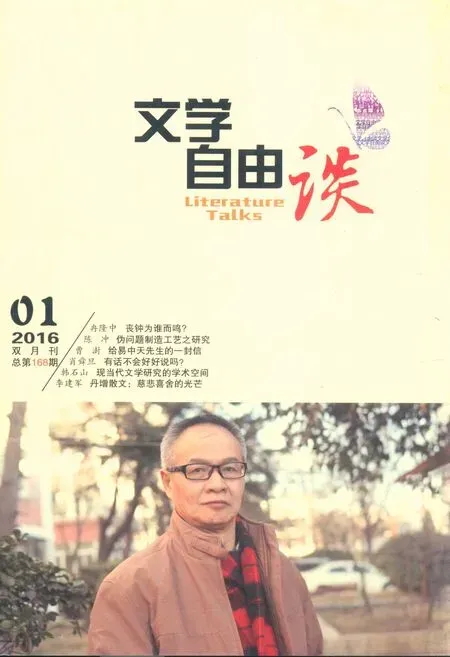伪问题制造工艺之研究
陈冲
伪问题制造工艺之研究
陈冲
12306验证码的文学意义
进入12月,春运火车票开始预售,网上抢票发令枪响。让众多摩拳擦掌已久的抢票者措手不及的,是铁路部门采用了新的验证码,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新的验证方式,即不再是简单地输入几个指定的字母数字,而是要在一堆图片中选出指定的物件。这个出人意料的举措,立刻引来一片骂声。真是说什么的都有啊!如果中国那句老话——千夫所指无疾而终——真的应验,恐怕铁路部门早死过一百次都不止了。区区没有春运期间乘坐火车的冒险计划,事不关己,袖手旁观,当个热闹看,不亦说乎?不巧的是,某一刹那,不知大脑中哪两根弦没有搭对,猛然间似乎有会于心,觉得这个极受诟病的验证码,却对文学颇有意义,套用那句现成话,说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就算有点过头,也不是过头得很严重。
这个“某一刹那”,是因为看到了数百种骂法中之一种:“12306验证码比高考题还难。”在有条件地认同了这个说法之后,我做了个延伸思考:它是不是比做硕士论文还难?思考的结果是,在相同的条件下,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把这个逻辑链再做个反推,那么就会推出这样的结果:对于那些不面对高考、不需要做硕士论文的人来说,验证码的难度要低一些。
验证码是个新事物,但这儿遇到的却是个古老的问题:人机关系问题。验证码的设计思路绝对正确。既然它的作用就是为了区别来者是一个大活人,还是某种机器(抢票插件或软件),那么采用的办法自然就是提出一些机器不能辨认、只有大活人才能辨识的选项。如果说这一批验证码的设计者还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地方,那就是他们设计之初没有想到与教育部门充分沟通。如果他们能了解,现在学校里所教的,大部分正是那些机器可以辨识的东西,他们理应放弃这种设计思路的。我们的学校教育,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已经成功地将两代至三代人中的大多数,教成了只能辨识那些机器可以辨识的东西的“学者”,这样的验证码,就很难将大活人挑出来了。
而在这样一个遗害无穷的过程中,文学中的某一部分,却扮演过而且仍在扮演着受益者的角色。那些由文学作品提供的机器可以辨识的东西,不断被只会辨识这种东西的读者欣欣然接受,并被其中的一部分佼佼者彰彰然称赞。这样一种供需关系,构成了一个自足的系统,并在不断循环往复中日益牢固和稳定。老一代佼佼者培养出第二代佼佼者,然后第二代正在培养着第三代。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们渐据要津,形成了学院派批评占据文学批评主流的局面,原来的主从关系也就颠倒过来,作家要使自己的作品得到批评界的认可,就得把它写成某种机器可以辨识的东西。那些只有大活人才能明白的东西,人家看不懂啊!当然,等到进入下一轮循环,作家仍然是受益者。既然批评家已经退化到只会辨识那些机器能够辨识的东西,对除此之外的事物不再有任何兴趣、感觉,作家也就尽可以放开手脚,施展《山海经》式的笔法,在那片生活的草地上或信马由缰,或纵横驰骋,逮着什么说什么,说到哪儿算哪儿。那可真叫一个尽兴,痛快!
举个例子吧。在一位著名作家(贾平凹)的一部著名作品(《老生》)里,有一大段“语怪”式的描写,讲述政府将金圆券作废给当地老百姓所造成的深重苦难。“政府发行了西北农民银行的纸币,金圆券作废了。”这个作废,不是停止流通、限期兑换成指定的新币再用,而是从根本上不再承认它是货币——钱了。一向喜欢哭穷的村民们,原来家中都存着金圆券呢,现在“全叫了苦”,“拿出来一卷的、一沓的、一捆的,哭着在门口烧”。洪家父子是“在院子里烧”,“儿子把钱整沓丢到火堆,他爹嫌整沓烧不透,让一张一张分开烧”。村里最有钱的王财东,“钱多得能砸死人”,他老婆把钱铺在炕上,“铺了一层没铺完”。“王财东没有烧金圆券”,“用油纸包了,装在瓮里,又藏在后屋的地窖里”,过些日子就“取出来一捆一捆摊在院子里晒太阳”。然后用了两页,写他后来怎样“脑子糊起来”,又怎样把钱埋在了北城门外后山根的祖坟上,祖坟进了水,“透过油纸把钱湿了,粘在一起,一揭就烂了”。这种事的真假,机器是无法辨识的,所以批评家们连眼角的余光都不会往这上面扫一扫。批评家们关心的是自己的论文。比如您可以在最新一期刊物上读到若干篇研究这位作家的论文,有研究“贾平凹的评价”的,有研究对贾平凹的某几部长篇小说如何进行“符号学解读”的。您甚至可以在某篇论文的末尾,看到某种标注,注明该篇论文是“X省社会科学基金《贾平凹XX研究》(项目编号:2014 XXX)”的“阶段性成果”等字样。您完全有可能看到,某位研究者认为在研究贾平凹的某几部长篇小说时,应该建立一种“社会三元模式”,即将小说中的人物划分为三个大项——正项、中项、异项(标出项)。您圣明,这样一来,机器就可以很容易地对小说进行辨识了。然而,您恐怕很难指望会有批评家去辨识金圆券作废问题。任何一个政府,有可能将正在流通的货币宣布“作废”吗?如果不让居民用旧币按一定比价兑换新币,那么新币将通过什么渠道投放到市场中去?这个地区是不是就得退回到以货易货的原始交易方式?否则,它的商品经济将如何运行?当这个地区里所有的居民全都彻底丧失了购买能力之后,商店里的东西还能卖给谁?
是啊是啊是啊,这些东西机器是无法辨识的。而一旦大活人们也失去了对它们的辨识能力,它们就成了某种无解的N 元N次方程,任由作家们去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了。
就像那个12306验证码。
这个过程持续到现在,不知不觉间就形成了一个特定的人群。标识这个人群的方法,虽然也可以采用年龄段划分,但更可靠的还是职称。在对浩如烟海的文学论文有了一定的阅读量之后,我发现其中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具有某种共同的特点,根据这种特点,我把这种论文命名为“副教授论文”。当然,我依据的是特点,并没有一一去查它们的作者职称。这个人群面对着专业生涯的最后一跳,需要发表够数并合格的论文去评教授职称。“论”什么和怎么“论”都是问题,但根本性的一条,就是得把论文写得机器可以辨识,以免“高评委”不知道该怎么给你打分。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我举了下面这条纯属偶然——我刚好在写到这一段时读到了它。它是这样开头(也就是立论)的:“当个人生命经验已经成为诗歌写作中的有效起点的时候,对于许多诗歌写作者来说,面临如何将个人经验的有效性转变为诗歌经验的有效性问题。”这儿“论”及的问题,不是太高深,也就是副教授一级的吧。对文学有一定认识的人都知道,“个人生命经验”从来都是一切文学写作的起点,非自今日始,亦不仅限于诗歌写作,但是由这个“起点”所开启的文学写作,能否成为一次“有效”的写作,则要由多种多样的因素来决定,存在着多种做出判断的可能性,比如其中的一种,就是看这种个人经验是否在写作中获得了普遍意义。很明显,这种判断,无论是认知判断,还是价值判断,都是机器无法完成的。所以得把那些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剔除,让它只剩下一个“个人经验”和“诗歌经验”之间的转换,机器就可以很容易地辨识了。而这样一来,可以“论”的“论题”也得到了充分的扩展。我想大家都知道,用来评职称的论文,必须是传播正能量的,拿一篇批判性的论文去参评,等于是故意让高评委们为难。现在好了,即使是那种以个人经验为起点,又止步于身边琐事的作品,比如我们常说的“一己悲欢”“杯水风波”之类,只要已经转变为“诗歌经验”了,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加以赞扬乃至吹捧了。
“为什么”和“怎么办”
收拾最近两个月的旧报纸,瞥见了一个大标题。向毛主席保证,绝非故意,实是因为那大标题位置醒目,字号又大,想不看见都难,这才看见了。那大标题是:“新媒体时代文学何为?”
这个“何为”,就是“怎么办”的意思。
我住的地方,是单位宿舍区,冬季取暖,靠一个大哥单位的锅炉供热,一大片宿舍楼里的住户,都习惯了冬天不低于20摄氏度的室温。去年冬天,在政府的多年敦促之下,也是那台锅炉实在太旧了,终于改为集中供热,与供热单位所签的合同规定,室温保持在18摄氏度(正负1度)。结果就总是在将到不到17摄氏度那个区间徘徊。住户们冻得实在难以忍受了,那天就说要每家去一个人,开个会,讨论一下怎么办。我没去。凡是一大帮人在一块儿讨论“怎么办”,都不会有任何结果,除非是有“大拿”事先已经拿定了主意,再让大伙表示一下同意,才会形成一个“决议”。事后听说,这个会也有人事先拿了主意,要去市政府上访,开会是为了动员大家参加,但这几个拿主意的人都不是“大拿”,没多少人听他们的,反倒是会上出了明白人,建议大家先想想“为什么”,然后再讨论“怎么办”。这下不对了。暖气为什么不热?您得先看看那是谁烧的。这家供热单位的全称里,写明了有“市投”二字。什么叫“市投”?就是由市政府投资成立的“公司”。你到市政府上访,去告市政府的公司,那叫什么?对了,叫“与虎谋皮”。明白了“为什么”,还有“怎么办”吗?没有了。冻豆腐——难拌!实际上,到了今年冬天,室温还是17度,但“怎么办”的问题却自行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各家想各家的办法。有些老人去投奔儿女了,那边的暖气热一些。我的办法,是在家里也穿上了棉袄棉裤,再不行就开空调嘛。
杨庆祥副教授就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问题,还写了一本相当厚的书:《80后怎么办?》。既然涉及怎么办的会不参加,同类的书也就没有看。据一位说话还算靠谱的朋友介绍,这本书里提出的最具针对性的问题,就是房子问题。我能意识到这说法有以偏概全的危险,那么厚一本书,不可能只说到房子问题,但又相信它可能抓住了要害,因为我自己也确实认为,这一拨人中的绝大多数,长大以后最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就是买房。如果说上一个十年那拨人,最不幸的就是赶上了取消公房分配制度,但房子总算还相对便宜,80后这一拨,却又赶上了房价飚升。然而你只要想一想,房价为什么会在短短几年里翻了四五倍乃至七八倍,立刻就能明白这种事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怎么办”的。实际上,这个问题可以说并不存在,也可以说已经解决,彰彰然明摆着的现实,就是这拨人中的绝绝绝大多数,并没有露宿街头。当然啦,猪往前拱,鸡往后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决之道,各人自去想各人的办法,一大帮人讨论“怎么办”,能有啥结果?至于其他一些烦恼,比如想买的东西买不起,想做的事做不成,那是每个世纪从00后到90后都会有的事,而且往往都是“怎么办”都办不成的事,真是没啥值得讨论的。然而,对于需要写论文的人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越是这样的问题,越是可以围绕它制造出大批量的论文,而更重要的是——这种论文是机器可以辨识的。
如果你基本上被我上面的研究说服了,不用我再多说,你就能明白“新媒体时代文学何为”是个伪问题了。“文学”何物?它是一个个作家所写的一个个作品的总和。正常地说,即使是同一个作家,也不会总写同一个模样的作品,那么,文学又怎么可能按同一个“何”去“为”?但是,越是这样的问题,越可以议论纷纷直至议论不休,因为它与作家的创作实践无关,而且机器很容易加以辨识。假如——我是说假如——有人突发奇想,说既然已经到了新媒体时代,贾平凹先生的小说里是不是也应该多一点现代意识?我猜想,拿这样的论文去评职称,多半会让高评委们很为难,还是那个理由——因为这种东西是机器很难辨识的。要说巧也真是巧,马上就碰到一个例子。在一篇论文里,就有这样的论述:“如能超越‘现代性’视域,并有效克服现代性理论话语及与之密切相关之文学史观念的偏狭,……围绕贾平凹作品‘落后’‘守旧’及‘反现代性’的批评,顿时失去了批判与解释的效力而变成‘伪问题’。”您瞧,如果有A,所以有B,这种推论,机器立刻就能辨识。从“有A”到“有B”,表明“逻辑”正在运行。须得是尚未被机器化的大活人,才知道正常的逻辑推论必须是从“因为”有A到所以有B,不能是“如果”。如果有人偏要坚守“现代性”视域,认为一个人既然活在21世纪,就理应用生活于21世纪的人的眼光去看世界,而不是用《山海经》的眼光去认识现实的生活,是不是那种“偏狭”的批判与解释仍然有效?
当然,这样的论述和论证,得大活人开动脑筋去好好想一想,而且应该还是相当烧脑的问题,机器肯定是无法完成的。
城乡对立与现代性
我所居住的城市有个雅号叫“国际庄”,它的由来,是因为从20多年前开始,当局就不断讲要把它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也是20多年前吧,这个城市出现了一个“电子城”,初时并不显眼,经过方方面面的持续努力,渐渐有了人气,最兴旺的时候,人多得摩肩接踵,在商铺间的通道上走,想走快点都不行。原因自然有多个,但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东西便宜。也不是便宜很多,就是便宜那么一点,大略说,同样的东西,100元里能便宜个5到10元。现在则是一落千丈了。前不久我去过一次,怎么说呢,简单说,一眼就能看出来,卖东西的人比买东西的人多。原因自然也有多个,但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停车费太贵。按物价局的规定,这个城市的停车费是每次2元,而电子城是每次10元,大的节假日20元。说真的,有些看上去很复杂的事,动脑筋一想,就这么简单。不知有多少人“举报”过多少次,商铺店主们还“抗议”过,据说物价部门也“管”过,可就是不行。其实呢,这个事你只要想一想它为什么会这样,就知道它不会有“怎么办”了。
什么叫“现代都市”?盖房子不用砖了就叫“现代都市”?有了20层以上的高楼就叫“现代都市”?有了高架路就叫“现代都市”?有了地铁才能叫“现代都市”?不错,这些都是一个现代都市必不可少的硬件,但也只是硬件。那么,“现代都市”又有哪些软件是必不可少的?夜总会和八大胡同?大量的洗澡和洗脚的地方?信访接待站?证券交易所?全天候堵车?大街上奔驰和“奔奔”发生刮蹭?这些都是软件,但先得有一个“系统”,这些软件才能运行。什么是现代都市的“系统”?对了,现代文明。不知您看电视时注意到没有,总书记回到他当年任过县委书记的地方,出现在电视画面里的一位人士,头上就蒙了一块陈永贵式的白毛巾,而这块崭新、雪白的白毛巾,便彰彰明矣地说明着电子城前收高价停车费为什么会没有“怎么办”。
如果在同一块地面上同时存在着城市和农村,且两者在生活方式上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那么这块地面上的现代文明,只能在两者的相互推动、相辅相成中同时建立,不可能先在城市中建成,再向农村“推广”,当然也不可能存在玩一把“二元对立”的机会。事实上,如果您能用大活人的眼睛去观察,您会看到当下的现实,是农业文明向城市的渗透,远强于现代文明向农村的渗透。整个中国的文明现状,现代文明还处在弱势地位,还远没有强大到足以跟农业文明闹“对立”。
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生命册》荣获本届茅盾文学奖,我很认同。它是不是这四年中最好的五部长篇之一不重要,那原本就是个可以见仁见智的问题,重要的是它获“茅奖”是实至名归,不是名至实归。这个“实”,就在于它相当精准地呈现了当前现实中的真实景象——农业文明不仅在乡村,也在城市中到处弥漫。令人措手不及的是,偏偏是在“茅奖”的颁奖词中,竟出现了“在从传统乡土到现代都市的巨大跨越中,李佩甫深切关注着那些‘背负土地行走’的人们”的字样。当然,这是机器可以辨识的,一边是“传统乡土”,一边是“现代都市”,二元对立,简单明了。可是如果你用大活人的眼睛去看,你看到的乡土早已不再“传统”,你看到的都市还远没有“现代”,这就让机器无法辨识了。我对“茅奖”的评委一向敬重,所以我想,肯定是因为不小心受到传染,一时不察,才弄出这种“副教授式”的验证码来。
连“茅奖”评委会都难免受传染,可见那细菌或病毒是个多么不可忽视的存在。印象当中,拿城乡二元对立说事儿的论题恐怕不下五六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一个离国际庄不太远的地方举行的某高峰论坛,论题是“城与乡:想象中国的方法”。这个论题的句式,是对人脑的一次严峻的考验,我勉强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偷懒,但无法确定对不对。怎样想象中国是个啥模样?方法有很多种,如果你想知道最省事的方法,那就是——先想象一下“城”什么样,再想象一下“乡”什么样,中国的模样就有了。这就显出这种句式的优越性来了。按这种句式,你不动地方就能立马设计出一系列类似的论题,比如“男与女:想象人类的方法”,“官与民:想象和谐的方法”,“人与机:想象论文的写法”……
得,又回到了人机关系问题。这个古老的问题其实是有特定前提的。它是替机器说话的。它强调的是有些人做不到的事机器能做到,所以它认为人对机器的干预越少越好,干预越少,做出来的产品质量越好,精度越高。这个原则在机械制造领域里是正确和有效的。大活人越来越被排除在工艺流程之外。曾经有人担心这会造成大量失业,殊不知这个过程反而提高了活劳动的价值。这是因为问题还有另外一面——还有更多机器做不到的事只有人能做到。所谓“新媒体时代”,从技术层面上说,就是程序时代。程序一旦编好,人就没事干了。但也正因为如此,那些编程序的人才能拿到较高的薪酬。
人啊,去做那些机器做不了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