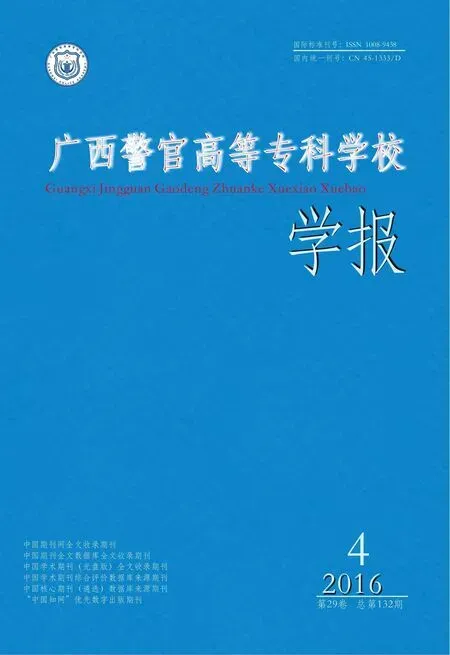触法未成年聋哑人的角色定位与保护处遇
陈 伟,王昌立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
触法未成年聋哑人的角色定位与保护处遇
陈伟,王昌立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401120)
未成年人心智发展的不成熟和聋哑人自身的生理缺陷导致自我控制和社会控制的双向失灵,进而引发与社会关系的恶性互动是导致该群体触法行为的根本原因。这类主体具有“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角色,触法未成年聋哑人的矫正和预防应当在角色定位澄清的基础上另行审视,转变对该特殊群体触法行为的守旧观念,形成权利保障与预防主导下的积极回应,以更好维系对触法未成年聋哑人的保护处遇,提前防范危害行为的发生。
未成年聋哑人;触法行为;角色定位;保护处遇
一、触法未成年聋哑人的现状分析
(一)“触法未成年聋哑人”的释义
在刑法专业槽内上,犯罪是指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了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由于未满14周岁的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故即使实施了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也不构成犯罪。那么,这一类在客观实施了犯罪行为、但不构成犯罪的群体该如何称谓,国内外学者及立法都做出了不同的回应。日本《少年法》将14周岁以下触犯刑罚法令的少年称为“触法少年”;美国《世界大百科全书》则将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称为“少年罪错行为”;台湾地区习惯上将未满12周岁之人触犯刑罚法令的行为称为“儿童犯罪”[1]。可见,对该群体实施的此一类行为没有统一的称谓,一般依照习惯予以称呼。
本文借鉴日本“触法”概念,并结合我国法律上使用“未成年人”术语的传统,将实施了犯罪行为的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聋哑人,以及实施了《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特定8类犯罪以外的14-16周岁的未成年聋哑人称之为“触法未成年聋哑人”。首先,“触法”一词,一方面明确了违反的法律类型——刑法,切合了本文所要探讨的如何对违反刑事法律但不承担刑罚的这一特殊群体如何处遇的主题;另一方面限定了行为主体的类型,只有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的违反刑事法的行为才称为触法,否则就是一般的犯罪行为。
(二)未成年聋哑人触法行为的新特点
1.触法未成年聋哑人呈现集团化新趋势
“言语构成的相同或相似是促使社会个体组成差异性团体的重要因素,于是掌握相同语言技巧的聋哑人就很容易聚集在一起形成固定的小团体”[2]。正是聋哑人在语言沟通上的一致性,使得该群体从社会中异化为一类特殊团体。在很大程度上,聋哑人犯罪团伙不仅仅是简单的犯罪实施过程的多人,而且形成了层次明晰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有专人负责组织团伙成员,有专人负责生活起居,有人负责寻找犯罪目标、掩护和实施犯罪,在犯罪过程中,他们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犯罪得手后按照已确定的分赃比例分得赃物。未成年聋哑人的触法行为不再是简单的个体现象,集团化的新趋势使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2.触法行为集中在财产犯罪方面
未成年聋哑人所涉及的触法类型大多集中在盗窃、抢夺、抢劫等财产犯罪上,而且作案手段较为单一,直接表现为偷盗或硬抢。这大概是由于未成年聋哑人自身条件的限制,难以实施诈骗等高难度犯罪。近年来,财产性犯罪占聋哑人犯罪的绝大多数,并呈上升态势。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在全国各地也陆续出现了未成年聋哑人的新犯罪类型,尤其在毒品犯罪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3.未成年聋哑人易受诱骗参与犯罪
由于聋哑人之间有着特殊的交流方式和与生俱来的心理认同感,犯罪团伙往往利用聋哑人此种天然的信任感,在给予一些物质诱惑后便取得其信赖,将其拐骗到违法犯罪团伙,强迫实施违法行为。从实践中犯罪团伙诱骗未成年聋哑人参与犯罪的方式上来看,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直接在聋哑人学校以暴力、胁迫手段强制在校聋哑人加入犯罪团伙;二是以网络社交媒体为平台,通过找工作、交朋友等虚假事由欺骗未成年聋哑人,并对其实施身体控制;三是通过给予某些物质恩惠引诱未成年聋哑人加入犯罪团伙。
二、自我控制与社会控制的双向失灵:未成年聋哑人触法行为的根源所在
未成年聋哑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以及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该特殊群体触法行为新特点,突出地呈现出导致未成年聋哑人触法行为的原因与一般犯罪行为的显著差异。因此,为切实有针对性地做好触法未成年聋哑人的矫正与预防工作,必须对该特殊群体的触法原因给予着重关注。
(一)生理与心智的双重缺陷导致自我控制障碍
未成年聋哑人自我控制机制,是指“他们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由知识、需求、性格、情绪体验、社会意识五个要素构成的‘心理纽带’对自我行为的约束”[3]。由于未成年聋哑人的特殊体质导致其在上述五个要素层面上都或多或少地出现短缺,进而导致该要素对自我控制作用力的减弱或灭失,出现自我控制障碍而实施一连串的触法行为。
1.语言与听力的长久性缺失造成社会交往缺乏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交流,只有有了语言才能进行广泛的社会交往,进而在一定领域内形成有着相同或相似价值观的社会共同体。生活在无声世界里的未成年聋哑人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通过手语进行简单的交流,无法用言语的形式与社会进行广泛的沟通,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隔绝了未成年聋哑人与社会的交往。一方面由于未成年聋哑人社会交往范围狭窄,造成未成年聋哑人性格孤僻,不愿和人交往;另一方面由于与社会交往困难,同时加之生理缺陷,常常导致社会对该群体的歧视,增加了该群体与社会交往的难度。语言和听力的长久性缺失不仅给未成年聋哑人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更是对其融入社会产生了无形的阻隔。
2.心智发展的阶段性缺陷造成社会认知能力减弱
未成年聋哑人尚处于心智发展阶段,正是由于心智发展的阶段性缺陷导致其社会认知能力不强,触法行为时有发生。“青春期阶段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阶段,充满了巨变和伦乱,导致青少年经历了许多动荡,这是这段时期的家常便饭”[4]。未成年时期是社会化的重要阶段,是由自然人向社会人过渡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的特殊心理决定了少年比成年人具有更多的犯罪倾向”[5]。未成年聋哑人心智的不成熟致使其尚不能完全辨认是非,进而选择适当的行为,反而出现易冲动、暴力性的不良行为。同时,由于未成年聋哑人的入学率极低,导致其通过学校教育加速社会化的渠道堵塞,社会认识能力显著低于同等年龄的未成年人,这也加剧了该特殊群体触法行为的严重性。
(二)社会保护制度缺失激发社会控制失范
社会控制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特拉维斯·赫希提出,其认为任何人都有犯罪的倾向,个体与社会的联系可以削弱或阻止个体进行违反社会准则的越轨行为;当此种联系相对薄弱时,个体就会无约束地随意进行犯罪活动[6]18。从社会控制理论出发,未成年聋哑人实施触法行为并非完全归因于个体,社会更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可以肯定地说,相对于未成年人群体,社会对未成年聋哑人的关注显然不够,反而歧视态度愈演愈烈,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该特殊群体与社会产生隔阂。
具体来讲,导致当前我国未成年聋哑人犯罪的原因,可以分别从社会保障力度不足、家庭教育错位、特殊学校教育缺失等方面作具体阐释。首先,社会没有为未成年聋哑人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导致其处于窘迫的生活状态,因贪财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再加之大多数聋哑人文化程度较低,欠缺相应的职业技能,不易找到较为稳定的工作,故缺乏稳定的生活来源,导致其无奈而实施侵财犯罪。
其次,由于聋哑人生理的特殊性,导致家庭教育错位,或放任惯纵或嫌弃不管。有些家长因对聋哑人心生怜悯,对其百般呵护、百依百顺,导致教育监管不严。有的家长对聋哑人有所嫌弃,对其不管不问,放任自流,将其推向社会。未成年聋哑人在家庭生活中找不到应有的关爱,致使出现了警方在解救被诱骗未成年聋哑人时,他们竟不愿回家,由此可见家庭对于未成年聋哑人成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最后,特殊教育学校普及率较低,导致聋童入学率仅为9%[7]。未成年聋哑人文化素质的低下致使其再社会化严重受阻。另一方面,现有的特殊教育体系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法制教育方面更是乏善可陈,大部分特殊教育学校没有开设法制教育课,缺乏对在校聋哑人的法制宣传和教育,使得相当数量的未成年聋哑人因不懂法而走上违法道路。由此可见,不管是整个社会环境还是家庭和学校等社会单位,都不可避免地要承担未成年聋哑人触法行为的责任。
(三)自我控制与社会控制的失灵引发个体与社会的恶性互动
未成年聋哑人触法行为原因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恶性互动上。首先,聋哑人自身的生理缺陷导致其社会化进程受阻,心智能力成长不完全,进而导致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较为欠缺,因而更容易实施违法行为。其次,由于聋哑人生理的缺陷致使社会的有色看待,既缺少群体认同的心理抚慰,又无应有的社会保障,社会对聋哑人的不接纳导致该群体无法顺利融入社会中,正常的社会秩序也无法约束聋哑人。最后,生理缺陷导致的社会不接纳,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聋哑人的心理抵触,致使其无法按约遵守社会规则、维护社会秩序,进而引发触法行为的发生。
由于未成年聋哑人兼具未成年人和聋哑人两类特殊群体的特殊体质,从而导致在自身控制方面存在不可挽回的诸多缺憾。社会层面的保护制度缺失加剧了前者对该群体的负面影响,进而无限放大这一缺憾,最终造成了未成年聋哑人触法行为的多发性和严重性。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自我控制机制失灵的内在原因和社会控制机制薄弱的外在原因是导致未成年犯罪的成因所在[8]193-195。但是,自我控制障碍与社会控制失范不是各自独立对触法未成年聋哑人施加不利影响,而是二者之间的恶性互动放大了这种不利影响,加剧了二者的矛盾,导致未成年聋哑人触法行为的原因相较于一般未成年人具有显著的复杂性。
三、“受害者”角色:触法未成年聋哑人的角色定位
未成年聋哑人触法行为的特殊性和严重性,一方面表现在行为主体的特殊性和发案率呈现陡坡式的增加,涉案人数不断突破,团伙作案、集团犯罪等现象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未成年聋哑人在其触法行为中“受害者”的角色定位。前者只是呈现出的问题表象,未成年聋哑人实施触法行为更深层次的严重性在于聋哑人不只是违法者,更是受害者。触法未成年聋哑人客观上实施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其作为违法者是对其行为进行矫正和预防的前提,如何有针对性地实施矫正和预防措施则要从该特殊群体实施触法行为的原因着手。
(一)社会排斥将未成年聋哑人推向“受害者”角色
从宏观上来讲,未成年聋哑人“受害者”角色主要体现在社会未给予该特殊群体足够的关怀,导致权利得不到保障而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致使其无法通过正当的行为实现自身所设目标或价值,从而被迫违背社会主流价值观实施越轨行为。同时,由于对幕后操纵聋哑人的不法分子打击力度不够,造成幕后操纵者无需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放纵”这种恶劣的行为,使得聋哑人团伙犯罪案件一直居高不下。社会保障及法律制度的缺失将未成年聋哑人遗忘在社会关注的角落,将其被动性地推向“受害者”角色,使其承担本不应承受的不利社会状况,造成与社会的隔阂。
在实践中解救被拐骗操纵的未成年聋哑人时,令人唏嘘的是有相当数量的未成年聋哑人不愿跟随警方离开犯罪住处,原因不是他们违法成瘾,而是担心他们被解救后仍无法融入社会,依旧遭到社会的冷眼相待,甚至会因为曾经的违法行为而变本加厉。这些担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目前社会状况确实未实现对未成年聋哑人全面的生活保障与足够的人文关怀。与其在此种环境下受人歧视,还不如继续呆在犯罪团伙中,至少每天有“事”做,有饭吃,有人交流。我们会感叹,目前的社会竟无法保证未成年聋哑人选择正确的行为,却逼迫他们实施违法行为,此种“受害者”角色可见一斑。
(二)拐骗操纵使未成年聋哑人成为“受害者”角色
从微观上来讲,未成年聋哑人“受害者”角色则表现在个案中该特殊群体易被拐骗操纵从而被迫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在牵涉未成年聋哑人的违法犯罪案件中,有相当数量的未成年聋哑人是受不法分子的蛊惑、拐骗甚至强迫而参与违法犯罪活动。这些不法分子有的也是聋哑人,他们利用聋哑人间天生的信任感获取信任,进而操纵实施违法犯罪。正是未成年聋哑人在心理上的不成熟性和生理上的缺陷性,导致该特殊群体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将其拐骗或诱骗加入犯罪团伙。在这一层面上,毫无疑问未成年聋哑人由于被诱骗而实施违法犯罪,本身就处于“受害者”的地位。
根据公安部2013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显示,公安部开展专项行动,摧毁了61个拐骗操纵聋哑人犯罪团伙,抓捕犯罪嫌疑人360余名,解救被拐聋哑人70余名。同时,全国各地也纷纷报道了操纵未成年聋哑人犯罪的犯罪团伙。如《沈阳晚报》报道,2014年沈阳打掉了震惊全国的特大扒窃团伙。该团伙成员多达数十人,流窜全国多个地区,从边远山区拐骗未成年聋哑人,暴力威胁强迫他们实施盗窃。2013年长沙市公安局成功摧毁了一个典型的以“找工作”为由操纵聋哑人扒窃的犯罪团伙,抓获团伙成员11名。从这些新闻报道中,可见清晰地察觉出实践中操纵未成年聋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普遍性及严重性。在这些案件中,未成年聋哑人“受害者”角色一直未曾改变,他们或被骗或被强迫加入犯罪团伙,被人操纵实施触法行为,成为幕后操纵者谋财的犯罪工具。
因此,社会对未成年聋哑人触法行为的关注不仅仅只是,或者主要不是为了如何对未成年聋哑人实施刑罚以惩罚他们的犯罪行为,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害者。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关注焦点应该是如何更加有效地保护这一特殊群体,防止其被不法分子所笼络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未成年人初次犯罪后社会对其采取的反应方式是否理性,与其未来是否会陷入犯罪的泥潭关系重大。”[8]严格贯彻未成年人司法“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能够让其深刻体会到社会的关爱,摒弃标签效应带来的自暴自弃的不良心态。反之,如果让未成年聋哑人承受过重的处罚,颠覆其“受害者”角色,必然造成心理失衡而抗拒复归社会。
四、权利保护的社会责任:未成年聋哑人触法的处遇与预防
正如笔者上述分析,未成年聋哑人无意识的生理缺陷和社会的不接纳是导致未成年聋哑人触法行为的重要原因,因而从刑法“意志自由”的责任刑罚角度来处理触法未成年聋哑人似乎不合时宜。对未成年聋哑人这一特殊群体触法进行矫正及预防时,必须考虑这一群体的特殊性质,结合未成年聋哑人犯罪的原因分析,探索出治标治本的对策。在聋哑人犯罪团伙中,受诱骗操纵的未成年聋哑人首先是受害者,其次才是加害者,因此对未成年聋哑人触法的矫正和预防应当在角色定位澄清的基础上另行审视。
(一)区别对待:触法未成年聋哑人处遇方式的特殊性
对于触法未成年聋哑人的矫正,在司法实践中也是问题重重,最引人关注的是司法机关教育改造的手段与聋哑青少年的认知能力不相适应[9]。正是因为未成年聋哑人有着特殊的语言方式和生理特点,理所当然地要求采用与正常人相区别的教育矫正手段和方法。因此,实践必须把握未成年聋哑人的特殊性,考究现行处遇方式是否适宜该特殊群体的矫正。
1.收容教养不适宜触法未成年聋哑人的处遇
我国刑法第十七条对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的法律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虽然有学者将收容教养的法律性质界定为司法保护教育价值措施,即为了给触法未成年人提供一种社会救济或社会福利。但是在实践执行过程中,收容教养却异化为所谓的劳动教养,收容教育机构依附于少年犯管教所,缺乏独立的教养场所。教养方式几乎照搬管教所自行制定的教养规则和教养内容,收容教养的内容除劳动教育薄弱外,与劳动教养没有本质差异。教养机构的封闭性、教养方式的简单性、教养内容的欠针对性,使得目前的收容教养沦为变相的监管和监禁。同时,劳动教养废止后,原有进行收容教养的场所不复存在,对未成年聋哑人保护式处遇也就成为水中之月难以实现。
2.社区矫正不宜扩展到对触法未成年聋哑人的处遇
《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制度纳入刑法范畴,引起学者们对这一制度的广泛关注。其中建议借鉴域外立法,将触法未成年人纳入社区矫正范围的呼声持续不断。可以肯定地说,对处于社会化关键时期的未成年人来说,实施开放性的社区矫正有利于其社会化进程,对矫正其行为顺利复归社会起着突出的作用。但是,具体到未成年聋哑人这一特殊群体,必须考量社会矫正是否真正能够对其产生有利作用。一方面,未成年聋哑人交流方式的特殊性导致其无法与社区矫正服务人员互动,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化力量在矫正中的作用。另一方面,社区矫正服务人员无法为未成年聋哑人提供适当的矫正手段,社会保护不力是造成未成年聋哑人触法的重要原因。对其行为的矫正应更侧重于给予相应的权利保护,使其在享有应有的社会权利中潜移默化地摒弃不良行为方式。然而社区矫正服务人员只是实施矫正措施的个体,无法提供更多的权利保护。
(二)特殊教育学校:触法未成年聋哑人处遇的主战场
1.学校教育矫正触法未成年人的源流
以学校教育的方式处遇触法未成年人是对触法未成年人进行矫正的一大创举,主要形式是“工读学校”。“工读学校起源于18世纪中叶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曾创办孤儿院,被视为近代工读教育之前驱。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自20世纪20年代起曾创办高尔基工学团,在当时起到良好的、积极的预防和矫正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10]。我国也于建国后不久开始创办工读学校,负责教育、矫正和挽救“不良少年”。随着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工读学校的强制入学转变为自愿入学以来,工读学校学生数量急骤减少,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工读学校以特殊学校教育的方式实现对不良少年的行为矫正,一方面弥补了普通教育无法开展教育矫正的空缺,以专业化的教育形式矫正不良行为;另一方面,避免了因强制处罚而带来的标签效应,便于不良未成年人顺利复归社会。同样由于聋哑人有着特殊的交流方式,一般工读学校难以为其提供专门的教育,导致其放任自流无法接受有效的教育矫正。
2.通过特殊教育学校矫正触法未成年聋哑人的具体构想
特殊教育学校是国家为实现残疾儿童教育而专门设立的封闭式教育场所,在解决残疾儿童入学、提高残疾儿童素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殊教育学校作为矫正触法未成年聋哑人的方式具有可行性。首先,特殊教育学校是专门提供特殊教育的场所,学校内有着统一的沟通方式,便于开展教育矫正。其次,特殊教育学校是一种隔离式的教育场所,较好的隔绝了社会不良风气对触法未成年聋哑人的影响。最后,特殊教育学校不仅开展文化课教育,而且还传授学生生活、工作技能,使学生学会一技之长,增加自力更生的就业机会。
一方面,建立触法未成年聋哑人强制入学和适时退学机制。为更加有效地发挥特殊教育的矫正功能,法律应明确规定强制入学的触法未成年聋哑人类型。既不能拉低强制入学标准,致使特殊教育学校人满为患,导致学生和教师的比例失衡难以开展有效的矫正工作;也不能过度抬高强制入学标准,致使触法未成年聋哑人得不到专业的教育矫正而为以后再犯埋下伏笔。笔者认为,应当从两个方面考量强制入学的标准:一是未成年聋哑人触法行为的严重程度;二是触法未成年聋哑人的一贯表现。即使未成年聋哑人只是实施了较轻的触法行为,但是其平时有不良表现,也应强制入学进行封闭式的教育矫正。尽管特殊教育学校不是刑罚执行机构,但是当具有矫正未成年聋哑人的功能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微弱的标签效应。因此,不宜将触法未成年聋哑人长时间封闭在特殊教育学校,应建立适时退学机制,保证复归社会。同时,强制触法未成年聋哑人进入特殊教育学校的目的是教育矫正其不良行为,当经过一定时间的矫正后,如果评估其已被教育成能够遵纪守法的学生,应该允许其退学或转学至普通学校跟班就读。
另一方面,设置针对性的教学内容,突出对不良心理和行为的矫正。虽然在特殊教育学校,触法未成年聋哑人与普通聋哑人融合在一起接受教育,但是针对前者的触法行为应该设置专门的教学内容进行教育矫正。因此,对触法未成年聋哑人的教育应明显有别于普通在校聋哑人,在教学内容上应适度增加心理治疗、行为干预课程,以突出对触法未成年聋哑人不良心理和行为的矫正。需要强调的是开展法制教育的重要性,要进行遵法守法教育,弥补未成年聋哑人社会意识结构缺失,强化基本的善恶观念和责任意识,使其遵从社会秩序规则避免不当行为的发生。
除进行上述文化教育与心理矫正外,还应该进行必要的劳动教育和技能培训。未成年聋哑人正处于心智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特殊教育学校应针对触法未成年聋哑人开设劳动课程,培养其劳动意识,避免产生或沾染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同时,还应对触法未成年聋哑人进行技能培训,教会其一技之长以便进入社会中可以自谋职业。通过前述分析,未成年聋哑人触法行为以财产犯罪为主,侵财是其触法的主要目的,如果教会未成年聋哑人自谋职业的本领,培养其靠自己劳动创造价值的意识,则可以阻断未成年聋哑人实施触法行为的动机。
(三)社会保护:预防未成年聋哑人触法的治本之策
触法未成年聋哑人的“受害者”角色不仅决定着对其实施有别于其他触法未成年人的处遇措施,而且在预防该群体触法行为时更应注重权利的保障。“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未成年犯罪处遇原则,当面对未成年聋哑人这一特殊群体时,既要坚持这一原则将其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更要真对该群体的特殊性,适当扩大权利保护的范围,弥补未成年聋哑人权利保护的盲区。因此,对未成年聋哑人触法行为的预防要做好以下权利保护工作。
首先,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未成年聋哑人提供有尊严生存的社会环境。国家应完善有关法规、政策为未成年聋哑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摆脱生活窘境,从源头上切断财产犯罪的动机。现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只是对未成年人保护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具体可行的操作性措施,因此,一方面,国家必须重视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使对未成年聋哑人的保护有法可依。另一方面,社会在提供必要生活保障时,还应鼓励未成年聋哑人就业。古人云:“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因此,要针对聋哑人的特殊体质开展谋生技能培训、创业指导等,并“强化就业信息集散平台功能,多渠道鼓励各企事业单位提供适残岗位信息”[11],帮助该特殊群体实现自身的价值。
其次,提高义务教育或特殊教育的入学率,提高未成年聋哑人的文化素质,塑造健全人格。从当前我国聋哑教育发展的现状来看,特殊教育的发展显著滞后于普通教育,教学资源稀缺,教学层次单一。因此,国家应加快特殊教育学校的建设,鼓励民间非营利性组织成立特教机构,并尝试扩充特殊教育的层次,将学前教育纳入特殊特殊教育的范围。由于聋哑人特殊的生理缺陷导致其无法正常沟通交流,无法潜移默化地接受主流价值观念,如果再缺失学校教育,未成年聋哑人就难以融入社会。特殊教育的功能不仅在于使聋哑人学会手语交流,更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特征,弥补生理缺陷导致的社会化困境,加速再社会化的进程。
最后,强化家庭责任,优化家庭环境,培养未成年聋哑人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道德操守。未成年聋哑人的家长应承担起比每一健听家庭更重的监护责任,不仅在生活起居上给予特殊的关照,在德智教育上更应付出足够的精力;家长不应将聋哑子女视为家庭负担,一味地将责任推给社会,冷落聋哑子女的家庭地位。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家长的一言一行都对未成年聋哑人身心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家长应该为未成年聋哑人树立正面的形象,并正确引导其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时,家长应避免对未成年聋哑人或放任或溺爱的两种极端态度,加强对其行动的监督、给予家庭的关爱。
总之,未成年聋哑人触法行为的发生率呈现显著增长,已成为不得不关注的社会问题。未成年人心智发展的不成熟和聋哑人自身的生理缺陷导致其在自我控制和社会控制的双向失灵,进而引发与社会的恶性互动是导致该群体罪错行为多发的根本原因。未成年聋哑人在其触法行为中的“受害者”角色,决定了对其行为的矫正和预防仅靠处罚是不当且无效的,只有针对其“受害者”角色设计适宜的处遇和预防措施才是治标兼治本之策。以特殊教育学校为依托对触法未成年聋哑人进行教育矫正具有天然的优势,是值得推广的处遇方式。同时,也应注意合理配置教学资源、科学安排教学课程、严谨制定评估机制,为教育触法未成年聋哑人提供强力保障。矫正只是被迫应对,预防才是理性选择。应通过社会保障、学校教育、家庭监管三个层面的无缝衔接,做好未成年聋哑人的权利保护工作,从源头上防范这一特殊群体触法行为的发生。
[1]田宏杰.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未成年犯罪概念之比较研究[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3):22.
[2]任荣升.聋哑人犯罪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1:6.
[3]李凤奎.对未成年人犯罪成因及其对策的探讨[A].温景雄,狄小华,张薇.少年罪错司法防治的最新动向[C].北京:群众出版社,2010:193.
[4]杰弗里·阿内特.青少年心理学[M].段鑫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
[5]刘立杰.少年刑法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6.
[6]特拉维斯·赫希.少年犯罪原因探讨[M].吴忠宪,程振强,吴艳兰,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
[7]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研究资料——全国残疾儿童基本数据[EB/OL].(2008-04-07)[2015-11-14].http://www.cdpf.org.cn/sjzx/cjrgk/200804_3875.shtml.
[8]张远煌.从未成年犯罪特点看现行刑罚制度的缺陷[J].法学论坛,2008(1):92.
[9]朱鹏程.聋哑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的特点和预防对策[J].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4(3):60.
[10]石军.中国工读教育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反思[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5(2):17.
[11]杨蓉蓉.残疾青少年劳动就业状况及促进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5(4):15.
责任编辑:覃珠坚
On Role Positioning,Protection and Treatment of Juvenile Deaf-mutes Violating the Law
CHENWei,WANGChang-li
(School ofLaw,Southwest Universityof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401120,China)
The juveniles'immature mental development and the deaf-mutes'physical defects cause bidirectional malfunction in their self control and social control,and in turn,malignant interaction with social relations,which basically breeds the group's violation of law.Those subjects play dual roles of"the victims"and"the inflicter". Rectification and precaution of juvenile deaf-mutes violating the law call for our efforts to conduct separate examinations,transform old-fashioned concept for the special group's violation of law and develop positive right protection and prevention-oriented responses so as to better maintain protection and treatment of juvenile deaf-mutes violatingthe lawand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such dangerous behaviors in advance.
juvenile deaf-mutes;violation ofthe law;role positioning;protection and treatment
D669
A
1008-9438(2016)04-0001-07
2016-04-15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45.1333.D.20160729.1503.002.html
2015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建设项目
陈伟(1978-),男,湖北宜昌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刑事法学研究。王昌立(1990-),男,山东枣庄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2014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西南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刑事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