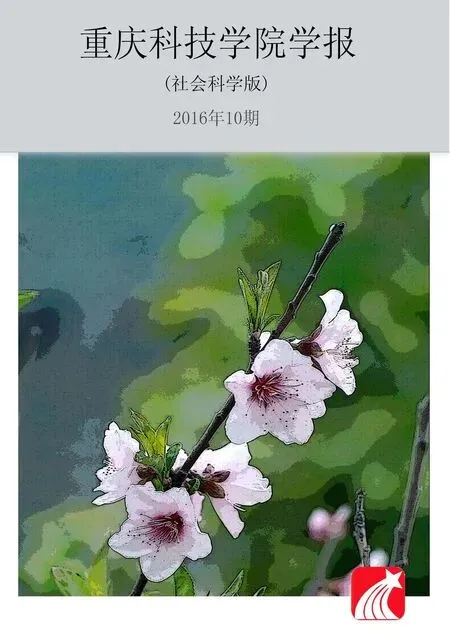时空变换下的第一人称叙事——析鲁迅小说中第一人称叙事的审美空间
李莎
时空变换下的第一人称叙事——析鲁迅小说中第一人称叙事的审美空间
李莎
鲁迅在《呐喊》和《彷徨》中运用了大量的第一人称叙事,以时间和空间的异同,将第一人称叙事结构分为3种类型: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第一人称叙事;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第一人称叙事;同一时间、同一空间的第一人称叙事。由此探讨了鲁迅如何将自己的体验和情感融合到虚构叙事中,让其作品成为既区别于传统小说,又有别于同时代作家作品的独特存在。
鲁迅;《呐喊》;《彷徨》;第一人称叙事;审美空间
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明显区别就是叙事结构的复杂化。鲁迅的小说以“表现的深刻和格式的特别”而享誉文坛。王富仁将鲁迅称为20世纪中国文化最为清醒的“守夜人”;李怡将鲁迅称为中国文化之“结”,除了对文化的深刻表现外,其作品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的“格式”。
鲁迅在《呐喊》和《彷徨》中用了很多的第一人称叙事。第一人称叙事有它的复杂性,作家若控制不好写作距离,不仅会给读者造成“我”即作者本人的误读,同时还会大大压缩审美空间。小说里的第一人称叙事是复杂的,而正是对于这种复杂性的不同把控,使得作家的水平有高下之分,其作品也有了优劣之分。
笔者以人称叙事为切入点,并以《呐喊》和《彷徨》中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为研究对象。《呐喊》和《彷徨》共计25篇。其中,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有12篇,包括《狂人日记》《孔乙己》《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故乡》《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虽然都是以第一人称叙事,但其策略和方式不尽相同,扩大了作者的表达空间和读者的阅读空间。下面从时间和空间的异同入手,从3个方面分析第一人称叙事的复杂性。
一、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第一人称叙事
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第一人称叙事是指在同一篇小说中,叙述者与主人公虽然都在讲述同一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情,但是二者明显处于不同的叙事空间中,一个是内叙述者,一个是外叙述者,二者对同一故事的讲述是有距离的。并且在故事发展中的参与度也是不同的,外叙述者往往是一个旁观者,而内叙述者即主人公是处于自我叙述的状态,他们分别构成了2个叙述层,这2个叙述层相互关照、相互阐释。这类小说有《狂人日记》《伤逝》和《孔乙己》。
《狂人日记》是以第一人称的日记体的叙述,但是在“我”叙述之前,鲁迅特别为其加了一个小序,这个小序是以“余”为叙事者,“余”的叙事是清醒的,“我”的叙事是混乱疯狂的,“余”和“我”构成了不同的叙事空间。“余”在序中说明了日记的来历,“余”是旁观者、是见证者,更是一个正常人对狂人的反观。“余”发现并整理日记的目的是“以供医家研究”。而日记中自言自语的“我”的想法是看似荒谬可笑的,“我”眼中的世界是一个吃人的世界,“我”在吃人的同时也要被人“吃”,虽然我知道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但还是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
从小说的结构看,“余”和“我”显然是处于2个叙事空间中,问题是作者为何在同一篇小说中用第一人称叙事构建起2个叙事空间?“余”的叙事可否不要?
如果去掉由“余”构建的叙事空间,那么,由“我”构成的叙事空间给读者的思考空间恐怕是不够的。首先,在逻辑上有问题。“我”的疯狂,“我”的狂人身份是由正常人去定义的,“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狂人,所以单个的“我”是没法以《狂人日记》的姿态进行叙述的。其次,“余”的叙事既说明了日记的来源,也为读者进行后面的阅读奠定了阅读基调,即一个患“迫害狂”的人的症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由“余”和“我”所构成的空间不仅仅是各自的叙述空间,还有第3个空间,即由隐含作者所构建起的空间,这个空间有作者的思想、态度,也有读者的感知和思考。“余”是中国传统的对自己的称谓,“余”的视角代表着传统的所谓正常人的态度和看法,“余”的心态是轻松的,态度也是冷静的。然而,“我”却是愤怒又恐惧的,“我”拼命地呐喊却是苍白无力的,“我”是常人眼里的疯子,他们认为的仁义道德的世界在“我”看来分明是“吃人”的。可以说,“余”的叙事空间是看客的“冷”,“我”的叙事空间是狂人的“热”,这一冷一热的空间碰撞出的是作者的彷徨与痛苦,读者的思考与共鸣。
《狂人日记》正是因为“余”与“我”的共同叙述,才使得作者有了更多的表达空间,也让读者不得不思考自己在“余”和“我”之间该如何定位。同样,《孔乙己》里面的小伙计,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让我们在见证孔乙己境遇的同时,也开始反观“我”所代表的群体。“我”的叙述淡然而冷漠,“我”的态度正是看客们的态度,通过“我”的视角见证了孔乙己的悲剧命运,在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力度加大的同时,也揭示了更多造成悲剧的原因。
《伤逝》的叙事类似于《狂人日记》,都是第一人称的独白,并且副标题“涓生手记”说明了这也是一种发现手稿型的小说,即有一个区别于“我”的人将手稿发现,身份类似于《狂人日记》中的“余”,只是这个发现涓生手记的人未出现在小说正文的叙事中,而在这2个叙事空间之外当然还有隐含作者的叙述。与《狂人日记》不同的是,这个发现涓生手记的外叙述者的消失让读者对隐含作者态度的把握更加扑朔迷离。
这种类似套中套结构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不仅可以减少作者直接介入文本,而且可以使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在全面展现的同时,也埋得更深、更复杂。那么,如何感知作者的真正意图?吴晓东在文章《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中认为,这是一种“反讽”的方式,这种第一人称叙事是具有反讽性质的,它在复杂化小说的内涵的同时,也使小说呈现出更丰富的价值判断和历史取向。但是,这种结构的第一人称叙事还不能完全说是反讽,毕竟叙事者与隐含作者的价值取向也并非完全相悖,并且隐含作者也不同于作者。正如杨义所说:“叙述者无非是作者在文本中的心灵投影,或者他使投影发生曲变的故弄玄虚的一种叙事谋略。”[1]206将第一人称叙事置于同一时间、不同空间里,构成一个外叙述者,一个内叙述者,二者在拉开距离叙述的同时,也给了作者更多的表达空间和读者更高层次的观察思考。
二、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第一人称叙事
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第一人称叙事指的是小说的整个叙事都是由“我”完成的,不存在内、外叙述,只是“我”在时间上一分为二,一个是过去的“我”,一个是现在的“我”,2个视角是重叠交叉的,“我”的叙述总体上是缓慢低沉的,整篇文章弥漫着回忆的气息。这类小说有《故乡》《社戏》和《祝福》。
《故乡》的叙述者是“我”,但是“我”却分属于2个阶段:一个是童年时的“我”。这个时候的“我”是无忧无虑的,父亲在世,家境也好,闰土是那个带着银项圈手握钢叉虎生虎气的少年,杨二嫂还是豆腐西施。另一个是成年后的“我”。这时“我”辛苦辗转地生活,没有大宅第,寓所也是租来的,而少年玩伴闰土已不是我记忆中的闰土了,他叫我“老爷”,他叫他的孩子水生给我磕头,杨二嫂也已失去了先前的美丽,变得凶悍刻薄并且自私。一切都在对比,记忆和现实在发生着猛烈的冲突,但还好,有“我”的侄儿宏儿和闰土的孩子水生作为这种冲突的缓和以及巨大失望中的希望。
沿着回乡这条线索,通过叙述者“我”的叙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叙述空间。这个叙述者“我”不再像前面讨论的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第一人称叙述,小说并没有一个外叙述者,仅仅是“我”来叙述,不同的是“我”的身份在发生变化,构成了2种不同的视角。
成年的“我”看到的故乡是这样的:时候既然是深冬……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
而童年的“我”看到的故乡却是: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西瓜。
正是这2种不同的视角,让一篇回忆性的文章有了冲击的力度,让读者顺着成人的视角回忆儿童,再从儿童的视角反观现在,在这种对照中时间对人无情的压力凸显出来,再加上整个空间笼罩的回忆气氛,在舒缓低沉里体会人与时间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通过不同时期的2个“我”的讲述表露出隐含作者悲哀痛苦的感情。
同样,在《社戏》中也有2个不同时期的“我”:一个是成年后对看大戏失望的“我”;一个是小时候去外婆家和小朋友在夜间摇船去看戏的“我”。现在的“我”因为2次在都市看戏失望而开始回忆儿时看的戏,想起十一二岁时看戏的快乐的日子,直到最后,成年的“我”还念念不忘看戏那夜:“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2]1362种年龄对看戏的不同感受,2种感受的不同笔墨的描述,成年看戏的经历是速成且无趣的,童年看戏的经历是娓娓道来和充满乐趣的,而这种对照流露出的正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更是一种对逝去时光的怀念。
回乡题材的《祝福》也是由“我”来叙述的,不同于《故乡》和《社戏》中儿童的“我”和成年的“我”的划分,《祝福》中的“我”是以对祥林嫂的回忆为划分点。现在的“我”回乡遇到祥林嫂对她的描述和听闻她死了对她曾经的事情的描述,更多的笔墨在过去的“我”见到过去的祥林嫂,让读者先通过现在的“我”看到祥林嫂的悲剧结局,再透过回忆,看到过去的祥林嫂,从而体悟这种悲剧的原因。
在同一空间中,由于时间的变化使小说呈现出更多的历史感,既将人带入回忆,又让人看到人与时间的关系,以及人面对时间的无力感。
三、同一时间、同一空间的第一人称叙事
同一时间、同一空间的第一人称叙事是指叙述者和主人公处于同一个叙事时间和空间,叙述者与主人公的立场大都不同,但这2个立场并无对错之
?分,是纠结与矛盾的,彼此关照,相互补充,不论正面还是反面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作者的自我表达。这类作品有《孤独者》《在酒楼上》和《头发的故事》。
《孤独者》《在酒楼上》和《头发的故事》中的叙述者和主人公都在进行对话,2个身份代表着不同的观念和态度,并且不管是《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和“我”,《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和“我”,还是《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和“我”都有着鲁迅的影子,2个人物彼此的交流仿佛是同一个灵魂的相互搏斗。
在《头发的故事》中,读者了解到N先生是通过“我”的介绍,“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2]43,但是N先生对于革命和启蒙有着自己的深切体验,并不是“我”所说的那么不通世故。他的诸如“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等言论让读者分明感受到他是清醒的,是“我”过于世故。《在酒楼上》中,“我”和吕纬甫有着许多共同点,我们都是教员时代的旧同事,曾经都是有觉醒意识的革新者,但是如今的“我”和吕纬甫却作出了各自不同的甚至相反的选择。“我”仍怀着年轻时的梦想,四处奔波,找不到归宿,是个漂泊者;而吕纬甫已不再做梦,回到现实生活中,关注的是生活中的事,为弟弟迁葬,为邻居家的女儿送剪绒花,他回来“也还是为了无聊的事”,“我”没料到他在教《女儿经》一类的书,他却说“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2]165吕纬甫是颓唐的,然而“我”又何尝不是,只是另一种彷徨。《孤独者》中的“我”与魏连殳其实都与社会有着隔膜,只是“我”还未成为魏连殳般的异类。魏连殳在祖母的灵前表现得像个局外人,但当亲戚们走后却又像狼一样嚎啕大哭,这种矛盾性不仅表现在丧葬方面,更表现在他后面的人生选择上,躬行了先前所憎恶的,成功了却也真正失败了。“我”和魏连殳进行了关于孩子、孤独和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3个方面的讨论,“我”和魏连殳各自的说法看似对立,其实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
纵观3个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在《头发的故事》中“我”是对N先生不满的,《在酒楼上》“我”对吕纬甫是理解关心的,在《孤独者》中“我”对魏连殳是感同身受的。叙述者“我”与主人公处于同一个时空,与主人公的距离在不断缩小。严家炎先生从复调的角度认为,“我”与主人公是组成复调的2种不同音响;一种是以独白的方式呈现;另一种是以客观的非我的形式呈现。笔者认为是恰当的,因为在这个同一时空中的主人公与叙述者之间并无太多的故事情节,大部分都是由对话构成,这种对话恰是作者自我的2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意识。
同一时空的“我”与主人公,犹如一个问题的两面,矛盾对立地存在却又相互补充,不能说作者更赞同谁,只能说他们2个都是作者矛盾彷徨思想的承载者,“我”既不是独白,也不是传声筒,而是有话语、有参与度的对话者。无疑,“我”与他体现的正是意识深处的两面性,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读者需要从整体上来把握,而不能单纯地从“我”的视角来看。
四、结语
总之,鲁迅笔下第一人称叙事是复杂的,叙述者“我”跳出了传统的关于自身的叙述,他将“非我”的叙述藏于“我”之后,“我”与“非我”相互补充,共同完成价值的构建。当“我”不再单单叙述“我”,主人公不再仅仅被叙述时,“我”和主人公之间就有了互补性;“我”并非传声筒,“我”是有态度的;“我”既可以打入事件内部成为故事一员,也可以跳出事件成为一个旁观的外叙述者;“我”既可以是现在的“我”,也可以是瞬间跳回过去的“我”;“我”既可以是一个对话者,也可以是价值观的重要和声者……时间和空间的变换,让“我”的身份有了更多可能性,“我”的叙述有了更多变化性,由第一人称带来的真实感,加上作者对“我”与主人公距离之间的把控,使得作者在更大程度上表达自己的同时,也增大了读者阅读的空间。希利斯·米勒在他的《解读叙事》中说,有些作品就像一个难以解释的符号,而正是这些难以解释的符号成为了优秀艺术的标志,艺术就是应该存在于完全澄明和完全遮蔽之间。鲁迅将第一人称叙事置于时空的变化之中无疑增加了作品内涵的隐蔽性,但也正是这种隐蔽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和流传性,并且形成了更大的审美空间,这也是其作品成为既区别于传统小说又有别于同时代作家作品的独特存在的主要原因。
[1]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鲁迅小说[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3]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编辑:文汝)
I207.65
A
1673-1999(2016)10-0069-03
李莎(1991-),女,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610041)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2016-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