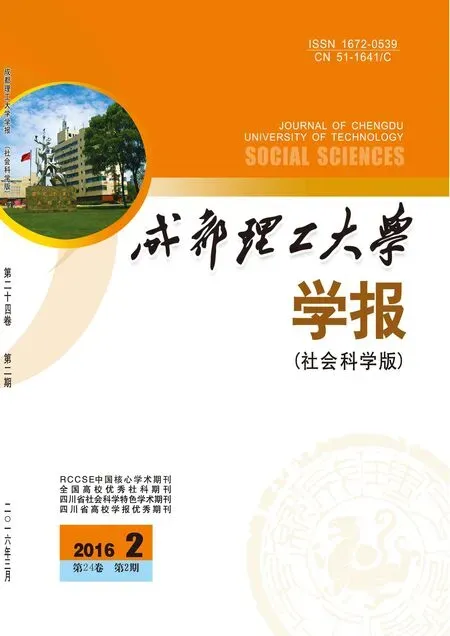论城管执法的物业化模式
王春业
(河海大学 法学院,南京 210098)

论城管执法的物业化模式
王春业
(河海大学法学院,南京210098)
摘要:当下,我国城管暴力执法不断,形象不佳,城管执法陷入困境之中。究其根本原因,是城管执法模式的严重滞后,难以满足日益精细的城市管理要求,必须对城管执法模式进行彻底变革。借鉴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经验,将城市执法物业化。为此,要将城市管理执法重心下移到街道和镇,由街道和镇作为政府代表与物业公司签订城市管理协议,由物业公司负责以市容秩序为重点的城市管理,城管机关则负责业务指导、培训、监督和考核。
关键词:城管执法;物业化模式;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述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同时,专门提到了城管执法问题,强调要“理顺城管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理顺城管执法体制,加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建设,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这不仅指出了当前城管执法的弊端,更指明了城管执法改革的方向。城管机关要执法,但更要加强服务职能。如何执法、如何服务,城管执法的物业化模式是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径。
一、城管执法困境源于执法模式的弊端
近年来,尽管城管执法人员勤奋工作、放弃休息、加班加点,真心为群众排忧解难办实事,为城市的净化、美化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些努力的结果,并没有获得群众的理解和社会的支持,人们对城管执法人员的印象依然不佳,并一直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形象极差。在一份“你心目中形象最差的是哪类官员群体?”(单选)的网络调查中,112张有效投票中有43票选择了“城管”,占总票数的38.39%[1],得票最高,足见人们对城管职业的印象有多差。在一份“你喜欢城管吗?”(单选)的网络调查中,165票中有77票投了“不喜欢”,占了46.67%[2]。而在网络传播的关于城管的信息中,绝大部分为负面信息。有人做过统计,媒体中城管形象的负正中三者比例大约为5:3:2,而国外媒体负正比则为9:1。在互联网中,如果纯算网友评论的话也是近九成负面[3]。而社会上流行的“公安管坏人,工商管富人,城管管穷人”的说法,隐含着社会对城管工作的某些不满或不认可。城管执法形象的负面性,使执法者的权威受到质疑[4],导致执法的威慑力降低,执法的效果遭到挑衅。把“城管”释义为专门欺压弱势群体的黑社会组织的有之;将城管等同于打、砸、抢的有之。一个设立初衷良好的制度,却陷于被人诟病的窘境,甚至有学者抨击为:“一个手握巨大权力却缺乏有效法律规制的行政执法机构,在实践中逐渐成为了一个张牙舞爪的小‘利维坦’”,“是一个布满人治烙印的怪胎”[5]。
对此,无论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在寻找原因,并试图开出根治的药方。比如,有的人认为,执法的困境与城管领导体制有关,在中央,城管没有上级主管部门;在地方,各地的城管部门名称及归属五花八门,缺乏统一的规制。有的人认为,目前的城管队伍不是完全按照公务员系列进行招录、培训和管理,人员编制相对混合,用了大量文化素质不高的临时工等,使得城管形象不佳;有的人认为,目前的城管执法方式主要以强制为主,缺乏柔性,缺乏与执法对象的沟通,缺乏为执法对象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应提倡柔性执法;还有的人认为,城管执法在媒体传播方式上存在问题,许多媒体在报道城管时,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往往不从正面来宣传城管执法人员,而是把执法中不好的一面无限扩大,给城管塑造了一个不佳的形象,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可能影响”的因素,但笔者认为,这些因素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因为,即使城管有了统一的上级主管部门,就能避免城管的暴力执法了?有了统一的主管部门,可能在管理上要规范一些,但这显然不是导致城管执法现实困境的根本原因。如果城管都实行公务员管理,由于城管执法所需人员缺口很大,那将使我国公务员的数量成倍增长,管理起来会更难,即便都是公务员序列,也不一定能收到好的执法效果。至于柔性执法问题,其实,我国部分地区也在尝试这种执法方式,例如,武汉的眼神执法、列队执法甚至“卖萌执法”,还一些地方的美女执法等,但只能管一时,并不能管长久。而媒体在报道时不排除有吸引受众眼球的目的,这也是所有媒体在传播时的共性,但如果城管执法的负面事情不多,即使媒体想做负面宣传也不会影响城管执法形象。
实际上,城管执法陷入困境的最关键的根源在于城管执法模式上。目前,城管的执法模式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城管机关亲自执法,直接与执法对象面对面,冲突事件在所难免。二是与城市执法的实际需要相比,城管执法人员数量严重不足,城管人员无法总是在某个执法现场,只能采取运动执法、突击执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无法静下来与执法对象进行交流,不能为执法对象解决任何问题,由于突击和运动的特点,城管与小商贩的“猫捉老鼠游戏”不断上演。三是城管执法仍是以强制性执法手段为主,典型特点就是推桌子、砸摊子、打人扣车,然后就是罚款[6],执法手段非常粗暴,特别是在对占道经营、流动摊贩执法中,经常违反执法程序,随意扣押、毁坏、侵占行政相对人的财产,甚至打伤、打死相对人等。可以说,“粗暴执法、粗暴管理”损害了城管形象、败坏了城管名誉,成为城管事业健康发展的一大毒瘤。
这种执法模式表明,城管执法管了许多管不好的事情,管了许多本该交给其他社会组织来管的事情,即管了许多不该由自己亲自来管的事情。再加上执法对象多为弱势群体,例如下岗工人、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以及谋生能力相对较差的人等[7],其境遇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人们的心理天平也就自然向他们倾斜。因此,如果城管执法模式不变革,城管机关的职能不转变,这种执法的尴尬现实还将继续下去,而且难以得到根治。说到底,改变城管执法现状的关键是一个职能转变的问题。职能关系问题是不同的管理职能该由谁来行使以及管理主体之间职责权限的划分问题[8],它渉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组织等关系。如果不能理顺这些关系,不能分清职责权限,就无法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无法实现城管执法机构设立的初衷。“成功的组织是把高层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这便使得政府基本上作为一个精明的买家来工作,以能够完成自己政策目标的方式利用各种生产厂商”[9]。
二、物业化模式为城管执法摆脱困境提供了全新思路
(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现代趋势
所谓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指政府将原来由自己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向社会公布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质量与数量、资金预算、服务期限及奖惩等,选择有资质的社会服务机构来完成,并根据社会组织或企业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支付一定费用的新型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这里,购买方或出资方是政府,提供者是各种社会组织或企业,后者可能是营利性组织,也可能是非营利性组织,服务的内容、标准以及双方的权利与义务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予以规定。
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理论依据,有不同的主张,形成了公共物品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等。其实,无论是什么理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最关键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政府作为公共组织,具有提供某些公共物品的职能,必须承担维护市场秩序、消除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规制自然垄断等职能。但政府的公共职能不意味着必须依靠政府人员和设施来亲自提供这种服务,政府可以通过决策来提供某些公共服务,并为这些公共服务买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李克强总理也多次强调,凡是市场能够做到的,交给市场;凡是社会能够做到的,交给社会。这里提出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权力边界和遇到交叉时的处理原则,即凡通过市场机制能调动积极性和有效配置资源的,政府就不要干预;凡是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才需要出面干预。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不仅取决于是谁提供的,更取决于这些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公众能否享受到高水平的服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本质就是由政府出钱,社会组织或企业提供服务,通过合同来管理,政府根据提供者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估、兑现。“政府本质上是一个安排者或着提供者,是一种社会工具,决定什么应该通过集体去做,为谁而做,做到什么程度或什么水平,怎样付费等问题”、“今天我们政府失败的主要之处,不是在目的而是在手段”[10]。
实际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现象在现实中早已有之,比如,深圳市政府就公共交通等向社会公开招标;上海市向“自强社会服务总社”、“新航社区服务总站”、“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三家社团组织购买禁毒、社区矫正和青少年事务等公共服务;湖南邵东县等地将辖区内夜间治安防控工作承包给了保安公司,实行治安外包,以及目前不少地方实行的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等,都取得了较好效果。而城管执法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方式,是政府引进企业参与城市管理、试图破解执法困境的一种办法。只要制度设计科学,发动各种社会力量作为城管触角延伸,联合开展公共管理服务,就完全可以实现行政目的,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城管执法的物业化模式可以有效解决城管执法的困境
城管执法机关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来进行执法模式的变革,实际上体现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管执法的范围和内容逐步扩大,现行的城管执法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城市管理的需要了,必须变革。
一是从城管执法所涉事项来看。政府的公共服务属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前者如国防、外交等,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只有政府才是唯一的供给主体;后者诸如教育、医疗等则不具有排他性,并不一定要由政府亲自来提供,应交给市场上最适合提供的主体来提供,以实现效益最大化。城管执法主要涉及到群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事情完全可以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来解决,完全可以将城市日常管理纳入市场化运作。而作为政府一部分的城管执法机关不必要亲自为之,只要进行间接地宏观把握即可,可以作为掌舵者,而不必充当直接提供服务的划桨者,体现了政府与社会的权力边界,也体现了政府在城市管理工作中角色的重大转变。
二是从城管执法管理所涉范围来看。城管执法管理的范围可谓点多线长面广,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来进行。但目前的城管队伍无论在人员数量上还是执法时间上都无法满足要求,更难以兼顾。于是,就出现了目前的突击式、运动式的城管执法现象,“轰轰烈烈”的执法活动在短时间内虽能收到“良好”效果,但一旦执法活动结束,违法行为又会反弹,屡治屡犯,收效甚微,形成社会顽疾。同时也出现了城管因人员不够只得聘用大量素质低的临时工现象,出现暴力执法、违法执法等不正常现象也就在预料之中。这也表明,城管目前的这种执法模式是政府想管但实际上管不了的一种落后的执法模式。城市管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科学、严格、精细、长效是发达国家城市管理最成功的经验。这是传统的城管执法模式所难以适应的。而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方式,让更多的社会组织或企业参与日常管理,可以有效破解城市长效管理的难题,实现城市管理的长效机制,并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为社会提供更贴近、更适宜的服务,同时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服务效率。
三是从长远执法效果来看。城管既当裁判员判定是否违法,又当搬运工清洁工清理违章物品,极易造成政府与违规商家和群众的直接冲突,造成恶性事件,不仅影响城管的形象,更是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形成群众与政府对立的局面。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方式,城管可以以更加超脱的地位来决策、监督和指导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避免与商贩等执法对象的直接冲突,也可以更加从容地解决社会组织与商贩间所发生的纠纷,避免把所有与城市管理中的问题统统加到城管身上,加到政府身上,给政府形象抹黑。
四是从社会管理的创新上来看。创新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为促进社会系统良性运作,为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会生活质量和提升广大民众幸福感而开展的规范、协调、服务的过程[11]。社会管理方式创新的最大特点就是发动社会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参与社会管理,把政府的事情变成大家共同的事情。而政府从各种繁琐事务中解脱出来,扮演着“政策制定者”、“制度供给者”、“公共服务购买者和监管者”的角色,起着催化、促进作用,更好地履行政府的管理职能,并有效地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城管购买公共服务,是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只有管理方式创新,才能带来服务水平的提升。
(三)我国少数地方城管执法物业化试点初见成效
城市管理实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式在国内少数地方已有了探索,深圳、成都、长沙等地就是典型代表。他们积极探索城管业务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物业化的新模式,其共同特点是城管的诸多业务由市场来做,引入优秀物管企业,政府做好监督考核,从尝试探索来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07年,深圳市地处关外和城乡结合部的宝安区在脏乱差最严重的西乡街道试点了城管物业化模式。试点前,该街道有100多名城管人员却要管好一个100多万人口的城区,要履行21项执法职能,城管执法人员力不从心,街道面临着“穿上城市外衣、留在乡村状态”的混乱落后局面。试点后,引入企业参与城市管理,让企业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西乡街道办和鑫梓润物业关系签订的《花园街区综合管理服务试验合同》,确定了物业公司需要提供的13项服务内容。经过几个月的实践,西乡街道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乱张贴、乱摆卖、职业乞讨等“老大难”问题得到了根本地遏制,立交桥下的绿化带、市中心的街心花园又能看到老百姓聚会、休闲的身影[12]。之后,成都市武侯区也借鉴了深圳的经验,引入物业公司参与城市管理,由政府购买物业服务,将城市管理的日常项目“外包”, 既解决了城管执法人员人手紧张问题,还从根本上解决了城市管理中的长效机制难题,使长期困扰城市形象的乱张贴、乱摆卖等老大难问题得到根本遏制[13]。2010年,湖南长沙市也开始积极推行“物业化”的城管执法新模式,引进有资质、有实力的物业管理公司进行精细化、规范化管理,使得城市环境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显著成效,城市管理市容秩序的24小时长效机制得到建立和巩固。实践表明,将城管执法进行物业化不仅不会出乱子,相反,会带来市容市貌意想不到的焕然一新。
三、城管执法物业化模式构建的具体建议
(一)将城管执法重心全面下移
城管执法重心全面下移,为城管执法物业化模式的推行提供前提性条件。
城管执法所针对的事项都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事情,而基层行政机关直接与行政事务发生关系,与行政事务关系最为密切,具有对地域特点、日常情况比较熟悉、执法经验丰富等优势。由最基层的行政机关进行执法更为合适,可以加强执法力度,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因此,要把城管执法权力的配置重心下移,下移到街道、镇一级,让基层担当主要的执法任务。执法权下移便于城市管理,可以有效地减少执法中间环节,解决了镇、街道工作人员对违法行为“看得见却管不了”、城管执法队员对违法行为“管得了却看不见”的现实弊端。先进国家的发达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等的经验表明,推行城管工作重心下移是一个必然趋势[14]。实际上,国务院早在2004年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就提出:“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市、县两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但这么多年来,各地的落实工作进展有较大差异,而且,怎样才算“适当”,以及下移到哪一级更为合适,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要求。目前,要下移城管执法工作重心,将城管的大部分职能职权移至街道、镇一级,特别是要将市容市貌等实行属地管理,全部移交至各街道和镇。充分发挥镇、街道在城市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强化街道和镇的属地责任。同时,要将人、财、物与责、权、利也划归街道统一管理,街道、镇的执法队伍要真正成了各自街、镇可以直接指挥、调度的队伍。明确街镇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权利与义务,做到城市管理重心完全下移,以建立长效、高效的城管执法体制,可先总结我国各地城管执法重心下移的经验,再全面推行,为全面推行城管执法的物业化模式做好准备。
(二)实行城管执法的全面物业化
所有的城管执法机关要积极实行“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物业管理公司参与城市管理。把这些工作作为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重要工作来做。
首先,引入竞争机制,选定从事城市管理的社会组织或物业公司。街道办事处是代表政府的一级机关,由它来代表政府对外公开招标,对参加投标的社会组织或物业公司进行资质审查。县区级城管机关要加强对招投标行为的监督,要规范购买公共服务的招标行为,坚决杜绝规避招标、虚假招标、串通招标问题以及中标后违法转包、分包等现象,营造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
其次,街道或镇政府与中标的社会组织或物业公司签订城市管理协议。明确物业化的范围、明确服务质量、明确工作标准、明确执法方式、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社会组织或物业公司的管理一般以市容秩序为主,包括负责城市绿化、环卫清洁、清理乱张贴、劝阻沿街乱摆卖、噪音扰民等即市面上的秩序;执法方式一般只是处理清洁、提醒、劝导、秩序维护等方面,但不能行使惩罚权。
再次,城管机关对物业公司进行专门培训。提供城市管理服务的社会组织或物业公司的相关人员必须参加岗前培训,培训合格后才可以上岗。在培训中重点强调物业公司的服务性,明确只能采取的方法,明确不能采取的诸如暴力、强制等方法。
此外,城管机关和街道、镇各司其职共同做好督促协议的履行工作。日常考核,以街道、镇政府考核为主,每月考核一次,还可以通过随时暗访等方式进行监督,并及时纠正社会组织或物业公司城市管理中的错误,同时进行经济上的兑现。而作为上级的城管执法机关,其作为领导机关对街道、镇政府进行业务指导、培训、监督和政策的把握等,负责协调、指挥、调动各辖区执法间的冲突和其他问题。并为所辖区内的物业化制定一套专业、科学、公正的评估标准体系,为下一步的考核评估做好准备。
(三)加强对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评估监督
作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一种形式,城管执法物业化模式能否推行并取得良好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监管是否有效和到位。作为提供服务方的社会组织或物业公司,为获得最大利润,往往会通过减低服务质量的方式来追求任务的完成,这就违背了政府寻求公共服务最大化的初衷。城管执法机关不仅要对整个服务运营情况的合理、合法情况进行监督,还包括对购买资金使用情况、服务计划、服务效果、服务质量的监督。监督的主要方式是评估。评估可分为中期评估、终期评估,也可以进行不定期抽查。要根据预先制定好的服务质量标准,对社会组织或物业公司城市管理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评估不仅要对照标准,还要广泛听取服务对象的意见和建议。作为服务对象的广大市民是公共服务的直接受益者,公共服务质量的好坏要以服务对象是否满意为标准。为保证评估的客观性,评估小组成员可由专家学者、政府人员、提供服务的物业公司代表组成,还可以邀请作为第三方的评估服务机构、会计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参与,这些机构拥有专业技术和人才的优势,使得评估更具有客观性、公正性、专业性和科学性。评估报告的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等,评估结果要定期通报,并将评估结果与拨付资金或是否续签协议相挂钩。
(四)积极培育城市管理的物业化市场
城管执法物业化模式改革虽然符合城市管理的改革方向,但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当下的社会组织发育得不够健全,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现实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很多地方缺乏专业的管理城市的物业公司,市场主体还没有完全形成。有一个对比的数据,广州市政府曾于2010年举办购买公共服务的供需洽谈会,参加的仅有34家社会机构,而我国的香港却拥有上万家承担着各种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的民间社会组织。无论是数量与规模,还是承接项目经验、专业工作人员、资金充足情况以及成熟度方面等,两者都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比较。单有政府购买方不行,还必须有高质量和数量规模较大的卖方,并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竞争者,才能形成有效的竞争,才能真正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为此,必须尽快培育一批档次高、规模大、实力强的专业化市场主体,以承接城管执法物业化模式的推行。目前,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培养,例如,引导现有的品牌物业管理公司拓宽服务领域,使其服务视角延伸向城市公共物业管理;向一些诸如环卫保洁公司等相关业务公司推广“城市管理物业化”运作模式,引导他们升级为综合城市管理公司。
总之,城管执法物业化模式是城市管理以市场化为手段、以市容秩序为切入点、以城管物业化为载体、以街面管理为突破口的全覆盖、全时段、全方位的长效管理机制,这个模式的有效推行将为广大群众创造一个清洁、文明、舒适、优雅的城市生活环境,既解决了城管的执法问题,更解决了城管的服务问题。
参考文献:
[1]官员形象最差群体城管排第一 百姓最恨贪腐渎职[EB/OL].(2014-11-27) [2014-12-08].http://survey.1diaocha.com/Survey/_SurveyDetails_depth_45485932029367.html.
[2]你喜欢城管吗?[EB/OL].(2014-11-27) [2014-12-08].http://survey.1diaocha.com/Survey/_SurveyDetails_depth_44994448998681.html.
[3]高明勇,王景兰.城管需要什么样的形象[N].新京报,2011-7-30.
[4]王春业.论城管行政执法队伍形象的重塑[J].西部法学评论, 2012,(2):20-35.
[5]杨解君,张黎. 法治视野下的城管综合执法体制研究[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9,(4):25-35.
[6]林龙,阿计.暴力执法 VS 暴力抗法——城市管理何时走出怪圈[J].民主与法制,2007,(9):14-15.
[7]石若坤. 城市管理行政不文明执法的原因及其改善[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33-36.
[8]颜迁锐.中国行政体制改革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77.
[9][美]戴维·奥斯本,特勒·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市政协编译组,东方编译所,编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12.
[10] [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周志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68.
[11]谢建社.中国社会工作创新与管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3.
[12]深圳有了“新城管” 物业化管理出成效[EB/OL].(2013-10-1)[2014-11-10].http://www.0574bbs.com/read.php?tid-485768.html.
[13]谢罗群.城管物业化——行业发展面临新机遇[J].城市开发,2009,(1):33-35.
[14]推动重心下移构建高效城管[N].南方日报,2010-10-11(03).
编辑:鲁彦琪
On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Mode Used in
Urban Management Law Enforcement
WANG Chunye
(Law school,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210098, China)
Abstract:At present, the violence enforcement and the poor enforcement image make urban management law enforcement get into trouble. The reason is that the mode of urban management law enforcement is too seriously lagging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urban sophisticated management. Thus, the mode of urban management law enforcement must be thoroughly reformed.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government purchasing public services, urban management may take the mode of property management. To this end, the focus of urban management law enforcement should be shift down to the office of the streets and towns. As governmental representatives, the office of the streets and towns sign the urban management agreement with the property companies. The property companie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urban management focusing 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city. And urban management authorities are responsible for operational guidance, training,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to the property companies.
Key words:urban management law enforcement; property management mode; the government purchasing public services
中图分类号:C93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2-0077-06
作者简介:王春业(1970-) ,男,安徽明光人,教授,法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行政法学。
收稿日期:2015-06-30
DOI:10.3969/j.issn.1672-0539.2016.0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