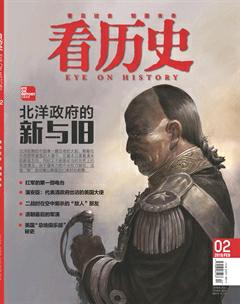大卫·妮儿:叩开拉萨大门的巴黎女人
绿衣

大卫·妮尔于1868年10月24日生于法国巴黎的郊区圣-曼德,她在修道院度过了“早熟而悲伤的少女时光”。封闭、幽禁的修道生活,却使得她拥有了一种与常人不同的性格——喜欢冒险,向往赴远方旅行。1886年,她离开修道院,前去拜谒比利时国王和王后,并在比利时王宫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
为了能赴远东探险,大卫·妮尔于1888年前往伦敦。在那里,她遇到了美国著名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历史学家和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摩尔根的夫人,并得以参加了伦敦的“神智学会”。她利用神智会的图书室和大英博物馆的藏书,开始研究东方思想,这些古典哲学和文学作品,更激发了她去东方远游和探求的愿望。回到法国后,她在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等高等学府选修东方文明课程,成为著名东方学家席尔宛·莱维和爱德华·福科的女弟子,继续这方面的探索。她在刚刚兴建的吉美东方博物馆度过相当长的“快乐时光”,尽情地接纳东方文化的滋养。这一切,都为她一生的探险之路奠定了方向。
初探雪山圣域
1890年-1900年这十年,是大卫·妮儿生命中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她从安静的图书室,从寂静的书本和静默的佛像面前走出来,走到真实的东方世界里,直面她所热衷研究的佛教、哲学思想。1890年,大卫·妮尔首次赴佛教故乡印度旅行,先在锡兰和印度学习佛教经典,特别是吠檀多派教理,并于1893年首次到达印度与中国西藏的边境,但无缘进一步探访,因为当时西藏已被英国控制,且基本是对外国旅行者封闭的。然而,这次旅行开启了她对西藏的向往,她其后许多年的努力,都在试图进入这片对外国人,尤其是外国女人关闭的禁地。
1910年8月,大卫·妮尔再次赴远东旅行,她搭乘“那布勒斯”号远洋舰从地中海起航,穿越红海,驶向印度洋。经过近一个月的海上漂游,轮船在科伦坡登陆,妮尔在这里开始了她向往已久的东方之旅。这段时间,她遍游锡兰、印度、锡金,在此期间,她搜集了大量关于岭·格萨尔(即格萨尔王)的资料,后来出版了《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
1912年,妮尔试图从大吉岭进入西藏,她这样写道:“在我的面前忽然间又出现了茫茫无垠而又神奇的西藏高原,而在远方以一种朦胧的幻景为界,标志则是一种戴雪冠的淡紫色和橘黄色山峰的混沌外貌。这是多么令人永世难忘的景致啊!它使我流连忘返,宁愿永远置身于这种妩媚的景色之中。”这次,她依然被遣送回来,没能够深入西藏。其后,她一直在想方设法,尝试寻找各种途径迂回进入西藏深处。
1914年,妮尔结识15岁的庸登喇嘛,这个曾求学西方的小伙子成为她朝拜圣地拉萨的忠实伴侣。1916年,她在庸登喇嘛等人的陪同下,未经许可就从锡金翻越喜马拉雅山到了日喀则,参观了著名的宁玛巴佛塔和扎什伦布寺,并拜见了班禅喇嘛。这是她第一次真正进入西藏,但迫于英国人的驱逐,又不得不于同年9月又回到大吉岭,后来她转而到缅甸、日本、朝鲜等地游历,两年后回到中国。
为了做好入藏的准备,在1918年到1921年期间,妮尔一直居住在青海的塔尔寺,为了锻炼体力,经常每天步行40公里,并完全以藏人的方式生活:煮茶、洗漱、读经和翻译。之后塔尔寺发生战乱,妮尔再次试图入藏,结果在巴塘,因为没有得到英国驻打箭炉(康定)领事的许可证而被驻守的关哨阻拦,最后不得不放弃原计划,改道去了玉树。在逗留玉树期间,她又准备经由禁地打开一条直通怒江的道路入藏,最终因哨岗查出庸登的行囊中携带的照相机、仪器以及稿纸而暴露,探险计划再次受挫。
1921年至1923年间,大卫·妮尔辗转在中原与西藏之间的茫茫戈壁、草原和沙漠之中。她曾试图从康定经通商大道进入西藏,后受阻返回羌塘(藏北牧场);她又从塔尔寺出发,首先绕过西藏东部,到达了康定,企图通过商队大道向拉萨挺进,接着又折回,在川康、安多等人迹稀少、未知的“禁地”,寻求通往圣地拉萨的通道,但又在距西藏百余公里的边城玉树被发现而遭遣返。1922年2月,大卫·妮尔又试图从玉树向南进发,经数月跋涉仍未成功。
终抵拉萨
1923年10月23日下午,大卫·妮尔离开蔡宗小镇传教士的住所向西藏进发。这是大卫·妮尔第五次向拉萨进发,终于进入了拉萨。这一次,已经55岁的妮尔化装成庸登的母亲,以上山采集植物标本的名义才最终到达了拉萨。
为防引起怀疑,她仍将行李存放在村庄里。至于跟随着自己和庸登的两个当地向导,她也盘算着要在到达大雪山后就将他们甩掉。当她到达将决定是否能够进入西藏的关键地点时,她看着眼前的大雪山,感到十分震撼,写道“巍巍的大雪山高高地屹立在晴朗的天空下,皎洁的月光照耀着巨大冰峰。它使我觉得,今天晚上那些冷酷无情的守卫者不像是不可逾越的屏障,而更像一尊令人敬仰的慈悲的神像站立于神秘狂野的门槛上,准备迎接和保护一位女旅行家。她虽然不太勇敢,但她对西藏的热爱再次把她吸引到这里。”
在这里,她开始实施自己的逃跑计划,她先是在一个山谷要求扎营,让一位向导去砍柴,然后对另一位向导声称她的脚受伤了不便前行,决定在此停留一个星期,研究当地的植物,请他不必再跟随。待砍柴的向导回来后,她又派他去别处送信和包裹。这样两名藏族人从不同的路回去,不会在路上碰面——计划成功了,她和庸登两个人终于可以轻松上路。
为了避免露馅,他们两个人一路都用藏语交流,为了实现两人的秘密沟通,妮尔甚至非常仔细地制订了一套秘密术语。为了不暴露身份,妮尔自己发明了一种易容术:用碾碎的炭末掺入可可粉涂面,用墨染黑自己的手指和头发,并按照藏族女子流行的做法,将牦牛尾和头发编在一起,而且路上一有机会就从锅底取来的油烟灰来擦双手和面部。有一次,妮尔不小心用手指搅拌了当地人送的酸奶和糍粑,致使涂在手上的油墨全化在了食物里,可为了避免被别人发觉,她还是硬着头皮吃掉了那些食物。
此外,为了行路方便,他们只携带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一把刀子、一顶薄棉布的小帐篷、铁桩子和绳索、替换靴子底的一大块皮子,以及一些酥油、糌粑、茶叶、少许干肉等。为了避开途中的村民,他们只能在夜间行路。由于不了解地理状况,道路上往往也没有路标,所以路途中很难估计距离和时间。因此,这趟行程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荒野中前行,经常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面对的是野狼、寒冷、口渴、饥饿,有时还被大雪封路所阻挡。一路上,她假扮成朝圣的藏族人,所以一些并非西藏信徒所拥有的工具,比如热水袋、手表、这类东西她都不敢轻易使用,更不敢花钱——在路上用银钱买东西是很容易暴露身份的。
他们一路风餐露宿,在夜间路过村庄和寺庙,尽量避免与人接触。偶尔,他们也会在村民家中过夜,睡在他们的厨房中,妮尔对一些人说教时,会被当成密宗佛教里的一位女性神袛“空行母”。然而,在给别人带来安慰时,妮尔自己却陷于一种时刻害怕被人识破然后重新被带回边境的焦虑。她这样写道:“因为每一个途中遇见的樵夫、牧民或朝圣者都可能识破这种装扮,再将这一切传到刚离开的村庄,或再由那里传播到边境,从而使得整个旅程中止。”幸好,由这些焦虑造成的动荡情绪,并没有一直扰乱妮尔旅行的兴致。沿途美丽的风光使得这股浪潮刚刚升起,又跌落下去,进入“一种令人陶醉的不安之中”。
在这一趟旅行中,为了赢得众人的信任,妮尔常常需要使用自己的演技——有一次遇到土匪,庸登几乎手足无措,可妮尔一会儿痛哭流涕装穷,一会儿又搬来佛教神魔严加诅咒,终于吓跑了土匪。妮尔戏称自己是最好的喜剧演员。
历尽万般艰辛,她的这次旅途终于得偿所愿地深入西藏腹地,可以一睹圣城拉萨的荣光。在到达之后的两个月里,她游览了拉萨的各处寺院,在布达拉宫最高的台阶上散步。
在法国掀起西藏热
当初,妮尔离开法国时曾对自己的丈夫说:“我要出远门,半年后就会回来。”可事实是妮尔一去就是13年,其后才回到丈夫身边。那时,通常情况下,一个外国女性在中国旅行常常要雇很多轿夫、仆人、翻译,甚至还有护卫。如在同一个时期,来自英国的女画家坎普在中国东部地区还是坐轿子旅行的。而妮尔却斗智斗勇、风餐露宿地进行着她的西藏之旅。这也难怪妮尔一回到法国很快就成了那里妇女们的偶像。
1924年5月,妮尔夫人离开日喀则,到达印度。她在印度又拜访了甘地和英国驻印度总督。印度、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各大报刊均有对她旅行的评论。1924年5月10日,妮尔回到了法国,受到英雄般的接待,并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大卫·妮尔热潮。1927年,世界妇女体育协会因为其徒步的东方探险而给她颁发了大奖。1929年5月,大卫·妮尔迁居法国底涅,并将在中国西藏和亚洲其他地区搜集的佛像、魔刀、金刚等运到居所,其居所被人称为法国的布达拉宫。
1925年12月3日,法国地理学会举办了大卫·妮尔“穿越西藏的尖兵”专题报告会。之后,她频频出席多国主办的藏学研究讲座和报告会。1926年6月,大卫·妮尔完成《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一书的写作,这是她第五次西藏之行的游记。本书读者甚众,掀起法国一股西藏热,当时的法国总统杜梅格也成了该书的崇拜者和热心读者。
“说真的,我思念那并非是我的故乡的地方。它上面的草原、荒漠、终年不化的积雪,还有那湛蓝明亮的天空,这一切时常萦绕在我的脑际……这地方属于另一个世界,它是巨人和神的国土,使我着迷着魔。”对这段入藏的旅行,妮尔一方面自称这是她一生中最幸福和难忘的日子,另一方面又说:“即使有人给我500万法郎,让我在同样的条件下,重新开始这样的冒险,我确信自己也不肯这样干。”
时局动乱间再度入藏
1937年底,妮尔获悉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非常难过,69岁的她决定再次入藏,她先到达中国佛教圣地五台山,不久又与庸登再次驻足于北京,从事学术研究,并与中国学者广泛交流,最后于1938年7月到达康定。
因时局动荡,1938年至1944年,她一直被困在四川,寄居于法国传教区,从事科学考察和学术研究。其间,她与西藏的瑜伽行者、黑苯和白苯教徒广泛交往。二次大战结束后,她回到成都,举办有关汉藏关系的讲座等。1945年7月,77岁高龄的她离开亚洲,回到法国底涅,在巴黎大学举办“藏传佛教几种特征”的研讨会,并连续出了几本关于西藏的书,如《西藏巡礼记》《永生和转世》《中国4000年的开拓史》。
1966年10月24日,大卫·妮尔度过其98岁生日,她亲笔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应该死在羌塘,死在西藏的大湖畔或大草原上。那样死去该多么美好啊!”三年后,1969年9月8日,大卫·妮尔在法国去世,享年101岁。在晚年,她一直盼望能再游故地。就在去世的前几天,她还拟定了一个经过西藏、青海、四川到北京的旅行计划。她去世后不久,法国成立了大卫·妮尔基金会,妮尔在底涅的住宅成了法国的西藏文化研究中心。虽然她最终没有能够回到西藏,但她的名字,与西藏、拉萨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
2008年,为了纪念妮尔,一队由10名法国妇女组成的摄影探险团来到四川,沿着当年妮尔在中国考察的足迹拍摄一部风光纪录片。虽然“青山依旧在”,然而那位被当作“空行母”的女性曾经走过的旅途是无法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