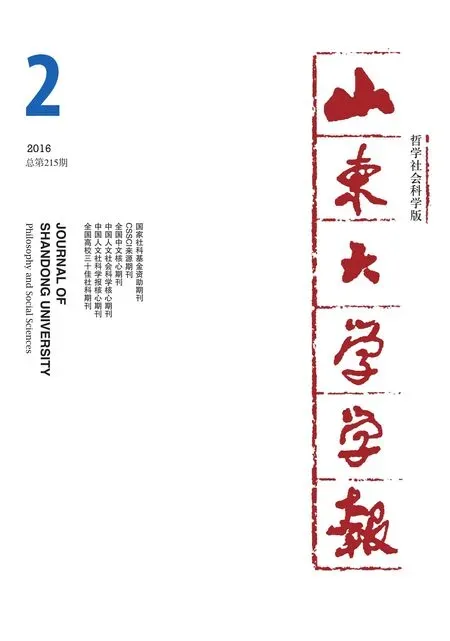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中的漂泊意识
翟瑞青
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中的漂泊意识
翟瑞青
摘要:20世纪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是中国新文学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中,一直有一种无所归依的漂泊意识,而且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呈现特点。如果把女作家的漂泊意识放置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可以发现其独特的意义与个性价值。在漂泊意识产生的机制和表现形态方面,女作家与男作家显然不同。女作家更加敏感于自身的性别特点,在抗拒男权中心文化的过程中,她们一直在寻找或者建构着自己所存在的文化,发掘女性长期以来被男权文化遮蔽了的个体生命意义。女性文化建构的过程是女性作家不断地向自我生命深处探寻着生命、精神与情感的着陆点,安放自己漂泊已久的灵魂,寻找自己存在的文化价值的过程。
关键词:20世纪; 中国女性文学; 漂泊意识
对中国女性来说,20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沉默几千年的中国女性日渐觉醒,知识女性不断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纵观20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可以发现,一直有一种无所归依的漂泊意识潜隐其中,而且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呈现特点。
“漂泊,作为人类的存在状态,一直受到古今中外文学家的青睐。漂泊,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母题也得到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关注,几乎所有重要的现代作家都曾涉足这一领域,并且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谭桂林:《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漂泊母题》,《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早已有评论者发现了现代作家浓重的漂泊意识,不过他们主要是从男性作家这一角度进行思考和考察的,或者只对某个女作家进行个案分析,缺少对整个20世纪中国女作家的整体考察,更难以从现象背后挖掘出最本质的内容。
曹文轩对“女性作家的流浪意识”简单地归结为:“女性作家的‘出门’是娜拉式的‘出走’,是逃出腐蚀性情、压抑欲念的‘温柔之乡’。……在女性作家眼中,女性似乎更有‘流浪的血统’。……‘走异路,逃异地’,是许多女性的命运。”*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8页。谭桂林则认为:“漂泊母题文学的兴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种具有重要文化意蕴的精神现象”,“漂泊母题兴盛的原因既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由乡村向都市的迁移趋势有关系,同时也是现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叛逆封建大家庭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生命形式在文学中的形象体现”*谭桂林:《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漂泊母题》,《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女性作家虽然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实际上还有更多更为复杂的原因。她们既有每个时期男性共有的诸如战争、工作迁徙、婚变、政治风潮,以及哲学层面上人的归宿感等这些由外而内产生的漂泊体验,又有自身性别、特点这些由内而外所造成的有别于男性的个体漂泊经验。如对父母的情感依恋,对婚姻、爱情的敏感与专一,对“家”的追寻,对母性血脉的追溯等。尤其是当女作家拥有了话语权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寻找自己的落脚点,试图把自己纳入时代的潮流之中。殊不知,自己与民族、时代之间的契合度,与男性作家相比,其间还掺杂着更多更为复杂的诸如人生、情感、爱情、婚姻家庭、事业、个性等等方面的诸多问题,这些都是整个20世纪难以解决的问题。
一
20世纪初,随着个性解放的脚步,女性解放也开始发出了自己的足音。一批知识女性开始冲出束缚她们的家庭牢笼,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和追求,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有的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第一批中国现代女作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了文坛。她们正是在对知识的渴求、对情感的追求、对美的创造过程中,提高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试图实现自我超越。
五四时期,作为第一代觉醒后的知识女性,与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的时代脉搏密切呼应。在广大妇女作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沉寂了几千年,像被剪去了翅膀的小鸟,在狭小的“家”这一牢笼里,已经失去了飞翔和鸣叫能力的情况下,在恶劣的环境中,她们毅然决然地为女同胞们肩负起重任,披荆斩棘,开辟出一条生路,并有着惊天地泣鬼神的豪情壮志、先觉者的觉悟、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想到中国妇女界的消沉,我们懦弱的肩上,不得不负一种先觉觉人的精神,指导奋斗的责任,……我愿你为了大多数的同胞努力创造未来的光荣。”*石评梅:《露莎》,傅光明主编:《石评梅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第146页。可是,刚脱离窠臼、翅膀还很稚嫩的她们,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是可想而知的,有时四处碰壁,以致身心疲惫、伤痕累累,甚至会身陷牢狱,或者流血牺牲,客死异乡,如离乡背井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刘和珍们。另外,大多数女作家出身于名门望族,她们在挣脱封建家庭牢笼,飞向不可知的外部世界,挣脱传统羁绊获得身心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长期可以依偎的血脉亲情,在独闯天下、云游四方的过程中,又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出路。当时妇女解放刚刚起步,家庭还像一个巨大的绊脚石横亘在她们面前,学校的大门刚刚为女性敞开一条小缝,社会环境还没有提供施展才能的空间,所以她们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自身的价值和追求难以实现,难免有流浪无归、孤苦无依、前途未卜之困惑。再加上忧患丛生、世事多变、家道中落、父母日渐衰老、婚姻爱情困难重重等客观现实,孤身只影流落天涯的她们更是呈现出难以承受的痛苦。虽然“羡慕流云的逍遥,忌恨飞鸟的自由”,但是故乡亲人始终像一根扯不断的丝线,牵引着她们前行的脚步。独闯天涯的孤独凄苦,故乡的牵绊,还有前途的渺茫,像几根无法挣脱的绳索捆绑着这些翅膀柔弱还没有经历过风雨的天边雏燕。正如庐隐《月夜孤舟》中的沙,原是漂泊的归客,归来后依旧漂泊,只能对着凉云淡雾中的月影波光,幽怨凄楚地质问无言的苍天。石评梅的《醒后的惆怅》《笔端的惆怅》《遗留在人间的哀恸》,庐隐的《寄天涯一孤鸿》《月夜孤舟》《愁情一缕付征鸿》《我生活在沙漠上》《何处是归程》《漂泊的女儿》,丁玲的《自杀日记》《莎菲女士的日记》等无一不是抒发自己飘零无依、无所停靠的孤苦之感。“天涯”、“孤雁”、“孤月”、“浮萍”、“孤影”、“漂泊”、“飘零”、“孤坟”、“荒冢”、“恶浪”、“苦雨”、“寒窗”、“衰草”、“寒烟”、“寒光”、“阴霾”等意象词汇,在1920年代女作家作品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经常见到的还有一些表现感觉的词汇如“哀鸣”、“悲鸣”、“冷寂”、“死寂”、“孤寂”、“寒颤”、“隐痛”、“漂浮”、“零落”、“凄苦”、“冷涩”、“冷酷”、“灰幕”、“渺茫”、“孤清”、“凄怆”等。
第一代女作家大多是以独立自足性不足、依赖性较强的女儿身份出现的,在五四个性解放精神的感召下,也急切地如男性一样成为叛逆封建家长、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代。但是,与男性相比,在内在理想与外在压力的交战中,她们对所要追求和争取的前途与命运更加充满焦虑与迷茫,承受着新旧文化更加激烈的冲突与夹缝的压力。
二

首先是被迫失家的痛苦。如果说第一代女作家的漂泊主要表现在主动外出留学或工作,创作中抒发的是一种作为未出嫁女子与传统家庭扯不断理还乱的思绪,以及工作无着、情感无所归依的痛苦的话,那么这个时期,女作家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动无奈的选择。这个时期的女作家大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拥有自认为可以托付一生的情感伴侣。但是,处在国土日渐沦丧、民族国家日益危亡、硝烟战火日益弥漫的背景下,她们的小家犹如在狂风暴雨的大海中一艘无法驾驭的小船,不仅随处漂泊,而且随时都有被冲毁的危险,夫妻、母子随时都会被拆散,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被湮没在狂涛骇浪之中。丁玲丈夫胡也频被杀,白朗丈夫舒群被捕,致使丁玲、杨刚、谢冰莹非常无奈地把孩子送回老家,这都是对她们作为女性在追求完美意义上家的过程中最致命的打击。另一方面,家乡故土逐渐沦入日本人之手,她们或被迫流亡他乡,或主动走上战场、保家卫国,无论何种形式,作为知识女性的她们在情感上都会有一种“国破家亡”的感觉。萧红在短篇小说《小城三月》和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散文《失眠之夜》中充分表达了对“家”的渴望和对故土的留恋。
其次是感情上追求男女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平等而不得的痛苦。即使在战争的背景之下,觉醒后的广大知识女性也没有放慢追求男女真正意义上平等的脚步。在长达几千年封建帝制的中国社会,男女不平等的封建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即使如子君经过了五四时期启蒙思想的洗礼,也难以从根本上消除深藏在意识深层的男权主义思想。这种事事时时处处都显露出来的男权主义思想和男女两性性别的不平等,让敏感、细腻的女性强烈感觉到,女性作为一种性别标识而被歧视、被欺骗、被背叛,作为弱者而被强者极力挤压,在危机四伏的社会中左冲右突的艰辛与磨难。由此所导致的情感上的无处寄托、无所归依,使得白薇、谢冰莹、萧红等知识女性相比无家的感觉更加刻骨铭心,随之而来的是漂泊意识更加凸显而强烈。其中,萧红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她集多方面因素于一身,是漂泊意识最强烈的作家。从小深受性别伤害之苦,为争取婚姻自由和上学的权力被父亲逐出家门,与萧军的感情又走到了崩溃边缘。怀了箫军孩子的萧红,凄惨地对朋友梅林感慨:“我为什么总是一个人走路呢?过去,在哈尔滨。后来,在日本,这回在重庆。我好像是命中注定要一个人走路的。世界上那么多的人啊。逃难的时候,你看看,成千上万的,跑警报的时候,几十上百万的。到了重要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只能是一个人。这是为什么?”*梅林:《忆萧红》,季红真:《萧萧落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仅有31年生命历程的萧红,既失去了赖以栖身的传统意义上的家,也没有找寻到情感可以寄托的所在,在有生之年被迫一步步远离故土却没有机会看到故土的收复。一生处在漂泊流亡之中,始终承受着无家的惨痛与情感的孤寂。从中国的最北端一路漂泊,行程几万里,在硝烟战火中,生命最终默默地终止在几乎是中国最南端的香港。
三
建国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和“男女都一样”的强烈影响下,广大女性普遍走上了工作岗位。“四海为家”和以另一种方式诞生的集体主义大“家”的出现,使得个人情感寄托的小“家”开始弱化,女性性别意识日益淡化。这让广大女性转移了自己的注意视线,由狭小的自我空间转向了外界广阔的社会大众,自认为只要求得政治经济上的解放,就会与男人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因此也大大缩小和遮蔽了生命和情感体验表现的艺术空间,暂时缓解了“漂泊之苦”,有了一种表面上看来当家做主人的强烈幸福感觉。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整个社会逐渐陷入了极度混乱的时期,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家庭伦理秩序被拆解、被打破,包括夫妻、母子在内的各种人际关系被纳入到阶级路线体系中进行审视,人们处在精神家园迷失的“失乐园”状态。

在作家们的笔下,陆羽(《羽蛇》)、尹小跳、尹小帆(《大浴女》)、吴为(《无字》)、黛二小姐(《无处告别》)既有对父母亲情长久的祈盼,又有对理想爱情婚姻撕肝裂肺的强烈追求,还经历了求职上的曲折和磨难,最终陷入精神困惑之中。归纳起来,这种寻找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亲情和爱情;第二,可以实现价值的事业;第三,精神家园的建造。有时候这三方面是缠绞在一起的,前两个方面最终指向的常常是第三个方面。
张洁的创作可以说是一直在寻找理想的爱情和婚姻,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这位1937年出生的女作家,历经时代风雨的洗礼,从《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到《无字》,笔下的女主人从对理想爱情婚姻的向往与追求、进入婚姻之后所面临的失望与无奈的残酷现实,到最后走出婚姻,招致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事业上的成功,却无法弥补感情上的无所寄托和自然情欲上的压抑,这样就使得她们个个显得那样孤独无助。在《无字》中,张洁追述了一家四代女人的生命故事,整整横跨了一个世纪,印证的是女性在整个20世纪的漂泊历程。这部几乎是作者自传体的小说,所描写的不仅仅是主人公吴为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经历,也是作者记忆当中女人“几乎没有灯光”的历史境遇,是女性在历史和文化中的真实处境。
在追寻过程中,有的作家把希望寄托在挣脱了中国历史和文化束缚的国外,禅月、尹小帆、陆羽、黛二小姐都把目光投向了异国他乡。然而,那里也并非理想之地。如尹小帆只有在回到故乡时才能够踏踏实实地睡上一觉,真真切切地撒娇使性;黛二小姐在美国只生活了三个月就毅然决然地打道回府等。
在以男性血脉为中心的文化谱系中,女性难以找到自己的精神文化谱系。与男性作家都把自己的精神之根深深扎在故乡这片土地上相比,女性作家很难在哺育自己长大成人的故乡找到精神归属,找到现实和心灵的故乡。即使如孙惠芬这样在辽宁庄河长大,又把文学之根扎在这个地方的作家,也仅仅是这里过节时候的匆匆过客,更别说在王安忆眼中,一直认为自己是上海这座大城市的外来户,好像中间隔着一层,始终无法亲密无间地融入其中。铁凝始终思念着寄居长大的北京,迟子建表现着外婆的北极村,但这都不是自己真真切切现实和心灵的故乡,不可能像鲁迅之于“鲁镇”、沈从文之于“湘西”、贾平凹之于“商南”,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那样,把爱恨交加的故乡看作生养自己的“血地”,是埋葬着祖先、也将埋葬自己的精神文化之地。在她们的作品中,飘荡着一群天南地北漂泊的灵魂。这种漂泊折磨着作品中的人物,更折磨着作者自己。因此,她们开始执着地寻找母系血缘谱系,试图通过寻找生命之根确立母系家族起源的方式,寻找自己的精神文化之源,进行精神上的寻根之旅,来摆脱纠结于内心的无根感和漂泊无依感。结果却是,《大浴女》中漂泊到福安市、说着北京话的尹小跳、尹小帆、唐菲,始终记挂着无法回归的北京;《纪实与虚构》中对“茹”氏家族的寻找也是虚妄。最后张洁忧伤地感叹:“我们没有故乡,没有根。我们是一个漂泊的家族,从母亲,到我,到禅月。如今的我,更是一无所有。”*张洁:《无字》,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56页。王安忆的结论是:“没有家族神话,我们都成了孤儿,栖栖遑遑,我们生命的一头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另一头隐在迷雾中。”*王安忆:《纪实与虚构》,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191页。《纪实与虚构》中的主人公,作为女性的“我”,从小到大自始至终都感觉到一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尽管她为自己的祖先虚构了一个辉煌的神话历史,在事件的纵横坐标上为自己寻找到了坚实的历史依据,可在现实生活中,她却是作为一个孤儿的后代,在上海以外来人的身份开始重新建构自己的人际关系。
既然女人的过往无法追寻,那么来生的灵魂归依何处?于是张洁“转而寻求一个灵魂的故地。可,人有灵魂的故地吗?我灵魂的故地又在哪里?寻找是一个怪圈,最终可能一无所得。所谓‘故地’,也许是个手也摸不着、脚也走不到,根本不知道在哪儿的地方。说不定就怀着‘回归’的假设,死在‘回归’的路上——这个结局倒也不错。但‘寻找’的过程,是一个让漂泊之人感到有所归属的过程。”*张洁:《无字》,第56页。石评梅凄凉孤单地病逝于北平,萧红不甘心葬身于乱世的香港,张爱玲死于异国他乡洛杉矶公寓而无人知晓,苏青的骨灰几年后被友人带出国门,生前要在自己的坟前立一块“文人苏青之墓”墓碑的愿望也难以实现,等等。一代代才女们凄惨悲哀的下场,不都是《红楼梦》中黛玉《葬花吟》中感叹的“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还有祥林嫂对人死后有无灵魂的强烈质疑?
新时期之后的女作家笔下,女人们不知所往、不知所终,普遍具有一种无所归依的生命悬浮感和无根感,有的甚至属于人类所共有的漂泊意识,显示出女作家在更深层次上揭示女性漂泊意识的同时,对女性自我、人类自我的认知也更加深刻。
四
毫无疑问,20世纪中国女作家的文学创作是中国新文学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男作家对自我的观照、对生命的深刻感悟与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展现,建构中国现代文化的过程,同样深深影响着她们。“文学必须受制于民族文化。”*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第189页。由于广大女作家更加敏感于自身的性别特点,在抗拒男权中心文化的过程中,她们一直在寻找或者建构着自己所存在的文化,发掘女性长期以来被男权文化遮蔽了的个体生命意义,对女性漂泊意识的呈现,尽管也有男性作家同样具有的“由文化的衰竭与断裂所生成的无根感”,实际上更多的却是女性文化建构的艰难过程。对此,徐坤阐释说:“无论在独立于男性文化之外是否真正存在着一个女性文化与否,母亲血脉链条在历史上的被割断毕竟是一个事实。过往的历史,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阳刚谱系的书写史。短暂的母系制社会过去以后,女性的生命血脉延续史就被割断了,不再见诸于记录。女人的生命链条无以追踪和接续。天地人神,宇宙万物,无论是神话的谱系、帝王的谱系,以及民间宗族、宗法谱系,无不是在记录和书写一部男性的血缘血脉史,女性谱系的书写之页呈现为一片空白。女性作为人女、人妻、人母,虽则拥有自己的姓氏和名字,然则那种依傍于父亲或丈夫的姓名,隐匿在一个庞大家谱当中的角落里,看似有名,实则处于‘无名’状态,其实是一部男权的文明史然。在一个强大的阳刚菲勒斯审美机制的垄断之中,母性的历史无从展现。在母亲形象的书写中,除了一个源自于神话传说之中的‘地母’原型在千百年来陈陈相因,余者多是统一于男人视阈之下,两性关系中作为男人之对象化关系而存在的女性。这种‘作为对象化关系之存在的女性’,不需要有什么独立人格和独到见解,女性的一切,在男性主体叙事人的解说之中”*徐坤:《双调夜行船》,《小说界》1998年第4期。。
个体心理学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以归到:职业、社会和性这三个主要问题之下。而每个人对这三个问题作反应时,都明明白白地表现出他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和最深层的感受”*阿德勒:《超越自卑》,徐家宁、徐家康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页。。显然,在整个20世纪,女性在这三个方面都没有很好地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如果我们把女作家的漂泊意识放置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可以发现其独特的意义与个性价值,在漂泊意识产生的机制和表现形态方面,女作家显然与男作家不同。首先,相比男性,女性还没有真正找到男女平等意义上的和谐,更难以挣脱情感方面的羁绊,无论是血缘亲情还是婚姻爱情。其次,在融入社会、争取个性独立方面,女性也无法与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王安忆对女性的界定是,“相对男性的社会属性来说,女性更像一种动物,更多自然属性,更注重个人的情感世界,她们天生地从自我出发,去观望人生与世界,即使如知识女性。”*王安忆:《我是女性主义者吗?》,王安忆:《弟兄们》,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第324页。所以说,女作家的创作更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生命与情感的需要,在体验生命的深度与丰富性方面甚于男性,比男性作家多了一层来自生命意识深处最本质的体认与感悟,在现代社会有着极为独特的建构意义。知识女性既想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中找寻实现自身价值的空间位置,又想在精神和爱情层面寻觅到女性的精神家园和情感归宿。一方面,在情感归属上,都在为积极争取男女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不仅追求父母之爱,还在更高层面上追求男女之间的情爱,寻找精神栖息地。由于性别特点,在寻找的过程中,她们充分显示出在男人面前坚强与脆弱、独立与依赖复杂、矛盾、纠葛的一面。另一方面,在妇女解放的步履中,知识女性已经渐渐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依附心理,依照男人来确定自己“家”的位移,而是随着自己或父母、丈夫学习或工作单位的流动发生着变换,“娘家”固然不是自己的家,作为夫家的媳妇,也同样失去了传统意义上那个固定的“家”的归属。她们不可能像男人一样,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准确地追寻到自己的故乡、根的所在。既然失去了夫家这块可以依附的根据地,她们就会感觉自己就如浮萍一样,漂浮不定,无可依傍,无可归属,处于无处扎根、无处认同的状态。有夫之妇尚且如此,更何况处于动荡不定的爱情婚姻关系归属中的女性!作为一个日渐独立、不想依附男人过日子的单位个体,在与男权文化抗争的过程中,她们在开始思考“来自哪里”、“归向何处”这些含有哲学意味的命题。男人可以依照血脉宗亲的传承,追溯到自己根系的源泉,女性的血脉根宗该如何追溯,也同样困惑着这些具有独立意识的女作家们。第三个方面就是,女性作家在20世纪不断变换的社会大环境下人生价值的归属与实现。这几个方面时常纠缠在一起,只是侧重点不同。纵观20世纪,女作家不断地在向着自我生命深处探寻着生命、精神与情感的着陆点,安放漂泊已久的灵魂,寻找存在的文化。
许纪霖对知识分子有过这样的界定:“知识分子永远是最不安分的,总是不愿被某个固定的模式禁锢,即使他们已被定位在社会体制的某一个环节上,仍然没有安身立命之感,总是要不断地寻求着突破与更合理的归宿。在灵魂深处,他们总是漂浮的,自由地漂浮着。”*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页。但是,“任何一个生命个体都要受到来自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自然环境的以及自身生理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作家的心态必然是复杂的”*杨守森:《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8页。。女性作家作为一个更为复杂的存在,其心态将是更加深幽而复杂。纵观20世纪中国女性的文学创作,她们在寻求和探索自由和理想的过程中对自身漂泊意识的呈现,体现的既是知识女性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对女性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一步步深入思考的过程,同时又是作为中国女性在整个20世纪性格特征和精神心理特征的整体发展概貌。
[责任编辑:以沫]
收稿日期:2015-09-16
作者简介:翟瑞青,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编辑部教授(济南 250103)。
On the Wandering Consciousnes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Female Literature
ZHAI Rui-qing
(Shando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Editorial Department, Jinan 250103, P.R.China)
Abstract:The literature works by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women writer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unique.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women literature writing, there has been a refuge for wandering nothing latent consciousness, which has its different rendering features though each period. If we placed the women writers’ wandering consciousnes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we can find its uniqu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ndividuality. Women writers have obviously difference between mechanisms and manifestations in terms of awareness generated by wandering from male writers. Since the majority of women writers are more sensitive to their own sex characteristics, they have been looking for the existence or construction of their own culture from the resistance to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in the process, in order to explore female’s culture which has long been obscured the significance of individual life. It is female cultural construction process that women writers constantly toward self life to explore the depths of life, spirit and emotion of the landing site, in order to place their own long wandering soul and look for the cultural value of their own existence.
Keywords: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female literature; Wandering conscious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