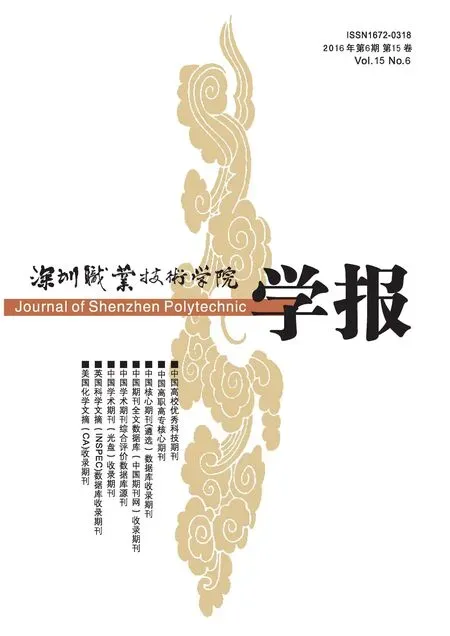家国秘史《白鹿原》
——谨以本文纪念陈忠实先生
张效民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 卷终
家国秘史《白鹿原》
——谨以本文纪念陈忠实先生
张效民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分析解读《白鹿原》的“秘”何在,纪念陈忠实先生。
《白鹿原》;“秘”;陈忠实先生
我第一次阅读陈忠实先生的巨著《白鹿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小说刚刚出版后不久。那时,我在四川一所师专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我为作品厚重的内涵和高超的艺术手法所震撼。但在当时,我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现代中国变迁史”这个水平上。现在想来,当时对扉页上巴尔扎克那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居然毫无感觉。这次重读《白鹿原》,我一翻开书,一下就被扉页上世界文学史巨匠的这句话所吸引。我的心受到重重地撞击,眼前似乎打开了一个新的境界。啊,民族秘史,这是引领重新认识、理解《白鹿原》的一把钥匙啊!
1
解读一个民族的秘史,关键在于破解这个“秘”字。中华民族、我们的家国的“秘”、《白鹿原》的“秘”在何处呢?这需要从“民族”二字说起。
什么是民族?按照权威解释,民族是指经长期历史发展而形成的稳定共同体,一群基于历史、文化、语言、宗教或行为与其它人群有所区别的群体就称为民族。
在原始社会,民族是在有一定血缘关系的部落发展起来的,首先是部落发展分化而形成的。
在封建社会,由于国家的形成,原始民族相互融合形成了新的民族。族人之间不一定有共同的血缘关系,而有着相同的国家。这是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及高峰时期,绝大多数民族雏形都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
对于这个定义以及民族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论述,我有不同看法。
从我国人种起源和民族形成,国家发展的历程来看,原始社会民族的形成与血缘、家族的发展紧密相关。上古北方神话传说中有女娲造人的说法。那是关于人类经历的第一个社会形态——母系氏族社会的传说。同时也折射出中国人类血缘关系的信息。传说中的上古八姓,姬、姜、姚、嬴、姒、妘、妫、妊,还有一种说法,这八大姓是姬、姜、姚、嬴、姒、妘、妫、姞。只有最后一姓不同。但相同的是,每一姓都从“女”字旁,这就透露出母系氏族的信息。每一姓都是女姓为首领的母系氏族。我国南方地区也有关于人类重生的传说。是说上古之时,洪水滔天,世上所有人类和生物都被淹没。只有一对兄妹于一个大盘瓠中得以幸存,为了人类的繁衍,他们兄妹成婚,生下的子女们继续不断繁衍出后来的人类。这是关于人类群居杂处时代婚姻状态的传说折射。这两个传说其实都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中国人的先民在远古传说时代,都是具有血缘
关系的,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以家庭、家族为基本社会单位来生存、生活和发展的。
随着历史的演进,人类从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黄帝则是上古时代父系氏族首领的突出代表。《国语·晋语》、《史记·五帝本纪》等古籍记载,黄帝出于上古八姓中的姬姓,他有四妃十嫔,二十五子,得姓十四人,共十二姓。具体那些姓,太复杂,这里不细说。但大致可以说,由这十二姓衍生出来属于黄帝族裔姓氏非常多,居于当今姓氏之首。至于炎帝,大家都知道,出于上古八姓中的姜姓。炎帝部落在与黄帝部落联合战胜、擒杀蚩尤,迫其余部南迁后,也留下一批姓氏。炎帝部落又被黄帝部落融合,其子孙姓氏也达百姓以上。我们今天称“炎黄子孙”就透露出中华民族的主体人群具有着炎黄二族的血脉,来源这两个氏族。黄帝五十二战天下咸服。也是以黄帝氏族为核心的部落管理天下事务。其后经尧舜禹三代,到夏朝禅让制度终止,建立“家天下”制度,经商朝再至周朝的分邦建国、以分封本族宗室于各地的封建制度形成,这种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一家一姓一族而统治天下的政治制度得以确立。因而说封建时代的民族是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群构成的说法是只看表象而忽略了本质,至少是经不起历史事实的严格检验的。
真实的历史事实恰恰相反。人类由最早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繁衍而来。由家繁衍而成为家族,再由家族繁衍而为部落,再由部落繁衍而成为民族。在这种持续不断的繁衍历史进程中,形成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为细胞、以家族为单位的“家族树”,再由若干个“家族树”而形成“民族林”。中华民族的主体就是这样从若干根深叶茂枝繁的“家族企业”而形成的巨型“民族林”。由此可以说,中国从古迄至整个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阶段中,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家族的繁衍史,发展史,家族内部和家族之间控制权力的争夺史、相互之间的倾害和残杀史,也是一部家族的迁徒史。鲁迅先生曾经深刻指出,二十四史就是一部“相斫书”,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一句话,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同家族的繁衍发展兴衰史。
2
统治权力的确立必然伴随制度的确立。制度是统治的手段,也是统治的工具。“家天下”统治的确立首先基于以宗法制度的完善,尤其根基于被统治者对于这种制度所体现的价值观念的真诚接纳和高度认同,这种“家天下”既然确立,并以《周礼》《仪礼》《礼记》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制度建构。迄至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孔夫子删定六经,游学四方,传播儒家政治思想;再经孟子等后代儒家的弘扬,《论语》《孟子》等成为儒家经典,完成了系统化的家国、社会治理思想和价值理念、行为规范的构建。忠、孝、仁、义,仁、义、礼、智、信;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存天理,去人欲;三纲五常、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妻贤等等儒家理念成为整个封建时代全社会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仁政、德政、王道等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统治者统治的最高评价标准和百姓对于皇帝以及代表皇帝治理地方官员的最迫切期盼。这个制度,就是所谓的封建宗法礼教制度。在这整套从国家到家族内部关系再到个人行为规范中,家族制度成为整个封建国家制度的基础支撑。在这套制度体系中,家就是缩小的、微型的国家;家长、族长就是这个微型国家中的王、国君。而国家则是放大了的家,所谓“家天下”、以天下为家。而国王以及此后的皇帝,则是这个巨大的家的家长、父亲。所谓“君父”。这就是所谓的“家国同构”。
这一整套制度经以孔子为最高代表的历代儒家的理论性细化、强化,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奉的统治思想,从而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主导思想和基本价值观和行为指南。由于统治集团长期的提倡和制度落实(比如宗法制度、科举制度及相关教育制度、祭祀制度、旌表制度等)、精英阶层的系统阐释宣传,最终形成了深刻影响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举止的具有超级稳定性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就规范、整合了包括农村社会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成为中国漫长、稳定的封建社会的文化心理基础。以后迄自于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中,尽管多次发生改朝换代的历史事实,但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制度和文化心理结构却并无改变。历史的事实是:一家一
姓的皇帝被推翻,另一家一姓的权势者成了皇帝。即使是造反起义的农民军领袖,在推翻了前朝统治之后,自己也立即登基作了皇帝。制度和文化一如既往,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一如既往丝毫也没有受到触动,仍然是这种以血缘为根基、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制度的牢固基础。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中,无论怎样改朝换代,总是走不出这历史的怪圈。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在大多数时间中,封建宗法礼教制度,以及几千年来由此形成的稳定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也保障了社会的有序运行和社会各个阶层、同一阶层人们各安所职、遵礼相处。这是宗法礼教制度的两个方面。认识传统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礼教制度,这两个方面都看到,才较为全面,较为深刻。
要说小说是民族、国家的秘史,我们中国延续数千年而未中断的封建社会的秘史,其“秘”就秘在这里,秘在这是一整套以血缘家族为纽带的、以家国同构为显著特征的封建宗法礼教制度:既是有效实施统治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也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还就是统治制度上层意识形态自身。这也为我们揭示《白鹿原》所蕴含秘密提供了一个根本的基础。
3
现在回到《白鹿原》。《白鹿原》描写了中国封建社会灭亡前至新中国建立这个历史时空中长安古城附近白鹿原尤其是白鹿村中发生的纷繁复杂的生治事件,并以这些事件串联出历时性的白鹿原的历史生活图景。我们确实可以由此感受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体悟历史变迁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沧桑之感。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目光停留于此,或许并未找到更深层次解读《白鹿原》的密码,因而也就不可能理解作品描绘的生活图景背后的深刻内蕴。
陈忠实先生在他的《〈白鹿原〉创作手记》中说到,为了创作这部长篇小说,“足足用了两年半时间,我的主要用心和精力都投入到我家屋后的白鹿原上,还有和白鹿原隔浐河可望的神禾原、少陵原、凤栖原和隔灞河可望的铜人原。白鹿原的西北端埋葬着汉文帝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夫人。凤栖原上埋葬着汉宣帝。神禾原是柳青住过十四年完成史诗《创业史》最后自选安葬自己骨灰的地方。秦始皇在铜人原上焚书坑儒,到汉朝又把他收缴天下兵器铸成的铜人搬来摆置在这道原上。从白鹿原东北端下原,沿灞河往东走不过二十多华里,就是挖出距今一百一十万年的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公王经。在白鹿原西端坡根下的浐河岸边,有一个新时器时期(约七千年前)半坡人聚居的完整的村庄。白鹿原至今仍流传着这个皇帝那个皇帝在原上或纵马或郊游或打猎的轶事趣闻;大诗人王昌龄在原上隐居时,种植蔬菜,下原到灞河逮鱼,也少不了吟诗;王维走得更远,从长安城东的灞桥乘一叶小舟,沿着白鹿原下的灞河逆水而上直到秦岭山中的辋川,留下千古绝唱;刘邦从鸿门宴的刀光剑影下侥幸逃生回到白鹿原上,也许是从我家的猪圈旁边的小路爬坡上到原上的驻地。”陈忠实先生写下这段话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解释说:“我不搞考古,对中国悠远的历史也马马虎虎,说以上的这些遗存的史迹景观,仅仅是想让喜欢《白鹿原》的读者,大致了解一下地理上的白鹿原的方位,以及文明进程中虽然早已冷寂的几点遗痕,多少可以感知这道横在西安城东不过二十华里的古原,和我们悠远的历史基本同步,没有隔绝,更不是世外桃源。”
请原谅我如此大段地引用陈忠实先生的原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认为这些文字准确表达了陈忠实先生为写作《白鹿原》而作的大量准备工作一一那是从历史源头上探索即将创作的作品及其人物与中国“悠远的历史"不可割断的文化血脉联系。他的作品所描绘的古原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物、人物各自的命运,不是孤立的,“不是世外桃源”而是“和我们悠远的历史基本同步,没有隔绝。”
《〈白鹿原〉创作手记》中还谈到北宋著名理学大师张载(横渠)及其弟子吕氏兄弟,引用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宣言式的语录,”说“从这四句语录就可以感知关中学派的精髓,也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我的灞河北岸的老乡党牛才子(引者注:《白鹿原》中朱先生的生活原型)的精神内质了”;他
还踏访过创造中国第一部教化民众的《乡约》的吕大临的归终之地,他说“这个《乡约》的文本,是中过宋朝进士的蓝田人宋大临的作品。《乡约》内容具体而又直接,毫不含糊,该怎么做人做事和不该做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规范性划界清楚,操作性很强。文字通俗易懂,简练顺口就很易记,显然考虑到受众绝大多数都是文盲这种实情”。“这个《乡约》里的条文,不仅编织成白嘉轩的心理结构形态,也是截至止到上世纪初活在白鹿原这块土地上的人心理支撑的框架”。他说“以《乡约》构建心理框架结构的白鹿原人,才从内在里显示着独有的共性和各自的个性”。“解构透视出白嘉轩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兴奋和痛快”。
陈忠实先生还谈到《白鹿原》创作之前认真阅读当地县志,从历史的记载中汲取写作的灵感和素材。也深化了对于白鹿原历史文化的认识,这些因素融入作者的作品,无疑为自己的创作凭添了文化的丰富和历史的厚重。
因此,我们可不要因为他那句“对中国悠远历史也马马虎虎”的话忽略了这段自述对于认识《白鹿原》所蕴含“秘史”的真正的、钥匙般的意义。
《白鹿原》中主要人物们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白鹿村,是一个聚天地灵气的神奇所在。传说是一只白鹿跃过此地,使这里的一切都变得生机勃发、毒虫虎豹敛迹,成为远近闻名的一方乐土。圣洁的白鹿就成为本地居民侯姓(或胡姓)兄弟心中的神衹。为占尽白鹿带来的福气,兄弟二人商量改换姓氏,老大一房改始为白,老二一房改始为鹿。并商定具有共同血源的白、鹿两姓共用一个祠堂,“白鹿两姓共用一个祠堂的规矩,一直把同根同种的血缘关系维系到现在”。如一个国家需要制度的维系一样,聚族而居的家族也必须以家族的制度规矩来维系。兄弟二人立下规矩,族长由白氏长门担任,子孙传袭。书中说,这“原是仿效宫廷里皇帝传位的铁的法则,属天经地义不容置疑”。到了白嘉轩、鹿子霖这一代,找到了维系家族和谐、有序相处的制度文化文本,这就是由北宋理学家吕大临按照儒家尤其是理学家观念,为教化民众而创制的《吕氏乡约》。每到家族发生大事,聚全族集体诵读《吕氏乡约》成为心须的仪程。对于违背《乡约》规定的,则施以处罚。这种处罚既有肉体的、也有精神的,比如对黑娃、田小娥、白孝文的处罚,既使被处罚者受到肉体的疼苦,也使被处罚者的精神受到折辱,丧失作为一个正常人的自尊自信,以至不能自容于这个熟悉的乡村社会。如此长期的强化性灌输由此建构了白鹿村人的文化心理,成为每个族人心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这样就把一个村庄里族长继承与皇帝帝位继承联系在一起,描述了维系家族的文化基础和依托,成为古代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缩影。而祠堂也就成为这一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物化象征。
4
家族文化心理结构具有代代传承、超级的稳定性。甚至超越了封建王朝的稳定性。其基本原因就是由于家族是具有直接血缘联系的人群组成的,这种人群既具有血缘联系的组带,又具有家族文化联系的纽带,还具有政治文化的制约。这种三重的联系与制约,在政治文化制约瓦解之后,血缘的、家族文化的制约仍然存在,并且这种制约对于个人心理、行为的约束具有超乎寻常的巨大力量。要打破这种力量对生活于这种力量控制之下的人的行为的制约,仅有外部社会的变迁是不够的。《白鹿原》通过具体可感的人物的遭遇启示我们,不触及、不打破乡村社会根本的心理文化结构是不可能的。
血缘的、家族文化的制约,最起作用的因素,是由于小国寡民似的乡村社会中,每个人的生存空间都只能存在于这个具体的环境范围内。一旦离开了这个范围的人能够获得个人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或者认同于一种新的政治、社会文化体系,那么这种制约的力量就将消失,最终将必然导致传统乡村社会以儒家学说为宗旨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彻底解构。或者说,个人欲望的释放、个人思想(包括文化心理)的解放,外部环境的彻底、真正的改变,形成的合力,将彻底地瓦解统治、维系乡村社会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心理构架,乡村社会将被一种新的文化心理所填充、所改变、所统治,乡村社会生活将
由此发生天翻地覆地变化。
《白鹿原》提供给我们的生活景象正好印证了这一判断。我们看到,作品主要描绘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共围绕农民运动所展开的合作与斗争、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残酷镇压和共产党人的持续顽强的反抗、解放战争的胜利与国民党统治的垮台,并在这个背景下表现生活在白鹿原上尤其是白鹿村中人们心理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部反映近代以来以至新中国成立历史时间乡村社会变迁史。但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确实是一部统治中国乡村几千年的文化心理构架的解构史。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国民党的统治,都未能触及乡村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以维护乡村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暴力革命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思想,既彻底瓦解了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制度,也彻底瓦了以血缘、家族为纽带、以祠堂为象征的乡村文化心理结构。这是一场比政治革命更为伟大深刻的文化革命。对未来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的影响是极其巨大、极其深远的。正如陈忠实先生在《〈白鹿原〉创作手记》中说,“《白鹿原》里的最后一位族长,依他坚守着的《乡约》所构建的心理结构和性格,面临着来自多种势力的挑战,经济实力相当却违背《乡约》精神的鹿子霖,是潜在的对手;依着叛逆天性的黑娃和依着生理本能基本要求的小娥,是白嘉轩的心理判断绝对不能容忍的;以新的思想自觉反叛的兆鹏和他的女儿白灵,他徒叹奈何,这是他那种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强势,唯一难以呈现自信的对手;他倚重的白孝文的彻底堕落彻底逸出,对他伤害最重,却撞不乱他的心理秩序”。这说明,在作家心目中,作为古老、传统乡村社会文化心理构架的象征人物,白鹿村最后一位族长白嘉轩,是这个文化心理构架一步步解构的亲历者,作为封建乡村社会文化心理的忠实构建者,维护者,他内心的纠结、失落和无奈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可以说《白鹿原》作为“民族的秘史”,其秘密就在这里:作者通过特定历史时空中生活在白鹿原上人们的行为,对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历史中最为潜在的统治基础、以儒家价值理念为思想基础、价值观念、以血缘、家族为纽带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了解构。这种解构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轨迹,具有十分重要的认识和启迪意义。
或许我们应该提醒读者注意,在解构这一心理结构的过程中,陈忠实先生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在查阅县志时,面对县志中那密密麻麻排列的贞烈妇女的名单,他“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浮上我的心里”。按照《乡约》规定所体现的价值理念,田小娥按照其自然本性的所有行为都标示出无疑是一个无可饶恕的荡妇,但在作品中,她却成为解构乡村文化心理构架的重要力量,并且得到作者的高度同情。而在另一方面,作者又对《乡约》的提供者、关学最后一位代表朱先生、《乡约》精神的化身、封建乡村社会价值观念的坚定维护者、从精神到肉体上摧残田小娥的直接责任人的族长白嘉轩以及一切思想观念和行为符合《乡约》精神和价值标准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对以鹿兆鹏、白灵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反抗意志也表达了崇仰之情。这就在对待《乡约》这一体现儒家思想和以之教化民众意图的文化心理构架,或者说对体现封建社会统治要求的价值理念表现出相互冲突的尖锐矛盾。我们认为,正是这种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作品形成了巨大的思想张力。这种思想的张力使作品的内涵呈现出丰富、真实的面貌,引导读者更加深入地去追寻和探究作品潜在、丰饶的内蕴。由此我们可以说,《白鹿原》既是一部辛亥以来近百年中国乡村社会基本价值观念、文化心理架构的解构史,也是一曲《乡约》精神的深沉、幽远的挽歌!这或许又是《白鹿原》中潜藏的又一隐密之所在吧。
5
旧的时代早已远去,新的生活仍然继续。今天,距离《白鹿原》描绘的生活终止的时间已过去了将近七十年。这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多少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的乡村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尤其是近四十年来中国的发展变化更是日新月异。与此同时,我们已经看到,当一个社会所崇奉的价
值观念被解构,个人自然欲望得到充分释放,而新的精神生活、价值观念系统又未能构建起来,人们的各种行为失去内、外约束的时候,将会发生何等可怕的事情!
今天重读《白鹿原》,我们似乎可从作品所反映的历史景象中得出某种启示:在激风暴雨般的革命或者其他内外部力量解构了基层社会的文化心理架构之后,我们社会稳定的心理基础必须认真扎实地重新构建,否则,被充分释放出来的人的各种欲望必然对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的冲击和破坏。我们应该反思,以《吕氏乡约》为代表的乡村文化价值体系,以朱先生、白嘉轩为代表的乡村文化和治理精英、以白鹿村为代表的旧时代基层以血缘、家族为单位的自治式治理模式是否真的一如是处,是否应该被彻底否定和抛弃?几千年来维系基层社会的传统文化是否可以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有序的全面小康社会起到正面积极的作用?是否可以在我们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以重新构建起与我们所处时代社会要求相适应的文化价值系统心理构架的进程中提供一定启迪、一定借鉴呢?或许是我们每一个读者都应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从我了解的情况看,当今家族文化正在复兴。一个续、修家谱,寻根问祖、祭拜祖宗,新建或修葺祠堂,发掘、整理和出版家训、族训、族规的浪潮正在形成。我认为这是对于我们过去一个时期过度否定家族文化这种乡村基层治理的文化模式的一种反拨。
历史有时显得诡异,文化应该继承,文学可以不朽。
Bai Lu Yuan: Secret History of Family and State—A Tribute to Mr. Chen Zhongshi
ZHANG Xiaoming
(Shenzhen Polytechnic, Shenzhen, Guangdong 518055, China)
This paper endeavors to interpret the ‘Secrets’ of Bai Lu Yuan, so as to commemorate Mr. Chen Zhongshi.
Bai Lu Yuan; secrets; Mr. Chen Zhongshi
I03
A
1672-0318(2016)06-0003-06
10.13899/j.cnki.szptxb.2016.06.001
2016-08-30
张效民(1954-),男,河南人,现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文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