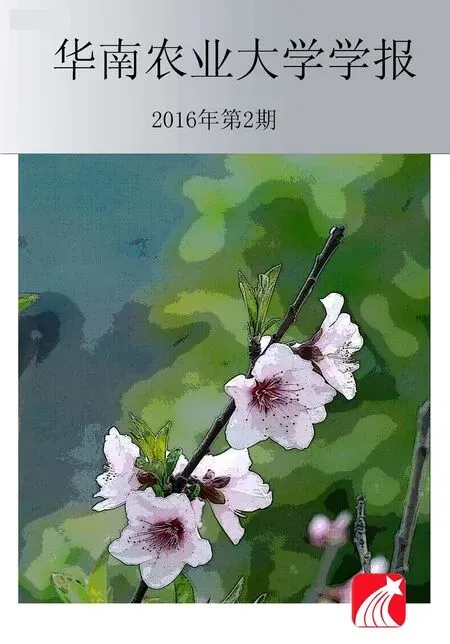能力结构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质量
李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361005;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550001)
能力结构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质量
李萍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361005;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550001)
摘要:从能力结构的角度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质量受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及其它控制变量的影响,而在控制这些变量后,个体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质量有着显著影响。其中,学习创新能力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或以创业决策等形式作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基础型、稳定型和发展型创业质量;实践活动能力通过参与的主观体验,以创业技能的操作与运用来提升三类创业质量;资源运营能力通过对社会网络等显性或隐性资源进行创造性整合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型创业质量,但其容易造成个体创业目标“游离”,导致稳定型创业质量的降低;自我管理能力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缓解压力与抵御风险,提升其稳定型和发展型创业质量。
关键词:农民工;创业;能力结构;群体特征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国外关于创业的研究可追溯至法国经济学家Richard Cantillon,他在1755年所著《商业概况》一书中首次提出企业家( Enterpreneur)一词。早期对创业的研究与风险联系密切,并逐渐发展到探讨其与创业精神、个体禀赋、个体经验等方面的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开始了从“个体性因素”为主向“结构性因素”为主转变的过程。由个体创业资金的匮乏延展至家庭经济支持的缺失[1],从个体禀赋到创业者个体素质的形成[2],随后再逐渐转移到创业者嵌入其中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与社会网络等方面,并形成了创业机会、创业网络与创业文化等代表性理论观点。对新移民而言,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准入限制、自身的语言障碍、低水平职业技能难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且社会网络规模小导致了信息匮乏等就业市场劣势,移民群体内部的凝聚力、非正式的信用、群体共享的隐性知识等移民群体的独特资源是驱动移民创业的主要原因[3]。在此基础上,“移民聚集区民族经济理论”和“移民市场保护理论”等代表性观点逐步形成。关于创业能力的研究始于Barney,其首先从资源理论的角度来观察创业现象,从而提出了创业能力的概念。创业能力作为个体特征的重要方面包含多个维度,如学习能力、行为能力等可认知的能力,以及自尊、自控等对创业有潜在影响的非认知能力等[4]。移民企业家在原属国和所在国这两种不同环境中不断平衡社会网络规模和网络范围,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应对不同环境的能力[5]。然而,由于第一代移民多为低收入群体且生育子女数较多,无力为其创业注入资本,导致其融资能力受到限制,因而专门由移民企业家投资的企业往往规模小,且市场存活率低[6]。
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研究。一方面是基于个体市民化意愿的视角对农民工创业动机进行研究。创业是农民工这一创业主体在对稳定生活际遇、经济效益以及体面生活形式的追求中实现自主性建构的过程[7]。返乡农民工通过在城务工期间不断获得现代城市社会的体验,对其精神世界或个人现代性产生影响,进而不断地建构自身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8],随着创业意识的增强,其创业资金开始不断累积,从而开展创业[9]。另一方面是基于社会网络与结构的视角对创业过程与绩效进行研究。虽然有研究认为,创业是一种系统行为,由于受到社会系统中时空的“束缚”,“创业神话”很难实现,绝大部分返乡者回到了传统经济结构之中[10]。但社会资本、服务环境等因素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企业绩效有着直接影响,政策支持和经营资源通过作用于服务环境对企业绩效起到间接促进作用[11]。关于农民工创业能力的已有研究发现,企业家能力越高,返乡创业企业绩效越好[12]。有学者从网络能力这一维度进行分析后认为,通过社会网络和产业网络的双重嵌入,获取所需的创业资源,是影响农民工创业能力的重要路径[13]。近年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进入学术视野,关于这一群体创业的研究开始浮现。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获取信息能力的增强,使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了更强的流动性和选择性,不再满足于仅仅靠打工为生,而是试图通过创业改变自己的生活[14]。而创业资源获取与创业机会感知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模式,生存型创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主导模式[15]。
从研究对象上来看,国外对移民创业的研究主要基于民族国家或种族的视角对其进行纵向发展或横向比较的研究,较之国内农民工群体的创业存在较大差异,而国内对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虽已得到较多的学术关注,但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在城市创业的研究较少。从研究主题上来看,国内外虽有学者对个体能力与创业的关系进行研究,但都将能力内置于个体特质中进行研究,鲜少将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国内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能力结构对其在城市创业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的研究极少。从研究方法上看,已有研究主要停留在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现状描述,对这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行实证分析则较为少见。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现实主体。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三高”特征及群体内部“精英”与“平民”的分化促使其不再囿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而将创业作为当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所采取的一种积极主动型的就业方式。创业不仅涉及个体行为,还需将其与所嵌入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网络进行有效连接,是一种系统行为。而个体可通过运用自身的各种能力来实现这种有效连接[16]。本文将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来探讨个体能力结构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质量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界定
1.因变量: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质量
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主要是指具有一定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现有的创业政策下,利用自身能力积极拓展与重构创业网络,识别、评估与开发创业机会,以达到一定创业质量的过程。本研究选取了8个指标来衡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质量。在对其进行因子分析之前,先进行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质量量表通过Bartlett’s球形检验表明: Bartlett值=2761. 917,p<0. 000,且KMO统计量为0. 683,表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运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对上述8个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质量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3个新因子。第一个因子主要解释“目前创业的年纯利润状况”、“目前创业的投资额”、“目前创业项目的规模”等指标,主要从经济的角度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收入等生存状态,因而将该因子命名为“基础型因子”;第二个因子主要解释“创业后收入的稳定情况”和“目前创业项目的影响力”等指标,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创业项目的持续状态,因而将该因子命名为“稳定型因子”;第三个因子主要解释“创业规模将持续扩张”、“创业的发展前景如何”和“创业项目的竞争力状况”等指标,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创业项目的内在潜力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因而将其命名为“发展型因子”,3个新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60. 870%,可以解释总方差的近61%。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质量量表的总体信度Cronbach’s alpha为0. 718,具有较高的信度。

表1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质量的因子分析
2.自变量:新生代农民工的能力结构
为有效测量新生代农民工的能力结构,在参考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16个指标,每个指标的答案分别为“很不符合”、“不太符合”、“比较符合”和“非常符合”四个选项,并用1~4分进行赋值,符合程度越强,分值越高,说明其能力也越强。这16个指标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 897,表明其很高的内在一致性。采用正交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法对新生代农民工能力结构进行因子分析,在保证特征根取值大于1、共同度大于0. 4的情况下,结合碎石图结果判断抽取4个因子,并根据其特征将其分别命名为“学习创新因子”、“资源运营因子”、“实践活动因子”、“自我管理因子”。从表2可以看出,由16项测量条目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力结构量表的4个因子分布构成合理,每一项测量条目在其因子上的载荷较高,累计方差变异解释量达到63. 982%。
(二)研究假设
创业能力的本质是不断整合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创业资源、商机和资金等,通过创业社会网络转化为企业的组织资源,再经过机会搜索和风险分担,实现创业资源的创造性整合和价值创新[17]。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三高一低”的群体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这一特征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学习能力较强,而拥有较高的职业期望和物质精神享受则表明,其不仅追求经济收入,并且对职业声望以及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有着更高的追求。但他们年青而且耐受力低,因而更倾向于冒险,当其在劳动力市场中遭遇困境与不满时,为了寻求生存而选择自主创业。
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能力越强,意味着其越能调动与利用自身的资源与社会网络,识别与把握创业机会,并及时抓住时机进行创业实践,因而能对其基础型创业质量有显著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一:创业能力越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础型创业质量越高。
H1a学习创新能力越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础型创业质量越高。
H1b资源运营能力越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础型创业质量越高。

表2 新生代农民工能力结构的因子分析
H1c实践活动能力越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础型创业质量越高。
H1d自我管理能力越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础型创业质量越高。
创业者的企业家能力越高,其管理能力和领导能力越强[11]。新生代农民工的能力越强,不仅能对自我实施严格的管理,也能对企业进行有效管理,持续为企业争取物质资源,不断优化资源结构。并且,还能有效地平衡风险与利润,准确预见风险,并帮助企业在危机来临之前规避风险,从而有效维护企业的稳定运行[18]。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二:创业能力越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稳定型创业质量越高。
H2a学习创新能力越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稳定型创业质量越高。
H2b资源运营能力越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稳定型创业质量越高。
H2c实践活动能力越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稳定型创业质量越高。
H2d自我管理能力越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稳定型创业质量越高。
新生代农民工的能力越强,其越能从战略上把握政策导向来规划企业的发展方向,并且强调创新以增强企业项目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推动企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并且通过适时适度扩大企业规模,以及利用营销手段来提升企业的影响力。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三:创业能力越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型创业质量越高。
H3a学习创新能力越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型创业质量越高。
H3b资源运营能力越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型创业质量越高。
H3c实践活动能力越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型创业质量越高。
H3d自我管理能力越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型创业质量越高。
(三)数据来源
此次调查实施的时间为2013年2月至7月。调查对象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城市创业、经商的农村人口,主要包括在农村长大而在城里创业的青年劳动人口和在城市出生、长大、在城市创业的“第二代农民工”两类群体。为了尽可能弥补以往有关研究中农民工抽样的缺陷,进行了两次抽样调查。第一次是采用流出地抽样调查,先采用立意抽样的方法选取福建、湖南和贵州三个省,再采取多段抽样方法,在现有的市(州、地)中按照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各抽取2个县(市、区),接着从每个样本县(市、区)中,随机抽取3个乡镇,再从每乡镇中各抽取60户农民工家庭,3省共抽中有创业经历或正在创业的1080户农民工家庭。然后,采取入户访问的方式从中选取1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第二次是采用流入地抽样调查,通过在商业聚集区采用“直接进店进厂”和“滚雪球”等抽样方法,在福建省厦门市和福州市,湖南长沙市和株洲市,贵州省贵阳市和遵义市,共抽取到720名有创业经历或正在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此次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1800份,收回有效问卷169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4. 2%。
三、统计结果分析
为深入探究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质量的影响因素,以调查对象的人口学变量、其社会阶层认同情况和收入状况等作为控制变量,以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能力作为自变量对其创业质量的3个因子(基础型因子、稳定型因子和发展型因子)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见表3)。首先对三个模型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检验,三个模型中各变量的VIF值(方差膨胀因子)均大于1且小于2,说明三个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而从回归分析结果中的修正后判定系数R2可以看到,自变量对稳定型创业质量的解释力最大( R2= 0. 286,P<0. 001),对基础型创业质量的解释力次之( R2=0. 239,P<0. 001),对发展型创业质量的解释力最小( R2=0. 167,P<0. 001)。
(一)从模型1中可以看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基础型创业质量的因素主要有年龄及其平方项、受教育年限、外出务工时间及其平方项、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和个人月收入自然对数。其中,年龄及其平方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前者为正,后者为负,分别为0. 209( P<0. 01)和-0. 005( P<0. 001),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基础型创业质量因子与其年龄的关系成倒“U”型,其顶点大约为21岁。①计算方法为将原变量系数除以平方项系数的2倍0. 209÷( 2×0. 005)]≈21。即新生代农民工基础型创业质量大约在21岁时最高。在21岁之前,其基础型创业质量与年龄成正相关,而超过21岁后,其基础型创业质量随着年龄的增加反而降低。已有研究也发现,农民工年龄与其创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其主要原因在于青年农民工面对创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思维容易固化,其创业绩效必然会变差[12]。受教育年限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 100( P<0. 001),表明受教育年限与新生代农民工基础型创业质量因子呈正相关,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其基础型创业质量的因子得分则提高0. 100分。以往研究也发现,拥有更多人力资本的创业者在经营企业时更容易成功[19]。外出务工时间及其平方项与新生代农民工基础型创业质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前者为正,后者为负,分别为0. 075( P<0. 01)和-0. 004( P<0. 01),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基础型创业质量因子与外出务工时间及其平方项的关系成倒“U”型,其顶点大约为9年②计算方法为将原变量系数除以平方项系数的2倍0. 075÷( 2×0. 004)]≈21。即新生代农民工基础型创业质量大约在外出务工第9年时最高。。外出务工时间小于9年时,其基础型创业质量与外出务工成正相关,而当务工时间超过9年时,其基础型创业质量会随着务工时间的增加反而降低。婚姻状况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 354( P<0. 001),表明婚姻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基础型创业质量因子呈正相关,意味着在抑制了其它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与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已婚者基础型创业质量因子上的得分平均要高0. 354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往往背负着家庭的责任与期望,或干脆以“夫妻档”的方式进行创业,因而在选择创业类型时倾向于保守和稳妥,选择投资小、见效快的创业类型。宗教信仰与新生代农民工基础型创业质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 433( P<0. 001),意味着在抑制了其它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与没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有宗教信仰者在基础型创业质量因子上的得分平均要高0. 433分。有学者指出,宗教信仰能改变创业者创业偏好,放松对创业的约束,进而对创业选择与创业绩效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20]。个人月收入自然对数与新生代农民工基础型创业质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 408( P<0. 001),意味着在抑制了其它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时月收入自然对数每提高1个单位,其在基础型创业质量因子上的得分将提高0. 408分。个人月收入的高低意味着创业资金的积累程度,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资金越多,越倾向于将其投入企业的运行之中,提升其基础型创业质量。
作为预测变量的能力结构对新生代农民工基础型创业质量施加着显著的影响。与新生代农民工基础型创业质量相关的因素主要有学习创新能力和实践活动能力。学习创新能力与农民工的基础型创业质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 219( P<0. 001),意味着在抑制了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新生代农民工学习创新能力每提高1个单位,其在基础型创业质量因子上的得分将提高0. 219分。实践活动能力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基础型创业质量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0. 074( P<0. 001),意味着在抑制了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新生代农民工实践活动能力因子每提高1个单位,其在基础型创业质量因子上的得分将提高0. 074分。可见,假设H1a和H1c得到了证实。
(二)从模型2可以看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稳定型创业质量的因素主要有性别、受教育年限、宗教信仰、社会阶层认同和个人月收入自然对数。其中,性别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 303( P<0. 001),意味着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男性在稳定型创业质量因子上的得分平均要高0. 303分。在创业过程中,由于要面临要建立婚姻关系或生育子女等问题,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稳定性会受到一定影响。受教育年限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 066( P<0. 001),表明受教育年限与新生代农民工稳定型创业质量因子呈正相关,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其稳定型创业质量因子得分则提高0. 066分。宗教信仰与新生代农民工稳定型创业质量呈显著的负相关,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 281( P<0. 001),意味着在抑制了其它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与没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有宗教信仰者在稳定型创业质量因子上的得分平均要低0. 281分。社会阶层认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稳定型创业质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 260( P<0. 001),意味着在抑制了其它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阶层认同每提高1个等级,其在稳定型创业质量因子上的得分将提高0. 260分。个人月收入自然对数与新生代农民工稳定型创业质量呈显著的负相关,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 377( P<0. 001),意味着在抑制了其它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时月收入自然对数每提高1个单位,其在稳定型创业质量因子上的得分将降低0. 377分。收入越高,选择的范围越大,新生代农民工越倾向于风险性高的项目或行业,或者急于扩大创业的规模,因而其稳定性程度反而越低。
学习创新能力、资源运营能力、实践活动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等四个因子均对新生代农民工稳定型创业质量施加着显著的影响。学习创新能力与农民工的稳定型创业质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 198( P<0. 001),意味着在抑制了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新生代农民工学习创新能力每提高1个单位,其在稳定型创业质量因子上的得分将提高0. 198分。资源运营能力与农民工的稳定型创业质量呈显著的负相关,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 274( P<0. 001),意味着在抑制了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新生代农民工资源运营能力每提高1个单位,其在稳定型创业质量因子上的得分将降低0. 198分。实践活动能力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稳定型创业质量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0. 124( P<0. 001),意味着在抑制了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农民工实践能力因子每提高1个单位,其在稳定型创业质量因子上的得分将提高0. 124分。自我管理能力与农民工的稳定型创业质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 090( P<0. 001),意味着在抑制了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新生代农民工自我管理能力每提高1个单位,其在稳定型创业质量因子上的得分将提高0. 090分。可见,假设H2a、H2c和H2d均得到了证实。
(三)从模型3可以看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创业质量的因素主要有年龄及其平方项、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和个人月收入自然对数。其中,年龄及其平方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前者为正,后者为负,分别为0. 210( P<0. 05)和-0. 004( P<0. 01),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型创业质量因子与其年龄的关系成倒“U”型,其顶点大约为26岁。①计算方法为将原变量系数除以平方项系数的2倍0. 210÷( 2×0. 004)]≈26。即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创业质量大约在26岁时最高。在26岁之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型创业质量与年龄成正相关,而超过26岁后,其发展型创业质量随着年龄的增加反而降低。原因在于随着年龄的增大,创业激情逐渐消退,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维持现状,导致发展受限。受教育年限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 043( P<0. 01),表明受教育年限与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创业质量因子呈正相关,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其发展型创业质量因子得分将提高0. 043分。婚姻状况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 221( P<0. 001),表明婚姻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型创业质量因子呈负相关,意味着在抑制了其它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与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已婚者发展型创业质量因子上的得分平均要低0. 221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已婚者的家庭经济压力和婚姻关系对其创业决策有着一定影响。宗教信仰与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创业质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 198( P<0. 01),意味着在抑制了其它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与没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有宗教信仰者在发展型创业质量因子上的得分平均要高0. 198分。个人月收入自然对数与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创业质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 170( P<0. 05),意味着在抑制了其它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时月收入自然对数每提高1个单位,其在发展型创业质量因子上的得分将提高0. 170分。
学习创新能力、资源运营能力、实践活动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等四个因子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创业质量施加着显著的影响。学习创新能力与农民工的发展型创业质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 083( P<0. 001),意味着在抑制了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新生代农民工学习创新能力每提高1个单位,其在发展型创业质量因子上的得分将提高0. 083分。资源运营能力与农民工的发展型创业质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 292( P<0. 001),意味着在抑制了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新生代农民工资源运营能力每提高1个单位,其在发展型创业质量因子上的得分将提高0. 292分。实践活动能力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型创业质量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0. 122( P<0. 001),意味着在抑制了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农民工实践能力因子每提高1个单位,其在发展型创业质量因子上的得分将提高0. 122分。自我管理能力与农民工的发展型创业质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 183( P<0. 001),意味着在抑制了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新生代农民工自我管理能力每提高1个单位,其在发展型创业质量因子上的得分将提高0. 183分。可见,假设H3a、H3b、H3c和H3d均得到证实。

表3 以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质量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能力结构的角度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 ( 1)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及其它控制变量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质量的重要因素。如受教育年限、宗教信仰和个人月收入对基础型、稳定型和发展型创业质量均有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越长,个人月收入越高,其认知水平不断提升,创业资金积累越多,越利于企业创业质量的提升。与没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有宗教信仰者的基础型和发展型创业质量都要高,但其稳定型创业质量却要低。迪尔凯姆认为,每一个宗教团体都是一个紧密团结和协调一致的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对它自身和它的团结有着十分强烈的感情”[21]。因而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创业时更易于构建与利用以宗教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获得来自宗教网络的共享信息以及各种形式的支持。但同时,由于受到宗教的教义、教规的束缚,其在创业过程中的某些行为会与教义、教规发生冲突,导致其创业的稳定性较差,尤其在娱乐、饮食等行业中进行创业更为凸显。
( 2)新生代农民工的学习创新能力和实践活动能力越强,对新生代农民工基础型创业质量越高,并且根据其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值可以看出,学习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大。新生代农民工的学习创新能力越强,越利于他接受创业培训与教育,掌握创业技巧。同时,在创业的各种具体情境与“场域”之中,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身体的在场与亲身的主观体验,与具体的实践技能相结合,利于其对创业项目的判断,从而提升其基础型创业质量。这与Ozkan提出的“学习能力及其它可认知的能力通过个体决策这一形式的对青年创业效果有重要作用”的观点一致[16]。
( 3)学习创新能力、实践活动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与新生代农民工稳定性创业质量呈正相关,而资源运营能力却与其呈负相关。这与预期相反,但可以从中得到启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规模较小,灵活性强,其资源运营能力越强,越不容易满足于现有的创业状况,而倾向于选择其认为有更多利润或发展前景的创业形式或创业项目。已有研究也发现,创业者社会网络中的潜在成员,以及网络的规模对其扩大创业规模,取得创业成功有着重要影响[22]。社会交往面广、交往对象趋于多样化、与高社会地位个体之间关系密切的创业者更容易有创新性[23]。
( 4)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创业质量受学习创新能力、资源运营能力、实践活动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等四个因子的影响,且均为正相关。学习创新能力不仅有利于创业知识与技能的掌握,还利于创业经验的学习与积累,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及其创业质量提供动力支持。已有研究认为,由于移民的创业活动是在陌生的场域中展开,其对于商业信息的获取和对创业机会的把握主要源自于信任和社会关系[24]。陈聪等人认为,在创业过程中,农民工创业面临的双重网络非叠加性质,使网络拓展能力成为农民工创业成长的关键[25]。新生代农民工的资源运营能力越强,越会充分利用与管理各种隐形与显性资源,增强创业项目的竞争力并适度扩大企业规模,对企业发展进行长远规划。此外,自我管理能力的增强,能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抵御各种压力与风险,在企业面对困境或危机时能予以理性应对,从而维持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1]FAIRLIE ROBERT W.The Absence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Owned Business: An Analysis of the Dynamics of Self-Employment[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1999,17( 1) : 80-108.
[2]BLANCHFLOWER DAVID G,OSWALD ANDREW J.What Makes An Entrepreneur?[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1998,16( 3) : 26-60.
[3]LIGHT I.Immigrant and Ethnic Enterprise in North America[J].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1984,7( 2) : 195-216.
[4]MURNANE RICHARD J,WILLETT JOHN B,LEVY FRANK.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Cognitive Skills in Wage Determination[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5,77( 2) : 251-66.
[5]PATEL P,CONKLIN B.The Balancing Act: The Role of Transnational Habitu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Balancing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J].Entrepreneurship,Theory&Practice,2009,33( 5) : 1045-1078.
[6]MUELLER ELISABETH.Entrepreneurs from Low-Skilled Immigrant Groups in Knowledge-Intensive Industries: Company Characteristics,Survival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J].Small Bus Econ,2014,42( 4) : 871-889.
[7]江立华,陈文超.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实践与追求[J].社会科学研究,2011,( 3) : 91-97.
[8]周晓虹.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考察[J].社会科学研究,1998,( 5) : 58-71.
[9]刘光明,宋洪远.外出劳动力回乡创业:特征、动因及其影响——对安徽、四川两省四县71位回乡创业者的案例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2,( 3) : 65-71.
[10]白南生,何宇鹏.回乡,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2,( 3) : 64-78.
[11]朱红根,解春艳.农民工返乡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2,( 4) : 36-46.
[12]朱红根,康兰媛.农民工创业动机及对创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5) : 59-66.
[13]庄晋财,芮正云,曾纪芬.双重网络嵌入、创业资源获取对农民工创业能力的影响[J].中国农村观察,2014,( 3) : 29-41.
[14]王正中.“民工荒”现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性选择[J].理论学刊,2006,( 9) : 75-76.
[15]刘美玉.基于扎根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机理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3,( 3) : 63-68.
[16]EREN OZKAN,SULA OZKAN.The Effect of Ability on Young Men’s Self-Employment Decision: Evidence from the NELS[J].Industrial Relations,2012,51( 4) : 916-935.
[17]JARILLO CARLOS J,MARTINEZ JON I.Different Roles for Subsidiaries: The Case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Spain[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0,11( 7) : 501-512.
[18]KIHLSTROM RICHARD E,LAFFONT JEAN-JACQUES.A General Equilibrium Entrepreneurial Theory of Firm Formation Based on Risk Avers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9,87( 4) : 719-48.
[19]SANTARELLI ENRICO,TRAN HIEN THU.The Interplay of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in Shaping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The Case of Vietnam[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13,40( 2).435-458.
[20]阮荣平,郑风田,刘力.信仰的力量:宗教有利于创业吗?[J].经济研究,2014,( 3) : 171-184.
[21](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社会学研究[M].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53-154.
[22]BAC MEHMET,INCI EREN.The Old-Boy Network and the Quality of Entrepreneurs[J].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2010,19( 4) : 889-918.
[23]张玉利,杨俊,任兵.社会资本、先前经验与创业机会[J].管理世界,2008,( 7) : 91-102.
[24]SMANS MELANIE,FREEMAN SUSAN,THOMAS JILL.Immigrant Entrepreneurs: The Identification of Foreign Market Opportunities[J].International Migration,2014,52( 4) : 144-156.
[25]陈聪,庄晋财,程李梅.网络能力对农民工创业成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3,( 7) : 17-24.
On Ability Structure and the Qua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LI Ping
( The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Department,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The Social Work Department,C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01,China)
Abstract:From the angle of structure of ability,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qua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qua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is not only affected by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s,and when all of those variables are controlled,it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individual ability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Specifically,by the way of improving the human capital or taking make-decisions as a form,the learning ability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s an impact on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al qua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the presence and subject experience,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skills,the practice ability improve the three kinds of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ignificantly; By integrating those dominants or recessive resources creatively,the operating capacity of resource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evelopment-oriented startup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but at the same time as it is easy to cause the individual business goals“free”,it leads to a lower quality of stable business; The self management ability is helpful to relieve stress and resist risk,and so as to improve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al quality of entrepreneurs.
Key Words:migrant workers; structure of ability; the quality of entrepreneurs; group characteristics
作者简介:李萍( 1982—),女,湖南冷水江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Email:1966351530@ qq.com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 12YJC840019)
收稿日期:2016-10-27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16.02.005
中图分类号:F323.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 2016) 02-004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