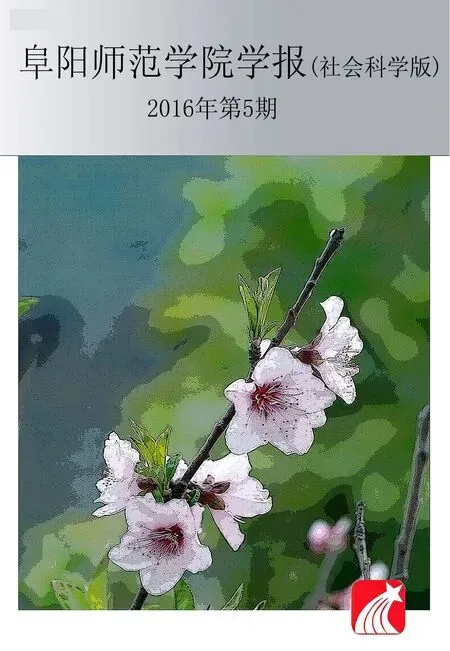柏文蔚与倪嗣冲治淮之比较
郭从杰,谢 静
(阜阳师范学院a.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b.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淮河文化论坛 主持人:吴海涛教授
柏文蔚与倪嗣冲治淮之比较
郭从杰a,谢 静b*
(阜阳师范学院a.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b.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民初时期柏文蔚和倪嗣冲都担任过安徽都督,然两人政见不同,不过均对治理淮河高度重视。柏文蔚着眼全局,系统性地提出了治淮主张,工程宏大,经费巨额,不仅需要中央统筹,还需要苏皖鲁豫四省协作。倪嗣冲的治淮考虑更多是从安徽自身出发,并将治淮重点放在皖北诸水,以有限的经费,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进行浚河与筑堤,历经数年并取得相应成效。柏文蔚治淮思想理想化背后与其居于国民党高层位置似有一定关联,其治淮主张的提出,更多可看作代表其政治呼声。倪嗣冲更多是作为一省地方长官,治淮举措更为现实,思考问题从省界利益入手,这与其追求在安徽的稳定统治存在关系。
北洋时期;淮河治理;皖北;柏文蔚;倪嗣冲
柏文蔚(1876-1947),安徽寿县人。武昌起义爆发后,柏文蔚参与领导光复南京,其所统军队后被改编为革命军第一军。柏1912年4月接替孙毓筠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1913年参加讨袁的“二次革命”,并出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一度流亡海外。倪嗣冲(1868-1924),安徽阜阳人。早年协助袁世凯编练新军,武昌起义爆发后,率兵自河南周口进入皖北,与张汇滔等率领的淮上军大战。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所部又与柏文蔚的讨袁军较量,并于同年7月担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自此倪掌控安徽大权,直至1920年9月因病辞职。
柏文蔚和倪嗣冲在辛亥革命期间属于不同阵营,双方发生两次集中性对抗,关系并不融洽,应当说,两人各为其主,政见不同。然而两人都是皖北人,家乡临近淮河,他们都重视淮患治理,本文拟比较柏文蔚、倪嗣冲在淮河治理这一水利兴修问题上的异同,并试图探讨其差异性背后的原因。
一
柏文蔚、倪嗣冲两人都重视治淮。柏氏自民元提出导淮兴垦条议至1946年为同乡王松斋的《导淮全书辑要》做序建言,前后30余年,自始至终关心治淮问题。倪嗣冲自1913年7月任皖督后,即开始谋划淮河治理,至1920年秋因病辞职,前后七年,期间治淮工程不断。
柏文蔚治淮思想系统性的考虑较早体现在《导淮兴垦条议》一文中,在文中他从淮灾的成因、导淮路径、屯垦和筹款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在导淮路径及治淮措施上他提出六点方案,即导淮由东北入海之正路、导淮自运筑堤束水归海之支路、导淮自运分泄入江之路、治洪泽、治皖北诸水、治沂沭诸水。柏文蔚认为“治长淮下部之水”,应因势利导,分别排泄于潮河口、高宝运河,自运河泄之于东坝,再分泄于沿江。治理淮河需要统筹四省力量,“窃谓长淮受害已深,非合皖苏鲁豫四省统筹大举,不足以收脉络贯通之效。苟此疆彼界,枝枝节节而为之,必至利害相反,旱涝不均,遏泄异势,纷争割裂,淮终不可治”[1]。淮水既治,溢出良田,对于耕种之区,可以采用兵屯、民垦、招垦的方式开垦。至于治淮的筹款,柏文蔚也拟出三点意见,采用借款、变通集股之法和参用国债票与彩票之法,“此筹款三法,请海内理财大家悉心研究,择一法以行。总之有利可偿。则无论借款与设法集款,均非难事。惟需政府提倡担保,以坚民信耳”。随之柏文蔚在军司令部设立导垦局,对于上述办法,逐一研究,各订详细章程[2]。
北伐进展顺利,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全国统一指日可待。柏文蔚于1928年初提出一系列的政治建设、军事善后计划等提案。对于治淮问题,他认为“导淮事业于今为急”,建议兵事定后,以被裁之兵从事导淮工作,可借债“以五千万导淮”。“文蔚于民国元年即抱屯边导淮两大政策,虽十七年来屡遭政变,未见实行,而此心此志,总思贯彻。”[3]387在1928年2月份提出的《导淮说明书》中,柏氏从利益、弭盗、裁兵、交通、防灾、政治等六个方面阐述了导淮理由,而列出的导淮办法共有七个方面,即设导淮局、导淮协会、导淮银行、筹备、施工、兴垦与筹款方法。导淮局为治淮的领导机关,导淮协会是导淮局的对应机关,讨论工程、筹款及评议方案,督促导淮局落实执行。导淮银行负责导垦工款。筹备期主要是将以前测量成绩整理、调查复测、勘定路线并进行地价登记,限一年完成。施工分三期进行,共十项工程。兴垦或令农人耕种,或兵垦,或由局召佃垦种。筹款方面,“依从前测量估计,定淮河干支各河工费总额为七千四百万元”,当然“其详细预算,俟勘定出海路线、实测各河工程后,始能确定也”[3]390-391。
在治淮理念上。柏文蔚一直关注的是整个淮河流域,不论是民元的导淮兴垦条议,还是1928年的导淮说明书,都着眼于全局,涉及豫、皖、苏、鲁四省。由于治理的是整个淮河流域,工程极为浩大,费用自然不少,1928年柏文蔚初步估算高达7400万元,且柏文蔚将治淮的重心放在疏导上,即在入江入海方面的考虑。
倪嗣冲对于淮河治理并无类似柏氏这样的全局观,在柏文蔚的治淮理念中,皖北只是其中一环。而对于倪嗣冲来说,其治淮的关注点就在皖北。倪就任皖督后,首先修筑颍上县境淮、颍湖堤沟闸,堤工从颍上南照曹台子至寿县正阳鲁台子。
1914年7月倪嗣冲致函徐世昌,报告查验皖北河工情形,倪嗣冲亲赴皖北各县查验河工,“现在工程告竣者,计蚌埠至怀远堤工二十五里,峡山口至鲁家口堤工四十余里,八里垛至三河尖堤工二百里,新河工程九十余里”“濉河暨北、西两淝业经勘估就绪,春间西淝下游已浚二十余里。迩来沿河居民纷请提前开工,以期祛除灾害。统计各河用款约在三百余万,迭饬切实核减,必须百万以外。本年五十万元,断难敷用,拟请将明年应拨之四十万元改于今年秋间提前先发,庶几易于竣事,伏乞鼎力维持。”[4]1661914年11月安徽成立了水利局。
1915年2月倪嗣冲被任命督办皖北工赈事宜,在蚌埠设水利测量局,任宗嘉禄为局长,从事皖北水系测量事宜,并在同年疏通亳县内漳河、越五河、龙凤沟、梭沟、乾溪口等河沟[5]112。在倪嗣冲的督办下,皖北水利工程逐次展开,“于是首浚濉河,次则北淝、南淝、沫、新、黑、濠、沱、茨等以及濉水上游之南、北、中三股河道,阅时三载,次第竣事。又于淮河北岸自凤台县之沫河口起,迄五河县止。南岸自霍邱县之灵水集起,迄盱眙县止,共修筑长堤达二千里。他如筹购机船、测挖河浅以利航路,建闸修坝,开通沟渠以资蓄泄,工程既多,费资亦巨。比年入夏,淫雨兼旬,而皖北未成灾象,溢出田亩甚多,此皆仰赖钧座苦心经营,造福桑梓至无量也”[4]415。
二
柏文蔚、倪嗣冲两人都对治淮较为重视,但两者在治淮具体举措上却存在差异。
柏文蔚主张裁兵导淮,“若以被裁之兵数万从事导淮”,则千万亩之地不难立致,而百余万被裁之兵,均将各得其所[3]387。而倪嗣冲更多考虑还是以工代赈,“建议政府与其从事放赈,不如就应浚之河,应筑之堤,应开之沟,择要兴工,以工代赈,洵称两利”[5]139。1916年12月18日《申报》报载:“办理河工者全为皖省官吏,而总其事者则皖省长倪嗣冲也,开工至今几及一年,初用工人四万两千,继而逐渐加添,今从事浚挖者确有五万余人。”[5]144应当说,当时倪嗣冲的治淮得到百姓的支持和拥护,“民间日睹情形,均能踊跃图功,昕夕工作”[4]166。
在治淮经费的预算与考虑上,柏文蔚的计划宏大,所需费用不低。1912年柏氏考虑“导淮及屯垦之费,至少约需二千万元”。费用筹措采取举借外债、集股或者发行国债票与彩票的办法[2]。1928年柏氏的估算已达7400万元,费用是让政府先垫支一部分,然后通过募集公债来解决,募集一万万元,以五千万元为导淮银行基金,五千万元为导淮专款[3]391。实际上,民初时期无论是中央抑或地方财政都极为困难,安徽的水利经费少之又少,如自1927年至1932年,除行政费后,单单就事业费一项而言,最多的一年为27 900元,最少的一年仅1000元,整个6年事业费总共为78 200元[6]288。
相对来说,倪嗣冲治河预算要少得多,他量力而行,边推进治河边向中央请款。1915年3月,财政部允于盐务盈余内分6年拨给安徽250万元,后来中央先期拨到银元150万,“计自三年冬季开工,先后支拨淮河工赈费472500余元,开浚寿县新开河、南陀河、北淝河、阜阳新开河、西淝河、茨河等。拨建筑沿淮圩堤工赈费135 000余元,亳县等开沟费7 000余元,购办挖泥机器经费52 000余元,及垫拨本年急赈67 000余元,四年凤怀宿寿等县赈款11000元。本处及转运员司一切开支共约110余万元。其阜阳新开河业经竣工,余如黄河水大不能兴工,淝淮等河正在继续浚筑。现计尚未动支之款约30余万”[5]139。由于浚河导淮以及散放急赈,悉赖此款,倪嗣冲严格督导经费的使用,在得知工赈局主任方汝济等侵吞赈款后,谕令痛责方汝济二百军棍,“旋令钉镣收禁,讯明尽法惩办。尚有株连者如某县邱某、某县彭某,为数颇多”[5]195。由于中央经费不能及时跟进,倪嗣冲还采用盐斤加价或田赋附加的方式来解决经费不足。
倪嗣冲治淮重点始终放在皖北,“此次开浚淝、淮、陀、茨等,各河仍以淮河归宿,其滨淮地亩则筑长堤以障之。寿县之新开河亦为宣泄瓦埠湖及上游阜六等县水道之用”[5]139。而对于皖北治水之次第,柏文蔚的考虑是“除颍州以上地势较高,无庸濬治外,其自正阳而下,直至五河长淮,两岸一律起筑堤防”[7]。而有意思的是倪嗣冲督皖后首先治理就是颍州辖内颍上、亳县的水系,这应与倪嗣冲是颍州人有一定的关系。
不过两人都对濉水的治理重视,柏文蔚主政时期访聘水利专家宗嘉禄,倪嗣冲上任后依然重用宗,后在宗的测量和规划下开浚濉河。“濉自江苏之萧、铜经宿、灵东趋五、泗,清季以来每届夏秋,霪霖横溢,沿濉三百里,横二十里田庐稼穑,悉在钜浸中,男妇老幼骨立菜色,逃亡乞食以数万计,见者咨嗟叹息,无可为计。”正是在倪嗣冲的治理下,“请命枢府得款百万馀,设立工赈处,召集地方官绅剀切劝告,教立程限,躬其不率者,越三年筑淮堤三百余里,浚渠塘以千计,而濉河亦同时告成”[5]284-285。
三
柏文蔚、倪嗣冲在治淮理念及具体措施上存在差异,因此其成效也就不同。
柏文蔚公开提出导淮兴垦条议后,于1912年6月17日致电袁世凯,称已派宗嘉禄、陈伯盟赴沪面商张謇、许鼎霖,讨论具体实施办法,议决苏皖合作,同时规划,并已派测量队,分测上流诸水。至于导淮经费,“闻张、许二绅言,政府已在大借款内列入一千万”,柏文蔚认为导垦本属两事,“仅言导则一千万之数能否敷用已不可必,继导以垦,更虞不足”,眼下设局规划、调查测量,则“应先筹拨十万为开办之费”[3]22。为弄清导垦路线和区域,柏文蔚随之要求民政长“从速召集本邑士绅,征求关于水道之图志、图说与近五年来灾情水势之说明书,或士绅有对于本邑水利之意见书”,要求一月内呈送[3]33。
可以说柏文蔚就任安徽都督后试图刷新政治,有所作为,导淮兴垦条议的提出就是例子。民初百事待举,如何处理轻重缓急就很重要。柏文蔚在1912年10月于省议会的讲话中对自己先前措施设想已有所反思,“文蔚任事之始,不自度量,颇思有所建树”“及其事实之呈露,往往出诸所期之外。故迩来心理为之一变”,就行政言之,当暂守消极主义,不当用积极主义。柏文蔚提出内政尤先注重于治盗、禁烟二事[3]105。柏文蔚的讲话中关于淮河的治理未有提及,加上当时政局不稳,柏氏治淮设想只能束之高阁了。1913年6月柏被免去安徽都督一职。柏文蔚对于淮河问题的关注并未停止,1917年4月江皖水利联合研究会在南京成立,柏文蔚还被选为理事长。柏文蔚还与孙中山深入谈论过导淮问题,主张导淮入海,并将自己收集的导淮资料献给孙中山,孙在《建国方略》中采纳了他有关导淮方面的建议。
北伐时期,1927年1月柏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旋于10月被蒋介石剥夺了军权,任其为北路宣慰使。1928年2月柏氏再次提出治淮主张,或许为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导淮委员会做了一些铺垫。实际上,由于柏氏的设想过于浩大,但在国民党政权尚未稳定时提出这一治淮方案,实难引起中央关注,自然也难以被当局所采纳。
1946年10月,柏文蔚为王松斋《导淮全书辑要》做序,文中感叹时光荏苒,治淮主张各有辩论,莫衷一是,柏文蔚仍建言从灌口入海。“余老矣,有志未逮,诚得当代伟人见诸施行,必可为长淮流域新辟一大农区,而富民富国,其利无穷。即或未能速成,而刊布此书,以广为宣传,则淮民知识宏开,亦必奋然兴起而急图之矣!”[3]415
与柏文蔚不同的是,倪嗣冲任皖督一职长达数年,这也为其持续推进淮河治理提供了职权上的保障。在倪嗣冲的督办下,皖北诸河包括濉、北淝、西淝等得到疏浚,“予皖人也,淮祸吾皖独烈,吾皖民之疾苦,又知之最深,讵能恝然不为之策?二年秋,既奉令督皖,四年复督办皖北工赈事宜。旌车所莅,目睹茭芦纵横,瓜蔓泛溢,流民之穷,而匪而丐者比比。是益怆然不能去诸怀。乃分设水利局于蚌山,并设平面测量所,遴员四勘灾区,从事实测。以支流之为祸也,首疏睢水,修堤达二千里,睢疏。乃次及淝、沫、新、汝、谷、茨、黑、濠诸河,闸坝塘堰罔不治。皖之北乃大熟,吾民咸让”[4]403。其间,倪嗣冲曾受省议会质问,要求就疏浚淮河等情答复,倪嗣冲就工期进展、河流的治理和费用支出情况作了详细说明[5]139-140。
应当说,柏文蔚的治淮理念是标本兼治,统筹兼顾,但受时局所限,方案最终搁浅。而倪嗣冲同样明白只有治本才能解决淮患问题,“虽然重枝蔓而轻本根,非予之初志也。本根之计,固梦寐不能忘导淮。今年(1919)夏,综核勘淮成绩,列图凡十有六。其计画仍主江海分疏,惟与时贤所议稍异,其途径犹惧规度之未尽也,敢以质之中西人士”[4]404。但在具体操作中,他从治标入手。
1919年9月倪嗣冲为导淮图说作序中提到:“征之近史,未及一世,而皖灾者九。呜呼,惨矣!夫良骥却百步,跛蹩至千里。盖行与不行之殊程耳。今之抱民瘼者,莫不昌言导淮矣。上而枢府,下而绅耆,旁及域外技师,抵掌喷墨,动盈千万言,纷若聚讼,惟龂龂于入江入海分,入江入海之争,而罔衷一当,以是卒凝滞隔阂而不能行,予心恫久矣。”[4]403倪嗣冲勇于担当,身体力行,“倪公时兼任省长,独慨然发愤,引以为己责,誓不为民除害不止”。通过筑淮堤、浚渠塘,“今又三四年矣,其田野日辟,其生产日饶,其人民日滋长而富庶,咸曰非倪公之力不及此”[5]285。
不过,倪嗣冲也为从根本上治淮做了一些调查准备。1920年5月,安徽督军公署、安徽省长公署咨送治淮调查图说致全国水利局,称“乃以入江入海迭起纷争,莫衷一是。与其空言无补,毋宁实地调查。当经会办禀承钧座派员会同苏绅王绍鹤前往江海各口实行履勘,遴委测量所组长余明德、齐群,会同水利协会主任王绍彬等,于前年夏间由蚌出发。王绅因事衍期,该委等遂单独前往。三月以来始行勘竣,制图十六,益以豫、苏两图,共计成图十八幅”。“会办呈请创办平面测量,调员购器,煞费张罗,岁逾三年,计测竣区域八万方里,绘成平面图三百余幅。”“嗣冲前办皖北工赈,即督饬该局派员实测,冀明真象。兹据该局呈送图说前来,嗣冲等悉心核阅,考据尚属精详,堪为研究导淮之助。除分咨外,相应备文,连同原呈图说咨送。”[4]415-416
四
柏文蔚长年追随孙中山,实为国民党元老之一,其考虑问题往往更为宏观,他对淮河问题的思考不仅是救济民生,更多的是政治诉求。柏文蔚的导淮思想集中体现在1912年的导淮兴垦条议、1928年的导淮说明书上。事实上,柏督皖期间多以借款度日,自然无力去落实治淮设想,而1928年的导淮说明规划,因时局未靖,军事仍在进行之中,也难以契合当时中央的关注重心,其导淮的倡议更多可以看作是革命家的政治呼声。
倪嗣冲属于北洋派系,1913年7月被袁世凯任命为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后,此后长期掌控安徽。对于倪嗣冲来说,稳定在安徽的统治是至关重要的,对于皖北淮水的治理,与其有效治理安徽直接相关,因此倪嗣冲的着眼点更多是从自己的省界利益来考虑,对于导淮争辩入江入海并未太多关注,而是重点勘察皖境水系,推动本省治河工程落实。1914年全国水利局成立后,苏、皖“原定计划由江淮水利测量局负责测量,共需测量经费87 536元,以皖七苏三比例由两省筹款,计皖省应负担61 270元”。1915年11月,安徽去函江淮水利测量局,要求停止合作,并要追回已拨之测量费10 212.5元。根据皖北水利测量所宗嘉禄的估计,若有安徽自行测量,应测面积6万余方里,仅需费7万余元,而江淮水利测量局在皖境仅计划测量2万余方里,却要安徽担负6万余元。全国水利局希望皖省能配合,但倪嗣冲不予接受[6]289-290。
苏皖协作中断,龚心湛总理居中调节,1919年江淮水利局再派柳汝砺代表来蚌,与倪嗣冲商量,议定皖省补测剖面,“与江淮测员双方进行,以资印证而免功败垂成”。随后倪令人“组织三十班分投从事,转瞬告成,益可资导淮计划之参考”[4]415。补测皖省剖面可以协作,当“水利交涉,案牍盈筐累箧,皖人与苏人争”“群构交问,纷纭纠结,势不可解”。倪嗣冲更多的是从安徽自身考虑,特别是将重心放在皖北[5]284。
综上而言,柏文蔚、倪嗣冲同属皖人,深知淮河水患的影响,因此都对淮河治理极为关注。柏文蔚导淮的整体设想过于理想化,一些具体的建议也存在技术性问题。应当说柏氏的导淮主张更多彰显的是其政治诉求,也就是说柏氏治淮的提出或借以引人对治淮问题的关注,或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凸显自我声音。相比柏文蔚,倪嗣冲治淮主张则更为现实,较多体现的是身体力行,他领导、组织、参与了淮河治理,虽未从根本上解决淮患问题,但其量力而行,治理皖北诸水,特别是筑淮堤、浚濉河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于淮河的治理,在北洋时期安徽历任军民长官中,无疑倪嗣冲的成就最大,这是难能可贵的。然受时代局限、财政、工程技术等因素制约,无论是柏文蔚还是倪嗣冲,都难能完成对淮患的根治。
[1]导淮兴垦条议[N].申报,1912-05-26(3).
[2]导淮兴垦条议(续)[N].申报,1912-05-28(3).
[3]孙彩霞.柏文蔚全集[M].合肥:黄山书社,2011.
[4]李良玉、陈雷.倪嗣冲函电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5]李良玉等著.倪嗣冲年谱[M].合肥:黄山书社,2010.
[6]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
[7]导淮兴垦条议(续)[N].申报,1912-05-27(3).
The Comparision between Bai Wen-wei and Ni Si-chong on the Control of Huaihe
GUO Cong-jiea,XIE Jingb
(a.School of History,Culture and Tourism;b.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Fuyang Normal University,Fuyang236037,Auhui)
Bai Wenwei and Ni Sichong both took the positions of governors of Anhui provin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Although they held different opinions on politics,they both took measures to control of Huaihe.Bearing in mind the overall interests,Bai Wenwei put forward the ideas of managing Huaihe systematically,which was a magnificent project and was full of great expense and not only required the plan as a whol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ut also required the corporations with the other provinces.As for Ni Sichong,he thought more from Anhui itself,attached more importance to the river in the north of Anhui,with the methods of delivering wages for the people who took part in the governing activities by limited expenses building dams,which came into effect after several years.Bai Wenwei's ideas of managing Huaihe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his high position in the Kuo Min Tang,which would represent his political demands.However,Ni Sichong's measures of governing Huaihe raised from the mutual benefits of the provinces was more practical as a magistrate,which was connected with his stable dominion in Anhui province.
Beiyang period;the control of Huaihe;the north ofAnhui province;Bai Wen-wei;Ni Si-chong
K928.42
A
1004-4310(2016)05-0007-04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5.02
2016-07-15
郭从杰(1976-),男,安徽太和人,阜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谢静(1983-),女,安徽阜阳人,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