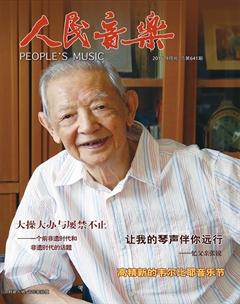武德内教坊与云韶府(院)
张咏春 郭威
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在唐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之对应的是唐朝中央用乐管理机构之扩充,开元内教坊、两京左右教坊、宜春院、梨园等先后见诸史册。查阅史籍可知,唐朝用乐管理机构名目较多,通过梳理、分类,我们发现其中许多机构以服务内廷为主要职能。因此,从内廷用乐的研究视角划分内廷用乐管理机构之类型,总结其特征,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唐代音乐史的研究,进而为探讨唐宋以来相关机构的发展脉络做好准备。
不同于开元内教坊,唐初武德年间设置的内教坊(武德内教坊)与武周“云韶府”、开元以来的“云韶院”一脉相承,属“后宫类型”,具有此类型机构之典型特征:以后宫仆役为音声承应者;职能方面礼俗兼备,但强调音声的娱人功能;为皇室“私人定制”,对外较少公开;与封建国家的主流音声传承体系相接通,表演当时的主流音声形式。
一、武德内教坊——云韶府(院)
(一)建置沿革
唐初的内廷之乐,直接继承自隋。然就目前所见,并未发现有隋代内廷乐专门管理机构的名称:弘又修皇后房内之乐……命妇人并登歌上寿并用之。职在宫内,女人教习之。①唐朝立国之初,于高祖武德年间,在内廷设置内教坊,这是唐代的第一个内廷用乐管理机构,其中承应音声之女乐被称为“宫人”。武周如意元年(692年),作为武则天机构调整规划中的一部分,为区别于“万林内教坊”,武德内教坊更名为“云韶府”:武德后,置内教坊于禁中。武后如意元年,改曰云韶府,以中官为使。②
按唐制,“凡京城决囚之日,上食蔬食。内教坊及太常皆彻乐。每岁立春后至秋分,不得决死刑”③。这一定例大约始自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撤乐”的意思不仅是停止音声表演,包括音声教习在内的一切用乐活动均在其日暂停④。文献中把武德内教坊与外朝主要用乐管理机构——太常相并列,足证武德内教坊作为该时期内廷专职机构的特殊地位。在开元年间新设诸机构之前,武德内教坊(云韶府)曾是唐王朝唯一的内廷用乐管理机构。
唐神龙年间,云韶府可能一度改回原“内教坊”之名。不过,从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颁布《内出云韶舞敕》诏书可知,“云韶内府”是这个机构在那时曾使用的官方称呼:“……自立云韶内府,百有余年都不出于九重。今欲陈于百姓,冀与公卿同乐,岂独娱于一身?”⑤当然,开元年间以来,随着宜春院等机构的设置,它已不是唐王朝唯一的内廷用乐管理机构,唐人又称其为“云韶院”。
经历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内廷用乐活动逐渐恢复,承应音声的内廷宫人不断得到来自宫闱之外新鲜“血液“的补充,作为管理机构的云韶院可能至唐文宗在位时(826—840)仍存。段安节之父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曾提及唐文宗时的云韶院:“翊善坊保寿寺,本高力士宅。……忽于破瓮中得物如被。……乃画也。……访于常侍柳公权,方知张萱所画《石桥图》也。……先帝好古,见之大悦,命张于云韶院。”⑥
(二)与开元新设教坊、宜春院之区别
武德内教坊、云韶府(院)的音声表演群体以后宫仆役充任,称“宫人”,活动范围往往被严格限制在深宫禁苑,仅供皇室享乐。这是其与开元新设教坊、宜春院之间最为直观的区别⑦。而开元内教坊、左右教坊的活动范围不限于御前,非为皇室“私人定制”。
按服务内廷的方式和类型,教坊乐人可分为高级技术官(教坊副使)⑧、在御前表演音声的“长入”供奉官⑨、负责教习内廷音声的音声内教坊众博士⑩以及在教坊组织下,每日分班入宫轮值的教坊乐籍{11}。其中,每日轮值的教坊乐籍人数最多,唐人诗作生动描述了教坊乐籍入宫轮值的情景:“青楼小妇砑裙长,总被抄名入教坊。春设殿前多队舞,棚头各别请衣裳。”{12}显然,这“青楼小妇”绝非常年幽闭在后宫之宫人女乐!
二、武德内教坊与云韶府(院)的执事群体
(一)人员构成
作为唐代内廷用乐管理机构的“后宫类型”,武德内教坊与武周云韶府、开元以来的云韶院在人员构成方面可分为两部分:乐官和宫人女乐。
乐官方面,武德内教坊与云韶府(院)的最高管理者称“使”。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唐玄宗任命宦官苏思勖为云韶使以掌管宫中之云韶院:……开元十三夏,授内侍。……宜加等数,可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省内侍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食邑三百户。又至开廿三,奉诏:……可进常山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检校云韶使。移风易俗,属此司焉。{13}
开元二十三年任命的云韶使苏思勖,其“散阶银青光禄大夫已经是三品,职事也是四品的内侍”{14}。对比太常之最高长官——太常卿,也不过“天宝初升入正三品也”。{15}由此不难发现,开元以来,即使在内廷用乐管理机构扩充的背景下,云韶院仍然在唐代内廷用乐体系中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
唐代后宫管理有内官、宫官、内侍省三大系统。其中,宫官“六尚”沿袭自隋代。
开皇二年,著内官之式……置六尚、六司、六典,递相统摄,以掌宫掖之政。一曰尚宫……二曰尚仪,掌礼仪教学。管司乐三人,掌音律之事……六尚二十二司,员各二人,唯司乐、司膳员各四人。{16}
武德内教坊与云韶府(院)的音声承应者均为女乐,来自后宫宫人(宫女)。在本机构内管理她们的技术官,自然也应是内廷女性乐官。唐代在宫官“六尚”的尚仪局之下,设置有司乐二人(正六品)、典乐四人(正七品)、掌乐四人(正八品,《旧唐书》载为2人),“司乐掌率乐人习乐、陈县、拊击、进退之事”。{17}
武德内教坊与云韶府(院)的女性乐人被称为“宫人”,其中多有来自外朝的乐籍中人,是宫人群体中有音声技艺者。唐代后宫内侍省下属之掖庭局,掌管宫人之名籍。按唐代籍没制度,“凡初被没有伎艺者,各从其能,而配诸司。妇人工巧者,入于掖庭”{18}。包括承应音声的宫人女乐在内,服各种杂役的宫人,名籍在掖庭,或有良家子,亦多有被籍没之贱隶。唐代的“掖庭女乐”所指就是宫人女乐,至中晚唐仍不断有乐籍中的女乐被纳入掖庭。
(二)宫人女乐的音声技艺
武德内教坊、云韶府(院)的宫人女乐,承担的音声职能可谓礼俗兼备,尤以承应礼制仪式之外的“俗乐”为主要职能。其音声表演具有以声色娱人的特征,为皇室“私人定制”,对外较少公开,具有极高的观赏性和艺术性,表演着所处时代的主流音声形式。
唐代之“礼乐”包括3种类型,即:用于卤簿仪仗之乐;用于礼制仪式之雅乐;用于礼制仪式之俗乐。唐代之“俗乐”具有双重定位,即:在礼制仪式之外,与礼乐相区别的俗乐;以及与礼制仪式相须为用,性质仍为礼乐,但与雅乐相区别的俗乐。{19}
唐武德内教坊“按习雅乐”{20}的职能承继自隋代,设立之初,于内廷承应礼乐中的雅乐。唐代礼乐中的雅乐,用于“五礼”中的吉、嘉、军、宾之礼。内廷宫人女乐承应的雅乐,则用于“皇后亲蚕”{21}等少数后宫吉礼仪式以及“上寿”“朝燕”等嘉礼、宾礼仪式。
不过,唐王朝在内廷教习宫人女乐,显然不仅仅是为了演习雅乐。武德内教坊、云韶府(院)的主要职能,实为承应礼制仪式之外的“俗乐”。
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宴设酺会,即御勤政楼……天子开帘受朝……太常大鼓,藻绘如锦,乐工齐击,声震城阙。太常卿引雅乐,每色数十人,自南鱼贯而进,列于楼下。鼓笛鸡娄,充庭考击。太常乐立部伎、坐部伎依点鼓舞,间以胡夷之伎。日旰,即内闲厩引蹀马三十匹,为《倾杯乐曲》……又令宫女数百人自帷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虽太常积习,皆不如其妙也。若《圣寿乐》,则回身换衣,作字如画。{22}
宫人女乐承应的歌舞伎乐是那个时代的主流音声形式。在太常乐师的指导下,宫人女乐习得并演出的《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圣寿乐》,“虽太常积习,皆不如其妙也”。足可见宫人女乐的表演具有极高的观赏性和艺术性。
唐代宫人女乐的表演具有以声色娱人的特征,表演内容多为礼制仪式之外的“俗乐”。与宜春院的内人女乐相比,宫人女乐之技艺水平虽有差距,却也具有一定水准。
德宗在位岁久……尝侍宴鱼藻宫……宫人引舟为棹歌,丝竹间发,德宗欢甚……{23}
为皇室“私人定制”,对外较少公开,是内廷用乐机构之“后宫类型”的重要特征。
贞观年间李元昌谋逆,竞以索要太宗御前弹琵琶宫人女乐为条件。
汉王元昌,高祖第七子也……知太子承乾嫉魏王泰之宠,乃相附托,图为不轨。(贞观)十六年,元昌来朝京师,承乾频召入东宫夜宿,因谓承乾曰:“愿陛下早为天子。近见御侧,有一宫人,善弹琵琶,事平之后,当望垂赐。” ……十七年,事发……太宗事不获已,乃赐元昌自尽于家,妻子籍没,国除。{24}
唐玄宗于开元十二年(724年)颁布《内出云韶舞敕》,向来为皇室“私人定制”的云韶宫人女乐可以对外公开表演:“……自立云韶内府,百有余年都不出于九重。今欲陈于百姓,冀与公卿同乐,岂独娱于一身?……开元十二年正月”{25}
可见,宫人女乐的音声表演专供皇室、以声色娱人,其群体较为封闭,即使贵为皇室宗亲也不能擅自求取。虽有玄宗御勤政楼对外展示宫人歌舞女乐,然而被选入内廷成为宫人女乐后,面向臣民公开演出者,除玄宗一朝在唐代仍属鲜见之事。
实际上,宫人女乐往往需要等到年长色衰后方能得以出宫重获自由,被放归的主要出路不外乎“入道”或“归家”。如唐人王建《送宫人入道》{26}所云:“弟子抄将歌遍叠,宫人分散舞衣裳……发愿蓬莱见王母,却归人世施仙方。”但如唐人张籍《旧宫人》{27}所云,宫人长期处于封闭环境中,一旦放归,家又在何处呢?“歌舞梁州女,归时白发生。全家没蕃地,无处问乡程”。
三、与外界之联系
“后宫类型”是内廷用乐管理机构的典型代表,其影响范围相对有限,却又不是孤立的存在。通过接受太常、教坊乐师之教习,不断吸纳来自宫闱之外乐籍的新鲜“血液”,唐代的武德内教坊和云韶府(院)实现了与封建国家主流音声传承体系之间的内外接通。
(一)教习。按唐制,地方官府的乐籍中人需进京轮值、轮训,这一制度保障了自宫廷到地方官府用乐的规范性、一致性{28}。以乐籍中人为主体,构建起唐王朝的主流音声传承体系。内廷宫人女乐被放归的主要出路是“入道”或“归家”,缺乏制度化的对外传授技艺行为,故影响范围实为有限。不过,为满足皇室用乐需求,保证以高水平音声供奉御前,武德内教坊和云韶府(院)必须与封建国家主流音声传承体系相对接,从而不断更新发展。
……长社王求礼上表,以为太宗时有罗黑黑,善弹琵琶。太宗阉为给使,使教宫人。陛下若以怀义有巧性,欲宫中驱使者,臣请阉之,庶不乱宫闱。{29}
由于宫闱禁地外人不可擅入,贞观年间的琵琶名手罗黑黑被“阉为给使,使教宫人”。贞观年间的武德内教坊与太常分工明确,太常兼管雅俗乐,故罗黑黑当是太常乐工。直接把外朝优秀乐工去势,以之教内廷的做法在唐代并非常制。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年)之后,宫禁更严,违制者当附律处死。
五年……太常乐工宋四通并给使王游道、长吉等入监内教。因为宫人通传消息,帝特令处死,仍遣附律。谏议大夫萧钧奏曰:四通等所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帝曰:……宫闱之禁,其可渐欤?……今喜得萧钧之言,特免四通等死,配流远处。{30}
既然太常乐工曾被去势后入内教习宫人女乐,太常乐工还可“入监内教”并为宫人通传消息,则太常乐署与内廷之关系渐明。开元年间之前,武德内教坊、云韶府内部有一定的教习机制,但负责教习内廷机构者,是太常所辖之乐署。通过贞观年间太常少卿祖孝孙亲自教习宫人女乐的记载,可以证明,内廷乐是与唐王朝主流音声传承体系同步发展的。开元年间之前的太常兼管雅俗乐,有太乐署、鼓吹署、别教院等乐署。既然太常少卿教习宫人女乐“不称旨”,此后还需再选“专业方向”更为接近的太常乐师“入监内教”。祖孝孙与宋四通先后入内教习音声,印证了武德内教坊、云韶府的确具有礼俗兼备的职能。
时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教宫人声乐不称旨,为太宗所让。珪及温彦博谏曰:“孝孙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顾问不得其人,以惑陛下视听。且孝孙雅士,陛下忽为教女乐而怪之,臣恐天下怪愕。”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何乃附下罔上,反为孝孙言也!”{31}
承应礼制仪式之外的“俗乐”是武德内教坊、云韶府(院)的主要职能。自开元内教坊设立后,教坊分担了管理俗乐的职能,亦参与对云韶院宫人女乐的音声教习。唐文宗时,后宫妃嫔联合教坊乐官、宫人女乐{32}构陷太子的事件,显现出教坊乐官与内廷存在密切来往。
(开成四年,839年)上泫然流涕曰:“朕贵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刘楚材等四人、宫人张十十等十人,责之曰:“构害太子,皆尔曹也!今更立太子,复欲尔邪?”执以付吏,己巳,皆杀之。{33}
(二)纳新。与封建国家主流音声传承体系之间的接通,不仅表现在音声技艺的教习方面,还表现在人员的更新与补充方面。“后宫类型”内廷乐管理机构下的女乐群体,其人员更新与补充主要通过从宫外籍没,或接受外朝进献女乐等途径。
(唐宪宗元和,809年)四年,(白)居易见诏节未详,即建言乞尽免江淮两赋,以救流瘠,且多出宫人。宪宗颇采纳。是时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内禁中,或言普宁公主取以献,皆頔嬖爱。居易以为不如归之,无令頔得归曲天子。{34}
文献中多有像于頔这样的唐代地方官向皇帝进献女乐的记载。这些来自各地的乐籍中人,把经过主流音声传承体系规范之乐以及具有地方特色之乐带入宫中,丰富了内廷乐,满足了皇室的音声享乐需求。
从宫外籍没是唐代补充内廷宫人女乐的重要途径,被没者的名籍在掖庭。这些被籍没者中,多有身负技艺的外朝乐籍中人,她们同样把经过主流音声传承体系规范之乐以及具有不同特色之乐带入宫中。至晚唐,懿宗即位后仍从宫外籍没女乐,配入掖庭。
(大中十三年,859年懿宗即位)国子司业韦殷裕于阁门进状,论淑妃弟郭敬述阴事。上怒甚,即日下京兆府决杀殷裕,籍没其家。殷裕妻崔氏,音声人郑羽客、王燕客,婢微娘、红子等九人配入掖庭。{35}
内廷宫人女乐与太常、教坊和宜春院等机构之乐籍,本质上属于同一个音声传承体系。云韶院宫人中的佼佼者,甚至可以成为高水平的宜春院“内人”之师。由唐文宗朝宫人沈阿翘之个案知,配属外朝官员的乐籍中人,因官员获罪被籍没入掖庭,成为宫人女乐,这属于同一个体系内部之人员流动。
大和九年(唐文宗,835年)诛王涯、郑注后,仇士良专权恣意,上颇恶之……时有宫人沈阿翘为上舞河满子。调声风态,率皆宛畅。曲罢,上赐金臂环,即问其从来。阿翘曰:妾本吴元济之妓女。济败,因以声得为宫人……上因令阿翘奏凉州曲。音韵清越,听者无不凄然。上谓之天上乐,乃选内人与阿翘为弟子焉。{36}
结 语
武德内教坊与云韶府(院),与唐代主流音声传承体系之间密切联系,属于唐代内廷用乐管理机构的后宫类型,供皇室专享的后宫宫人,主要以歌舞女乐娱人。宋代皇宫内的仙韶院是唐代武德内教坊与云韶府(院)的后继者,其以歌舞女乐专供皇室,极少对外公开,具有极高的观赏性和艺术性。然而,唐文宗朝曾设置“仙韶院”,该机构与同时期的唐代云韶院有何不同?与宋代同名机构间有无联系?元、明、清时期,这种后宫专设女乐群体,并配备专门管理机构的做法戛然而止,其中原因又是为何?凡此种种,值得进一步探究。
① [唐]魏徵《隋书》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54页。
②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8,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44页。“万林内教坊”即原来的“内文学馆”,主要职能与音声表演没有直接关系。
③ [唐]李林甫《唐六典》卷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
④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50,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40页。“(唐太宗)朕今庭无常设之乐,莫知何彻,然对食即不啖酒肉。自今已后,令与尚食相知,刑人日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并宜停教。”
⑤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8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21页。
⑥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12—813页。
⑦ 宜春院女乐称“内人”,整体技艺水平高于云韶之宫人。关于两者之间关系,将另文探讨,此不赘。
⑧ 《旧唐书》卷176,第4568页。“教坊副使云朝霞善吹笛,新声变律,深惬上旨。”
⑨ [唐]崔令钦《教坊记》,《中国古代戏曲论著集成》,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3页。“诸家散乐,……以每日长在至尊左右为‘长入”。下文因构陷太子事件,被唐文宗所杀的筚篥名手刘楚材,就是教坊长入供奉乐官。
⑩ 《新唐书》卷48,第1244页。“开元二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
{11} 《旧唐书》卷17上,第531页。唐文宗太和三年,“敕兵戈未息,教坊每日祗候乐人宜权停”。
{12} [唐]王建《王司马集》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全文电子检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13}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96页。
{14} 赵晨昕《唐代宦官权力的制度解析——以宦官墓志及敦煌本〈记室备要〉为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49页。
{15} 《旧唐书》卷42,第1792页。
{16} 《隋书》卷36,第1106—1107页。
{17} 《唐六典》卷12。
{18} 《旧唐书》卷43,第1839页。
{19} 项阳《俗乐的双重定位:与礼乐对应/与雅乐对应》,《音乐研究》2013年第4期。
{20} 《旧唐书》百官志卷43,第1854页。内教坊“武德已来,置于禁中,以按习雅乐,以中官人充使”。
{21} [唐]萧嵩等《大唐开元礼》卷48,文渊阁四库全书全文电子检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皇后亲享先蚕之礼“太乐令设宫悬之乐……诸女工人各位于悬后”。
{22} 《旧唐书》卷28,第1051—1052页。
{23} 《旧唐书》卷14,第410页。
{24} 《旧唐书》卷64,第2425—2426页。
{25} 《唐大诏令集》卷81,第621—622页。
{26} 《王司马集》卷5,第611页。
{27} [唐]张籍《张司业集》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28} 项阳《轮值轮训制——中国传统音乐主脉传承之所在》,《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2期。
{29}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3,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41页。
{30}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10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96页。
{31} 《旧唐书》卷70,第2528—2529页。
{32} 《新唐书》卷82,第3634页。“即取坊工刘楚才等数人付京兆榜杀之,及禁中女倡十人毙永巷”
{33} 《资治通鉴》卷246,第7941页。
{34} 如中晚唐“内人”女乐的选拔标准降低,这些地方官府进献的女乐入宫后未必都是“宫人”,也可能是“内人”。《新唐书》卷119,第4300页。
{35} 《旧唐书》,卷19,第679页。宫人女乐群体多为贱隶,也或有自幼选入内廷之良家子。
{36} [唐]苏鹗《杜阳杂编》卷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13—614页。
[本文为国家社科艺术学青年课题《宋以来中国封建王朝中央用乐管理机构研究》(课题立项号13CB101)的阶段研究成果]
张咏春 中国海洋大学艺术系副教授
郭 威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英涛)
——评陈辉《浙东锣鼓:礼俗仪式的音声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