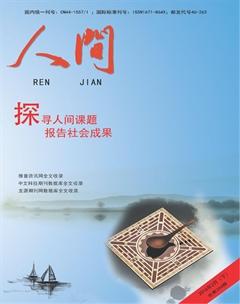零落成泥碾作尘
摘要:《戒指花》是格非二零零三年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格非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家,但是以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创作发表的《欲望的旗帜》为临界点,格非小说由先锋叙事特征开始转向关注现实生活。《戒指花》便是这样一部小说,它的主题便是发现被社会大众所忽略的现实存在的生活。这篇小说短短几千字,却讲述了个人初心的“玫瑰花”在强大的社会混沌中“零落成泥碾作尘”的故事:丁小曼所行走的世界是七窍不分、混沌不明的,她间或从现实中发现自己偏离了初心,她往往同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按照自己的初心行走,事实上,混沌世界的强大让这颗本来盲目、随波逐流的心根本上失去了选择的余地。这个故事是令人深感无奈的,令人一方面怒其不争而在另一方面又是绝望无怒的。《戒指花》文本当中引用了博尔赫斯的诗歌《雨》——作为小说主人的主人公的丁小曼大学学习的是西班牙语专业,熟悉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从这种安排上,读者不难看出作家格非对博尔赫斯、对诗歌《雨》的喜读,以至于用这首诗歌来联袂这部小说,可以说,诗歌《雨》连同小说中连绵不绝的雨一起奠基了故事的整体格调。
关键词:《戒指花》;失落;初心
中图分类号:J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18-02
一、初心吹落成尘
博尔赫斯的《雨》的第二节写到:“谁听见雨落下/谁就回想起 /那个时候/幸福的命运向他呈现了/ 一朵叫玫瑰的花/ 和它奇妙的/鲜红的色彩。”这里,诗人的诗绪由窗外的毛玻璃上的雨飘进了过往的永不复会的雨景中去,想起了曾经命运向自己展示的玫瑰花,这玫瑰花寓意一颗初心,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下对未来懵懂的期冀。这样的一颗初心有着玫瑰花般的“奇妙的/鲜红的色彩”,有着玫瑰花般的清香,如今这清香和色彩依附在连绵过大河两岸、连绵过古往今来的长长的雨线上进入了沉浸回忆的诗人眼睛和鼻子,进入了诗人内心的最柔软的部分。
对于丁小曼也一样,下雨无疑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不错,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前此刻,与都在下,而且现在的雨令人回忆起过往的雨,然而过去的雨中的景物早已经不复当年了——那废旧的庭院不复存在,那枯木葡萄架上的黑葡萄不复存在,甚至父亲已经不再活着了。对于丁小曼来说,“她的玫瑰凋萎了,正在腐烂。她甚至觉得自己的脑子也正在一点点地烂掉。”过去的雨过去的那一刻,丁小曼的玫瑰花——丁小曼的初心——已经零落成泥。而吹凋丁小曼玫瑰花的有两股劲风。
第一股风,起自丁小曼自身的性格弱点,即丁小曼面对来自家庭、社会的压力时并不能坚持己见,无论自己是对还是错;当家庭意见与个人意愿相顶触时,丁小曼会放弃自己的意愿,当判断社会是错时,她还是会选择顺从。而更多时候,仿佛存在的便一定是合理的,丁小曼并没有意识去作是非判断,而是随波逐流。在这些放任自流的过程中,初心被遗忘在储物间的底角,被厚厚的灰尘覆盖。小说写到丁小曼独自在玉米地转悠的时候回想起自己没有实现的抱负,她的母亲想让她学植物学,而爸爸想让他学习垃圾处理,为了同时讨好他们两个人,她两个专业都报,最后却被录取在西班牙语专业。可见,丁小曼并非真的有自己的抱负,所谓抱负不过是来自父母的期望,丁小曼没有自己的选择,她的专业是父母、成绩和学校帮她选定的。小说还通过细节交代了丁小曼和上司邱怀德之间的关系,这些细节主要存在于双方短信来往之中,而邱怀德之所以迷恋上发短信,是因为这样显得时尚。邱怀德说:“当初我第一次请你吃饭时,你说不可能,可后来呢?”
后来的短信又有:“你还没有告诉我肚脐眼下那道疤是怎么回事。”再看丁小曼的回信:“虽然你是我的领导,但我不得不说你这个人真是有点无聊。”这些暧昧的短信表现着两人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之所以会出现大抵是因为丁小曼架不住邱怀德的软磨硬泡。
第二股风,起自社会,丁小曼自身的弱点重要体现为随波逐流,这种性格如同一张白纸,社会是画家,婚外情正是庸俗世风在丁小曼身上的兴之所至的“才情”体现。小说《戒指花》当中的社会是乱象丛生的:人性冷淡、金钱主义、谣言四起以及色情暴力的低级趣味都充斥其中。小说是以采访一则引爆网络的假新闻为线索的,中间穿插着的是真实的小男孩家的苦难。小说当中出现的人物无不是带着人性的负面因素出场,如果说邱怀德体现了婚外恋和假新闻,那么丁小曼一开始采访的民警便是玩忽职守的形象;那个只有付钱才肯带路的老人体现的是金钱主义和教师师性的堕落;那关门撞破了小男孩鼻子的邻居阿姨便是对“远亲不如近邻”的结构;众多网友对性的热议和对受害者的忽视既体现了人性冷淡,又体现了网络趣味的庸俗。晓得在丁小曼这张纸上挥毫泼墨的是这样一位画家,便不难理解丁小曼的初心为何会落实不到纸上,为何会凋零在泥路上被来往的车轮碾作尘土了。
二、重新发现初心
新闻的采访过程是丁小曼重新发现初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重要人物便是小男孩。这是一个苦命的小男孩:他贫穷,“背着一个洗得发黄的小书包”;他瘦小,“哪怕是让目光轻轻一碰,也能触摸到他突出的肩胛骨。”他天真,拿着四十多块的零钱向丁小曼炫耀“我有很多钱。”他童稚,说死去的妈妈生活在抽屉里,说上吊的爸爸飞在半空中不掉下来。他无忧无虑地唱着一首悲伤的歌,他被邻居撞破鼻子很快便不以为然。他的苦难被“96岁的耄耋老者奸杀18岁花季少女”、被“巩俐自杀”的假新闻和噱头所遮盖不被世人所关注;他的苦难也被他自己的天真、他的童稚、他的童年的眼光所掩盖,不被他自己所见。但正是这样一个小男孩充当了一个心灵清洁工,不仅揭下储物间的封条,还清扫了丁小曼心上厚厚的蒙尘,使她重新发现初心。
震惊丁小曼的不仅是小男孩的苦命身世,更在于解开小男孩身世之谜的过程。小说当中的小男孩可以算得上天然的文学家。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雅各布森认为文学性是指“使某一作品(文本)变成文学作品(文本)的性质。”对此,俄国形式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看法是:“文学性是指对词语进行安排和加工的技巧,是将事物‘奇异化、将形式艰深化的艺术手法等等。”格非在塑造小男孩形象的时候显然实践了这一理论。于是“文学性”不仅仅是小说的特点,更成为小说当中小男孩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本领,读者从中感受到文学力量,小说当中主人公丁小曼同样从中感受到震撼的力量。如果小男孩身上不存在这种力量,不仅他的悲惨就真的成了如邱怀德所说的“每天都在发生”的故事,小说也会因此而黯然失色。
丁小曼发现了并关注缺少注意、没人关注的小男孩的悲惨童年,她觉得身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有义务、有责任去报道这件事情已引起关注。这个时候,邱怀德却提出不同的看法,这不同的看法也是来自新闻界的现状:跟着观众的欲望走,观众喜欢读奇闻异事、明星八卦、色情暴力,就不该去报道令人生厌的悲惨的故事。这种情况下,丁小曼开始忧虑,开始感受到新闻的病症,感受到良知的挫折——假新闻怎么能比小男孩口中这首催人泪下的裹挟生死内容的歌曲更具有报道的价值呢?生命的初始之心在这种碰撞中重新被发现。
三、无从回归的绝望
博尔赫斯的《雨》有着强烈烈的情感表达,表达的是对父亲的思念。这个感情的表达是强烈的,诗人强烈的表达着渴望,渴望回到那永不复回的过去的时刻,渴望见到那株曾经挂满黑葡萄的葡萄架,渴望听见天黑时父亲回到家里说话的声音。但诗人是理性的、节制的,尽管渴望,尽管幻想,但诗人在幻想之前便说明这一切只是曾经发生在那个不复存在的庭院里。过往无从回归,这里面包含着无尽的失落,无尽的绝望。
格非的《戒指花》同样表达着无从回归的初心。小说中的丁小曼发现了初心,但无从回归。她还是要听从邱怀德的意思,去北京报道“出了事情的刘晓庆”,而放下眼前的小男孩。
这大概是格非选择用小男孩唱的那首悲伤的歌曲作为小说结尾的原因。格非在这里表达的是绝望而非给人以希望,毕竟吹落丁小曼初心的是社会的病症,社会没有改良的时候,任何个人的初心回归都是空谈。而小说当中的这首名为《戒指花》的歌曲是疾病中奄奄一息的母亲绝望的唱给终将失去父母的可怜的儿子的,歌词写得是眼泪,唱的也是眼泪,包含着无尽的悲痛,无限的牵挂和无边无际的绝望。
作者简介:周越强(1992-),男,汉,河北邢台人,硕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