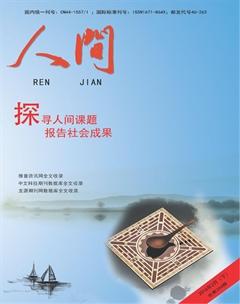浅谈地图作为史料在思想文化研究中的价值
摘要:地图,作为一种无言的历史,在中国古代社会出现的世界地图主要有三种。佛教地图和传教士绘制的地图是伴随着外来文明的进入中原地区,与中国本土所绘制的地图产生了强烈反差,是对暗藏在中国本土地图背后的“天圆地方”和“内诸夏而外四夷”的自我中心意识的有力冲击。
关键词:华夷图;南赡部洲图;山海舆地全图;天圆地;方内诸夏外四夷;自我中心意识
中图分类号:K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52-01
古语有云:“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宋朝郑樵曾说“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①。此时的“图”,是指一些在史书中出现的插图,自然也囊括了地图。在史料中,以图示意,更容易表现一些文字语言无法描绘的内容,在图像中寻觅理的内涵。而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更是历史悠久。绵延的绘图史,能够使后人直观地了解空间因素和图中展现的社会因素的变化,从而认识和理解历史。地图,作为一种史料,在历史地理领域中学术价值极高。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作用。通过针对同一区域,不同绘图者在其主体思想的影响下绘制出的地图可能截然不同。地图,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研究当时绘图者乃至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的切入口。就以中国古代出现的天下图为例,主要出现了三种风格迥异的地图,分别是中国本土人绘制、西方传教士绘制的地图和佛教地图,其中暗含的思想观念更是显而易见。
以地图为史料,研究思想文化领域的相关问题在近些年来逐渐为学术界所重视。这一新趋势的形成与福柯所著的《权力的地理学》有着紧密联系。众所周知,福柯十分推崇“话语与权力理论”,即“一切话语背后都有权力,而话语本身也会成为权力”,通过对地理学领域的空间位置、领土等背后的权力进行具体分析,将纯碎地理延伸至政治领域。地图,是以人为主体描绘成的客观“有限真实”,之所以为“有限真实”即是以“自我”中心的主观视图,也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客观视图。这种视图,因为被描绘者观看、回忆、描述之后,夹着个人的感觉和观念等主观因素影响下绘制而成。
在古代中国描绘世界的地图中,就带有较为独特的天下观。在古代中国素有“天圆地方”的特殊空间感觉,这种观念使中国人自认为一直处于世界的中心,周围的都是蛮荒之地,正如五服制一般由王畿向外围层层延伸,文明程度随着距中心的距离的拉长而逐渐降低。古代的《华夷图》、《职贡图》等图中在中原王朝的周边出现许多面积很小国家。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欧亚大陆交往便一直绵延,唐朝尤为繁盛,到了元朝更是形成了横跨亚欧的大帝国。照理而言,当时人应该对中原王朝以外的地区了解应该相对深刻。但是,在宋人所绘的《华夷图》中,对于周边国家的描绘并未有所改变。这种传统能沿用至明朝为止,足见其“中心大而边缘小”的观念作祟。这种主观的地域想象源于其中国传统“内诸夏而外诸夷”的涉外理念。明朝的海防地图更是印证了这一点。海防是明朝保证国家边境安稳的重要政策,许多海防地图在这个时期出现,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胡宗宪《筹国图编》和万历十五年化龙序刻《全海图注》等。多数海防图一改传统地图北上南上的传统绘法,但是依旧保持古今绘画的方法,即一般“远景为上,近景为下,外境为上,内镜为下”②。中国大陆被放置于全图的下方,而把大海和可能入侵的地区放置于上方,中国大陆海岸沿线标注军事设施。这种鲜明的双方对峙情形,清晰地将“内外”、“上下”与“中国四裔”区分开来。这种绘制方法,明确划分了“自我”与“他者”的问题。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在世界地图的绘制中表现的淋漓尽致。这种自我中心的观念面对佛教传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佛教关于世界有着独特的思想观念。据佛教《阿含经》记载,世界共由以须弥山为中心分布的四个洲组合而成,中国只是南赡部洲的一部分。根据地图《南赡部洲图》可知,中国在其的东部一角。究其源头,佛教是由印度经过中亚或南亚传入中原地区,在其思想观念中印度自然便是世界中心。这与中国传统天下观相冲突。为使佛教迅速在中国传播,天下之中在印度的说法逐步淡化,多元文明中心的说法开始兴起。所以《佛祖统纪》中的十二幅附图中,佛教徒志磐所绘制的《东震旦地理图》、《汉西域诸国图》、《西土五印之图》等三幅图,就构造了由三个中心组合的世界。三幅地图存在的三个文明中心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内诸夏外四夷”的观念。
到了十五六世纪,伴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带来了各种西洋的知识,其中包括欧洲的世界地图。在古代欧洲出版的各种地图上,尤其是世界地图,都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即在周围常常点缀图像,就是在地图空白标志各种见闻和奇物。如托勒密《宇宙志》1482年版和《地理学》1511年版中所附录的地图,其边缘地区就有代表十二月不同风力的鼓着嘴吹风的头像。利玛窦《山海舆地全图》便保持了这一传统,在南极空白处补充了许多动物。不仅如此,利玛窦在对《坤舆万国全图》进行解释的时候,对地球进行了专门的叙述,“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浑沦一球,原无上下,盖在天之内,何瞻非天?总六合内,凡足所伫即为下,凡首所向即为上,其专以身之所居分上下者,未然也”。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描绘了当时利玛窦将地球说传入中国后的社会反映,“利玛窦神父是用对中国人来说新奇的欧洲科学知识震惊了整个中国哲学界的,以充分的和逻辑的推理证明了它的新颖的真理经过那么多世纪之后,他们才从他那里第一次知道大地是圆的”。
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文字的记载是当前研究主要依据。而地图,作为一种对历史的叙述,逐步进入思想研究者的视野。文字可以直观表达,而以人为主导绘制而成的地图虽然表现的是“客观真实”,但是其实际是一种主观观念的表达。作为绘图者会在主观情绪的影响下,对地图中的要素进行选择性的取舍,比如在方位、比例、位置和色彩等方面的选择。这种取舍或选择,便是研究者在思想文化领域研究值得关注的其中一点,也极富有学术价值。
注释:
① 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岳麓书社,2013年,,第79页。
②(明)郑若曾著《郑开阳杂著》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8页。
作者简介:朱倩(1991-),女,汉族,山东省济宁市人,硕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专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