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季奇:“棋子”的悲剧
湘溪
3月24日,在科索沃战争爆发17周年的日子,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刑庭)做出判决,认定波黑塞族前领导人卡拉季奇的“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战争罪”等十项罪名成立,判处其40年监禁。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又一次将20多年前的波黑战争的是是非非摆到了世人面前。
对于一头白发、70岁的卡拉季奇来说,悲剧起源于波黑战争——从1992年到1995年,波黑在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的过程中,塞族、克族和穆族三方矛盾激化,在外部势力的支持、干预下大打出手,造成了二战后欧洲规模最大、最为残酷的种族战争。有资料显示,共有27.8万人死于这场战争,200多万人沦为难民,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卡拉季奇正是当时波黑塞族共和国的总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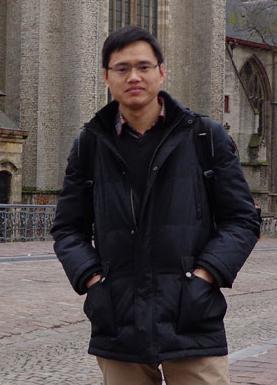
谁来为这些丧生于战祸中的冤魂负责?1993年,在美国主导下,联合国设立了前南刑庭,追究战争责任,卡拉季奇、前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米洛舍维奇等人毫无悬念地成为被追捕的对象。卡拉季奇被控的主要罪行之一就是要为1995年7月发生的斯雷布雷尼察事件负责,事件中波黑塞族军队被指控对斯雷布雷尼察的7000至8000名穆族男子进行了大屠杀。在审理过程中,卡拉季奇表示对该事件“不知情”,没有下达过屠杀命令,但对军方犯下的罪行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卡拉季奇的悲剧在于,他只是南斯拉夫分裂这个“棋局”中的一颗“棋子”。波黑战争打得如此惨烈,与南斯拉夫历史上不同时期各民族之间聚积起来的仇恨积怨有极大关系,其间既有相对强大的塞尔维亚族对其他民族的“压迫”、“强行同化”,也有克罗地亚族在纳粹德国占领时“为虎作伥”、对塞族及其他民族的”种族屠杀”,谁是谁非可谓错综复杂。因此,在南斯拉夫解体、各民族相互争夺地盘与利益时,卡拉季奇与米洛舍维奇等”政治强人”就成为维护塞族利益的“英雄”。而卡拉季奇从1995年被前南刑庭指控追捕到2008年最终落网,其间藏身塞尔维亚长达13年。但从克族与穆族的角度看,卡拉季奇与米洛舍维奇则是不折不扣的“屠夫”。同时,由于塞尔维亚和波黑塞族与美欧关系搞得很僵,他们也自然被西方视为“眼中钉”。
在历史的宏观背景下,上世纪90年代从前南分裂出来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包括寻求独立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先后都成为外部强权介入巴尔干半岛局势的“棋子”,波黑战争的结局也基本上取决于外部因素的意志。当年与卡拉季奇、米洛舍维奇差不多的“政治强人”,如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黑山总理久卡诺维奇也都对当时的战争与杀戮负有重要责任。然而,图季曼和久卡诺维奇先后向西方“靠拢”,成功实现“转型”,因此非但没有被押上前南刑庭,反而分别成为克罗地亚和黑山的“国父”,而米洛舍维奇2006年3月病死在海牙监狱,卡拉季奇则面临牢狱之灾。这也正是大部分塞尔维亚媒体认为前南刑庭判决“不公”、追求的只是“选择性正义”的根本原因。就连海牙法庭的一位前检察官助理都承认:在图季曼等前南战争主要人物都去世后,对“战争罪”进行公正的审判“变得不可能”,而只审判塞族人会更加歪曲这段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临时性的前南刑庭,还是之后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强势美欧国家利益的烙印。德国“外交政策”网站称,国际刑事法院从成立之初就被担心成为西方大国“以人权名义对付弱小国家的武器”,甚至会沦为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如果彻底抛开“双重标准”,或许有很多政治人物会在海牙受审。2003年美英侵入伊拉克后,国际刑事法院曾收到240封信件,要求立案审查联军犯下的各种战争罪行,但国际刑事法院选择了沉默。
卡拉季奇始终逃脱不掉“棋子”的命运。如今,塞尔维亚于2015年底开始与欧盟就入盟问题启动谈判进程,而另一方面,当年美欧为削弱塞尔维亚而支持的波黑穆族,甚至接纳过来自阿富汗的“圣战”分子,波黑成为西巴尔干诸国(塞尔维亚、波黑、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黑山)中最后一个提交入盟申请(2016年2月15日)的国家,与此同时,穆斯林难民则已成为欧洲最头痛的问题。
显然,悲剧并不只是卡拉季奇个人的宿命,在世界格局的棋盘上,弱小国家始终只能是“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