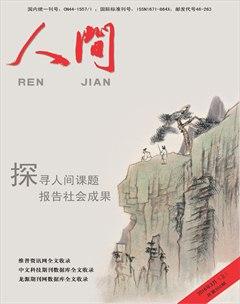人性的探索与反思
摘要:《审讯桌》是一部颇具后现代主义特色的作品。小说通过主人公“我”在接到翌日被审讯的通知后的漫漫长夜里,对以往无数次审讯的回忆,展现出一幅幅审讯制度下人的精神、心理异化,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画面。本文以异化主题为切入点,探究了马卡宁《审讯桌》中的人性异化现象。审讯桌将现实中的人们分成了审问者与被审者。审问带给人们长期的精神压抑与自由束缚,导致了心理与性格的扭曲与病态。审问者形象具有施虐破坏倾向,体现了人性的自私与贪婪;与其相对的被审者形象具有受虐迎合倾向,时刻感受到自我的卑微与弱小,屈从于强权;审讯桌不仅是集体强权的象征,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唯一纽带。
关键词:马卡宁;异化;审讯桌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00-03
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马卡宁是当代俄罗斯文坛最具实力和声望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活动始于60年代中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作为“40岁一代作家”的重要代表而令人瞩目。1993年,其后现代主义作品《铺着呢子、中央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又译《审讯桌》)摘取了俄罗斯布克文学奖的桂冠。马卡宁在小说中描绘出人的精神、心理的自我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异化的全景图。小说由主人公对以往无数次在不同委员会“谈话”的回忆构成。作品的主要艺术时间是主人公参加工作委员会例行审问的前一天夜里。借助反逻辑与怪诞手法,马卡宁揭示了在极权主义社会中人类生存的荒诞性困境。
一、《审讯桌》中异化的体现
在小说《审讯桌》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政权之间的关系都是靠这张铺着呢子、中间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来维系的。这张普通的桌子严格地划分了两种相互对立类型的人:一种是坐在桌子一侧没有名字、只有可以代表身份的审问者,另一种是坐在桌子另一侧的被审者。桌子是权威的,令人不可接近的,它掌控着每个人的思想与灵魂。不管是地下室,精神病院,法院,还是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均摆放着这样的审讯桌,它代表着集体的权威,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同时监视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一)审问者——施虐狂。
在这种压抑的社会氛围中人们无法追求积极自由,在这种残酷的现实生活中人们无法找到精神与情感的归宿。因此,人们寻找另一种极端的方式以重新获得内心的自由。小说中审问者具有施虐与破坏倾向,与之相对的被审者具有受虐和迎合倾向。
马卡宁笔下的审问者形象,几乎都无一例外带有异化特征。他们的情感与思想都背离正常人的伦理规范与道德追求。这些人格异化的畸形人物不仅无法掌控自我人生与幸福,还常常对他人的生活和命运施加影响,成为审问制度的傀儡。小说《审讯桌》中的审问者们是由坐在审讯桌一边的十至十二个人组成的。作者根据其外貌或性格特点分别为审问者们起了别号:“社会愤怒分子”、“爱提问题的家伙”、“当书记员的人”、“前党员”、“党员”、“美人儿”、“年轻的狼”、“老头”、“白头发戴眼镜的女人”等。 在审讯过程中,审问者们表现出虐待狂倾向,展现了人类丑恶的一面,贪婪与无穷尽的占有欲成为了他们的审问标签。在《审讯桌》中,审问者认为自己拥有绝对和无限的统治权,是集体意志的代表,他们强迫被审者依赖自己在审问过程中,他们总是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对待被审者。例如,“前党员”显得威风凛凛,充满着掌权者的幻觉;“社会愤怒分子”把被审者当做自己的仇敌,“恶棍”,“母狗”,“狗杂种”是其对被审者的蔑称;“年轻的狼”在审问时蛮横无理;“党员”出于一种先天的优越感,一如既往的把坐在桌子对面的被审者都看成小人物,感觉自己支配着被审者,不仅用威严地加重的语气质问与呵斥。有时甚至产生对被审者实施暴力行为的渴望。审问者的这种蔑视他人的心态与暴力的行为实际上是由于其内心深处对统治权的贪婪欲望。在审问者眼中,被审者不过是一个实现其统治愿望的工具和手段。
在弗洛姆看来,“施虐狂动力的本质,就是享受由完全主宰他人所带来的快感。”[1]审问者习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被审者的痛苦上,看到被审者遭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他们更是在一旁幸灾乐祸。在审讯中,审问者主动去羞辱及伤害被审者,一心一意想看被审者的狼狈相。小说中审问者的形象具有明显的有权力的极权主义性格,他们仰慕制度权威,愿屈从于这种权威的制度,同时也渴望自己能够成为权威,迫使被审者屈从于自己。在审问者们看来,世界是由有权者与无权者、高贵者和卑贱者这些对立的两极所构成的。在审问者心中,一直深藏着一种破坏性因子,时刻等待发泄。在大多数时候,审问者总是想方设法把这种无端发泄的破坏性装扮成是合理的,从而令整个审问者群体和被审者都相信这是合理的,并自认为个人的这种破坏性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通过研究审问者的这种破坏性心理,不难发现,这种表面合理、实质不合理的破坏性,选择谁作为破坏的对象、用什么借口作为破坏的理由对审问者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这种破坏性是埋藏在审问者内心的一种激情,并总能找到要加以破坏的对象——被审者。审问——这一恐怖手段作为一种恐惧,不仅见于受害者,也见于制造者本身。恐怖手段是人的生存的外化和客体化的产物,是社会制造的混乱,即人的堕落、人本性的异化和不自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审问者也是不自由的。
《审讯桌》小说中的被审者选择了“重占有”的生存方式,试图将被审者的身体和精神占为己有。一方面,审问者“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与其贪婪的本性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审问者的这种“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对被审者强烈的性欲。被审者成为满足审问者生理需要的工具,审问的继续将逐渐激越审问者的性欲,并把其推向人性病态的边缘。
(二)被审者——受虐狂。
在审问的长期压抑下,被审者日渐感觉到安全感的丧失与孤独感的吞没,怀疑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生命的意义,日益感到自己的无权力与不重要。他们选择屈服于审问的权威,放弃了个人的自由,在被审者可怜的表现背后,却潜藏着深深的孤独与不安,在他们可怜的面孔背后,其实也不乏一个可悲的灵魂。
被审者在审问中觉得自己是卑微和弱小的。面对审问者的质问,被审者只能表示悔过地耷拉下脑袋,无言以对。他们被迫回答审问者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了被审者的个人隐私。当被审者的回答得到的是审问者长久的沉默时,被审者会转而怀疑自己的想法与行为。这种对自我的怀疑表明被审者潜意识里已经把自己看作卑微的有过错的人,并且不容原谅。被审者时而也会产生示威的心态,这种无意识的示威行为暴露的不仅仅是被审者的反抗情绪,还有隐藏在其内心深处的无限的自卑。无休止的审问带给被审者一种深深的卑微感、屈辱感和无能为力感。尽管被审者内心一直抱怨这种挥之不去的卑微感甚至尝试着除去这种卑微感,但审讯却驱使他们认可自我的渺小与卑微。事实上,承认卑微,无能为力,承认罪行只是被审者无声的妥协,而他的精神世界却永远无法找回那份属于自我的平等,那份无罪的舒坦与释然。在小说中,这种微不足道的个人的缺点与错误却成为审问者评判个人道德与人品的重要依据,由此凸显了审问的无理与荒诞。然而,面对这样无理性的世界,被审者的任何反抗都是无意义的,审问已经将他们定性为有过错的人,而这种过错本身也决定了被审者在审问中低人一等的地位,从而被审者很容易被卑微和无能的感觉所吞噬。
可悲的是,小说中的人们身处在这样一个异化的时代:任何情况下都将有一张同样四周坐满人的桌子。审问者都将同样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进行挖掘,找到他们感兴趣的隐私,翻出来仔细探讨一番,即使这与审问的目的没有丝毫关系。审问的理由是五花八门的,就像审问者的问题一样,与真实审问的实质内容相比却显得可有可无。在这荒诞与异化的艺术世界里,被审者的结局是悲凉的,死亡成为了大多数被审者的宿命。审问这一日常生活中平常的事件带给人们精神的压抑和恐惧,异化着人们的心灵。被审者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在生活中找不到明确的方向,失去了自我,忍受着他人对自己一生无情的评判。
(三)桌子。
马卡宁将审讯桌放在小说总体架构的核心地位,并且围绕着“桌子”这一意象,展开主人公“我”对于桌子的种种情怀的描写。桌子是政权的象征。在小说中,它是所熟知的同志审判会举行的地方,它代表着一种政权的威严,政权通过它对人们的思想实行监控。在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审问在苏联人民的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带给他们挥之不去的阴影。与此同时,桌子的形象也深深映入同时代人的脑海中。在小说中,桌子、地下室、精神病院、电话审问桌这些形象被紧密联系起来,这些形象均与审问息息相关:它们是进行审问的工具或场所。桌子形象填满了主人公的意识并且不断变化着,它失去了桌子原本的物体轮廓,地下室、精神病院、电话审问桌是它自我更新的每一个阶段。从形式上看,如今的审问与地下室时代和白大褂时代的审问不同,似乎更具人道主义,因为被审者只是坐在桌子旁回答一些问题,但究其本质却是一样的:集体意识强加给个人,从而剥削个人的思想与精神自由。任何审问形式隐藏着权威的桎梏与压迫。个人命运如出一辙,很难获得真正的自由。审讯桌是这种“匿名的权威”具体形象的体现。这种匿名的权威无形中劝服个人摒弃自我,其中包括个人的尊严与自由。个人却无力抵抗,理由是令人无法抗拒的,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为了集体与人民的利益。
在这场残酷的竞技中,掌权的审问者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无力的被审者成为可怜的牺牲品,等待他的是个人精神的践踏与不容辩解的罪行。在审讯中,这两种身份是固定的,不可改变的。审问桌像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横跨在二者之间。而审问者群体是不可分的,正如审讯桌本身是不可分的那样。维系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精神与心理交往的纽带是审讯桌。每个人都和主人公一样,时不时等着传唤到审讯桌后面去谈话。包括每个审问者在内,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类似的审问。可以说,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总是处于审问被审问的无序的更替状态。可以说,审问桌成为联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唯一纽带,这是产生社会悲剧的原因。这条纽带起到的作用是极其消极的,它将人与人的关系推向了深渊,冷漠与自私成了同代人的通病。人们无法通过审讯桌打开自己的心扉,走向他人,走向外在世界,只能固守自己的内心,终生与孤独相伴。
二、主人公的异化与救赎
“俄罗斯文学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作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痛苦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3]作为一个成长于苏联灰色、沉闷的“停滞”时期的作家,马卡宁深深体验了同时代人所感受到的失望与消沉,更加强烈地渴望个性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在《审讯桌》中他全方位地描写了审问压迫下人的异化现象,但是单纯的揭露并不是作家的最终目的,作品中充斥着作者本人对拯救人类精神异化的探索与初步尝试。主人公“我”是生活在审问下失去自由的人们的缩影,焦虑、恐惧、孤独是普遍的社会情绪。为了找回自我,主人公主动与外在世界建立联系,对曾经压迫、侮辱自己的审问者,选择了爱与原谅,但这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精神的解脱。马卡宁借助主人公死亡这一悲剧性结局道明了自己的存在主义见解:在集体强权和极权主义的社会,人无法在现实中找到心灵的自由,死亡成为了精神解脱的唯一途径,对于主人公来说,他的心灵救赎相对于死气沉沉的审问而言,就是坚持自我的思想和对自我个性的维持,是一种间接与现实世界对抗的姿态。审问占据了主人公悲剧的一生,不断侵蚀着主人公的精神与心灵。马卡宁通过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展现了个体丧失自我的一系列心理感受:焦虑、恐惧与孤独。这从另一侧面揭示了审问的残酷性与人存在的荒诞。“马卡宁的主人公总是远离人群,社会政治现状并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他所关心的是人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生命的形而上学”。[2]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在时代的背影中显得渺小甚至不乏无奈和迷茫,但他所具备的人性之善、在黑暗中为寻求自我付出的努力、他的相对独立自由的精神存在,正是他鲜明的个性和生命价值所在,也是他能够走向自我救赎的根基所在。心理与精神的焦虑、恐惧和孤独证明主人公尚未完全失去自我,他在这个荒诞的社会中仍然以个人微小的力量反抗着审问。
(一)主人公的恐惧与孤独。
审讯使主人公的生活充满了焦虑和绝望,这是一个共同的恐惧,它也是同时代人对自身存在的虚无的恐惧。主人公恐惧的不仅仅是审问者,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社会审查和审问制度,也是社会的整个压抑的氛围。主人公毫无预料地被抛到这个陌生、混乱的世界,以个人的生命反抗着审讯的枷锁,从而证明作为一个人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审问制度剥夺了人精神上的自由,让人无时无刻处于自我反思、忏悔的状态。生命的苦难不可抗拒,恐惧永不会消失,人生处于永不停止的挣扎之中。
马卡宁在关注审问对人性造成的创伤和扭曲之外,还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疏离与个体的孤独。小说中的审讯桌就像一堵隐形的墙,隔在了人与人之间。在审问桌前,人们扮演着两个相对的社会角色——审问者与被审者,这两种身份的定位已经决定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地位,因此,正常的情感交流更无从谈起。掌权的审问者总是透漏着自己的淫威:虚伪做作、冷漠自私,有意或无意之间将被审者与“集体”隔离。被审者感受到的只是审问带来的人格侮辱。审问使人们丢弃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平等、关爱、友善、诚恳与信任,而变得自私、冷漠和充满敌意,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并且随着审问次数的增多而越来越深。
人在社会中受到挫折,失去归属感时,总会回归家庭,向家人诉说心中的话语,从而得到精神的慰藉与心灵的支持。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家庭是人际关系的重要载体,是人心灵的港湾,而小说中主人公的家庭却无法成为其精神与心灵的栖息地。家庭成员之间的疏远和隔离,加剧了主人公的孤独处境。审问是强制性的,家人无能为力,只能被迫接受这一现实。作为旁观者,即使他们体会到主人公内心的激动不安,但自己力所能及的仅仅是简单的言语劝慰,给予生活层面的关心与支持,所有这些却不能带给予主人公精神层面的慰藉。然而主人公对家人封锁了通向自己心灵的大门,成为封闭在自我的精神堡垒中的孤独者。
马卡宁敏锐地感受到同时代人面临精神异化的威胁。生活在充满审问的病态、畸形的社会环境下,人与人之间健康的、美好的感情会越出正常的范围,取而代之的是相互间的猜疑与冷漠,孤独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人的结局。作品中主人公的孤独感不仅是其个体的心理体验,这也是现代人普遍存在的一种消极的精神状态。尽管孤独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暗点,人们对孤独的感受普遍是痛苦的,马卡宁却将这一幅冷漠无情、人与人无法沟通的孤独图景细致地体现在作品中,引起人们对孤独这一生存状态的深思。
(二)死亡与解脱。
小说结尾,在走向死亡的瞬间主人公获得了精神斗争的胜利。主人公的死亡具有以下两重意义:首先,主人公的死亡是对审讯制度的无声反抗。审讯制度不仅影响着个人,同时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审讯压抑个体的精神,使每个人内心充满负罪感,终日处于激动不安的状态;而整个社会表面上充满秩序,实际上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主人公寻找解救自我的途径,努力追求个体的人格独立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寻找做人的尊严,但他发现,在这个荒谬的社会体制下,与他人接触的热情换来的是他人对自己的猜忌。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交流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任何途径能帮助人们走出孤独与恐惧。只有死亡,这一终极存在方式才可能将人的自我从沉沦中警醒。死亡不仅是主人公此世生命的无意义,生命的腐朽,而且还是来自深处的标志,它表明存在着生命的最高意义。主人公的微笑是作者对审讯制度的嘲讽,审讯对人精神的压抑在死亡临界点达到了极致。主人公用自己的生命进行反抗,这也是小说的悲剧性所在。其次,死亡是主人公心灵的救赎与解脱。主人公总是处在一种被质问、被审判的位置,精神自由是遥不可及的。在审讯制度下,自由和束缚之间不可避免地交替循环,而个人的独立和自由意味着孤独与恐惧。一方面,对精神自由的不断追求使个体化日益发展,自我意识不断增长,即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另一方面,追求自由的过程却使人的内心世界逐渐封闭,精神上陷入孤独与恐惧的困境,变得越来越孤独。在死亡的瞬间,主人公意识到,只有死亡,才能展示个体生命的深度,显现终点,只有终点才能赋予生命以意义。只有死亡,个人才能永远逃脱思想的束缚,精神才能获得永恒的安静与自由。
小说的这个令读者感到压抑的结尾所体现的并非是对异化的社会的彻底绝望,相反,马卡宁正是以此提倡人们与异化的社会进行坚决、甚至永无止境的抗争,他希望人即使面对黑暗荒谬的社会处境,也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永无止境的抗争中找寻光明的所在,追寻心灵的自由。
参考文献:
[1]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陈学明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59.
[2]汪剑钊.别尔嘉也夫集[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6.
[3]Роднянская И.. Сюжеты тревоги Маканин под знаком “новой жестокости”[J].Новый мир.1997.(4).212.
作者简介:史倩芸 (1991.02-),女,汉,甘肃,在读研究生,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