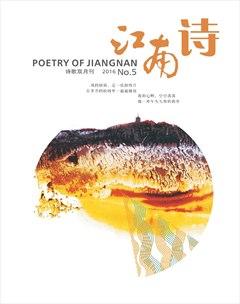飞行纪事:伤疤
在右侧机翼的下方
是连绵不断的群山
间或有几座兀立的山头
四周被雾蒙蒙的
城市或乡村包围
那些街道、房屋和农田
通往山巅的小路依稀可辨
如同体内的经络
或者发丝中的纹路
那些大块裸露的泥石
它们是大山的伤疤
需要多年时光才能痊愈
但已留下永恒的记忆
如同我们生命中的某些时刻
那些难忘、痛楚的时刻
虽然时光流逝
不会再被别人瞧见
它们仍然会隐隐作痛
作者简介:蔡天新,诗人、随笔和游记作家,浙江大学数学学院教授。近作有《美好的午餐》,随笔集《数学传奇》,游记《里约的诱惑——回忆拉丁美洲》,摄影集《从看见到发现》,主编《现代诗110首》、《冥想之诗》、《漫游之诗》。
乐意你们每日走过我的身边
裤角轻擦草叶的窸窣声,如我
从未息止的忆想:屈辱的片断,过失或者原罪
只是别把碑石上的名字念出声
生来如影随形,不离不弃
夭亡,亦不能脱却它在尘世的烦扰——
这远远晚死于性命的羞愧
睡 姿
靠紧西墙的一张宽敞的大床上
每天夜里我一人独睡
或仰躺成舒展的太字
或右侧卧左侧卧,辗转反侧
我晨勃的兄弟有了三个明确的指向:
仰卧时朝向上帝
右侧卧朝向虚空
左侧卧,则朝向隔壁的寡妇
深呼吸
我必得如此深深地呼吸
吸入吸附在白雪上的冷光
这些被时间污染的颗粒
吸入自闭,吸入蝙蝠的黑
吸入一匹赴约的病马
和一具月亮残缺的肉身
这口气憋得足够长
现在我要依次呼出寒气
呼出无知的肺炎
呼出一盏薄雾中辨识路径的灯火
——呼出转场的草原,那儿牛羊走远
剩下一地西风的碎片
拉 链
我太久的沉入了时间的黑地
像蚯蚓僵死于过冬的泥土之暗
我一个人的孤独亦是岁月的孤独
没有指南针,我只朝着认定的方向一意孤行
雪水渗入地表,惊蛰令环境松软
我依然前行在时间的深处
似有铧犁与换了铁掌的牛蹄穿过田垄的声音
犹如缝在皮肉上的拉链哧啦豁开
露出体内的秘密,和疼
一个人的孤独莫过于
从暗无天日到重见天日的孤独
稻草人
一个女人站在秋风下的黄昏自语:
你对我说,你喜欢我的眼睛
嘴唇,肚脐,和说不出口的隐秘
你说通往我体内的入口
都是灌送爱的通道
多畅快呀——
这些年来,你依次退出
我的身体闲置那儿,风吹雨淋
日渐褪色,枯败,散落
像个稻草人
警 句
生活在底下,对上边的事物
我说不出它们惯有的状态
比如吊灯日夜悬于头顶
但我说不出烧坏了几盏
剩下的能否点燃暗淡的时光
也曾有过晴明的日子
初阳起自朝露
轻风送它日上中天
即是西落,亦有彩霞贴金
余晖映照蝙蝠多褶的翅羽
这么多年,我已记不清黑色的反光
往事如此安静
让我拥有别样的活法
在一天的尽头停下脚步
此地甚好。我忍不住自言自语
突然冒出一个警句
光 点
一只乌鸦穿过早到的春天
叫声落在孤寂的夜里
这黑更甚于夜的光点急促地闪动
吉祥的小鸟
寒冬的信使
有着火炭一样的能量
弹出的弧线是冬天最后用力拉紧的弯弓
自身反坐回凋敝的境地
确信一粒冰渣滴向解冻的尘埃——
那被草叶擦亮的翅膀
露水里升起的旭日
这些人
坐在登机门左侧连排椅上
我目睹瘦长的人群
人手各执一张纸牌,缓缓通过检票口
鱼贯而入一只大鹰的胃里
这些人——
天南地北,男女老少,平头百姓,大咖阔佬
……我最后一个起身过卡
追到天上,与他们一起验证命运
星 辰
我从昏暗的窗口探出头来
天边星辰孤单,叫我辨清风的走向
我摆摆左手,仿佛听见召唤
我用自己的方式作出回应——
朝下看和朝后看是一样的
投在空床上的影子一如大地的苍茫
柳 絮
柳絮飞扬,再多也不是雪
柳絮没有雪的那种干净的白
没有雪漫天寒凝的静气
柳絮在浮尘和花粉里飘游
这些春天脱下过冬棉衣抖落的皮屑
随之被春风掩埋
结 局
化成灰,你也能认出我是谁
化成灰,我也能认出你是谁
太平盛世,生当逢时
我有月亮对于秋天的敏感
我有死亡对于死亡的认知
作者简介:邵纯生,山东高密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多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刊》、《诗探索》、《诗歌月刊》、《诗选刊》和《山东文学》等报刊,多次入选年度诗歌选本,曾出版《纯生诗选》和《低缓的诉说》等诗集。
老屋在半山腰
平常,能听到窗外竹子的呼吸
但今晚,暴风雨在房前屋后冲撞
竹子抖得像打摆子的孩子
屋后的小溪,在暴雨中簇拥着冲出山谷
这一切都在几十年的时光中消失
而今晚,它们又随着一场暴风雨返回来
今晚有暴风雨,今晚我九岁
在挂钟巨大的滴答声里
我在安睡
外婆对着油灯,在补
一双磨破底的旧袜子
旧 事
那时我还小
十三四岁的样子
我挑着两蓝子山芋
跟在三叔的后面
要在黎明前赶到集上去卖
走了五六里的山路之后
我们在舒庐干渠的大堤上歇脚
马槽山消融在沉沉的夜色中
初冬的田野多么干净
空气清冽,大地安宁,星空辽阔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的星星!)
身边的渠水闪着幽暗的冷光
霜“淅淅”地降落在枯草叶上
这是广袤天地间我能听到的唯一的声音
星空的种子
月光先是落在一片荞麦地的上方
然后缓慢地漫延开来
山谷变成了乳白色的河流
树在夜晚的阴影越发沉重
但它的声音——它的叶子在风中
哗哗的声音
是透明的
叔叔指着大王岭的山凹
对我说:你五爷爷三月里死了
就埋在那
我们抽着烟,好久没有说话
萤火虫像星空撒下的种子
在这乳白色的河流里游
一只夜鸟
突然"喳"地惊叫一声
扑楞楞从林间飞起
越过山脊,飞到对面的陆家洼
如果是在白天
我就能看到
它张开的一对黑色翅膀下
几根白色的羽毛
夏天中午的一阵微风
家乡人给我带来一袋老家的板栗
像一袋坚硬的褐色石头
栗树种在老屋对面的山坡
巨大的树冠在山顶上堆出另一座山
宽大的叶片
在夏天中午的一阵微风里
哗哗喧响
家乡人,我想问问你
我家老屋前的两棵枣树是否还在
它们还会在每年春天
开出淡黄的
小米粒一样密密的花朵吗
你见过我的爱人吗
她是不是赤脚走在山路上?
周围花草香气包裹着她
油松、山毛榉、桦树耸入云天
而她,赤脚走在山路上?
果马河
果马河在小岭湾冲出
一片宽阔的河滩,和
一个叫蛇信子的水潭
水芹、杂草、河滩上高大的胖柳林
一群蜻蜓,在七月
震耳欲聋的阳光下
飞进果马山谷
我熟悉河滩上的一棵树
它每年七月能洒下
和我命运一样大的一块荫凉
斑鸠在枝叶间,用低低的"咕咕"声
召唤伴侣,一阵风
像透明的血液
在林间流动
门
父亲葬在大王岭向阳的山凹里
爷爷奶奶也葬在那里
墓地隔着一条清澈的小溪
正对着山下的老屋
我觉得他们没有死
只是把住处
由山下搬到了山上
山里人都搬到山外去了
只有生了绝症的二叔
一个人住在老屋
像在守着墓地,守着自己最后的日子
等着有一天
也搬到山上去
二叔每天凌晨起床
在黑暗的厨房里,对着一尊佛像
喃喃祷告
我也起床了
我看见慢慢发白的窗户外
走过我昨夜的一个梦
梦走了,它的重量和气味
还留在我身体里
许多墓碑散落在大王岭上
把不同年代的时间
紧紧压在同一个平面上
这些墓碑像一扇扇紧闭的门
每年都有访客,但这些门
从没打开过
孤 独
雪下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天晴了,阳光和雪光
在山谷里混乱地闪烁
整个山谷在冰冷的光里燃烧
我走在果马河宽广的河滩上
河水在冰雪下无声地流淌
这山谷的寂静,刚撕开一个小小的缝隙
又迅速地合上
几只斑鸠在雪地上盘旋
它们的食物藏在冰雪下面
藏得比罪孽还深
我看着太阳在果马山谷一点点地升起
在空旷的河滩上,我的孤独是那么地虚无
作者简介:严寒,男。做过锅炉工、矿工、茶农、教师。早年游历北方各省,现定居江苏江阴。诗文散见《诗刊》、《扬子江诗刊》、《诗江南》、《西部》、《重庆文学》、《雨花》等各刊及各种选本。
一
我们先说一说段跟这首诗无关的话题
说一下摄影者们摆拍的场景
她沉醉自己的飞翔 在峡谷的上空
她在努力的模拟一朵花的姿态
打开自己 旋转 跳跃 收拢
她的双脚想挣脱大地
她变幻的气味难以捕捉 她舒展着
手臂 朝着不确定的方向
把自己一次次的送出
天空 流水 浮云以及过路的风
她把自己一一呈上
她把自已分裂成无数个碎片
送给了前世的荒原和未知的今生
这峡谷 一个伤口的隐喻
一朵罂粟在肆意的燃烧自己
她借助于阳光和空气
把随身携带的基因
慢慢的合成了体内那个致命的毒
阳光清澈 戈壁茫茫
这都是我的想像 当目光落下的时候
我却在追溯一段遥远的时光
二
我们端起了杯中的酒
无数次的表白 放纵自已
我们感动于酒的辽阔
我们也感动于酒的偏执 总是迷失于
自己制造的假相
我们总在脱口而出的时候欲言又止
其实我们知道
没有吐露的那一部分最接近真实
还是那个坐在对面的人
到如今我们还在用酒杯交换着彼此
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快感
其实就是坠落的一瞬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违背自己
当真相终于来临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自己苦心经营的
是多么虚弱的人生
我们明白冲动和善恶只在一念之间
人间和地狱也只有一步之遥
此时你看到了
这深不见底的峡谷
多么像一个人欲望的本身
三
我突然想转过身去 如果能看到
过去的时间
这里多么适合向你表白
此时可以上刀山下火海 直到
天崩地裂 海枯石烂
你不用怀疑自己的耳朵 在这里
你用眼睛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誓言
这段话多么的不合时宜啊
其实当我们抬起左脚的时候
右脚就已经后退
四
这尘世总是无穷无尽
我们总会无缘无故的发岀叹息
大地上静静的
你看到的漫山遍野 艾蒿萋萋
它们都会在瞬间陷入停顿
还有什么能够证明我们无数次
描述过的事物
还有多少陌生让我们难以确认
岂止是十年啊
当一切都无法证明的时候
我们只能再留下一段十年的空白
想像一下吧 还要动用多少剩余的人生
才能把这段空白填满
五
我又回到了前面那个无关的话题
关于峡谷
所有的经历都是致命的
我们拔岀双脚
梦魇却在一路相随
杏花在寒冷中张开了翅膀
汽车和拖拉机一路驶过
它们碾过碎石子,灰尘飘起又落下
这像是去年的春天 一个孩子
在路上 走着走着就没了踪影
黄昏里 河水东去
杏花在寒冷中张开了翅膀
它们飞离地面
像是谁提着的一盏灯 去了
另一个天涯
只剩下这棵老树了
它的动脉硬化 内分泌失调
身体里储存了更多的难言之隐
多少年了
冰冷的骨骼里仍然抽出了
细细的叶片
你说过,给盛开者以孤独
或是让孤独者盛开
你也说过,谁能给寂寞者
更高的天空
晚风又一次穿过喀拉达拉
穿过了村庄更深的寂寞
这纠结的命运啊 我们总也
望不到头
我前面的山
一
那些年 我看到的只是一个隆起的身躯
白色的雪峰 黑色的松林
触手可及的云朵 布谷鸟山南山北的飞
这是我在喀拉达拉看到的最远的地方
如果我离的再远一些
就能够真正看见一座山的样子
看清它储存的阳光 雪莲 冰川
一只鹰的背影 和岩石上的荒凉
看清它一望无际的麦地 收割后的葵花
炸开的苦豆子远走他乡
如果我能再安静一些
就能够展开对一座山的想像
想像它内心的千沟万壑 回肠百转
想像它的衰草迷茫 暮色中的羊群四散
如果我再用心一些 或许就能够理解它
隐藏的背面和另一个世界
理解它一条河流的冰冷和高处的绝望
最好是我再能有一点悲悯之心
能够唤醒它的记忆 唤醒那些
奔跑的风沙 大雪覆盖后一个村庄的
哀伤和惆怅
二
夕阳终于落下
群山筑起了黑色的城墙
我们一直在黑暗中虚构自己的命运
用自已的生活去模拟另一种生活
我们不知道自已的天涯就是另一个县
而另一个县的隔壁就是另一个国家...
我们从未登上过前面的山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天涯可以望断...
一枚月亮低低悬挂 我前面的山
这个夜晚 在一个人的中年停顿下来
我看到河坝里水落石岀
世界如此安静
除了河水你听不到一丝声响
多少年 我们把一座山当作刻度
用来衡量时间
当我们抬头仰望的时候
却好像从未认识过
作者简介:王兴程,笔名十里路,上世纪70年代岀生于江苏赣榆,长于新疆伊犁。有诗歌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北方文学》、《文学界》、《诗潮》等刊物。现供职于伊犁州直某机关,伊犁州作家协会理事。
追忆.N年前夜宿乌镇
室内的灯
幽暗着、一地的宁静
屋外的水流
轻叩着、沉默的窗沿
浪漫的夜
呼唤着我的脚步
夜色中的河水
压抑着千年的激情
流淌成无字的歌
古老的拱桥
守候着前世的相约
站立成无言的画
一轮满月
梦一般地、挂在头顶
月色,像情人的眼波
温柔似水
远处
一叶乌篷船
渐行渐近
有笑声、融在月色里
漾在水波中
小船,摇碎一池碧波
摇醒我的梦
却向梦境更深处、漫溯
……
时光的影子
我踩着时光的影子
徜徉在熟悉的校园里
迎面走来一个女孩
恍惚光阴回溯三十年
那个青涩的身影
从树荫下飘过
带来一阵诗意
如此陌生又如此熟悉
如此贴近又如此疏离
过去的日子如一条河流
潺潺流过我们的记忆
岁月踏着轻快的舞步
旋转在路旁、枝头
老树把岁月的沧桑雕刻成年轮
藏在树干深处
而风,正与树叶低语
四季流变总能带给它们
不同的惊喜
影子时长时短、时浓时淡
灯火阑珊处
有什么在我心头驻足
如爱因斯坦的手
弹拨起柴可夫斯基的曲
还有上个世纪的诗笺
从众人的寂寞中逸出
飘向一个人的繁华与盛宴…
乡 愁
乡愁是童年时住过的旧瓦房
是家乡黄昏的炊烟袅袅
是小路那头家人等待的目光
乡愁是爸爸菜园里的南瓜
在孩子期盼的眼中长大
乡愁是母亲亲手做的小吃
在游子的记忆里飘香...
乡愁是儿时梦想的蝴蝶
扑扇出理想花园的芬芳
乡愁是灵魂深处的渴望
在生命的长廊中永远回荡...
岁 月
我的往日,如风儿飘逝
寒冷的冬季
雪花定格在隽永的记忆里
窗外的树在雪的覆盖下
幻变成国画中的情韵
隔着一堵墙 还有一道岁月
我们欣赏着同一片风景
那条河 还是原来的模样吗?
杨柳低垂、湖水浅唱低吟
隔岸传来排舞声
打破了内心的沉寂
此刻 有阳光射进窗帘
如雪般的白得耀眼
我不知记忆是被雪埋了
还是被太阳晒化了
只知道心里流淌着融化的雪水
听着它忧伤而柔美的歌
仔细闻闻吧
还带着腊梅的幽香呢!
仿佛在诉说
我们曾有一个
多么美好的冬季…
古老巷陌
岁月的风,穿过时光长廊
飘散了、伊人倚楼怅望的目光
历史的雨,洒落在古老的石子巷
冲淡了、青春年少的步履徬徨
模糊而寂寥的身影
穿过悠长而静寂的小巷
消弥于、门外的一米阳光
只有往日的故事
依然在风中传唱
还有那不老的希冀
依然在梦的那头
守望
一树花开@早春二月
一树梅花
装扮着二月的早春
把岁月的墙角妆点成
诗画
庭院中
几枝腊梅随着冬季一起老去
却仍送出最后几缕
幽香
午后的斜阳守着门儿
翻晒着旧日时光
回望来时路
那年青的影子 依然在途中
盘桓
守望
作者简介:汇泓,本名罗卫红,女,浙江临海人。现任职于浙江省政府部门。
这些丰腴的滋养
现在在周遭飞翔
它通过门前的一架蔷薇
叶上的一只瓢虫
点燃了寂静
她深深地伏下头
一段脖颈因岁月更加清晰
倒映着时光
她鱼一样游动
扩展开雨后的清凉
她停下来
现在在树上
再次靠近——她一定认为
这是夏天给她的一个口信
光阴越来越旧
天空是在鸟声里一步步升高的
床前的窗台渐显出一幅
你说是美景也好
你说是群雀图也好
我捏捏鼻子
修整后的花草散发着
淡淡的欢快
人生是需要一段空白的
静谧倏忽而起
春枝在时光里曵动
仿佛是被静谧撞击了一下
寻找孤独
当别人在极力回避
我在拼命寻找,它藏在一只茶盏里
一朵小花里
一片竹片里
它的气息常常是这样的:
一个石臼是它的回音
一只酒瓮是它的脚印
它,迟迟疑疑
昂立,在空旷的午后
颤栗只是一瞬间
我端起一杯茶
分明看见有一条尾巴
在水中一闪,就不见了
邂逅清晨
当夜的衣被一件件剥去
窗台上的远方清新无比
连我也是澄澈的
光的衣有了金的形状
它们到处飘飞
一会在墙上,一会在树上
一会在江面上
一会跟一个少女走了
一会躲在一个鸟巢上
为什么不跟一段光线奔跑呢
它能穿过一座座峰峦
穿堂风
挂在童年的鼻尖上
一架伺机而动的丝瓜与蒲扇上
一把太师椅被摔了一只脚
能否看见
被小姨掠走的记忆比南瓜花大、南瓜花香
现在就坐在板凳上
我看见,童年捧着一把野草莓
在叽叽喳喳的燕巢下
在廊柱与廊柱之间
欢度日月
一张老竹椅,一盆指甲花
三只母鸡,一架石磨
在岁月里穿梭、静好
——苦难都藏在板壁的缝隙与开裂的
木椽……茶香中,不知它们能否
认出:斑鸠的喧闹里,山河依旧,草木青葱
一个杯子
很久以前
我就看见你在洗一个杯子
洗了又洗
一一透明、纯粹、光洁
你拿着
洗了又洗
很久以前
我就看见你在洗一个杯子
相碰时
发出一种叮叮当当的音响
纯金一样的音响
你拿着、握着
盛入夜色似的液体
在光亮里
有一种夜色的意义
你拿着个杯子,在手上
洗了又洗
渐渐地就把你的边沿
洗薄了
像你的年龄
作者简介:林新荣,浙江瑞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瑞安市作协主席。有作品发表于《北京文学》、《青年文学》、《星星》、《诗潮》、《诗歌月刊》等,曾主编出版《中国当代诗歌选本》、《中国当代诗歌赏析》、《震撼心灵的名家诗歌》、《快乐心灵的寓言故事》等。
比加索:立体的梦境
一些最闪光的,永恒的人和物
总是大隐隐于市井的某个角落
那是一个贵族建筑的扑朔迷离
迷宫,镜子,放飞鸽子的窗口
以自画像形式自画一个人成长
一张十多欧元门票可以无数的
旅客的通行证,却无法通行你
一生的艺术长廊,它悠长深邃
不是以你长寿,而以画笔丈量
你的天赋爆发父亲的才情花蕾
你不甘于跨栏短跑,而是独僻
一条无人问津的蹊径,以长跑
跑出了一个立体派的世界纪录
你跑进学院,跑过五只猫酒吧
巴黎的陆离怪诞涂抹众生之相
现在还在路上以毫秒的速度定位
又将高低远近各个视觉制造魔方
我惊讶于惊讶,三五岁的小眼神
抓住梦境,以比加索命名的梦境
让点集中成线索,体积面对体积
威尼斯:水的另一种形成
天空飘着细雨,落在中国
就酿造成了水酒的绍兴城
溺水三千,宠爱在意大利
一个神秘微笑的蒙娜丽莎
另一个是貂裘换酒的秋瑾
当我遇见那个在水一方的
女神似曾相识又不曾想起
“记忆是相会的一种形成
忘记是自由的一种形成”
泪水滑落,水位在上涨
威尼斯,水的另一种形成
沟通要有多少通灵的桥梁
在道与道,在窗与窗之间
贡多拉,我的城市的媒人
能歌善舞,放声我的太阳
建筑一个梦境给你,巴塞
当钟声回荡山谷,石头回答
在蒙特塞拉特家谱里,我们
每一个人,信仰自己的自然
当我们遇见中国老庄
天作被子,地可为床
在天地中间我们安祥
当我们遇见安东尼高迪
我们生活,我们的海拔
建筑在巴塞的梦想之上
我们以前无知现在也无知
一个人竞是无数人的圣经
一个人竞是无数人的赞美
我们五个兄弟,五块石头
五个指头,伸出你的图纸
指向天堂,也在指向窄门
我们没有假日我们在奔波
在手脚架上我们装饰风景
风景却永远装饰不了梦境
梵高,我的爱像你的生命一样
梵高,我的爱怎么像你的生命一样
短暂的,我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光
色彩灰暗,让忧郁贫穷和疾病缠身
你不是始终和着太阳的方向旋转么
你不是向日葵,把赞美当成秋天吗
梵高,我的爱怎么像你的生命一样
脆弱的,我们无法把握自己的时光
奶酪面包,妻子和几个苦命的孩子
一支画笔种出了荷兰,麦田,土豆
郁金香,风车,却种不出阳春白雪
梵高,我的爱怎么像你的生命一样
叛逆,被博物馆一次次复制衍生
你把一个黎明,摁进无数个黑夜
你把一个遗言,奔跑成无数个你
而最后的枪声,让右手永别左手
梵高,我的爱怎么像你的生命无言
而不如你油画一样高高地被敬仰
米罗:诗集的封面
星星,月亮或者太阳
都是很儿童的符号了
女人在下,飞鸟在上
飞翔过后,留下静谧
你不知道米罗是什么
我也只是他死后很久
的一个过客一个粉丝
他也不明白我们为何
选择他做诗集的封面
一滴红色滴进绿草中
黑色横行绿与黄之间
在黄色上,蓝拥抱黑
我很讨厌,两个圆点
把各自拉的那么遥远
在那黑色的银河两岸
想象一下,如果我是
蓝的,你宁愿做那只
黑天鹅吗?让那蓝天
画下你的飞翔的浪漫
无论改,不改变方向
星星月亮和太阳在上
鸟在女人和天空之间
米罗逍遥在现实之外
我们总逃逸不了画面
作者简介:陈墨,浙江青田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公开出版诗集、散文集、石雕理论研究专著10多本。现任青田县作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青田印学基地秘书长、浙江丽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