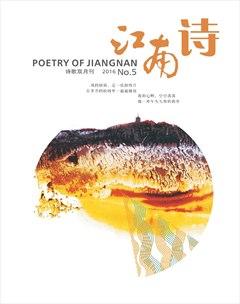更多的春天和秋天
主持人语:
这是郭晓亮构思独特的一个散文作品,现实、历史的回忆、想象以及大师们的文本穿插在对新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这片土地的叙述上,就像他在文章里提到布罗茨基曾说“文学就是一部字典,就是一本解释各种人类命运、各种体验之含意的手册。”那么这篇精心写就的散文也是理解这几十年来这里的人们命运、各种体验的一种尝试。(江离)
一
“哈扎尔之夜”,东方式的奇想和“梦的拼贴花”。世界的一只眼睛长在石榴树上。一个游魂被自己的影子迷惑,深深地走进那血肉的大地。捕梦者的一览无余,真的是说来话长。夜半,亚西亚的雨追着风,雷电放出百合花中的羊群,雷电有着像牧羊人一样的好年华,雷电无所不在,雷电使狂热的女子失身、胆小的男人出走。然后是一页书在南风吹进的三联灯台上翻开,阵阵迷香袭来,萨洛尼卡的康斯坦丁说出新的梦语。秋天,杜布罗城,降下玫瑰花雨,巴夏的果园里有哗哗的雨声,撒母尔.合罕发现自己站在另一个马刀和苹果的梦中。夜行的王宫与村落,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南辕北辙。这里除了梦,什么都不属于他,不属于他的还有这梦的无数世纪之后,密布城市的灯光。对着窗外荒凉的秋天,我的手心发烫,沙发上精装版的《哈扎尔词典》刚刚合上,但它幽冥般的巨影依旧笼罩着我。我的驱体内已经潜入另一个人的灵魂,非凡的米洛拉德.帕维奇的灵魂。
二
天空像城市上空睁开的一双大眼睛,远远地看着春天的这个早晨。一条大街向南敞开,车和行人稀少。被太阳光压得低低的那些平顶房子,灰暗,简陋,散乱,不规则地出现在老榆树的下方。从路中央开过去的公交车、卡车、拖拉机的后面,都拖着长长的黑烟。街两边的人行道空阔,一辆三轮车停在附近一家铺子的门外边,那里,有一支由市民排起的长长的队伍,市民们手上都分别拎着装有小空塑料瓶的那种木头盒子、和一张用白纸印的表格。两个身穿蓝色大褂的送奶工,手脚麻利地从三轮车上卸下四个装满鲜牛奶的大铁皮桶,然后开始给市民们打牛奶。他们给每个市民打完牛奶后,都要用圆珠笔在递过来的表格的空格里划一道斜杠,以表示该市民今天的牛奶已经打走。早晨的太阳光掠过屋顶和树丛,开始照射在街头,路面上飘过来浓浓的沥青味儿。队伍在缓缓向前移动,这队伍中也有我。这是1986年四月乌鲁木齐的一个早晨,我清早来到沙依巴克区经二路市牛奶公司供应点,在等待打取预先订购的自家牛奶。
三
哼哧哼哧地,用尽全身的力气,我终于把一个红色大木头箱子,从外公家西屋的床铺底下拽了出来,然后就势四扬八叉地躺倒在地上,大口喘着气。在那个时间,整个西屋里都是从我嘴中呼出去的口臭味儿。而就在这时候,门外面的大院子里,刚刚下了一只蛋的那只老母鸡,突然报功似地扯开嗓子“嘎嘎!”“嘎嘎!”叫起来,而且叫个不停。“该死的老母鸡,什么时候下蛋不行,偏偏在现在!”嘴中连珠炮似地唠叨着,我一股脑从地上跳起来跑到院子里,朝站在南屋鸡窝前面正不亦乐乎地叫着的老母鸡冲过去,把它赶跑了。稍稍安静了片刻,我环视了一遍外公家的前院、后院、还有院门外临街的动静,还好,没有任何人影。于是急忙返回到西屋,蹲在那个红木头箱子的前面,慢慢打开了它。这个下午,对我而言,是个极其难得的好时机,大哥、二哥、外婆和其他大人都出去了,家里只剩下我一人,于是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我眼前的这个木头箱子,是大哥去年高中毕业后,从察布查尔县上带回牛录外公家来的。自出现的那天起,一年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在关注它。我关注它的兴趣点不仅仅在于它里面装的东西,而且还在于伴随而来的大哥的一些异乎寻常的举动。其实,平日里大哥极少搬动或打开这个木头箱子,即是偶而打开也完全是避开家人的,更别说让我这个小淘气鬼去触碰它了。有几次我发现大哥打开它也都是一瞬间的事情,根本没有看见他在里面放下或取走什么东西。只有最近的一次是一个下午,我正在灶房里喝水,忽然看见大哥一闪身走进西屋,快速移动并打开了那个箱子,取了东西后便匆忙离开屋子。在他走出去的那一刻,我隐约瞧见他腋下夹着一本厚厚的书——正是一本书,激发出我愈加强烈的兴趣,并导致了今天铤而走险的这一幕。现在,我像个小窃贼一样轻轻打开了这个神秘的木头箱子,一个被大哥隐藏起来的世界终于刹时间展现在我面前——啊!满满一箱子的书,整齐码放在里边!有精装本的、简装本的,有封皮带人像的、不带人像的,(而且全部包着牛皮纸的皮子)看得我心脏砰砰地直跳,几乎停止了呼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书籍啊!一时间里,惊喜,羡慕,慌恐,不安等诸多滋味交织的复杂心情,难以言表。匆匆忙忙地,我随手翻看了摆放在最上面的几本书,发现多数是那个年代禁读的小说,有:《青春之歌》、《家》、《红楼梦》、《复活》等等。仅凭当时有限的判断能力和社会大环境耳闻目染的影响,我能感受到在家里存放如此多的禁书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同时我也明白了大哥让它们回避家人的作法,既是出于无奈,也是对于那样一个时代的呼应。在这样一股强大的无形的压力的驱使下,犹豫了一些时间以后,我抵御住眼前的诱惑,合上箱盖,再次极其费力地把装满书籍的木头箱子推回原来的位置,然后坐在那里继续回味,心里感觉到的就是暖暖的幸福。这是发生在20世纪七0年代初的一件往事。
四
《天堂电影院》不在天堂,而是在西西里岛一个叫詹多卡的村庄里。时光流转的四月,紧随两根铁轨到达的是令小多多痴迷的又一个春天。那火车在叫,那投影机在转动,那村庄是个陌生的国度。幕布高挂的长夜,放影师艾弗达的话外音就是那个纯真年代的进行时。男孩、女孩、中年人、老年人坐在月色笼罩的老式影院里,幸福或者忧伤地,用视觉演义另一些人的人生——
五
如此遥不可及的秋天,我在乌鲁木齐的家中明显感觉到正在离去的和到来的东西。秋分临近,树叶见黄,枯萎。东南风一连狂挂了三天三夜,天空被吹得如同一张薄薄的白纸,飘在城市的上方。透过这张白纸,我能看见刚刚流逝的夏天躺在一张睡床上,去远方旅行了。眼前没有鸟儿也没有风景,更没有可以穿着清凉的短裝走过去的一天。天气预报和各种传言都在证实、都在讲述一个更加剧烈的天气骤变过程,即将出现。微信里甚至有人在提示:出门要填加衣服,要带雨具。是的,几乎可以肯定,徘徊在遥远西方天际中的寒云,很快会冲杀过来,把这一年带到终点,并让时光一样暗淡的大地回归冬天。裸露在你我中间。
六
太阳从厚厚的云层中露出小半张白色的脸来,照亮我所在的这片街区。红绿灯仍在闪动。斑马线和水泥大道,车流和向右排列的树木,商铺与电子屏幕,在人行道上持枪巡逻的特警,骑着电驴穿梭在人群中的快递员,一股晨风从背后吹过去,我的眼睛跟不上快速飞落的树叶。这是乌鲁木齐九月的早晨,四下里,有洒水车经过的鸣笛声。快节奏的城市表情,一一与我的目光交峰。现在,我就在这里,在黄河路一条巷道的路口,准备穿过马路走到对面去。和我并行的是一个维吾尔族姑娘,走到路的对面时,她大步跨过来站在我面前,用比较重的南疆口音,柔声细语地向我打听自治区中医院所在的位置。我以同样轻声的语调告诉了她。当她转身离开时,我才发现她的左腿走路一瘸一拐的,是个残疾人。我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我一直目送她消失在远处的街景中。
七
在那一年秋天,低低的飘在山田上的云是黑色的。从云里下下来的雨是黑色的。长在田里的秋麦粒是黑色的。用马匹拉进牛录的两轮马车是黑色的。在后街生产队空荡荡的大院子里,从马车上卸下的麻袋是黑色的。黑色的不透光的夜晚,在水磨沟石磨房里磨出的面粉是黑色的。早晨,掉到树下的苹果在滚动,下面的叶子是黑色的。一只公鸡、四只母鸡静静站在外公家的草棚里,那草棚是黑色的。我洗过脸,站在镜子前,外婆用一块旧毛巾给我擦脸,那块旧毛巾是黑色的。一股强烈的发面饼的味道,开始从灶房里冒出来,我来到灶房,坐在餐桌前,看见摆在餐桌上的发面饼也是黑色的。
八
如果把天空当成一面镜子,我就可以看见那个烟囱一样垂直飞行的年月。乌鸦们聚在白杨树上的很长时间里,公社的广播一直响着。那广播在催促、在用它尖硬的喊叫把一种不祥之音,灌进全镇人的双耳里。外公站在自家的果园里。外公的脸色凝重。一只大头蝇在他周围飞来飞去,他的太阳穴上的血管轻微地跳动,他发出的叹息被秋天的风带到我身边。外公在看着离他几步远的地方正向下挖坑的三个外孙。方儿哥、石头、还有我,我们响应公社政府的号召,从这一天起,开始在外公家的果园里挖地道。一把镐头持续的刨挖之后,方儿哥头上冒出热气。方儿哥从挖过的地方挪开身子,那里有厚厚一层刨开的土,石头和我拿着铁锨在往旁边的地上铲那些土。那广播还在持续地响,广播声传过巷道在果园上空经久地回荡着,外公和我们的影子,长长的投在果园里。一把镐头,两把铁锨,上下左右挥动的三个人的六肢,那土越挖越多,那土坑越挖越深,渐渐挖到了方儿哥的腰部、胸部,显出洞口的形状来。这时,外婆出现在隔开果园的栅栏那边,在喊吃午饭了。
九
苹果树上醒目的大红苹果,沙枣树下瘦了一圈的方儿哥的脸,从我手中滑落的柳条框子,顺着梯子向上慢慢爬出洞口的石头。这一天,是太阳光直直照射在外公身上穿着的白衬衣的一天,也是我们三兄弟用去十五天的时间,挖好自家地道的一天。下午五点的钟声敲响了,指针指向西北偏西的方向。外公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果园里。外公经过葡萄树和梨树的浓荫,来到三个外孙那里。外公站在我们面前时,我看见他的手上抓着三个鸡蛋。我们三兄弟靠得很近,我们在等。外公开口了,他冲着方儿哥说,地道挖了有多深多长?方儿哥说,有三米深十米长了。外公说,挖得可以了,你们收工吧。他把手中的三个鸡蛋分别递给三个外孙。那鸡蛋是热的。我们头顶的太阳光也是热的。外公转身走开了,果园的树木长得高高大大,像一道有形的墙,把我们与外面的世界隔开。我们坐在地道洞口周围的土堆上,剥掉鸡蛋皮,狼吞虎咽地吃掉鸡蛋。这个时候,公社广播站的广播又响起来。那广播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在播报在这一天已经播报过数次的通知,说的是与我们牛录边境相邻的那个国家,随时准备发动一场战争。全体社员及村民必须提高备战意识,加紧各家各户挖地道的速度。为了指导各家各户挖地道,公社今晚9点继续在广场放映电影《地道战》,欢迎各家各户前来观看等等。听到放电影的消息,石头和我像打了鸡血似的兴奋起来。我们毕竟还是个年龄十岁左右的孩子,只图着夜里和牛录里的小子们聚在一起玩耍,而根本不去理会广播里所说的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一前一后穿过果园率先跑进外公家的大房子,把广播里的消息告诉了外公。
十
说到九月底,乌鲁木齐有个适宜于从近处观察社会侧面的黄昏。在秋风横扫落叶的五一东路,当街灯依次照亮车流拥塞的马路和左右两边的铺面时,一个小女孩,像精灵似的越过前方的路边护栏杆,走进自治区中医院科研楼一楼的旋转门,出现在该医院住院部大厅。大厅里有当班值勤的保安、几个身穿病号服来回走动的病人及家属。小女孩的突然出现,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当她静悄悄走地到那几个病人和家属身边,叔叔、阿姨地轻声喊着,伸手递出一本杂志时,他们才看到了她。小女孩穿着一身篮色校服,瘦瘦弱弱的样子,显得异乎寻常的矮小,在她的另一只胳膊下面还夹着十来本杂志。小女孩用近似哀求的声调,在苦苦地,一遍一遍向他们叫卖着,仿佛在叫卖的,是她最不情愿失去的东西似的。那声调缓慢、清脆,令人心动。正是她异样的声调吸引住了在这一时刻从打此地经过的我和小舅子的目光,我们收住脚步,招呼小女孩过来。小女抱着一摞杂志跑了过来,非常利落地递给我俩每人一本,并且用那种充满期待的目光直盯着我们的眼睛看,口中还是念念不停地说叨着:叔叔买一本吧。叔叔买一本吧。我们接过杂志后瞧了一眼才发现,俩人手里的两本杂志一模一样,都是3年前发行的同一期《南方人物周刊》。我俩又翻看了一遍小女孩腋下夹着的那些杂志,也都是同一期《南方人物周刊》,而且这样一本过期的旧期刊她要卖10元。即是这样,出于同情心,我和小舅子还是决定各买一本。在付给她钱的时候,我们顺便询问了她的一些情况。小女孩的家就住在附近,父母亲均无固定收入,她今年读小学六年纪,从去年开始,每天放学后小女孩就在这家医院里卖杂志。挣来的钱除去上学的费用外,还要贴补家里的开支。听了她的一番话,我们感到心里紧紧的。于是,在转身离开时,又忍不住多看了两眼小女孩那张分外瘦弱的小脸。
十一
月亮开始时,只是一个黄色的小不点。月亮的影子出现在灰色楼群的尖顶上方。渐渐的,月亮升起来了。月光在四处生长,月光里有今年春天的广场、街道、商店、理发店、十字路口、红绿灯,月光里也有走在大街小巷中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汉人、回族人、蒙古人、塔吉克人、乌孜别克人、锡伯人。春天的风,在轻轻呼号,树枝上长出小小的绿芽来。一辆公交车开着开着,开到离这行文字很近的地方。这里是这座城市的心脏地带,俯下身,我就能听到在同一维度,与我的心脏一同跳动着的城市那颗巨形的心脏。一座城市同样也是有生命的。只要你去关注它、倾听它,就可以感受到它鲜活的生命体征。
十二
德里达写到:“诗人的本质是个体与其人民的群体生活的关系,而圣徒的本质却是人与上帝的关系。”而我正在使用的这些文字呢?它本质上难道不也是个体语言与其无穷大的语言王国相互依存的关系吗。
十三
又是个草叶上沾满露水的早晨。通向南面的秋麦田在牛录以西的旷野。在黄土路两边车辙里深深碾压过去的老式车轱辘,咕咚咕咚地向前转动着,把车的所有的重量,统统留给了正在承受它们的这片土地。的确,“承受是相互的”。此时此刻,套在车辕里的一头母驴,和坐在驴车上的一大一小两个男孩子,也在承受生活带给他们的重压。他们自幼生活在这里,成年累月非同寻常的经历,以及耳闻目染的那些东西,使他们过早地成长起来,成为一名名幅其实的劳动者。现在是深秋季节,秋收已过,南面的麦田里有成堆成堆打完场丢下的麦秸杆。他们知道,在冬天,那些麦秸杆可以用来给牛羊当草料。他们也知道,牛录每一年的冬天都很漫长,没有足够多的草料,外公家的牲口是过不了冬的。今天是个星期天,不用去学校。清早起来,两个男孩听从外公的吩咐,套好毛驴车,带上两把杈子、两捆麻绳、还有吃的,便从牛录出发了。他俩要赶在傍晚天黑前,把一驴车麦秸杆运到牛录的外公家来。现在,那稍大一点的男孩侧身坐在驴车靠近驴屁股的位置,扬起手中鞭绳抽打在驴屁股上。驴屁股的毛皮上面留下一道很长的鞭印。毛驴加快了步子,几乎小跑起来。驴车经过的地方,扬起一股尘土。天气是干躁而清澈的,那尘土跟着驴车在向前移动。连片的望不到尽头的岌岌草丛出现了。过了岌岌草丛,是大片的荒草地,从这里开始,地势逐渐增高,顺着眼前这条笔直的土路一眼望过去,在极远的高地上,有连绵的麦田。那里就是牛录秋收后的秋麦田。经过六、七里路的行程,临近午时,人与影在背后形成一条直线的当口,两个男孩儿赶着他们的毛驴车走到了那里。
十四
这是午后直愣愣瞅着两个男孩儿的大太阳。麦田里的每一株麦茬上都留有太阳垂涎欲滴的灰色眼睫毛。只要有风吹过,它们就会掉下来,掉到下面干巴巴的土里。在西边光亮的麦场中央,两个男孩儿正在用铁杈子,往驴车上杈着那些金黄色的秸杆。秸杆里掺杂着大量碎屑一样的麦糠,只要秸杆被杈起来,它们便跟着被抛撒在空中,然后落在毛驴和男孩儿们身上。时间久了,周围的空气中也满是细碎的粉末一样的东西。男孩子们在呼吸这种空气。男孩子们开始感到呼吸困难。于是扔掉手中的杈子,走到麦场的另一头,站在那里大口呼吸没有被麦糠污染的干净空气。太阳这时偏到了西边的河谷之上,河谷的深处有野树林的阴影,几只乌鸦掠过河谷朝这边飞来。乌鸦们飞到麦田后便落下来在麦田里四出觅食。男孩子们休息的时间并不算长,他们一言不发地回到麦场中间,继续往驴车上杈那些秸杆。驴车上的秸杆已经摞得有半间房子那么高了,大男孩儿扶着小男孩儿爬上车顶。秸杆细软又深,小男孩儿沉下去了半个身子。他在努力地用身子压、用脚踩踏车顶顶上的秸杆。经过一番折腾,车顶中央出现一个大坑,大男孩儿继续往大坑里杈秸杆。太阳再向西边移下去两条胳膊那么长的距离的时候,驴车上面的秸杆已经杈到杈不到的位置了。大男孩儿从地上拣起备来的马绳,把一头扔给车顶的小男孩儿。他们用尽最后的力气前后左右拉着、拽着、绑着,把一驴车小山一样高高的秸杆,绑得紧紧绷绷,严严实实,完全与驴车连成一体。当一切都干到妥当之后,小男孩儿拽着马绳,从车上滑跳下来,接着,男孩子们赶着驴车,离开麦场,踏上回家的路。
十五
在谈到流亡作家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时,约瑟夫.布罗斯基写到:“我们全都在为一部字典而工作。因为文学就是一部字典,就是一本解释各种人类命运、各种体验之含意的手册——其中的语言就是生活对人的所言。它的功能就是去拯救下一个人,拯救新来者,使他不再落入旧的陷阱------因为,去弄清生活词汇的含意,去弄清你所遭遇的一切之含意,这就是解放。”《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
十六
必要的停顿。时间回到过去的时间。1977年的春天,在大戈壁吐鲁番盆地中央蜿蜒的一小片绿洲,风和沙在兵营外咆哮的四月,四列新兵全身行装,刚刚在操场上集合完毕。他们个个精神饱满,气势十足,他们的眼睛全部投向正前方离他们十步远的地方,那里并排停着两辆老式解放牌军用卡车。那卡车上罩着深绿色篷布,篷布的一侧有编号,两辆军车分别编为一号车、二号车,显然,眼前的一幕,已经在暗示行将开始的一次远行军。队伍里鸦雀无声,每个新兵脸上的表情几乎都是一样:肃穆,安静。只有从鼻孔之间呼出的气息,能稍稍感觉到他们略微紧张的心情。如此遥远的一个春天,这是命运对他们作出选择的时刻。迈着方步,一个军官从营房里走出来,走到队伍正前方中间的位置站定。军官用眼睛扫视了一遍全体新兵,然后口中喊出口令:“全体都有,立正!”“稍息!”队伍闪电般呼应着,唰唰地做出齐正的动作。接着,军官照着化名册开始点名,队伍中有一半的新兵被点了名。军官命令被点了名的新兵上1号卡车,没有被点名的新兵上2号卡车。队伍迅速分成两列,上了卡车。卡车立刻发动起来,吐着黑烟,开出营区。卡车沿着一条柏油公路向西行驶,行驶到第一个路口时,车队分开了。一号车左拐,开向南。2号车右转。开向北。左拐的车上有我,它把我和另外20名新兵,带向数百公里之外的巴轮台,我将在那里的崇山峻岭中,接受为期三年的工程兵军营生活。而开往北面的另一辆军车,则把其他20名新兵,送到乌鲁木齐的兵营。他们所遭遇的经历要比我们好的多。好的多。
十七
在讲到东方一座古老的城市时,诗人布罗斯基人运用了“尘土”这个意象。他写到“尘土!这怪异的物质,扑向你的面孔!它值得注意:它不应被隐藏在‘尘土这个词背后”。顺着这个意象继续展开想像,我即刻联想到一支由挖掘机、搅拌机、高架起吊机合流而成的钢铁大军。当下,在其来势汹汹的突进面前,即是最遥远的省份,也找不到一处能够抵御它们的边界。它们一日千里,攻城拔宅,所到之处,留下了满目令人啼笑皆非的“新景观”。2015年夏天,回察布查尔故地一次短暂的寻游,让我目睹了这支钢铁大军,正在那片土地上上演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八月的炎炎烈日之下,在熟习的庄稼地与乡野之间,那引擎的轰鸣声,扑面而来,掀起令人目眩的尘土!座落于牛录里的一个个老式庭院被推到,铲平,顷刻之间,变成一片触目惊心的新工地。而仅隔两墙之距,另一个被强行复制的牛录已然在加速度的克隆之中。只是,一眼看过去,它们就像一个突然闯进来的变异物体,矗立于视野之中,显得即过于庞大,又过于外在。实在难以承载所有原乡人的家园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