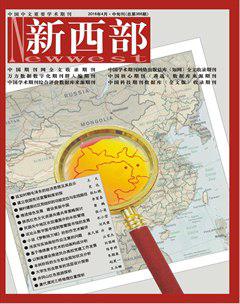二程与嵩阳书院
【摘 要】 嵩阳书院作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文章梳理了嵩阳书院的渊源。阐释了宋代二程在此讲学传播了儒家学术思想,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也使嵩阳书院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在二程过世几百年以后,嵩阳书院又重新高举传播二程思想的大旗。本文通过对二程在嵩阳书院的讲学活动、耿介在嵩阳书院的各种活动的分析,以期更好的理解二程与嵩阳书院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 二程;嵩阳书院;耿介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是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古代社会培养了大批经世安邦的人才、传播不同学派的学术思想,而且还通过讲学、祭祀等形式改善了周边地区的学术风气、民俗教化等,所以书院对古代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嵩阳书院作为宋代全国四大书院之一,与二程及其学说有着密切的关系,二程把嵩阳书院作为讲学的基地,传播学术思想,培养了大批人才。在二程去世后,其学术思想仍然被嵩阳书院的学人代代传承。
一、嵩阳书院的历史沿革
嵩阳书院在经历了嵩阳观、嵩阳寺、太乙观等多种身份的变化才形成了书院。《中国书院史》介绍:“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登封县城三公里外的嵩山南麓太室山脚下。面对双溪河,背靠峻极峰,西依少室山,东傍万岁峰。”
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大德生禅师创建嵩阳寺。东魏天平二年(535年),《中岳嵩山寺碑》中记载道:“大德生禅师,以此山,先来未有塔庙,禅师将欲接引四生,卜兹福地,创立神场。乃北背高峰,南临广陌,西带峻涧。于太和八年岁次甲子建造伽蓝(寺院)。”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又改为嵩阳观,为佛道二教的活动场所。唐高宗弘道元年(683年)春、冬两季,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两次到嵩山,把嵩阳观当作行宫,曰奉天宫。唐代有许多文人墨客到嵩阳观游玩,如韩愈、白居易等,后改为太乙观。后唐靖泰元年至三年(934-936年),进士庞式曾在此聚徒讲学。五代后周时期,周世宗根据名士所请,奏准在此设立太乙书院,为宋代嵩阳书院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清代王日藻曾说:“夫五代日寻干戈,中原云扰,圣人之道,绵绵延延,几于不绝如线矣。而书院独肇于斯时,岂非景运将开,斯文之未坠已。”[1]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被赐名太室书院。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下令西京(洛阳)官员重修书院,并赐名“嵩阳书院”。
二、二程在嵩阳书院的讲学活动
嵩阳书院位于宋代都城汴京西南二百余里的中岳嵩山之阳,地理优越,环境清幽,远离尘世喧嚣。景日昣就曾说到:“嵩少名胜,山抱水环之区,无地不染梵尘。”
优越的地理位置、优美的环境吸引了大批名师宿儒到这里讲学。地以名胜,学以师闻。宋代,到嵩阳书院讲学者众多,其中最为出名的莫过于二程。王日藻《嵩阳书院碑记》记载:“两程夫子应期而出,先后提点嵩山崇福宫,昌明正学,于是濂洛关闽递接薪传,俾尼山之渺旨微言,昭昭若揭日月,则诸儒之功诚不容泯灭也。”[2]二程是同胞兄弟,河南人。大程即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小程即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
早在熙宁五年(1072年),二程随父亲程珦管勾嵩山崇福宫,嵩阳书院毗邻崇福宫,二程就时常到嵩阳书院讲学。王安石变法之际,朝中政见分歧,崇福宫就变成反对变法者投闲置散的场所,二程当时就是众多反对变法者中的两名。“二程曾领崇福宫之职,常在嵩阳书院讲学,各地学者慕名而来,多的时候有生徒数百人。”[3]二程把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合在一起,吸取了佛教、道家中有益的成分,对传统的儒学加以改造和创新,形成了新儒学。
二程在嵩阳书院讲学十多年,教学内容主要以《四书》、《五经》为主,朱熹曾说:“伊川先生之学,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标指,而达六经,使人读书通礼。”
在讲学的同时,二程还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时的怀疑精神,二程说:“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于仲尼,得他言语,便终身守之,然未必知道怎生是,怎生非,此信于人者也。学者需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夺亦不得。”由此得知二程反对学生死读经书,要有怀疑精神和自信心,不能盲目信奉传统的儒家经典,要有自己的新观点,同时程颐还曾提出:“不惟科举至上”的观点。
二程在嵩阳书院讲学期间,除了参与讲学、学术研究的活动,还亲自为书院制订学制以及学习考察的详细条例。程颢也亲自为嵩阳书院制定学制、考察等规条。渊博的学术知识、高尚的人格吸引了全国各地学者,众多人不远千里来此求学,其鼎盛之时,“崇堂讲遗文,宝楼藏赐书,赏田逾千亩,负笈者云趋。”
二程在嵩阳书院讲学,不但传播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培养了大批人才,如杨时、游酢、范纯仁等等,为理学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在众多优秀的学生中间,杨时对于二程思想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多年以前,杨时曾求学于程颢,学成归闽时程颢送他远去时就曾说道:“吾道南矣。”表达了当时程颢对杨时传播理学寄予厚望。多年以后,杨时再次北上求学于程颐门下,就发生了“程门立雪”的故事。后来杨时南归以后积极传播二程思想,其中他将理学传播于罗从彦,罗从彦传于李侗,李侗传于朱熹,朱熹集百家之长,最终完成了对理学的改造,被后人称为“程朱之学”。
三、嵩阳书院对二程思想的传承
北宋三兴官学以后 ,嵩阳书院逐渐衰落,最后竟沦落到被变卖的地步,“垣墙聚蓬蒿,观殿巢鸢鸟,二纪无人迹,荒榛谁扫除。”嵩阳书院荒废多年,其中北宋后期至南宋的历史还有待考证。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年),嵩阳书院曾被改名为成天宫,成为传播道教的场所。在元惠宗至正年间(1341-1368年),又被改为嵩阳宫,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之后。随着官学的衰落、统治阶层对书院控制的减弱,嵩阳书院又逐渐复兴起来。明嘉靖年间,登封知县侯泰重建书院,聘师招徒,为纪念二程在这里讲学的成绩,还专修了二程子祠,但是无论从师资质量还是生徒数量都和宋代相差甚远。“明末兵乱,倾圮殆尽。”嵩阳书院“又废于兵燹,无半椽瓦甓之存,即汉封将军三柏亦焚其一。”[4]
清朝康熙初年,面对嵩阳书院的残碑断碣,和宋代二程在嵩阳书院讲学时期的繁盛有着天壤之别,中州学者普遍感觉有复兴嵩阳书院、振兴二程学术的责任,提出“辈居近伊洛,当使二程之学大振于今日。”[5]
书院的建筑设施是书院进行各项正常活动的基础,所以复兴嵩阳书院的建筑是复兴二程思想的物质条件,同时还可以为书院师生营造二程思想的学术氛围。中州人士怀着复兴二程学术思想的满腔热情开始了嵩阳书院的复建工程。
康熙十二年,登封知县叶封的《重修嵩阳书院记》中记载:“登封接迹伊洛,其学术风教,不甚相悬,又嵩岳多奇,四方达人高士自远而至,苟有向往之心,不患无观摩之益。而自宋以来五六百年,卒未有起而名世者,由于振兴之无自也。先是,崇福宫有太室书院,建自五代周时,宋至道间,赐《九经》。景祐间重建,改为嵩阳书院,废于金元。明嘉靖间,知县侯泰即嵩阳书院故址复建书院,祀二程先生,仍曰“嵩阳”。诸生以时讲业其中,又废于兵燹,无半椽片瓦之有。即汉封三柏,亦焚其一。余每过徘徊慨息,思兴复之,未暇也。今年二月,始相度故基东南十步,筑堂三楹……有宋韩公维、吕公诲、司马公光、程公颢、颐兄弟、刘公安世、范公纯仁、杨公时、李公纲、李公邴、朱公熹、倪公思、王公居安、崔公与之几提举主管崇福宫者,皆大贤名世,可为吾党矜式,以名宦中无祀,祀于此。
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登封叶封于故址东南十步远的地方,筑堂围墙,重建嵩阳书院,同时修建了诸贤祠,祠内供奉“提举主管崇福宫程朱而下十四人”,分别是程颢、程颐、朱熹及司马光、韩维、杨时、范纯仁、吕诲、李纲、刘安世、李邴、倪思、王居安、崔与之。不久,叶封升迁京职。康熙十六年(1677年),登封名儒耿介继叶封未成之业,继续扩建,经他努力改善,书院各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改善。此时的嵩阳书院“门庭孔峻,堂庑翼然。祭菜鼓箧有节也,讲习弦诵有所也,饔飱膏火有资也。”其中为了纪念在嵩阳书院讲学的理学大师程颢、程颐、朱熹三人,耿介专门建造了先贤祠,此前“先是程朱三子合祀于诸贤祠,介以书院宜重道统,故专祀焉”。耿介撰写的《创建嵩阳书院专祀程朱子碑记》中说道:“书院之来旧矣。中祀两程,遭罹兵燹,随圮。前令楚黄慕庐叶公始创,为堂三楹,以终宋之世凡带崇福宫衔者十四主合祀之。余谓书院宜重道统,程朱例有专祠,于是直南为殿,专祀程朱。”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林尧英建讲堂,讲堂挂有称赞“二程”的门联:“满园春色催桃李,一片丹心育新人。”此堂的建造就是为了纪念程颢、程颐在嵩阳书院讲学。在讲堂的东山墙壁上,悬挂着《二程讲学图》,描述了二程正襟端坐在嵩阳书院的二将军柏下正在进行讲学,数名学生围坐在四周全神贯注地听讲。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耿介建造纪念孔子的先圣殿,孔子在儒学中地位尊崇,但是从建造时间上还没有先贤祠早,可以看出嵩阳书院对二程的重视。康熙、乾隆时期,嵩阳书院迎来了继北宋之后又一次盛况,被称为“中州之白鹿”。清代末年,朝廷废除科举制度,嵩阳书院被改为高等小学堂。
如果嵩阳书院单从书院建筑上来表达对二程的重视,作为一个书院来说仅仅是表面上的,并没有传承二程思想。讲学、藏书、祭祀作为书院的三大规制,可以全面展现一个书院的办学思想、学术追求等。因此,想要全面了解嵩阳书院对二程学术思想的传承深度还是要从这三方面探索。
山长是每个书院的文化象征和精神支柱。嵩阳书院也不例外,耿介作为嵩阳书院的山长,一直以复兴二程学术思想为己任,并把这种思想贯穿在书院的各项工作之中。
耿介作为嵩阳书院的山长,对理学造诣颇深。耿介尤其喜欢程颢的“内主于敬而外行之于恕”,因而将敬恕作为自己的堂号。耿介的学术思想大致概括为三句话:“以敬为体,以恕为用,归本与存诚。”著作有:《孝经易知录》、《理学要旨》、《中州道学编》、《大梁书院讲学存稿》、《嵩阳书院志》、《敬恕堂文集》等。张塤的《嵩阳书院记》中说道:“耿先生发挥圣学无馀蕴。读其所辑《理学要旨》一编,深切著明,悉宗之程朱夫子者也。”
耿介在《自课》中讲到:“学者先要端趋向,孟子只是愿学孔子,主意先立得定,故后世言道统者,必言孔孟。程朱之学,孔孟之学也。学不宗程朱,则途径先差,总使好高耽虚,终是去道甚远”。徐乾学在《嵩阳书院记》中曾讲到:“先生之教人以程朱为宗,一切放言诐辞无所用,而所谓敬义、博约之大指,固圣贤全体大用,会于一原之学。”此外,还有“嵩阳书院得先生复振,无不向风慕义,立雪其门,从此真儒辈出,关闽濂洛之统,于今有传人乎。”[6]
从耿介的《敬恕堂文集》中关于嵩阳书院的课程安排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二程理学推崇者,耿介所列出生徒要学习的书籍如《理学要旨》、《孝经》、《通鉴》、《礼》都是儒家的经典著作。朱熹曾说:“伊川先生之学,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指标,而达六经,使人读书穷理。”可见二程对《四书》、《五经》的重视,耿介让学生学习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理学经典,都是对二程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冉觐祖的《朱阳书院记》中曾写道:“静庵先生居嵩阳最久,与逸庵先生相砥砺,一以程朱为宗。”
嵩阳书院不仅在讲学内容上和二程思想保持一致,在培养学生人品方面也显示着高度一致。二程在嵩阳书院讲学期间,程颢曾说:“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存诚敬存之,不须防检,不须求索。”程颐倡导培养“希学希圣”之士, “当是时,学于程颐之门者,固多君子。”为继承宋代二程重视学生道德修养的传统,清代嵩阳书院强调人的品德修养。耿介十分注重学生的道德修养,提出“道学问”是以“尊德性”为基础的,在他制定的《嵩阳书院学规》中记载:“书院同人,皆有志于圣贤之学,须从德性涵养中来,致知力行,而后可渐渍,以几于道。今有逾一年,或二年三年,而气质犹未变化,德性未见涵养,殊非设立书院之意。”《辅仁会约》的第四条:“学生须以培养道德品质为先务。功夫在于能做到克己,严格区别义和利,克去私欲,才能光明伟大,为圣为赞。”
另外耿介在《嵩阳书院志》中讲到:“学务以洛闽为宗旨,孔孟为要归;其教人务以主敬为根本,恕为推敬。总欲体天地生物之仁,以不负天地生我之意。”这里耿介明确提出学习的目的是以做人、明经为主要,重视道德教育。耿介《嵩阳书院讲学纪事》中讲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万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7]从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嵩阳书院的教育其实就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教育,目的在于培养维护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纲常。
嵩阳书院除了在讲学方面重视对二程学术思想的发扬,还借助书院祭祀来表达对二程学术思想的传承,让学生参与祭祀过程,体会书院的学术追求,培养学生的学术认同感,加强嵩阳书院的学术凝聚力,激励学生继承、发扬二程的学术思想等。
嵩阳书院有先圣殿、道统祠、先贤殿。耿介的《嵩阳书院志》中记载:“每春秋祭丁之次日,以少牢一祀先贤祠。或县令亲祭或委学博代祭。每春秋二仲朔日作古释菜之礼,用诸果品菜蔬12器祀先圣。书院山长率肄业诸生行礼。”还有告文:“维康熙年月日,某官谨以牲醴之仪,致祭于先贤程子纯公、程子正公、朱子文公之神曰:惟神表章圣学,昭若日星。继往开来,启迪无穷。书院再建,祀典宜先,仲春(球)朔日,特牲告虔。尚飨。”《嵩阳书院志》记载:“诸贤祠用三牲行礼不用祭文。”
从上可以看出,孔子地位虽然尊贵,但是其所在的先圣殿无论是祭祀规模还是建造时间都比不上二程所在的先贤祠,足见二程在嵩阳书院地位之高。
从宋代二程在嵩阳书院讲学开始,二程的思想便逐渐影响到它的各个方面,即使在二程过世几百年以后,中州人士仍然高举复兴二程学术思想的大旗,重建嵩阳书院,传播其学术思想,足见二程的学术思想对嵩阳书院的影响之深。
【参考文献】
[1] (清)耿介.嵩阳书院志[M].卷之二,嵩阳书院碑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2] 宫嵩涛.嵩阳书院:中州教育史上的明珠[M].中国文化遗产,2009.
[3] 李国钧.中国书院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4] (清)耿介.嵩阳书院志[M].卷二,嵩阳书院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5] (清)张沐.南阳书院学规[M].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6] (清)耿介.嵩阳书院志[M].卷二,嵩阳书院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7] (清)耿介.嵩阳书院志[M].卷一,沿革.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于晓红(1989-)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学历: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