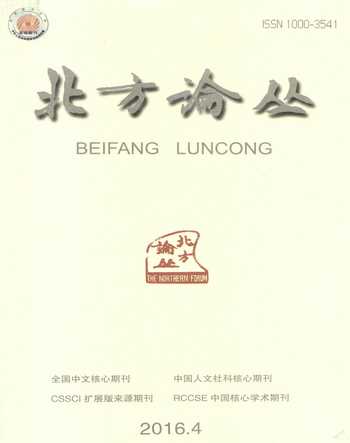“集体无意识”与中国古代的“乡愁”书写
赵云彩
[摘要]乡愁是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体现了人类普遍的“集体无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对于家乡、乡愁的描绘,具有久远的传统,留下了丰富的文字书写记录。对于乡愁的书写,古人常常立足于家国忧患的视野,出于一种自觉的表达。这就使得“乡愁”与古代知识分子的情感归宿问题关联起来,具有了“精神还乡”的纵深内蕴,成为古代文人精神建构途径之一。经由个体对于家园、家乡、国家的情感的艺术化表达,中国古代的乡愁书写不仅仅限于个体的抒怀,同时也具有了群体性的特征和追寻族群生存意义的哲学高度,体现了丰富的精神内蕴与人文特质,是中华民族精神资源的宝库。
[关键词]集体无意识;乡愁;易代;民俗志
[中图分类号]15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4-0018-04
近些年来,人们不约而同产生一种对于过去文明的眷恋。这种思潮也影响到了文学领域,表现为乡土文学的内容的抒写,以及作家作品中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乡愁”意识。这种呼吁回归传统、回归理想家园的思潮,其实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体现,有着久远的历史。在许多古代文学作品中,人们描绘家园的种种美好,在一定的时期,如社会动荡、家园沦丧的时刻,这种对于家乡的情感又会上升为爱国情怀。文人们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对于家园、国家的情感,有激情澎湃的诗词歌赋,也有冷静客观的家乡民俗志。从本质上说,这些作品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体现了古人对于家园、国家的挚爱。从深层次说,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
一、从“思乡病”到“集体无意识”
在西方文化里,“乡愁”或“怀旧”的英文是“nostalgia”一词,起源于希腊语“nostos(返乡)”,以及“algos(痛苦的状态)”,连起来便是指一种思念家乡的焦虑状态。该词最初创立于17世纪,由一位随军医生所创,主要用以指称远离家乡的士兵出现的抑郁、沮丧的症状,也即思乡病。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词逐渐远离最初的医学或病理学的本意,具有了更多的精神、文化方面的指向,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文学、心理学、哲学等领域。
而在中国古代,关于离愁与怀乡的书写却十分常见,其中包括个体层面的离愁别绪、思乡之苦、千里寄寓,也包括更深层面的家国忧患、易代之痛、乱世悲歌。文学中许多常常出现的表示离愁别绪的意象,都可以看作是“乡愁”的代名词。这些书写源远流长,古今勾连、彼此映照,形成了丰富的文化积累。
中国文化中这种古今共通、几乎是出自惯性与偏好的对于“乡愁”反复书写与艺术表达,可以用“集体无意识”这一概念来进行概括。“集体无意识”由瑞士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大师荣格,在1922年发表的《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一文中提出。“集体无意识”学说认为,在人的心理的深层,由遗传保留着许多原始的、祖先的经验或种族记忆,这样的经验或记忆构成了人类普遍性的精神。“集体无意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影响了我们的精神视野,人们可以通过其间接的显现来对其进行认识。这些间接的显现包括梦、文学作品、艺术象征、人们的生活,以及行为方式等。积淀在“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始意象和原型,是人们进行文学创作、艺术构思的动力和源泉。人们正是通过艺术的创作,来追寻逝去的家园和记忆,与远古的先人进行精神的沟通,为心灵提供栖居之所。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浓郁的乡愁情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有着安土重迁的情怀,对大地、家园有着深厚的依恋感。古人对于理想家园,有着近乎一致的构想,体现了农耕文明的人们“安土重迁”的生活追求和人生理念。既然家园如此美好,离开家园、家乡之后,自然会心生不舍与留恋。在远方追忆故乡,因为空间的阻隔,故乡的风俗与人情,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有了别样的体验,而且离家越久,这种滋味越醇厚,形成一种浓郁的“乡愁”。这样的感情,从心理的层面来看,与西方文化所说的“nostalgia”,即某种思念家乡的“分离焦虑”,有着极为近似之处。对于故园的描绘、种种离愁别绪的抒发,皆可归因于对于故乡亲情、血缘,以及温馨生活的具象象征,各种意象也进一步积淀成乡愁文学的原型。这样几乎深植于人们血脉中的、与生俱来的意象与记忆,为古代文人反复歌咏吟唱,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二、个体情感在国家层面的表达
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为神话原型批评学说奠定了基础,神话原型批评重视神话的作用,认为神话中蕴含了民族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追求。神话原型批评以英国人类学家费雷泽的《金枝》为奠基,到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为集大成者。弗莱融合了荣格和弗雷泽的观点,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以及文学是“移位的神话”的论点。在文学创作中,集体无意识常常以原型的形式出现,神话作为也最容易表现集体无意识的艺术形式,可以折射一个民族的精神理念。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同样流传着许多神话,这些神话中体现了先民的智慧以及胸怀黎庶、兼济苍生的精神。不论是女娲补天,还是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都毫无例外地贯穿了这种精神。尽管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占主导的儒家文化少了几许神圣性与宗教性,而多了积极的入世态度以及世俗的色彩,但对天下苍生的关切情怀与神话传达的精神是一致的。
中国的“乡愁”文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历代文人均有所发挥。这一方面缘于文化基因中的济世情怀;另一方面,由于儒家的传统教化。受到传统文化浸润的古代文人,在无形中秉持着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和行为准则,认为个人对国、家、社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他们立足于现实社会人生,自我抒怀的同时也兼及家国遭际、人伦大爱等问题。如果说古代文人在和平时期较多地关注小家,专注于家园的细描,那么,在非常的历史时期,比如,战争或国家沦亡时,动荡的现实打破了平日生活的闲情逸致,人们胸中对于家园的感情自然而然地升华为对国家的感情。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或者说本就是同一种情感,受到不同的外部激发,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表达。如果不囿于个人的感情和视野,将对乡愁的表述置于更为宽泛的层面上,将古代文人在非常历史时期的独特体验与家国情怀联系起来,就可以清晰地发现,乡愁与家国、故国具有内在的精神联系,成为中国文学的特定意象和表现形式,彼此间一直是一种互文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的乡愁以及对家乡的表述,也就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和意义。
古代文人表达情感,以诗词歌赋为大宗,这是因为在古代,诗歌具有“言志”的功能,人们习惯于借诗歌来阐发个人的情志,因而产生了大量具有家国情怀的诗篇。一般认为,屈原是将个人命运与国家遭际联系在一起,对国家的命运表现出深切忧患的代表。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的精神,一直是后世人追慕的理想。杜甫的诗作同样表达了对国家盛衰的忧虑,以及对普通民众的同情。他的诗无时无刻不在忧国忧民。有的学者推举杜甫为中国文学乡愁诗人之“鼻祖”,认为杜甫首创了“乡愁”一词。杜甫的诗表现的“是天下兴亡,是人民利益攸关,是浓浓的故园亲情、手足血脉同胞之爱,以及人间世的普遍人性、人道、爱憎,直面现实的勇气,更有着对美好和平自由生活的向往与深情呼唤”。
词本是“诗之余”,一般被认为是不适宜“言志”,其主要功能是抒情。长于写词的文人,在抒情的过程中也流露出浓郁的家国意识。较为著名的如南唐后主李煜的《破阵子》,抒发了一个昔日帝王的悲伤和落寞:“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词作表达了国家破败、家园沦陷之后,对于昔日繁华的留恋和追忆。这种今昔对比的落差,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内心的震撼尤为激烈。除此之外,李煜还作有《子夜歌》《望江南》《虞美人》等多首脍炙人口的词。不可否认,这些词作能够打动人,是因为作品本身朗朗上口,具有婉转流利艺术特征。但是更重要的是其中渗透的那种国家沦丧,时空变换、往昔不再的无奈感,更容易激起人们的共鸣。
作为普通文人,同样有着深重的忧患与对国家的赤忱。如南宋词人李清照,本是浪漫的词人。在她的创作前期,词中所写均是小儿女的闺愁别绪。金人人侵,家园沦陷,词人南渡之后,其词作风格大变,在个人的身世之感中渗透了家国意识,不同于明媚的少女时代:“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凉生枕簟泪痕滋。起解罗衣聊问、夜何其……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词文流露了词人浓厚的身世飘零之感,是抒发一己之情,也是抒发乱离人对故土的追怀,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南渡的其他词人如朱敦儒、张元干、叶梦得等人,创作均受时局影响,写作了大量的忧时愤乱之作。这样的文学创作,使得先人传承下来的关注苍生、伤时济世的情怀得到不断强化。虽然社会地位与身份有别,但南唐后主李煜故国之思与普通文人的乡愁叹惋,在感情基调与内心指向上却是一致的,均属于自古以来绵远的“黍离”之悲。
与汉族出现的文学形态相比,少数民族的天然本色,使得其家园的情怀更具有悠远而苍凉的意味,充满了恒古的悲情。汉代以来流传着一首匈奴人的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这是一首匈奴人与汉朝军队对垒,在汉军的打击下连连失利挫败后吟唱的一首歌。歌以借喻的手法,表达了对失去家园的悲怆和愤懑。乱世激发的追怀故国、思念家园的情怀,无论中原人,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感受都是一样的。战乱、动荡是非常态的,人们都希望回到正常的生活秩序中,因此形成一股向心力:抨击战争、怀念往昔。这些作品中均饱含着深刻人生的哲理与浓郁的家园意识,彰显了别具风情的对于家国的情怀。
显然,这样的家国之思,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局限于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对故乡的定义和家园范畴,而是融入了个体对于人生、理想、族群的情感寄托,上升到了哲学的维度,具有了永恒的精神层面的意义。成为了一个多层面的包蕴深广的文化场域。这样直接或间接地书写故国、故园、反映乡愁主题的文学作品,借助于原型意象反复渲染,贴近人们的心理,能够达到移情动情的作用,传达了作为个体的生命相似的经验体悟,展现了中国人的家园意识与精神怀想。
三、民俗志:一种特殊的乡愁表达方式
故乡在时空上已经属于过去。“乡愁”是一种对于过去生活的追忆和留恋,通过回忆与想象重构起故乡的原貌,是文人们试图弥合时间与空间造成的巨大差异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努力。通过这种努力和书写建构起来的故乡,具有了诗意的光辉,是人们心灵栖居的乐土。
除了直抒胸臆的诗词歌赋作品,我国古代还有一种特殊的文献,同样属于对家园、家乡的书写,其中渗透了浓厚的“乡愁”意识。这样的文献一般称为古代民俗志,如《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这些古代的民俗志与文学作品不同,书写内容主要是某一地域或都城的风土人情、市井百态,表现方式多是客观的记录,而不同于文学的抒情。民俗志在传统的典籍分类体系中,一般被列人史部之地理类,然而其兼有文学与史学的特质。在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过程中,这一类作品也被写入文学史中,是被作为文人笔记而存在的。将它们划为文学作品未尝不可,因为它是文人撰写的具有文学色彩的作品,在客观的叙事之下的一种艺术化的表达。而列入史部,是因为这些作品多是客观的记述,传承了史家一贯的“实录”精神。这样的作品与古代的地方志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不同的是,方志的编写多是在国家的主导下完成,体现了一种国家大一统的意识;而民俗志的撰写,多是由文人自觉的书写完成的。
在诸多民俗志中,有许多写于社会的非常时期,如战争带来的家国倾覆、江山易代时的以记录中华民族的民俗生活为主的民俗志。战争的存在,几乎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与族群发展的每一个进程。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战乱中烽烟四起,国祚覆亡,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园被摧毁,昔日的亭台楼阁已经化为残垣断瓦。战争同样摧毁了人们精神的故土,人们成为四处漂泊的受难者,精神无所归依。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急于抓住点什么。他们用文字详细地记录过往生活的种种,记录旧时的风俗、风物,记录曾经的繁华,以此来追忆、缅怀旧时的家国,重建心灵的故土和家园。这样的记述客观上也起到了传承文化、记录习俗的作用。在这种非常时期,文人们普遍具有一种“以志存史”的使命感和自觉的书写意识。此种情况下的民俗志,渗透了明显的家国意识,通常表达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和寄寓。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历史时期之一,这一时期出现的表现家园被毁、生活乱离的文学作品很多,如以曹操、曹丕、蔡文姬等人为代表的慷慨悲凉的建安文学,南朝时期庾信《哀江南赋》等,这些作品均以生动的笔触书写了乱世的种种情状。同样的思想与寄托,也表现在民俗志笔记里。此一时期出现的北朝文人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是一部与郦道元的《水经注》并称的著作。作者杨衙之感于战乱带来的巨大创伤,以此书记录曾经繁华与安宁的生活。书中详细记述了战乱前后洛阳城的变化,以诸多佛寺的历史变迁与盛衰变化,抒发了浓郁的国家兴亡之悲。《洛阳伽蓝记》也是较早的借描绘故城的风貌与习俗来寄托对故国、家园的感情的民俗志著作。
到了两宋之际,与《洛阳伽蓝记》类似的民俗志书写达到了一个高峰。两宋王朝鼎革,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与以往的王朝易代不同,北宋被金人所灭,南宋亡于蒙元。对于深受儒家文化濡染的汉族文人士大夫而言,他们文明昌盛的故国被一向受其鄙视的蛮夷所毁灭,这种挫败是一种巨大的耻辱和不能承受之痛。他们忧心中华的文化也像江山社稷一样,被摧毁而至覆灭,于是急于展现出知识分子的担当。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一些文人以诗词抒写壮志与恢复河山的抱负,表达对故国的深厚眷恋与怀想。一些文人如孟元老等,以民俗志这种书写方式,记录曾经的繁华与兴盛,表达内心的故国之思。民俗志书写在此一时期出现了一个高峰期。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署名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盛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代表。这些作品描绘的是旧时都城,同时也是在描绘自己家乡、故国。这样的民俗志多是对于人们日常生活习俗,市井百态的记录,展现了处于旧时社会和平安宁时期人们衣食丰足、安居乐业的适意之情。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写于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后,作者在文前叙述了写作的缘起是为了保存北宋繁盛时的风俗,并喟叹:“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同样,吴自牧在《梦粱录》前的自序也有“缅怀往事,殆犹梦也”之感叹。这些民俗志以“梦”“旧事”“繁盛录”为题,带有明显的追忆色彩,表明了对逝去过往的眷恋和无力感。与此同时,这些致力于重现往昔、重建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在书写民俗志的时候,也坚信文字书写所具有的记录历史与保存文化的特殊功能。在他们看来,唯有以一种遗民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担当,通过一种事无巨细的对于往昔繁华的记录,才能使得眼下已经灰飞烟灭的事物得到阐发和重现,才能使已经逐渐被世人淡忘的文化与习俗的神圣意义得以彰显,再现往日的光辉。
透过这些客观、冷静的民俗志的描绘,可以使人们深刻地感受到,遭遇乱离的人们,虽然后来的生活也可能安顿下来,但人们情之所系、心之所向的,仍然是旧时的家园和昔日的生活。也许现实的生活并非不好,而最让他们眷恋的还是往昔的家园。人们利用民俗志,详细描写家乡的市井百态,日常生活,以及种种宫廷典礼,王室逸闻,以此追忆一个国家繁盛时的景况。在这里,物化的家园已经被摧毁了,文人依靠文字来构筑精神的家园,安顿灵魂。凭着记忆和想象建构起来的家园,遮蔽了它的不足,放大了它的光辉,比曾经的真实存在还要美好。
综上可知,中国古代文人对于家乡、乡愁的书写,有和平时期恬淡生活的描绘,有不得已离开家园的愁绪,更有家国倾覆时的哀痛与追忆,其中渗透了对适意生活的向往和今昔对比的失落。人们渴望回到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不断地寻觅一种精神与心灵的归依之所。说到底,人们苦苦追寻的,是一种温暖的归属感。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这是人的集群性的体现,是人类普遍的“集体无意识”的体现。从集体无意识的层面上来看,种种艺术化的书写,是出于对大地母亲的眷恋,更是一种“万物有归”哲学诉求的表达。人们习惯于描绘自己家园,用文字精心构筑了一个个美好的栖居之所,供他们自己,也供后人容身休憩。通过这样的文字书写,人们可以获得某种心灵的慰藉,这种安慰可以使得渺小的个人在历史的荒原中有所依凭,不致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