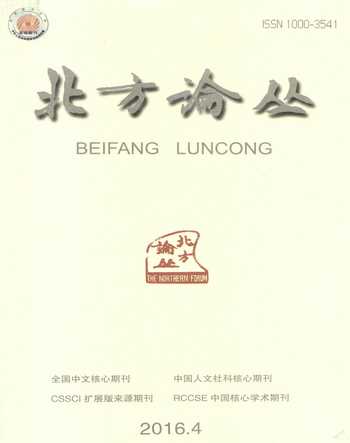康德:基于“理性事实”论证道德法则及其问题
毛华威
[摘要]康德基于“理性事实”论证道德法则主要集中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其论证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将“理性事实”解释为论证纯粹实践理性实在性的起点,试图通过实践理性的实在性论证道德法则;第二,把“理性事实”理解为道德法则的意识,试图通过道德法则的意识来说明道德法则。虽然康德基于“理性事实”对道德法则的论证有可取之处,但这种论证仍然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一,道德法则自身的实在性如何得到合理解释,除非能够提供进一步的说明,否则康德难逃独断论的嫌疑。其二。如果不能证明从道德法则的意识可以推论出理性事实,那么这一主张显然是没有意义的。
[关键词]康德;理性事实;道德法则
[中图分类号]B5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4-0107-05
一般而言,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对道德法则所进行的演绎论证,很难说明由自由如何演绎出道德法则来。康德也注意到了这种困境,他在《实批》中说:“道德法则的客观实在性不能由任何演绎,由理论的、思辨的或者得到经验性支持的理性的任何努力来证明”。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康德放弃了这种演绎论证的方法,而改用其他的论证理路?如果说,道德法则的客观实在性不能由演绎来证明,那么康德为什么还在《实批》中设立诸如“纯粹实践理性诸原理的演绎”等内容?
一、从“理性事实”向道德法则的论证
通过比较《纯粹理性批判》和《实批》关于原理演绎的论证,我们不难发现,康德认为,尽管两者都是称为“原理演绎”,但两者在本质上是有差别的。其原因在于,人是有限的存在者,人的认识能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达到对无限完满事物的认识。所以,对于《纯批》中的演绎,我们可以预测到它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但《实批》中关于道德诸原理的演绎,我们却无法进行有效地预测。从哲理上看,知性的诸原理和经验对象相关,经验对象按照自然规则被统摄在知性范畴中,从而知性可以把握经验对象。这样一来,知性的诸原理虽然是先天的,但人们可以通过经验对象来印证该原理。然而,在道德实践领域,我们却不能像经验界认识知性原理那样认识道德法则。因为道德法则是独立于经验而实存的,它完全脱离经验界,所以,道德法则涉及的认识对象并不能在经验中找到,它本身就是对象得以存在的根据。因此,有学者认为,康德虽然在《实批》中提到演绎一词,“可能只是在强调一个重要的可能性,即他现在相信我们无法实现这一演绎”。
康德确实认为,通过演绎证明道德法则的实存性是有困难的,但这是否表明康德完全放弃了演绎论证的方法?通过《实批》可以看出,康德并没有放弃演绎论证的方法,而是表现出对这一方法的依赖。“取代徒劳地寻求对道德原则的这种演绎的,是某种别的东西,而且是完全荒谬的东西,因为它反过来自己充当一种玄妙莫测的能力的演绎原则……自身不需要任何辩护理由的道德法则不仅证明了自由的可能性,而且在认识到这一法则对自己有约束力的存在者身上证明了它的现实性。”由此可见,康德并没有放弃对道德法则的演绎证明,他认为,先验自由是道德法则得以成立的基础,而道德法则是认识先验自由的前提。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自由的来源,那么康德会说,自由就内在于人的理性本性之中,对于它的来源,人类的认识能力达不到对它的认识。对此,学者贝克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康德在《实批》中所使用的“批判”一词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康德通常所使用的批判的否定含义;另一方面,则是含有肯定意义的使用,即“除非是纯粹的,实践理性才能是立法的”。众所周知,康德写作《实批》的目的不仅仅为了在经验界批判实践理性,更重要的是证明纯粹理性是实践的、是立法的。用康德自己的话说,必须“完备地说明实践理性的可能性、其范围和界限的原则”,因此,对实践理性批判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给出道德法则的过程,即说明实践原理的有效性、可能性和作用范围。所以,贝克认为,这个过程,“就像理论理性中给自然立法的基本原则,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被揭示出来那样”也是积极肯定的。由此看见,《实判》中的批判一词,包含肯定和否定双重含义,换句话说,即便是不通过演绎论证方式,《实批》也具备完全的论证过程。不仅如此,康德认为,实践理性批判是对《奠基》论证中的深化,而且在不同程度上解决此前论证中的问题。
如果说,康德在《实批》中提出不同于《奠基》里的论证方式,那么这种论证方式是什么?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学界历来存有争论。争论的原因在于,康德在《实批》中提出“理性事实”的概念,并且对“理性事实”的含义表达模糊不清。有些学者认为,康德“理性事实”概念本身隐含着矛盾,“如果理性被定义为一种先天的认知能力,那么就很难看出它如何包含任何事实的东西”,因为事实性应当属于经验领域,而理性则要求认识的纯粹性。不难看出,康德所说的理性事实,我们既不能证明,同时也不能怀疑,显然它带有明显的本体论格调。正因如此,人们可能会认为,康德道德理论仅仅依赖一个先天事实,致使康德被一些批评者们指责为,背离了最初的立场,陷入了直觉主义。另一些学者认为,康德理性事实的主张是一种独断论,理由是他在后期相关著作中宣称,“他的实践哲学是独断的,并且只有他的理论哲学才能被称作批判的”。哈贝马斯也指出,康德基于理性事实推导出道德法则的论证是不充分的,把理性视作为道德主体的先验能力强制性地支配着人的道德实践,并不能得出人遵守道德法则的自由本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康德在《实批》中的论证方式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理性事实含义的认同。虽然康德基于理性事实的论证,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和批评,但有些学者依然对这一论证抱有很大信心,他们认为,理性事实概念非但不是独断的,而且之后的演绎推理也不是权宜之计;康德通过理性事实的概念表明:实践理性批判不仅阐明了道德法则和自由的真实性,而且这种替代此前演绎论证的策略是成功的。他们之所以得出这样结论,是因为“纯粹理性能够是实践的,亦即能够独立地、不依赖于一切经验性的东西来规定意志——虽然这是通过一个事实,在其中纯粹理性在我们这里表明自己实际上是实践的,亦即是通过理性规定意志去行动所借助的道德原理中的自律。”
综上所述,对康德《实批》中论证理路的争议,无非是围绕着“理性事实”展开的。为了澄清康德这一论证理路,我们不得不考察“理性事实”这一概念的含义。
二、“理性事实”与道德法则
在《实批》中,我们不难发现康德对“理性事实”的表述:“通过一个事实”、“仿佛好像是一个事实”等,对于具体的事实到底是什么康德并没有给予明确的定义。这样一来,无疑造成了我们理解这一概念的难度。然而,纵观《实批》不难发现,康德所谓的理性事实大体包含六种含义,它们分别是:道德法则的意识、意志自由的意识、道德原理之中的自律、道德法则本身、一个不可回避的意志规定和某些行动的前提。
按照贝克的解释,理性事实的六种含义最有可能的有两种:第一,理性事实作为道德法则;第二,理性事实作为一种道德法则的意识。前者无非是说,“道德法则尽管没有提供希望,但却仍然提供了一种从感官世界的一切材料和我们的理论理性应用的整个范围出发都绝对无法解释的事实,这个事实指示着一个纯粹的知性世界,甚至积极地规定着这个世界,使我们对它有所认识,亦即认识到一种法则。”由此可见,在《奠基》中作为演绎道德法则的结果,在这里直接被当作论证道德法则的前提和条件。贝克宣称,“唯有一个通过理性自身被给予理性自己的法则,才能够成为被纯粹理性所知的先验之物,并成为给予纯粹理性的一个事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克认为,康德所说的理性事实只能是道德法则,因为在康德那里,纯粹理性的唯一事实必须是先天的。后者理性事实作为一种道德法则的意识,无非指我们具有道德法则的意识这一个事实,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从道德法则的意识中直接得出道德法则。在此基础上,贝克指出,理性事实的两种含义有很大的区别,它们关系到康德论证道德法则的成败。第一,理性事实作为道德法则是《实批》论证道德过程的前提和条件,这是没有争议的。第二,理性事实作为道德法则的意识,它仅仅表明我们具有道德法则的意识,并不能直接说明道德法则的实存性。换句话说,从道德法则的意识之中,推论不出道德法则本身来。然而,这一点却是“康德论证成败的重要环节”。显然,证明道德法则作为理性事实是有困难的,也即从道德法则意识的实在性,推导不出道德法则作为事实的结论。此外,道德法则作为先验事实,很难让人们接受。因为康德在《纯批》中,明确宣称人不具有认识先验事实的能力,所以,道德法则作为理性事实的主张很容易遭到人们的否定。如果说,理性事实的定义指的是它作为先验事实,那么这将意味着我们无法再进一步的对它做出解释。
然而,贝克认为,“纯粹理性的事实”有可能被解释为“给予纯粹理性的事实(fact for Pure reason)”和“关于纯粹理性的事实(fact of pure reason)”两个不同含义。其中前者指“某个事实作为客体对象被纯粹理性直接所知”,而后者指“存在着纯粹理性”,它作为一个事实“被理性自反性地(reflexively)知道”。当我们将道德法则解释为“给予纯粹理性的事实”时,由于人类并不具有先验直观能力,因此,道德法则不可能以一种直观客体的方式被理性所了解。
尽管通常所说的事实,人们只能通过经验的或者先验的直观获得,但人类作为有限的存在者必然缺乏先验的理智直观能力。因而道德法则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事实”,康德认为,道德法则“独立地作为先天综合命题把自己强加给我们,这个先天综合命题不是基于任何直观,既不是基于纯粹的直观也不是基于经验性的直观”。所以,贝克主张:“道德法则是一个自返的事实,而不是直观的事实”。显而易见,这里的事实根本不需要通过直观方式获得,是纯粹理性自己“给予”自己的一个事实,或许,康德因此才主张它“仿佛”是一个事实。
毋庸置疑,贝克的第二种解释比较符合康德哲学本身的立场,康德认为,在实践的意义上,不仅超验客体可以获得实在性,而且先验的道德知识也具备实在性的特点。因为“一种经验性上无条件的因果性的概念在理论上虽然是空的(没有适合于它的直观),但毕竟总还是可能的,并且是与一个不确定的客体相关的,而且取而代之的则是在道德法则上,因而,在实践关系中赋予它意义,所以,我虽然没有任何直观来规定这概念的客观的理论实在性,但它仍然有可以在意向和准则中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现实运用,亦即有能够被告知的实践实在性;这对于它甚至在本体方面的资格来说也是充分的。”因此,在实践领域中,对象的实在性含义,并不是指在经验中确定实存,而是指应当存在的必然性。然而,康德在《实批》中,提出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观点,用他自己的话说:“事情仅仅取决于这个能够会转变为是,也就是说,人们能够在一个现实的场合仿佛是通过一个事实来证明,某些行动无论是现实的还是仅仅被命令的,亦即客观实践上必然的,都以这样一种因果性(理智的、无感性条件的因果性)为前提条件”。显然,康德要表达的意思无非是从“应当”能够推出“是”。但争议的焦点也在于此,“应当”到底能否推出“是”,也即能否把应当的事情或对象(尚未发生)等同于实践上必然的事情/对象。毫无疑问,康德坚信在实践领域,“应当”是能够推出“是”的,也即如果某个对象是被纯粹理性所要求的,那么就存在充分的理由承认它是能够实存的。用康德自己的话说:“如果不承认这种实践意义上的事实含义,命令、义务等道德要求就会丧失约束理性行动者的合理性与权威性。”
此外,贝克认为,所谓道德法则不仅是给予纯粹理性的事实,同时也是关于纯粹理性的事实,所以,康德才把它表述了“纯粹理性能够是实践的”这一事实,它才同时成为给予纯粹理性的一个事实”。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贝克宣称,如果能证明“纯粹理性能够是实践的”这一主张的实在性,那么道德法则就被证明具有康德意义上的事实含义。贝克给出的理由:第一,道德法则只对意识到法则的理性存在者才有效,而只要意识到道德约束力或道德法则,就意味着关于纯粹理性的实践性主张是真实有效的;第二,如果反对第一点,就要反对规范性的基础,“而这就好像试图通过理性来证明理性不存在一样荒谬”。所以,对一个自由的理性存在者而言,必然是法则首先对其产生约束力,理性存在者才能够与之相冲突。由此可见,纯粹理性的实践性主张具有现实性,一方面由于道德法则唯一表达的理性自律,这就等同于纯粹理性是实践的这一内容;另一方面,道德法则“既是关于纯粹理性的、又是给予纯粹理性的唯一事实”。
由上述分析不难得出,贝克在论证道德法则是纯粹理性事实的过程中,第一种观点使用了理性事实作为道德法则本身的含义;第二观点则直接把道德法则的意识当作理性事实来使用。但问题是,道德法则的意识能否直接当作理性事实?如果把道德法则的意识当作理性事实有无合法性?罗尔斯不同意将道德法则的意识直接当作理性事实的主张,他说:“道德法则作为理性的一个观念仅仅是一个观念,和不朽以及上帝的观念一样,它或许缺乏客观实在性,并因此不能被用于任何东西”。按照康德理解,人类的道德意识完全可以支持论证道德法则的合理性,我们不仅可以在《实批》中找到相关论述,而且在《奠基》中,也有类似的证明。唯一的区别在于,《奠基》中所论证的结论,在《实批》中变为论证的前提和条件。所以,理性事实应该“作为理性存在者(reasonable beings),我们意识到道德律是对我们而言最高的权威性和规范性的法则,并在我们平常的道德思考和判断中这样认可它”。换句话说,道德法则作为理性事实,意味着我们意识到它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综上,无论是把道德法则是理性的事实当作论证纯粹实践理性实在性的起点,还是主张道德法则的意识就是理性事实的论证,它们都是基于康德哲学中“理性存在者”的概念进行的。显然,“理性存在者”无疑是康德道德哲学中至关重要的概念,因此,对它的阐释直接关涉到我们对道德学说的理解。
三、“理性事实”论证道德法则的问题
如果说,“理性存在者”在康德道德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问题是,它在康德文本中到底指的是什么?“理性存在者”这一概念在康德整个哲学中又经历了哪些演变?
众所周知,康德在前批判时期,就已经意识到了道德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的关联,他把道德称为一种自由选择的能力(free power of choice),用康德自己的话说,它通常具有“人性和人类的目的,即人性与人类的普遍目的的必要条件”。显然,康德认为,道德作为人的一种义务,约束力来自于人的自由选择的能力,同时这种选择能力和人类的目的相关。换句话说,道德约束力要依赖于人的自我意志。但是,康德早期对于道德主体的解释,倾向于一种理性心理学立场,我们从他早期的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他说:“当我谈论灵魂时,那么我就是在严格的意义上谈论我……因此,通过内感官的内部直观,我意识到我的全部思想”。所以,早期康德对道德主体的理解充满了心理学色彩。不难得出,康德所说的灵魂具有实体(substance)和自发行动者(agent)的含义。可以认为,前批判时期,康德所谓的主体、自我、灵魂等概念,它们的含义基本相同。
具体言之,道德主体作为自发行动者,这个主体“是所有断言、所有思想、所有行动、所有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思维的存在者所传达出的所有可能判断的一般主体。我只能说:我是,我认为,我行动”。因此,道德主体所具有的自发性是绝对的。尽管“我只能说:我是,我认为,我行动”,但这种自发性是无法驳倒的。换句话说,只要道德主体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受原则决定的,意识到自己行为是按照原则主动发生的,那么这就表明道德主体具有了先验意义上的自发性,也即先验自由。用康德自己的话说,“这样一个能够意识到其自身的决定和行动的主体就是具有绝对自由的”。所以,康德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的自由。如果说,人类没有自由,那么意味着所有的道德实践命题都将失去有效性。因此,康德宣称,涉及道德,我们必须将自己设想为处于理性心理学之中,不依赖任何经验,以区别于一般的经验性的实践自由。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预设在我之中有一个自由;我必须是一切行动的第一因(first cause)”。由此可见,即便是我们无法设想自由,但这并不影响自由的存在,因为“自由是我们一切实践行动的一个必要条件”。
毋庸讳言,康德在早期就已经意识到道德主体自由的属性,直到批判时期他对这一自由属性依然青睐有加,只不过做了更加详细的阐述。特别是在《纯批》中,康德说:“道德必然也预设自由(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是我们的意志的属性,因为,道德援引蕴涵在我们的理性之中的、原始的实践原理作为自己的先天材料,而不预设自由,这些原理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了道德不再需要别的任何东西,只要自由不与自己本身矛盾,从而毕竟至少是可以被思维的,没有必要进一步洞察它,那么,道德性的学说就保住了它自己的地盘。”显而易见,道德的基础是自由,自由是认识道德的前提和条件。此外,在“纯粹理性的谬误推理”部分,康德对理性心理学给予了驳斥:“理性心理学中的辩证幻相基于理性的一个理念(一种纯粹的理智)与一个一般能思维的存在者在所有方面都不确定的概念的混淆。”所以,康德认为,理性心理学的思维主体并没有实在性,只是“我把对我经验性地确定的实存的可能抽象与自以为对我能思维的自我的一种孤立地可能的实存的意识混为一谈,相信认识到我里面的实体性的东西就是先验的主体,因为,我在思想中只有一切规定作为知识的纯然形式而当作基础的意识统一性”。在上述对主体的阐释中,康德已经注意到必须要把纯粹理性分为理论应用和实践应用,如果不做区分的话,那么诸如理性心理学的谬误将会再次出现。在康德看来,人作为有限的存在者,既有感受性能力能够对感性杂多产生回应,同时又有理性的能力,可以把感性杂多统摄到范畴之下。因此,人作为行动者同时具有两种品格,一种经验性的品格(empirical character)与一种理知的品格(intelligible character)。“所以这个活动的存在者就此而言将会在自己的行动中不依赖于并且摆脱一切自然必然性这种只在感性世界中才见到的东西。我们关于这个主体就会完全正确地说,它自行开始了它在感官世界中的结果,而不是这个行动在它里面开始了自身”。因此,可以说,实践视角提供了说明这个主体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尽管康德试图通过“理性存在者”的两种品格来阐明自然属性与自由属性,以及自然法则和自由法则能够在一个主体身上同时运行,但正如贝克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阐明仍然存在问题:第一,如果将道德法则是理性的事实当作论证纯粹实践理性实在性的起点,这表明我们接受康德主张的“道德原则既不具有也不需要一个演绎”的观点。但问题是,道德法则自身的实在性如何解释依然存有争议,除非我们能够提供进一步的说明,否则康德难逃独断论的嫌疑;第二,如果把道德法则的意识理解成理性事实,这一主张或许能够避免上述困境,不过该主张自身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关于道德法则的意识,来说明道德法则和纯粹实践理性的实在性,正如贝克指出的那样,尽管很容易理解,道德法则的意识是一个事实,但道德法则本身的实在性却难以解释。然而,康德论证道德法则的核心就在此处,假如不能证明从道德法则的意识可以推论出理性事实,那么这一主张显然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