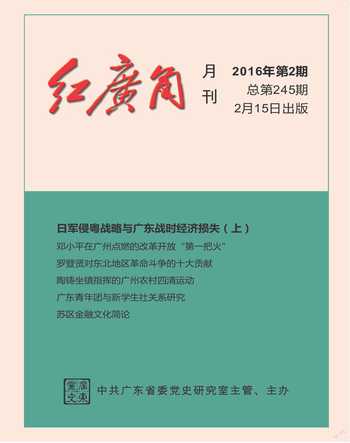广东青年团与新学生社关系研究
沈志刚
【摘 要】新学生社是广东青年团成立的一个外围学生组织。成立新学生社开展学生工作既是党、团革命战略调整的反映,也是广东青年团顺应革命形势的策略性抉择。广东青年团在新学生社的成立、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对新学生社的领导主要通过社中团员为纽带来实现。新学生社对广东青年团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促进了团组织的扩大,也为青年团的后续工作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广东青年团;新学生社;关系
新学生社,原名广东新学生社,是广东青年团顺应革命形势变化而成立的一个外围学生组织。在新学生社存在的三年时间里(1923年6月到1926年6月),广东区党团的学生工作主要通过新学生社开展。目前,已有学者重视对新学生社的研究,但主要侧重于介绍新学生社的历史活动及其历史作用①,而对广东青年团与新学生社的关系研究还未有涉及。本文主要分析广东青年团成立新学生社的原因以及广东青年团在新学生社的成立及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并对广东青年团如何领导新学生社做一番介绍,以就正于读者。
一、广东青年团成立新学生社的原因分析
青年团是从学生运动入手逐步发展起来的,从留存文件中不难发现,青年团的早期工作,主要就是学生工作,正如时任团中央书记的施存统所说,“就本团各地实在情形而说,还是以学生为中心的”②,以至于青年团常被指斥成了“学生团”③。少年共产国际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信中也指出:“你们的革命工作成功大部分在学生界之中,团员也以学生为多。”④相对而言,青年工人农人的工作却进展缓慢,甚至“实未开始”⑤。这种状况反映了早期青年团更擅长做学生工作,并对学生运动已有经验。广东是全国最早成立团组织的地区之一,上述情况在广东也同样存在。据1922年4月维仁致忠夫等人的信中所说:“五一已近,我们应当筹备,此地工人中尚难活动”⑥,同年5月,广州的青年团进行了改组,重新登记的团员有四百多, “我们团员学生居多”⑦。既然如此,便引出一个问题,即改组以后的广东青年团为何要成立一个外围学生组织来开展学生工作,而不是亲力亲为,何必要增加一个中间环节,舍近而求远呢?
时任团广东区委书记的阮啸仙在给团中央书记施存统的信中,曾言明组织新学生社是为“做学生普遍的运动”①。所谓“普遍的运动”即区别于之前一党、一团的“特殊”运动而言。这其中体现出的是首先党、团开展革命运动的战略调整。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便提出社会革命的口号,对任何党派都采取关门主义态度,因此党的活动空间和社会影响力受到很大限制,党组织发展缓慢。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党的早期领导人逐渐认识到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想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首先必然要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因此,中共二大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制定了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青年团的工作也紧随党的方针迅速做出调整。中共三大进一步制定了与国民党合作、开展国民革命的方针。广东青年团改为从事“学生普遍的运动”,便是上述的战略调整在学生工作中的具体反映。
但是,即便是青年团调整战略为从事一般性的普遍学生运动,也完全可以亲力亲为,并不必然要重新成立一个外围组织。广东青年团成立新学生社来具体负责学生工作的开展,也有其策略性的考虑。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便“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并深入工人中去做群众工作。尽管最初人数很少,“却立刻使旧社会一切腐朽势力深感恐慌”,以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处在萌芽状态时就被斥为“过激主义”,而“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所以中共甫一成立,便“不得不处于非法的秘密状态”。②加之刚成立的中共由于斗争经验不足,过早提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革命口号,不仅使应者寥寥,更被视为“其祸甚于洪水猛兽”。
青年团是一个群众性组织,处于半公开的状态,早期团的组织和影响力都强于党。但也正因如此,党的许多工作都由青年团出面执行③,这反过来却造成“这一年来本团几乎绝对没有做自己独立的青年工作”④。这一时期的党、团关系亲密,甚至职权交叉,人事重叠,使得青年团带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并曾一度被反对者攻击为“中国共产党的机械”,甚至导致一些团员“竟因此退出本团”⑤。故而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发文疾呼,“我们须认定本团不是一政治组织”,“我们尤其不宜使我们政治色彩太浓,使青年望而生畏”⑥。广东的学生,“多半属于资本家或中产阶级的子弟”,广大的贫苦青年,对于现在教育“早已无丝毫享受的机会”⑦。因此,在这样的学生群体构成中,以中国共产党或者青年团的名义直接开展工作,有很大的阻力。故如阮啸仙所言,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好拿S.Y.名义做公开运动”⑧。
而且,陈炯明叛变以后,“诸事消沉得很”⑨,青年团的工作也不似从前,“只能半秘密进行。珠评(按:《珠江评论》)已被查禁,团址因被监视已迁”⑩,而且“同志既惹起注意,活动稍形秘密”,团的工作与发展均受到很大影响。因此,恢复活动后的青年团,痛定思痛,吸收公开活动的教训,从而增加中间环节,也可说是经验的总结。
即便是增加开展学生工作的中间环节,实行间接领导,也本不必重新成立一个新组织,毕竟开展学生工作的首选平台,应是学生联合会。正如团一大作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关系之决议案》所指出:“学生联合会为学生的结合,为我们在学生中宣传主义的最好场合”。①广州的学生联合会成立较早,在五四运动期间,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此时的广州学生联合会却以联络感情,切磋学问为宗旨,“屡次开会都不足人数,会务无法进行”,“该会实不能成为学生群众团体,且缺乏指挥能力,毫无用处”②。在这种情况下,“粤区议决以S.Y.学生同志做中坚,组织‘广东新学生社,纠合各校革新分子,来做学生运动”③。
综上所述,新学生社的成立,是历史的合力促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从国共合作以后的两党关系来看,足见这一策略的智慧。但是广东青年团在议决成立新学生社时,有无预见到国共合作可能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新学生社的成立及发展沿革
1923年初,陈炯明被逐出广州,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重掌广州政权,广州的革命形势逐渐转好,这是广东青年团的学生工作得以开展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活动开始迅速恢复,前已述及,新学生社是团广东区委以学生中的团员同志为中坚成立的,因此,早期新学生社的骨干力量俱由青年团输送。
1923年5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改组成立,阮啸仙、刘尔嵩、郭瘦真等人当选为委员,周其鉴、罗琦园、杨匏安为候补委员,阮啸仙为书记。④阮啸仙、刘尔嵩、周其鉴等人曾就学于广东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他们是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学生领袖,具有丰富的学生运动经验。广东的学生运动在五四以后逐渐消沉下去,早先的五四领袖如张启荣等人很快被军阀收买,在学生中失去了威信,后起的阮啸仙、刘尔嵩等人便成了五四以后广东学运的中坚分子。
1922年,阮啸仙从甲工毕业,创办了爱群通讯社,社员主要是甲工的学生。该社主要通过组织宣传新文化、学生运动的资讯或文稿投向各大报刊,获取稿费以维持运转。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进步稿件“多不为黄色刊物所采纳,所以稿费不多”⑤。爱群通讯社由于经费不足,维持困难,曾被社员戏称为“无饭社”,但在当时它却是党、团以及工会活动的大本营。
爱群通讯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新学生社的前身。所谓“新学生”,便是区别于受封建传统教育的旧私塾学生而言。新文化运动后,当时很多杂志、社团都以“新”立命,诸如《新青年》、《新潮》、新民学会等等,“新学生”这个词也不少见于时人。在五四运动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就曾经有过新学生社,并有《新学生》杂志创刊发行于1920年1月15日。此《新学社》曾刊有署名谪瀛的《我对于<新学生>的感想》一文,对新旧学生有所界别,“旧学生的根本错误就是:不知求学为什么?……只知糊糊涂涂随着人家去求学”;而新学生“对于从前的死思想、恶习惯,要完全打破……对于未来社会要负完全责任”⑥。同期还有《“新学生”做的事》一文,主张“男女教育平等,开女禁、废除考试制度、实行学生自治”⑦。可见此新学生社主要致力于文化运动,所涉及也主要是教育的内部问题,带有“和平派”①的倾向。
广东青年团主持成立的新学生社,虽然沿用了“新学生社”的名号,创办的刊物也同样叫《新学生》,但二者已有截然不同。后成立的新学生社,以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纲领,并将学生视为“政治方面的一种新革命势力”,认为“这种势力是大可以救济垂毙的中国的”,进而号召青年学生做“代表全国国民的领袖”,引导劳苦群众来进行国民革命运
动,②充分体现了其革命性。
前已述及,广东新学生社是以团员中的学生同志为中坚成立的。而此时团员中的学生同志多来自党、团工作基础较好的甲工、高师、公立法政、省一中等十所学校,“社员一百十人,遍十校,都是各校很活动的分子,而S.Y.居多数”③。新学生社成立初期,其组织小,人数少,影响弱,鉴于新学生社的实际力量,团广东区委指示新学生社先靠已有的成员,逐渐打开局面。
第一,先“纠合各校革新分子”,抓住关键人物,“整理或组织校学生会”,以学生来影响学生。再以一校为据点,逐渐向外活动,以学校来影响学校,将新学生社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第二,从学校革新及学生自治运动入手,切实为学生本身利益而奋斗,并以此为切入逐渐将学生团结在周围。例如,一次某校发生学生与校长争教育经费风潮,粤区即令该校同志及新学生社员合作,尽力设法援助并最终取得胜利,该校学生感觉到“我们为学生谋利益之非虚语而发生好感”④。第三,凭借已有力量,参与各种社会政治活动来扩大影响力。新学生社刚一成立,便立即投入到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中,负责诸如登记党员、组织演讲队、起草宣传大纲,以及建立区党部、区分部等工作;再如,新学生社在“其他各团体十分放弃,广州学生会也不尽力”⑤的情况下,毅然独立联络了“中国广东国民外交后援会”举行示威运动,支援孙中山收回“关余”的斗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新学生社的声名逐渐在学生中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认识新学生社。
草创时期的发展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到1924年3、4月间,“新学生社日见发展,很能得学生群众同情。”⑥“该社在广州方面已取得学生监督地位,并扩充到各县镇去,社会上也颇得群众同情。”⑦新学生社在广东学生中地位的变化,也可以从稍后发生的教会学校反教风潮中得到印证。1924年4、5月间,广州“圣三一”学校的一些进步学生想要成立学生会,但遭到校长的严令禁止和辱骂。该校学生难受其辱,遂发动反教风潮,值得一提的是,爆发风潮时,在“该校并未有同志”的情况下,学生“竟来新学生社投诉,请求援助”⑧,可见新学生社在当时学生中的影响力之一斑。
经过一年多的发展,新学生社的影响渐渐覆盖广东的各县、镇和乡。为响应邻省各地请求组织分社的要求,广东新学生社于1924年11月23日召开大会,决议将“广东”两字删去,改称“新学生社”。自此,新学生社的活动遂扩散至邻省,甚至香港也成立了分社。大革命初期,“党在广东青年学生中的工作主要是通过新学生社来开展”⑨。
三、广东青年团对新学生社的领导方式
新学生社是当时广东青年团的外围组织,这从留存文件以及当事人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均可互为佐证,并无疑义。但是,广东青年团对新学生社如何实行领导,却都语焉不详,未有资料对此专门介绍。笔者从留存史料及当事人回忆文章中,尝试对团广东区委对新学生社的领导方式做一番梳理。
新学生社在公开场合,只是“主张国民革命的一个纯粹学生团体”,“本社的团体是完全具独立的性质”①。在其颁布的纲领和征求社员通启中,以及以新学生社的名义参加的各种公开场合,都是以国民革命为号召,希望有志于国民革命的青年学生加入。而且新学生社在公开名义上并非团广东区委的下属机关,新学生社也不是以共产主义公开建社,新学生社在台面上仅仅是左派学生组织的形象。因此,新加入的青年学生并不清楚新学生社与广东区党、团组织的关系,他们加入的初衷只是为了国民革命的目标。这样一种组织形态,就决定了广东青年团对新学生社的领导只能是幕后的、间接的。因此,笔者认为广东青年团对于新学生社的领导,主要采取人事上的“组织领导”,而非思想上的“主义领导”。
新学生社刚成立时,成员基本是青年团成员,“非S.Y.成员不甚多”②。刚开始招募的新社员,大都是“S.Y.学生同志”发展,这些同志开展学生工作的经验丰富,社会活动能力很强,对新入社员能发挥领导权威。因此,这时团广东区委对新学生社的领导主要通过团员领导社员来实现。
新学生社逐渐发展壮大以后,该社于1923年12月底进行了改组,选出第二届执委会,作为新学生社的领导机构。选出的七名委员中“同志五人——啸仙、善铭与赖玉润(高师)、杨石魂(工程)、卢季循(一中,新入),非同志二人——郑尘(法大)、沈学修(女师),俱是女生”。③这里不难看出,在执委会中的青年团成员,不仅数量上占多数,而且也相对“资历深厚”,青年团完全可以实现对社执委会的领导。1924年11月新学生社召开扩大改组会议,在改组后的执委会中,“我们同志(S.Y.)在中可以完全指挥,并实际指导工作”④。
新学生社“组织法与S.Y.同”,下设分社、支部、小组,在广州有总社,在广州工作基础较好的学校里设有支部,其它各地的有分社,“支部有支书,小组有组长”⑤。值得注意的是,总社对下属分社、支部的领导作用也是通过内中团员为纽带得以实现的,换句话说,如果分社或支部内无团员,或者团员不能发挥核心领导作用,那么总社对分社、支部的领导作用便很难发挥。例如海丰新学生社分社由海丰原来的新生社改组成立,“学生的权柄操在新生社的手里”,但是“新生社不受我们团体的指使”,“他们包办了海丰新学生分社,被校长及长辈先生所利用还不自觉”⑥,因此总社对海丰分社就不能起领导作用。再如中山县的新学生社支部,“没有C.Y.做中心指导,其结果大不好,极阻碍中山的青年运动”⑦。
诚然,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因为不单是总社,下面各县市的分社、支部一般也都由当地团组织主持成立。但是,这少见的情况却从侧面反映出青年团对新学生社的重要作用。综合上述情况,不难总结,广东青年团对新学生社的领导方式为:团广东区委领导新学生社执委会,执委会领导新学生社各地分社(支部),领导作用的发挥通过执委会及分社(支部)中的团员来实现。
四、结语
广东青年团顺应革命形势,提出成立外围组织新学生社来开展学生工作的策略,极大地促进了广东区党、团学生工作的进行。广东青年团对新学生社的成立到发展壮大,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新学生社也对广东青年团的发展有着积极的贡献。当然,由于时代所限及一些主客观原因,新学生社也逐渐暴露出太出风头、包办学联等问题而不得不被整顿乃至停止发展。但是,新学生社在其存在的三年时间里,其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笔者认为,新学生社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对广东青年团的发展有所助力。
第一,新学生社直接为广东青年团输送了人才。新学生社作为团的外围组织,也承担着为青年团物色、培养、输送人才的任务。新学生社刚成立不久,新会分社的负责同志就十分注意将“富于革命性而可造就的分子”,“使之加入S.Y.”①。在新学生社的发展过程中,团广东区委也十分重视训练新学生同志,以“渐渐引导他们到我们团里来,切实为无产阶级来奋斗”②。到新学生社因为形势变化,行将停止发展之际,团广东区委进一步指示:“应尽量在社员中吸收同志,以扩大我们的组织,不可使一般进步青年学生停顿在新学生社中。”③赖玉润(先声)对发展团员的情况也做过如下说明:“普通学生先吸收入社,经过一时期考察和锻炼后,够条件的再吸收入团,确实进步的学生,亦有直接吸收入团的。”④新学生社对广东青年团发展的贡献也可从下面的数字统计中得到证明:1924年3月份,广东的团员总数一共是131人,其中学生93人,约占总人数的71%⑤。到1926年6月底,团员总数(此时已改称共青团)已达2248人,学生1053名,约占总人数的47%⑥,新增团员中的学生数量增加了不止十倍。
第二,除了直接向广东青年团输送人才之外,新学生社通过积极努力的活动,也间接地促进了青年团工作的开展。首先,新学生社发动广大学生参与国民革命,提高了青年学生的思想觉悟,为新学生社消亡以后青年团的后续学生工作奠定了基础。新学生社通过宣传动员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如支持收回“关余”案、“非基督教运动”、促进国民会议运动等,逐渐将青年学生发动起来,引导他们走出校园,参与政治活动,打破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观念,使青年团后续的学生工作减小了阻力。其次,新学生社引导青年学生走向工农,提高了工农的思想觉悟,促进了青年团工运、农运的开展。新学生社主办的广东平民教育运动,从教员到教材都由新学生社选定,使得广大的青年学生得以与工农直接接触,不仅促进了工农文化水平的提高,也提高了工农的思想觉悟,这大大促进了党、团工运、农运的开展。最后,成立新学生社开展工作的外围工作法,为青年团积累了学生工作经验。新学生社在开展学生工作的过程中,固然存在很多问题,并最终在统一学运的口号下,团广东区委决定“停顿其工作”,使之“无形中消灭了”⑦。但是,这种成立外围组织开展工作的思路为广东青年团之后的工作提供了借鉴。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