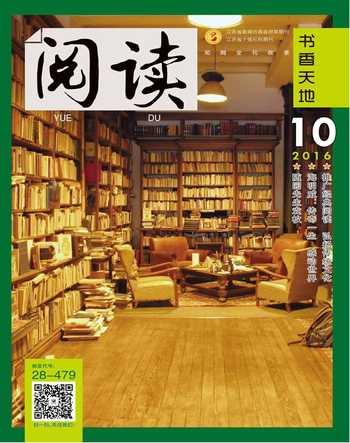你一开口,就暴露了等级和阶层
◎河南人、东北人惹了谁?
郭德纲的相声里,特别爱开这样的玩笑:街头,一位穿着人时、美艳动人的金发女郎,突然转头,飘出一口浓重的河南口音:“姐,恁长类真齐整!”于是满堂捧腹大笑。
还有,网友们调侃的姚晨模仿福建人和东北人玩儿成语接龙:心心相印——印(认)贼做父——父(互)相伤害——害(还)想咋地!
首先,严正声明,我们从来不认为,哪一种方言生而就应该被调侃或者嘲笑,相反,今天我们想揭示的正是这种调笑的背后长期存在的刻板印象——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娱乐圈的全民港台腔或者春晚小品30年不改的棒子茬粥味儿吗?
其实,口音歧视与等级刻板印象,绝非中国独有。历史上,为了寻觅向上流动的机会,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往往模仿上层口音。但20世纪后期,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英美国家的上层开始主动增加下层口语词汇,一些人专门请了教师,调整自己的高贵口音。
◎“欲入上流,先仿其音”
口音歧视由来已久。古罗马时期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西塞罗,出生于罗马东南一百公里外的Arpinum,西塞罗对此非常避讳,极度推崇罗马城里贵族口音的拉丁语,盛赞其为“没有错误、无比悦耳”,而评价乡下口音极其“粗鄙”。
在古代中国,同样有颇多有趣的例子。南北朝时期,北方南渡的士族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中说:“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颜之推的意思很明白,闺秀家家的,要是说一口糙话,将来怎么见人?
更有意思的事出现在武则天时代。
为了打击士族,武则天起用了不少寒门出身的酷吏,他们的寒门口音相当受鄙视,士大夫阶层纷纷撰文取笑。
《大唐新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侯思止出自皂隶,言音不正,以告变授御史。时属断屠。思止谓同列日:“今断屠,宰(鸡云)圭(猪云)株(鱼云)虞(驴云乎)缕,(俱云)居不得(吃云)诘。空(吃)诘(米云)弭(面)泥去。(如)儒何得不饥!”侍御崔献可笑之。思止以闻,则天怒谓献可日:“我知思止不识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献可俱以鸡猪之事对,则天大笑。释献可。
这位侯官爷的方言之土,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吧。
近代以后,有声传媒的流行,使口音的重要性突显。不少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口音费尽心机,尤其是政客。传媒高度發达的英国,政客的口音造成的影响被无数倍地放大。
撒切尔夫人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步在英国政坛崛起。但她一口林肯郡口音的土话常遭到无情的攻击。有评论员恶评她像“一只从黑板滑下的猫”。当时,撒切尔夫人已年过50,不得不请了皇家国立剧场的发音教练为她纠正口音——效果很不错,天资聪颖的撒切尔夫人几年后就摆脱了林肯郡土话,开始以一口英国上层流行的RP音纵横政坛。
现代中国的政坛,人们也注重遮掩口音上令人难堪的联想。
如成长于大院的特殊子弟,虽然讲北京话,但会控制口音中儿化音出现的频率,以和平民百姓的北京土腔拉开距离。电视采访更能说明口音的社会压力——接受采访时,多数官员无论如何也要憋出普通话来。
◎从模仿上层到学习下层
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美却出现了一个稀奇的变化——原本高高在上被众人模仿的上流社会,开始模仿平民口音。
英语世界上层口音的代表——女王音就很明显。
每年圣诞节,英国女王都有面向全国的致辞演说,伊丽莎白二世已演说超过50次,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她使用的都是典型的英国王室口音。近期,则越发向她的臣民靠拢——最显著的变化:trap的元音/ze/越来越接近/a:/,前者是高贵的贵族用法,后者则偏向平民。
女王的子孙们也是如此。威廉王子结婚时,已经有人指出他口音中的“贵气度”尚不如出身平民的凯特王妃。哈里王子的口音也很不堪,简直和伦敦小地痞差不多。
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出身上流家庭,就读于著名的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从小就说一口上流口音。但他和撒切尔夫人一样,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口音——只是方向与撒切尔夫人相反,开始模仿各种下层口音和乡村土语。
美国也有类似的现象。
相对旧大陆,美国的社会基础较为平等,并未形成欧洲式的贵族阶层,社会阶层流动也相当剧烈。它的上层社会属于美国东北的新英格兰地区,那些最初来到新大陆的英国新教徒们,其家族在美国生活的历史有三四百年之久。他们被称作“波士顿婆罗门”,历来是波士顿社会结构中最高的一层。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波士顿婆罗门也很简单——听口音。波士顿婆罗门们有自己独特的口音,在波士顿四百年历史中,这种口音始终是上流社会的重要标志。
20世纪后期,波士顿婆罗门口音却遭遇了一场大危机,越来越不受欢迎了。不但一般的波士顿人无心模仿,不少波士顿婆罗门,尤其是有志于投身公共事务的人,也极力避免被人听出。粗糙统计,今天仍使用这种口音的人数不到千人。
现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就出身于一个波士顿婆罗门家庭。1980年之前,他的讲话录音都是纯粹的波士顿婆罗门腔调,从政后,他渐渐抛弃了波士顿婆罗门口音,而学了一口美国普罗大众的通用美腔。
前总统小布什则做得更绝,能一整套地改造自己的形象,出生于东北部康涅狄格州的他,放弃继承本来高贵的波士顿口音,而选择了成长所在地德州口音,生生地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南方德克萨斯州牛仔。
◎口音背后的政治学
大众传媒的扩张,以及不断完善的民主形式,让口音问题变得非常微妙——说到底,口音的改变是一个取悦于人,向固定阶层靠拢的过程。
20世纪初之前,英美民主仍局限在较高的阶层,政治家并不需要向民众展示自己的形象。本质而言,下层模仿上流口音是为了让别人觉得自己更加聪明、优雅、可信,从而让自己更有可能获得成功,他们对于上升的希望,都寄托在眼前这些谈吐优雅、世代高贵的贵族身上。
20世纪80年代之后,权力的天平发生改变,政治家们不得不在无处不在的媒介中,至少在明面上讨好民众,所以他们改变了长期沿用的口音。尽管上流口音往往和聪明、优雅、可信、富裕等特质联系在一起,但它同时是冷漠和距离感的象征。使用更为贴近下层的口音,能有效地获得选民的好感。
二战后,西方传统阶层的分布受到冲击,跨阶层交往频繁。出身上流社会的人需要和各类阶层打交道。投票式民主制度下,政治人物取得占据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下层的支持尤为重要。因此,出身上流社会的卡梅伦、布什、克里等人要把自己的上层痕迹抹去,不惜打造粗鄙的西部牛仔形象。
中国的口音取向更多是地域性的——春晚语言类节目就体现得非常明显:衣着光鲜的正面人物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北方口音出现于农民、保安、清洁工、民工等角色,至于各种南方普通话,多为“小男人”“娘娘腔”“骗子”所使用。
人们会将地域的经济、文化、政治实力排名带入到口音的等级中,形成心照不宣的刻板印象——假如听到某福建腔的人在电话中跟你讲述一个宏大的商业计划,很多人都会在第一时间挂断电话。同样,正式的学术会议中若出现赵本山式的东北腔会令人立刻对该学术会议的质量产生严重的怀疑。
20世纪90年代,香港电影和香港商人长驱直入,粤语受到普遍青睐。而21世纪后,大陆的投资占比越来越大,不少香港人也调整舌头,学习普通话变得更加实际。
但是,受中国政治因素的影响,部分经济落后地区的口音却长期在荧屏中占据高位。主旋律电影中,不管其他配角家乡在哪里,都只能讲一口没有个性的普通话,只有个别领导人,会潇洒地跳出规则外,一口方言贯穿始终。
(摘自微信公众号“群学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