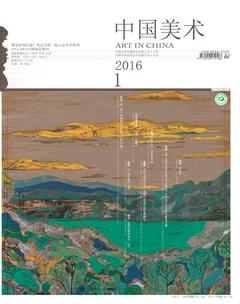观念之下的消解、想象与批判
“我更有兴趣去电影院而不是美术馆去观看艺术。”
“尽管我从来不承认我的作品具有女权主义思想,或是政治宣言,但事实上,我的每一件作品都是以一个处在现实文化中的女性角度进行观察的结果。”
辛迪·舍曼
作为女性艺术的代表人物 美国女艺术家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的成就在西方后现代艺术中举足轻重,她一贯地使用特定美术的、电影的或流行媒介作为参考的框架——B级电影、杂志的插页、时装、童话故事、古典绘画、色情作品、超现实主义摄影和恐怖电影支撑
她总是用幽默的手段、强烈夸张的寓意转化角色。在她的影像中,真实与虚拟经常混杂在一起,她狂热地用怪异形式嘲笑那些被夸大的既定类型的形象,创造出令人震颤的荒诞作品。她的作品中多表现出来的女性主义色彩,为她的摄影带来了不同一般的文化批判意义。
一、观念艺术与摄影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中期,观念艺术在西方风行一时,艺术家使用物质、语言和照片来提示有关艺术与世界的想法与定义,质疑既成的体制化了的艺术制度、艺术市场、艺术与艺术作品的本质。绘画之死,新的艺术游戏规则而非美学规则正在静寂中酝酿出一个世纪的暴风骤雨。同时,从观念的角度把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作为一种新的表现方式,也受到注目。虽然这些新的表现方式已经不再是传统架上绘画式的表现,但作为作品,毕竟需要一种鉴证与传播的手段。此时,摄影作为一种记录方式被运用到观念艺术中去。摄影与这些表现方式的结合,既引起了艺术传播方式的变化,同时也引起了对于摄影自身的再思考,观念摄影艺术作为一种手段为艺术家与评论家开辟了表达与探讨的新领域。
后现代艺术是对现代主义强调纯粹、理性的断然拒绝,它质疑唯新是求的正确性,对传统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它以开阔的视野、丰富多彩的艺术实践来证明创用之于艺术的重要,在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反思传统、丰富对艺术史理解的契机。作为后现代艺术一支的后现代摄影,一般被认为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其时间下限则可以一直延续至今。
观念艺术、后现代艺术以及后现代摄影理论的成熟为观念摄影艺术家的成长开辟了道路,生于20世纪50年代、成长于70年代的辛迪·舍曼就是其中的一位,她经历了摄影艺术地位的提升阶段。在60年代中期以后,艺术家们开始表现出对摄影这一艺术手段的浓厚兴趣,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将摄影纳入自己的艺术表现中,在客观上起到了提升摄影艺术地位的作用。艺术家对摄影的介入使得摄影与美术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作为绘画出身的舍曼参与到“艺术家——摄影家”这一共同体存在的潮流中。进入70年代,摄影表现的虚构性得到重视,一些摄影家开始尝试运用各种手法将自己的经验、想象和欲望表现出来,自拍作为一种能极好地表现艺术家本人创作意图的手法深受青睐。舍曼曾说:“我有时也意识到自己并不确切知道从照片中得到什么启示,因此很难明确要别人怎样做,所以把这种启示告诉别人更是难上加难。当我自己来工作时,我只用一面镜子来召唤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直到我看到它。”但她曾经郑重声明,她的摄影作品应该归属于观念艺术范畴,观念主要表现在对作品的分步处理而形成的系列之中。
二、舍曼式“作者之死”的消解意义
法国当代文坛领袖罗兰·巴特曾提出了“作者之死”的命题,他认为读者诞生的代价就是作者之死。“作者”的概念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以及英国经验主义、法国理性主义对个体与人性发现的结果,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实证主义发展出来的典型的现代神话。人们在日常文化中能找到的作品意象,都集中在作者方面,集中在他的个人、他的历史、他的爱好和他的激情方面。显然这一“作者”的概念与上帝、创造者、自我、意识、认同等概念是密不可分的。
舍曼关于《无题电影剧照》系列作品的创作,试图在消解作者意识的存在,她把自己装扮成处在特定景致中的熟悉但却令人难以辨认的电影中的女主人公。她利用自拍的形式,实际上是把自己融化在各种不同的角色中,比如,二流女星、家庭主妇、职业妇女、豪门怨妇,以消除自己作为主导者的面目,让观者去解读领悟。这些看似刻意的装扮实质上却是一种消解,因为当一个人去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且所采用的是大众传媒中令人熟悉的表情与形象时,就把个人与时代的博弈感呈现在观者的面前,个人已经消失,作者已经消失,剩下的就是一个大众传媒时代带给我们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当我们面对这些看似熟悉却又无法对号入座的作品时,舍曼的自我隐藏与消失使人们注意到大众传媒塑造女性形象的单一化和模式化,这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巧妙的反思的契机。因此,舍曼式的“作者之死”并非真正的消解,而是为了给与观者更多的思考空间,从这一角度上看消解也是一种意义,如果舍曼想以这种消解来对抗所谓的意义的话,她其实也依然在杜尚以来观念艺术的大框架下并没有更多的突破。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哲学只是把一切摆在我们面前,它既不解释什么,也不推演什么,因为一切都已公开地摆在那里了,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舍曼从《无题电影剧照》系列到《屏幕后的射投》及《中心插页》系列,其本质是一种呈现着的消解。之所以是消解,源于这种呈现的不确定性,在观众观赏舍曼作品并试图确认其作品某种含义时,因为她提供了如此众多的形象,所以她阻挠了观众要通过自己的想象来认识她们的企图。舍曼曾言:“有些人告诉我,她们记得我的意象之一的电影来源,但是,我心中完全没有电影。”而这种不确定性犹如一种模糊状态,具有更大的威力,特别是当女性艺术家邀请女性观众用传统男性观念来定位作品的受众时所造成的不稳定性和模糊感,通过一系列的作品来突出这种模糊状态。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性别身份的显著矛盾并未解决反而是被加强。舍曼的作品就这样十分轻松地走入打着文化烙印的再现结构,她通过故意的消解强迫我们思考问题的真实性。
三、从追求真实的局限里解脱出来的想象与批判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舍曼的《时装》《童话》《灾难》系列则在道德性上批判了艺术上对身份、神话原型的塑造以及这些因素呈现出的社会心理特点。《历史的肖像》系列在探讨一个表现与再现的体系,表达的意图是一切人像作品都是刻意而为之,真实性不再有强调必要。90年代早期的“性图像”系列则被认为是含有刺耳的道德倾向性和令人无法忍受的喜剧性。更为绝妙的是,一些道德上的反映在其作品恐怖奇异的外观下是复杂与含糊的,而清晰地弥漫在她影像中的是不恭的幽默和荒诞的观念。
从《时装》系列开始,舍曼开始试图创造自己艺术的发展线索。评论家克雷格·欧文斯评价舍曼说,虽然她“也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令人仰慕的美人拍成照片,但她是不肯被人挂在墙上欣赏的”。1983年开始,舍曼参照时装摄影完成了四组作品:第一系列为《采访》杂志而作,舍曼毫不奇怪地创作出与耀眼的广告截然相反的形象。这些模特儿看起来是可笑的,穿着迷人的时装又使她们很开心。第二批作品在为法国《时尚》杂志的设计而拍图片时,舍曼的设计比以前更为古怪,模特儿形象有的沮丧,有的满脸是夸张的皱纹,有的甚至是杀人犯的样子。1993年舍曼为《哈泼市场》杂志拍的作品,形象富于幻想,充分利用服装来制造完全不同的舍曼,背景也转换为戏剧布景。在《时装》系列中,舍曼首次展示了一种阴暗的情绪。在谈到受时装公司邀请为他们设计作品时,舍曼说:“从一开始就有些东西不适合我,好像存在冲突。我挑选了一些我想用的服装,结果给我送来的是完全不同的服装,我发现他们使用起来非常无趣。我开始取笑,不是取笑服装,更多的是取笑这种时尚。我开始在脸上涂一些疤痕膏,以使自己变得丑陋。”时装广告总是向消费者许诺他们的衣服可以将穿着转变为一个完美的形象。正如所有的广告一样,时装摄影大规模制造了一个永远不能满足的欲望。我们追求最新潮的款式,但明年就会被取代。时装广告的真正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新鲜的衣着形象。而舍曼的时装摄影则暗中破坏了这一切,讽刺了公认女性美的标准,揭露了广告人的煽动本能。
而这一时期,给舍曼带来事业发展新突破的创作是她的《童话故事》系列。1985年,舍曼把时装作品中的破坏性因素在《童话故事》中发展到更高的一步。她的影像变得真正奇怪和超现实了。从《童话》系列开始,舍曼开始逐渐减少个人形象的参与。这些形象极不寻常,不仅因为有恐怖的因素,而且也在于我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于看那些悦目的东西。用剧场中所有的工具,包括戏剧性的灯光、鲜明的色彩、服装、假体、假发和支撑物,她创造了明显是假的、幽默的而不再是打乱的形象。一些作品呈现的是极其荒诞的结构,它们更多的是玩具娃娃,而不是人。美国著名童话作家和民俗研究学者杰克·希普斯在评论童话故事时曾说,“作为一个社会化的关键因素……让孩子们发现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并检验人们对世界的假想。”童话风格对儿童的影响极其重要,我们平时接触的童话故事大都归结为女孩幸福地等待王子的到来,而舍曼的《童话》将这种陈词滥调进行了某种思考,从童话这个切口展现恐怖、暴力、人造、幽默等风格也许有一种全新的美学的尝试。正如舍曼曾说:“恐怖和童话故事中的那种掺合着恐怖的诱惑真是制造不可思议的好办法……真实的恐怖过于深奥,我的这些东西很容易理解,也很容易接受,但它同样可以影响你的心理——尽管它是假的、幽默的和人造的。”如果仅仅将舍曼的《童话》理解为风格学,结合舍曼的《灾难》系列,影像变得更加面目全非,令人讨厌,她使用同样的戏剧手法和幻想的形象来构筑同样奇异的场景。在这些作品中,身体被围在中间。从童话故事中跑到这里来的动物与玩偶结合在一起,成为变形了的人体,在突出对厌恶之物用一种绚丽的摄影方式的展现中,使观者经受着视觉的考验,由此产生追问与思考。在另外一个意义的阐释维度里,1986年至1989年,她的《童话》与《灾难》系列中惨不忍睹的场景与当代社会中的暴力和明显混乱形成相对的关系。虽然身体政治也遭到攻击,但我们仍然为我们个人的身体极其适应性所困扰。在将身体作为社会比喻的分析中,L.芬克尔斯坦因认为,在西方文化中,对身体的控制是身份的象征。19世纪欧洲文学史上的许多突变角色都是一种社会不公正对待的结果,而他们也都接近人性。这或许是他们为什么招人迷恋的原因,因为“我们好像隐藏了另一个自我,一个未显露的受压抑的一面,……因为我们生活在对它的恐惧中,我们知道它有可能在任何时候爆发”。舍曼作品中那遭受到攻击的身体形象揭示了这隐藏的一面,而且抵制着我们日常从大众传媒上看到的理想化和虚饰的偶像。关于舍曼作品恐怖和悲惨内涵的探讨中,茱莉娅·克瑞斯特娃写道:“她的作品不仅仅以默默无闻者,我们文化中的边缘人物为主体,这种恐怖表达了我们的呐喊和我们对未来的担忧……”
《历史的肖像》系列作品中,舍曼将自己装扮成历史上各种不同的贵族、凭空想象的英雄等,在有些作品中,她把自己化妆成男性,在这种变性处理中,她使用了和杜尚相似的策略。为了调侃古典绘画大师对女性解剖学上处理的笨拙,她自己戴了假胸乳。她回到艺术史主流的叙述以反讽既存的秩序,将符号的使用方法还原至荒谬与混沌的境地。舍曼对古代绘画大师作品绝对怪诞的篡改,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一种创作方法上的解放。如果说舍曼在控诉男性本位文化的暴力性与迫害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在这一系列中,她真正攻击目标应是形成文化特性的历史文化传统。
舍曼的“性系列”作品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政治攻击氛围中产生的,在这期间,宗教势力抬头,检查制度与表达自由之间的对抗成为突出的问题。舍曼从逼真的色情描述的老套中走出来,用假生殖器和分裂的人造模型去扮演带有性特征的身体,更直率地贬低施强暴的行为,比许多血腥恐怖的幻影更令人不安。虽然超现实主义摄影家采用粗暴的方式使人体模型变形来表现的手法并不是什么创新,但是舍曼的不同点是用具有明显性征的男女人体模型来贬低性欲的事实是非常明显的。作为女艺术家的身份深深地影响到该系列作品的风格,这一方面比男性艺术家汉斯·贝尔莫割开的女性偶像更充满力量。
四、现实生活中的舍曼退缩与羞涩,直到自我消解
从最初的电影剧照系列之后,舍曼作品坚持一贯的大幅尺寸,色彩夸张,最后变成极其阴森可怕的影像。舍曼则变得越来越隐秘,直到自我消解。这两方面的自然展开有机地进行了很多年。舍曼自己不再是更甜的、温文尔雅的,而完全是不装腔作势的,将其无限创造力投射到作品当中。1995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全部收购了舍曼《无题电影剧照》系列作品,这意味着这类观念性摄影作品与其它艺术品具有同样的价值和地位,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1997年,由女性艺术家麦当娜提供赞助,舍曼全部作品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1999年,舍曼荣获哈苏基金会颁发的哈苏国际摄影大奖。哈苏国际摄影大奖可视为摄影界的诺贝尔奖,基金会注重把奖授给在摄影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摄影家。
2003年到2004年的《小丑》系列成为舍曼对女性形象的总结:“小丑,一直是我最喜爱扮演的角色,我认为世人喜欢看到。‘快乐的小丑,也因为如此,小丑只能将悲伤留给自己,这和‘女性的角色扮演何其相似?”“小丑”这个形象符号,与“面具”“童年”“娱乐消遣”这些信息相关联,也同“倒退”“畸形”的意义紧密联系,这样的游戏尺度总是被舍曼维持在她和主题之间,这个距离可以给观者一个自由度去联系和补充她具象化着的一些角色的故事,借此贯穿渗透和突出整个作品。
2008年舍曼又创作出了《贵妇》系列作品,以此讽刺上流社会虚荣且精神空虚的老女人。从这一系列中我们可以看到《无名电影剧照》中的魅力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些全色彩的图像继续吸引着我们探索的目光。从此舍曼的艺术生涯完成了一个圆圈。
在生活中,舍曼总是显得有些害羞和退缩的样子,她是安静的、严肃认真的,幸福地结了婚的人。在街道上,没有人会注意到她,猜想她就是辛迪·舍曼。她的生活几乎就是以她作品的假面目出现。在作品中,她通过表演的方式来表达另一个人的世界,她对自身和替身的运用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探索她对独特的自我形象塑造与阐释的空间。正如舍曼曾说的:“我喜欢一种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影像,很难表达其中的意义,这将解决我所有的问题,就是试图提供一个不包含其他人的故事,仅让他们在画框外,一些事情就“咔嚓”一声完成了。”
(陈真,中国美术馆)
组稿/苗菁 责编/苗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