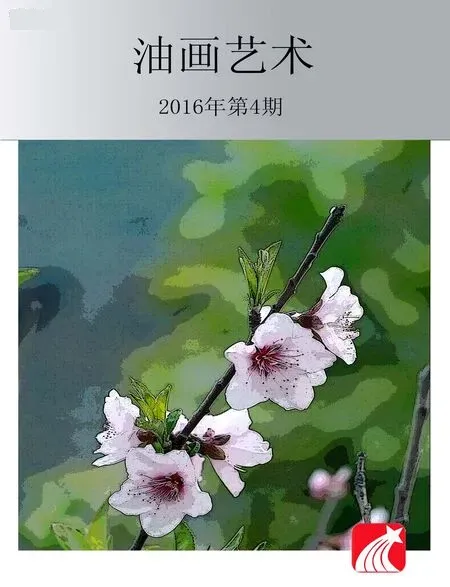喻红:从“目击成长”到景观剧场
文
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藏品中,有两件喻红的作品,经常被展出并引发话题:一件是喻红本科学习期间画的《大卫》素描头像,整开的大纸,刻画得极为深入、到位、细致与生动,这件作品往往被用来说明央美的学生是如何既有才气,又有一扎到底的功夫;而另一件作品是喻红本科毕业创作,题为《川》(1988年),画的是一组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迎风而走的形态,最前面的女性,大概是喻红自己身影的写照。这件作品除了色彩、造型、笔触等的成熟精彩,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些年轻人的形象都被斜拉着并微微变形,身体的重心旁落,有些失衡,尚未走出校门的喻红似乎已敏感地意识到他们这一代人走进社会可能面临的种种失衡和变形,画面中有一种不安的、扭曲的复杂情绪。年轻的喻红似乎很早就有自我意识感,有深情的自我顾盼和反刍,且自觉不自觉地将这种感受表达出来。之后,她开始用“纪年体”绘画,用记叙逝水流年的笔法,摹写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心理和生命形态,自己与外部世界构成的种种关系等。“目击成长”系列组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应该说,关注自我、关注自我的生命状态的创作方式,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喻红艺术创作的基本特点。20世纪90年代前后,“目击成长”与喻红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以年表式的系列组画记录自我成长历程,喻红的艺术一直与自我一起“成长”。
2009年,我在广东美术馆任馆长期间,策划推出了喻红“时间内外”展览(郭晓彦策展),当时展出的作品主要是“目击成长”系列及丝绸、聚酯系列作品。我从女性多关注自我甚至有些“自恋”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指出:“‘成长’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一个持续的梦与现实的过程,这里交织着个人、家庭、社会、历史的种种因素,交织着幻想、希望、感性、现实,等等。男人的世界更多的是现实和社会的世界,而女人的世界往往是充满了个人和感性的色彩,但在喻红的艺术表达中,在‘目击成长’的独特图式中,流露着在我们无法回避的大的历史社会背景下,作为女性的个人对生活、情感、行为、过程的种种安静而细致的感受和关怀……这种关怀延伸着,在她后来的以丝绸为媒介、以聚酯为材质的创作中,婴孩、女性与柔弱、优美的丝绸所产生的关系,与冰冷、坚硬、透明的聚酯所构成的隐喻,无不指向于对生命,尤其是一种柔美的生命的关怀。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赵波事件’的描述和演绎,对她那戏剧式的美丽和被残害的呵护的刻画,一再提示着生命的脆弱和优美。”[1]
对于喻红来说,这种对自我和生命的持续关怀,既是她艺术表达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也似是她的归宿。作为一位女性艺术家,她对身体、生命的敏感和执着,一直没有改变。她的“目击成长”系列,目前还在继续进行着,她说,这个系列的创作会伴随着她的生命旅程 ;但“时间内外”展览,也呈现喻红艺术创作另一条线索的出现。我们不难发现丝绸系列作品的舞台性效果追求,“我们俩”系列(2007年)、《天井》(2009年),以及稍后的《天梯》(2008年)等作的出现,到近期的《云端》(2012年)、《坤乾》(2014年)、《游园惊梦》(2015年)、《百尺竿头》(2015年)等,她的画面更像一座承载景观的剧场。巨大尺幅、大开大合的画面,不再只是自我形象描摹,而更像一座舞台,融入了繁复、华丽、众声交叠的内容。夸张而强烈的布景,交互出演的众多人物,扭曲郁结的形态举止, 恣肆地展开着自己的种种表演,画面充满戏剧性细节。一种景观式的剧场接连不断地出现在她的画面中,现实的奇观,个人的幻觉,社会的仪式,参与者与旁观者角色的游移,表演的欲望与幻象的交织,而这一切,带来的是画面情绪的复杂多变,有惊恐不安,有迷茫疑虑,有装腔作势,有无奈彷徨……
我一直在留意和关注着喻红艺术的这一变化,她似乎在游移,或者说游移中贮蓄着变化,一种重大的变化。从画面的情绪、形象的精神气息、物象和色彩的戏剧性,到尺幅、结构和视觉的景观感,等等,都在发生重大变化,有很强的不安感,即强烈的不稳定性。在这样的不安中,似乎能看到喻红在寻找什么:生命脆弱无奈又华丽如歌;死亡之躯被放置在葱茏茂盛的万物中,生与死相互映照;老林、孤树、旷野,残阳如血,为罩着塑料膜的少女提供一抹“隔膜”的春光;水银随处流淌的土地上,男孩俯卧于上面,四周是勃发的仙人掌花蕊;云端上包裹整齐的死婴,云梯边上享乐的男女,手拉手飞离蘑菇云的情侣。喻红用一种二元分裂的极端方式,摹写世间万物相离相吸的情景,这一幕幕都是戏剧性的,充满不可理喻的悖论。在这批作品中,喻红似乎有意地将自我抽离,艺术家作为一个在舞台之外的导演,设置、调配着戏中之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对奇观式的生命存在于奇观般的境况的忧伤和感叹。

喻红 奥菲利亚布面丙烯 250 cm×300 cm 2016年
我们所处的正是一个被不断描述为景观的社会,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景观社会”[2]理论对现代化的社会奇观,包括人的奇观、物的奇观、行为的奇观,及奇观背后的构成方式和目的性,都做了刺痛式的概括和揭露。景观正日益把社会变成一个表演性的舞台,而无处不在的社会表演进一步加深了社会景观化的程度。德波所指的“景观”,其深刻之处在于其逻辑上的普遍性,而景观的巨大能量和潜在性的权力正越来越严重地蚕食、扭曲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将所有的一切都变成景观,抽空人类日常存在的血肉性,使人的异化,人的感知、情感、行为的异化成为社会表演的主角。
不知景观社会的特点是否已为喻红所敏感捕捉。从喻红谈及她这一阶段艺术创作时常使用的“戏剧感”“布景”“舞台”“戏剧化的色彩”等语词看,她对这方面显然有所体察,她这一时期的画面表达与她所观察的社会特点,应有某种敏感而特殊的关联性。她将诸多互不关联的细节整合并置,放在巨幅的画面中,构成互为对话的关系,隐含她独特的景观处理态度。
而喻红的创作表现出来的戏剧感、表演性,这使我想到所谓“剧场”的概念和相关的理论,尔文·戈夫曼[3](Erving Goffman)运用“戏剧”的相关概念和语言,对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进行了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学分析,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方式与在剧场中的表演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包括剧本、在场性、误演与即兴、前台与后台、印象控制、角色与面具,等等,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剧场”,而我们在其中各自扮演着相应的角色,并以剧场的方式和规则出演、转换、调整着自己的行为。有意思的是当这样的“剧场”变成了景观,当景观式的剧场用其相应的“奇观”“异化”的规则上演着一幕幕奇葩的悲喜剧,作为演员的人,也成为景观的一部分,或成为景观本身。

喻红 守株待兔布面丙烯 300 cm×150 cm 2016年
于是,“巢居”的现代时髦年轻人在布满监视器的高高的空中,无助地等待着、翘望着,但等待的是否是剧场里一个叫作戈多的演员?(《百尺竿头》2015年)蜷曲伏贴在地面,似乎在倾听大地融化的金属声音的孩童,使我联想到那幅一只秃鹫在安静等待孩童慢慢死去而可以一饱饥肠的著名照片——凯文·卡特(Kevin Carter)摄影作品《饥饿的苏丹》,孩童在像毒花一样融化着、扩散着的水银融流当中,安静地倾听销蚀着自己的声音(《金属的声音》2016年);而在现代景观化的游乐园度假村的废墟里,充满荒诞感的“盲人摸象”“水中捞月”“刻舟求剑”等,充斥着戏剧化的场景和演绎着错位荒谬的情节及寓言(《游园惊梦》2015年);还有,那些惶恐不安的云空、灾祸诡异的天象、乱流惊变的大地,而置身其中的芸芸众生,戏剧般地各得其果,各乐其乐。(《云端》2012年、《坤乾》2014年、《日月同辉》2014年、《大风起兮云飞扬》2016年)这一切都在这样巨大的景观剧场中一幕幕地上演着,而在这样的剧场和戏剧化的强烈灯光下,生命显得如此的荒谬、苍白、诡诞,人也如此的奇异、疯狂、不安和无奈。
从“目击成长”到景观剧场摹写,尽管途径和方法不同,关注、关怀生命一直是喻红艺术创作的主线,表演性也隐约贯穿其间。在“目击成长”系列作品中,择取特定的社会背景,讲述自我成长的故事,客观记录之外,也有自我与外部世界达成特定关系的表演。即便一些作品描述的背景年代闪烁着不安动荡的青春、政治、社会的因素,画中的人物形象、形态,包括色彩和造型,呈现的是相对天真、轻松、祥和的感觉,尤其是当从两联画变成三联画,由一人、两人世界变成三人世界时,有一件作品,画面是喻红坐在一边,安详地看着女儿快乐天真地玩耍着,那种感觉似乎是生活中的母性的喻红。然而,生命总会面对一个复杂现实的社会,生命本身也会在一个日益成为景观、剧场的社会中变成了一种无奈的景观,有责任感的艺术家总会在景观化的生命情境和他者化的剧场现实中,去关怀被异化了的人和被异化了的生命。于是,我们在喻红近些年来的作品中看到,她隐喻性地借助一些著名艺术家作品,如约翰·艾佛雷特·米莱(John Everett Millais)的《奥菲利亚》、亨利·卢梭(Henri Rousseau)的《梦境》等的画法或图式,表达她对人美丽而脆弱的生命及爱的关怀,同时,也以巨大的画面尺幅和戏剧化、布景化的形象、色彩,及游动错乱、电影镜头的视觉结构,来营造其社会人生景观化的剧场感。
其实,我们正一步步地跟随着喻红的眼光和镜头,走进一个个景观剧场,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自己生命的和社会的角色。
2016年7月29日 于燕京绿川书屋
注 释
[1]王璜生:《时间内外的“女性”:关于喻红》,载《喻红:时间内外》,江西美术出版社,2009,第6页。
[2]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尔文·戈夫曼(1922年6月11日—1982年11月19日),加拿大裔美国人,著名社会学家及作家,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最富影响力社会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