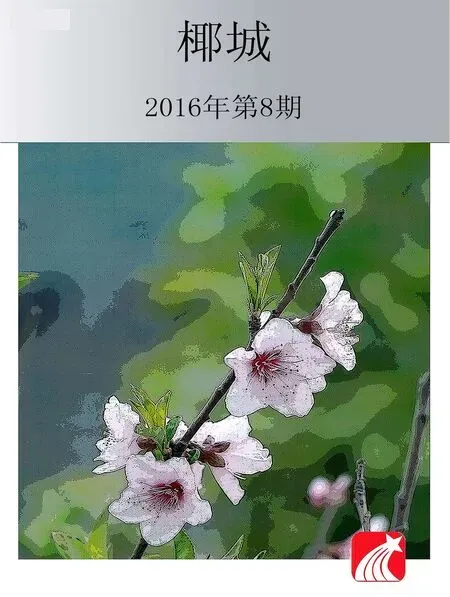天空的那朵白云
■赵丰
天空的那朵白云
■赵丰

打开窗户,雨不知什么时候停止了,天空出现了多日未见的白云,乡野的炊烟也挺起了腰。雨已经下了一个多星期,淅淅沥沥的让人心烦。下雨的天气里,很少有人打扰,我也不会选择出门,读书,写作,思考,喝茶,抽烟,让思维凝滞在窄小的空间里。这些日子,桌上、床上放着海德格尔的书:《走向存在问题》《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真理的本质》《演讲与论文集》……随便地翻着,并不系统的阅读,往往是精彩处读过好多遍,有些段落干脆就放弃。这是我的阅读习惯。
对于海德格尔的关注,是从他那句著名的哲言开始的。他说:“模糊性是智慧固有的美德。”在智慧的表达这个问题上,千百年来,先哲们从来都是非常谨慎的。他们确认,真正的智慧,是无法用语言说清楚的。如果非要用语言去表达的话,那也只能是模糊的表达。因为智慧潜藏于生活中,沉淀于思想者的思维活动中,如要给智慧下一个定论,那智慧最终会成为一个僵死的东西,成为灵魂的枷锁。纵观中外先哲们的智慧之思,苏格拉底、孔子这些号称人类导师的大家,他们在传道之时采取的是“述而不作”的方式,没有留下自己表达思想的文本。有关他们的思想著述,是他们的学生根据当时的课堂笔记整理得来的。哲人们之所以“述而不作”的理由,我想与智慧的模糊属性有关。这让我想到了智者学派里的高尔吉亚,他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无物存在;既就是有物存在,也不可认识;即使能认识,也无法表达清楚,把它告诉别人。”
在我看来,真正的智慧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充满了永恒的魅力。它不是僵死的教条,能给人以启迪。这样想来,海德格尔的话是对的。真正的智慧确实需要一个模糊的表达方式,否则,智慧就会变成教条。比如中国哲学中的《论语》《道德经》《庄子》等,从它们诞生之日起,经历了漫长岁月流沙的漂洗,今天我们仍在读它,仍在启迪着人生。否则,于丹在讲《论语》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听众,会有那么多的学者和听众在争论。争论不是坏事,有争论才会产生真理。正因为《论语》的模糊性,它的多重理解和歧义,才使它产生了无穷的魅力,从而成为中国哲学的经典,启迪着人们的智慧。佛家讲“转识成智”,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智慧只能呈现,而无法说出来。说出来了,也就什么都不是了。这也应了维特根斯坦的那句名言:“对不可说的,要保持沉默。”《道德经》里也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只要讲出来了,就不是道了,但智慧总是需要表达,这也是中外一切思想家们的无奈和苦恼。
在沣河岸边的秦渡镇,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春天的时候,我在河水里看见到的是蝌蚪。黑黑的身子,在水里傻乎乎地摇摆。那时,我无法把它和青蛙联系起来。外婆那时还精神着,她拄着拐杖站在我身后,冷不防说出一句:蝌蚪是青蛙。就这么五个字,简洁明了,我却半信半疑,蝌蚪怎么会是青蛙?青蛙的头呢,腿呢,哪儿去了?
外婆那时在我家住着,她平时很少说话,一旦开口便让人没头没脑。譬如,她肚子饿了,便唠唠叨叨:神仙才不吃饭呢。人不吃饭就成神了。她那么瘦小,脑子里怎么就装着那么多古怪的东西?在我的记忆里,外婆总是穿着一身黑衣,又裹着脚,在院子里晃悠。几十年的岁月过去了,我才恍然大悟,外婆不是常人,她说的话表面上看来有点思维混乱,可是她说出来的都是智慧之语。童年的我不理解蝌蚪是青蛙的事实,外婆表达得也很模糊。我在想,如果把那个“是”换成“变”那不就明确了吗?可是外婆偏不这么表达。大约在她看来,模糊的表达更好。小的时候,我常常把外婆和蝌蚪联系在一起,生出一些怪念头。譬如坐在池塘边,我的脑子却在想:水里的蝌蚪整天想着什么?岸边伏着的身体是我自己的么?
外婆的一生填满了苦难。在她三十岁时,外公就离家出走了,从此再无音讯。外婆用其一生守候着外公的归来。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她的“生存是在深渊的孤独里”。但她在表面上从来不会悲观,中年思维正常的时候,她总是说着幽默的句子,即使后来思维混乱了,她的声音也会散发出哲理般的味道。
扯远了,还是回到海德格尔身上。
1889年9月,海德格尔出生在德国巴登——符腾堡洲的梅斯基尔希镇。他的父亲在镇上的天主教教堂任司事,母亲也是天主教徒。在天主教会的资助下,海德格尔读完了中学,后来又在弗莱堡文科学校学习希腊文、拉丁文。然而,让他成为一个哲学家的起点则是布伦塔诺的一本著作:《论亚里士多德以来存在者的多重含义》。此后,他便翱翔在哲学的天宇上,最终成为一片令人仰望的白云,成为二十世纪西方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
1927年,海德格尔发表了《存在与时间》。这部书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他的名字也因此蜚声西方哲学界。?还是在两年前的一个秋天,一个远在深圳的学生给我邮来了这部书的中文版。它的出版者是三联书店,译者是陈嘉映和王庆节。尽管早已听过海德格尔的大名,但一直没有机会读他的作品。炎热的日子里,我啃着晦涩的文字,一知半解却满怀激动。当我读到二百九十七页的一段文字时,莫名的共鸣终于涌上心头。
那段文字是这样的: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空盒子,我与万物被放置于其中。实际上,有一个我(主体)与一个世界(客体)相对而立是后来才发生的事,原初的本源世界是此在与世界水乳交融不分彼此的世界,换言之,此在生存着“在世”,我们可以称这个世界为“生存世界”。此在生存着,在世界中存在。在这个生存的世界上不仅有在者,还有其他的此在。此在一开始就与其他的此在共同存在,这就是“共在”:他人与我共同在此。
文字的表达虽然模糊,但含义明确不过:人与万物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这就是存在的本质。外婆和我,沣河和蝌蚪,还有森林和海洋、高山和流水、泥土和茅草、熊猫和野鸡,都在同一个地球上生存着,共同拥有一个生存世界。当然,这部书还有许多哲理性的论述和句子,但对我来说,这一段话就够了。
儿时的小镇,并不像现在这般喧嚣,到处是洁净的空气,生活以一种原生态的方式呈现着。夏夜,一条街的人们都搬出竹床,在沣河边乘凉。躺在竹床上,凝望着深邃的星空,我有时会感到莫名的恐惧。外婆说一个人就是一颗星星,那么我会是哪颗星呢?我会离开这小镇飞到天上去么?那时的我,还没有学会仰望星空,觉得那就是一个深渊——生命的深渊。大人们摇着蒲扇,我却在颤抖,想着我就要离开地球了。童年和少年,那样的恐惧常常侵袭着我,当我仰望星空时,当我思考宇宙的浩瀚时,当我反思自身时,这种情绪就悄然光临,令我焦虑不安,感到自己身处的小镇如此渺小。那时,周围的一切似乎都不再熟悉,我看到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充满未知与威胁。如果这种焦虑持续不断,我可能就会成为医学上被分类为“广泛性焦虑症患者”了。
最早,我是在帕斯卡尔那里找到了对于这种体验的共鸣。“这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让我感到恐惧”。帕斯卡尔,这个伟大的数学天才与禁欲主义者在上帝那里找到了慰藉。还有叔本华,这个悲观却理智的虚无主义者,毕生都为人生的意义所困惑,对于未知与死亡的恐惧伴随了他一生。在死前的那一刻,他写下一句话:“我们终于解脱了。”他带着笑容,离开这个让他爱恨交织的世界。而海德格尔,却给了我无比宽慰的感觉。我曾经有过的那种特殊的情绪体验,被海德格尔称之为“畏”(这个词在德语中意为焦虑),被他认为是本真此在(领会与追问存在的状态)的基本现身情态,他的“此在”即为追问存在的存在者(此在是对人的规定)。他使我明白,我所身处的世界,有如此多的人类和物体,他(它)们陪伴着我一起呼吸,一起面对着未知的世界。幸福的感觉,有时是孤独,有时是群居。
非常喜欢德国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一首诗的名字:人,诗意地栖居。这首诗后经海德格尔的哲学阐发,表述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他是借此阐释他的存在主义。其实,荷尔德林写这首诗的时候,已是贫病交加而又居无定所,他只是以一个诗人的直觉与敏锐,意识到随着科学的发展,工业文明将使人日渐异化。而为了避免被异化,他呼唤人们需要寻找回家之路。正如他在《远景》中所描述的那样:“当人的栖居生活通向远方,在那里,在那遥远的地方,葡萄闪闪发光。那也是夏日空旷的田野,森林显现,带着幽深的形象。自然充满着时光的形象,自然栖留,而时光飞速滑行。这一切都来自完美。于是,高空的光芒照耀人类,如同树旁花朵锦绣。”不难理解,诗意地栖居亦即诗意地生活,而诗意则源于对生活的理解与把握,尤其是内心的那种安详与和谐,那种对诗意生活的憧憬与追求。
我童年生活过的小镇,完全符合诗意地栖居这样的命题。沣河、沙滩、蝌蚪、青蛙、竹床、蒲扇、洁净的白云、静谧的夏夜、深邃的星空、河岸上倒垂着枝叶的柳树以及在树上歌唱着的蝉,还有我的外婆。这些在我看来都是诗意的生活场景。海德格尔阐释道:“诗意完全表现在诗人想象力的非现实游戏中……进一步讲,也许两者相互包容,也就是说,栖居是以诗意为根基的。如果我们真的如此推断,那么,我们就必得从本质上去思考栖居和作诗。如果我们并不回避这一点,就要从栖居方面来思考人们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人之生存……”他最后的结论是:“无论在何种情形下,只有当我们知道了诗意,我们才能体验到我们的非诗意栖居,以及我们何以非诗意地栖居。只有当我们保持着对诗意的关注,我们方可期待,非诗意栖居的转折是否以及何时在我们这里出现。只有当我们严肃对待诗意时,我们才能向自己证明,我们的所作所为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对这一转折作出贡献……”
在屋里呆困了,趁着雨后的清新走向田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离开书房,向后伸展着双臂,做着深呼吸走近一片桃林。桃子即将成熟,散发出香气。抬头凝视着空中清晰可见的白云,忽然感觉到海德格尔就隐身在其中。他嘻嘻笑着说:哦,你就是存在,你在诗意地生活着。
天空的那朵白云,是属于海德格尔的。我这样的想象,海德格尔大约不会质疑。
海德格尔所理解的人的存在是指人的原初的具体的在世活动及其方式,以及对这些活动和方式的体验。中国的百姓认为土地是粮食,是农夫,是龙的血肉,是天下苍生的欢乐和悲愁,而在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的意念里,土地是云、水、阳光糅和的诗篇,是人的起点和归宿。瞧,这就是百姓和哲人的巨大误差!海德格尔所谓“在世”,并不是指人对世界的认知活动和实践活动,而是指以直接意识、情绪体验等方式与世界上的物和人的交往活动。人的一生是通过情绪和情感表现出来的。而人的存在中,最能显露其存在本身意义的,就是对烦、畏、死这些情绪的体验。
存在、在世,一切都是这样明确,这样鲜活。感谢海德格尔!
我还感到兴趣的是,海德格尔对老子十分推崇,晚年研读并翻译《道德经》。这让我对他拥有了无比的亲切感。近期读到一篇文章:《迈向一颗星——与马丁·海德格尔的交往》,其中专辟一节题为《来自曼谷的僧侣》,介绍了作者所见所历海德格尔与东方世界的接触和遭遇。文中写到,海德格尔的工作室挂着一幅中文书法作品,上书老子两句云: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书法出自台湾学者萧师毅之手,乃后者因海氏之邀所书。此作之旁,是一尊日本木雕,为一禅宗和尚也。道释相映,颇有东方氛围。
海德格尔认为,人最大的“畏”就是“畏死”,但这种“畏死”,不等于日常生活中的贪生怕死。“畏死”是人对“向死而生”的认知。人只有认识到自己是“向死而在”的,才能筹划自己,设计自己。因此,“向死而生”就是提前到死中去,不要死到临头了才去思考死亡。但是,我们普通人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所以,普通人仅仅是怕死,想逃避死亡。而本真意义上的“向死而在”,是把死看作是“最本己”的可能性,是人的一种真正的本质。懂得了这一点,就可以从沉沦中清醒过来,就能够敢于面向死亡,也就有了高度的自由,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实现自我的一切可能性,并从对死亡的体验中,反顾人生的价值及意义。中国佛道讲求的修行过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死亡的认知过程。
应当说,海德格尔在哲学上取得的成就是奇特而巨大的。但是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他一直存有争议。对他的思想的评价,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有人说他的著作是一个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还有人说他是极具激活他人思维的思想家,甚至有人说他的思想只是一种根植了故弄玄虚的神秘感。由于他曾经加入过希特勒的纳粹党,使人们对他的评价更蒙上一层政治和情感的色彩。但无论如何评价,大多数人还是承认,他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哲学家伽达默尔对他的评价,我以为非常中肯:“这是一个用其思想影响了人们长达半个世纪的人,一个施放出无可比拟的暗示力的人。”
海德格尔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思想家。他所经历的世界变化是疯狂的人类所进行战争的屠杀和科学技术的征服。一切存在都好像被人类控制一样,人类无所不能的占有着世界上所有的财富、资源。可是,世界却由于这样的政治格局陷入战争的灾难之中。整个世界陷入到从末有过的混乱,生态环境出现了明显的退化。人类精神文化轴心欧美世界的价值标准引起全世界的反思。海德格尔先后思索了技术、科学和存在本身的问题,对座驾之上的一切现代社会都采取怀疑的思想进行批判。他明确指出,人类忘记了存在开始时原初的智慧,现代社会遮蔽我们之上的就是虚幻的世界,而人类陷入到已经到来的灾难深重中。他发出了对诗意与哲思的追问,才使他提出了完全不同于以往思想家的思路,去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危机,对生态环境开始深入的思索。
1976年5月26日,海德格尔逝于德国梅斯基尔希。巧合的是,我的外婆也是在这一年逝世的,也是在5月,比海德格尔晚了三天。而且,外婆的出生年月也和海德格尔一样:1889年9月。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手舞足蹈,差点跳了起来。天啊,外婆和一个哲人竟然相约着在同一个地球上生活了八十七年。这是怎样的一个巧合呢?外婆死去三十多年后,我才认识了海德格尔,由海德格尔我想起外婆,并理解了外婆的一生。世界何其大,世界何其小。如果不是空间的因素,外婆一定会走近海德格尔。
我站在雨后小城之外的一片桃林边,高空是洁白的云朵,远处是巍峨的秦岭。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我伸长精神的脖颈仰望苍穹。意念里,海德格尔是天空的那朵白云,是永恒的存在。而外婆,是那朵白云透射在地上的影子。
“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须有入于深渊的人们。”这是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文章里说过的。我把它作为名言警句,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承受世界之深渊,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又是何等果敢的勇气。要承受,就要进入。敢于面对,敢于拯救深渊里的人们,这是一个哲人的精神气魄。唯此,我才直言不讳地说:海德格尔,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