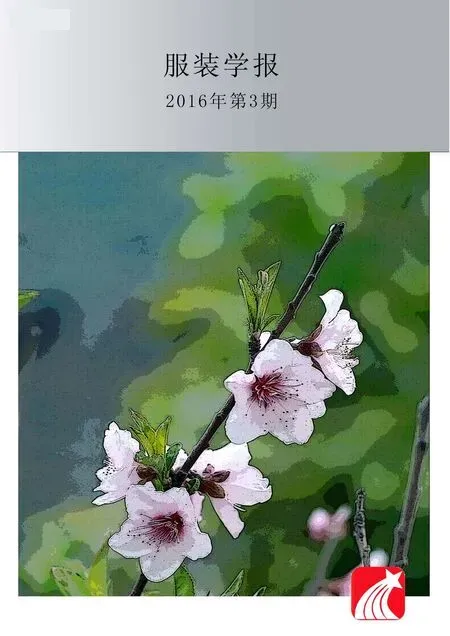20世纪20年代中西方女装的比较
李楠
(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学部,北京 100024)
20世纪20年代中西方女装的比较
李楠
(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学部,北京 100024)
运用平行比较与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从20世纪20年代的时代背景入手,通过对中西方女装在形态构成、功能意识及着装观念方面的研究,认为20世纪20年代既是中国与西方服饰的交汇点,也是传统服饰与现代服饰的分水岭。从而得出结论:20世纪20年代西方女装实现现代化,中国女装则开始向现代化起步,从而明确20世纪20年代是现代女装的源与流。
现代女装;20世纪20年代;中西方;比较
20世纪初,西化思潮波及中国,此时的西方女装也较早被介绍到中国来,如林语堂的《论西装》[1]、张爱玲的《更衣记》[2]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西方女装比较研究开始繁荣起来,已经涉及到文化影响比较[3]、穿着观念比较[4]、服装样式比较[5]、服饰功能比较[6]、审美精神比较[7]、中西方文化比较[8]等方面。但是,许多学者对中西方服饰文化比较中的差异涉猎较多,常常忽视中西方服饰文化中所体现的相同之处,没有进一步探讨中西方服饰文化在各自的变迁中表现出来的共同规律。
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是一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碰撞交流的历史。从服饰方面来看,这时的中国女装,开始有意识关注人体形状,同时保留中国传统服饰的气质,服装由直线裁剪变为曲线裁剪。而此时的西方女装,则恰恰相反,一改西方历史上的曲线美,为古典的曲线裁剪注入现代的直线裁剪。前者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由近代向现代的过渡期,后者所处的时期恰好是西方历史上有名的现代艺术较兴盛的时期。双方虽然相距我们近一个世纪,且分属不同的文化,但可以说两者都反映出时代转型期所带来的特有的服饰变革,体现出女装现代化进程所留下的进步烙印。
文中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中西方女装在现代化的成因、特征和变迁规律等诸方面的比较研究,揭示20世纪20年代中、西方女装所蕴含的现代精神,将现代女装的研究引向深入。
1 中国与西方的交汇点
20世纪20年代是中西方服饰的交汇时刻。西方的殖民运动裹挟着现代服饰文化一起涌入中国。面对强势文化的入侵,中国在反帝、反侵略进程中先是被动地后来又主动地与西方服饰发生交集,向现代服饰迈进;同时,西方也受到中国服饰的冲击,带给现代服饰许多新的风格和思路。事实上,现代女装这时已呈现出鲜明的交汇特色。
1.1裁制上“直线”和“曲线”有了现代新解
“线条”本是几何名词,其功能是勾勒轮廓、连接形状和分割空间,它可以强化人的视觉反应,线条的笔直或弯曲往往显示出更具活力或婉转的特征。服饰中的曲线与直线有三层含义:① 不同的裁剪法,即直线裁剪和曲线裁剪,分别代表了中西方不同的两大服装体系。大相径庭的剪裁方式让悬垂的中式服装像一副装饰画,而西式服装则更像一具华丽的身壳。② 服装的外形线。“在现代表述流行的概念中,常见line(线、线条)这个词,其实在服装上,它是轮廓线的简称”[9]。③ 体现服装突出强调的两性人体差。通过曲线强调女性的胸腰臀,进而将曲线作为女性的性别符号。通过直线强调男性的笔挺,进而将直线作为男性的性别符号;其中,服装的裁剪线与人的着装意识之间存在着最直接的关联。
20世纪20年代开始,直线裁剪和曲线裁剪作为传统的中西方服装的核心区分到此为止(见图1)。中国女装这时出现的各种改良,带着西方的味道,由清式刻板的直线裁剪,逐渐演化为显露体型的西式曲线裁剪,为了表现自然人体的美与舒适,对人体开始塑造。西方女装此前(15世纪初—20世纪初)一直是曲线主题,这时突然反传统之道而行,回避传统的夸张女性三围的方式,趋向自然人体线条的展现。不容忽视的是20年代东方文化对于西方服饰变革的影响,设计师们从神秘的东方获取新的灵感,当东方服饰的直线裁剪与西方内部的服饰现代化变革一拍即合时,西方社会的服饰流行从结构到装饰都焕然一新。
结构和外形都是服装的核心,共同的核心必然有共通的借鉴和转换之处。20年代中、西方女装共同呈现为自然的外观,通过贴身的剪裁追求自然形态。自然线条成为现代女装的基调。而直线裁剪和曲线裁剪,不作为现代服饰文化的关键词,仅取其结构技术上的现代意义。
1.2造型理念“平面”和“立体”互融共生
工业文明到来之前,“平面”和“立体”是影响中国和西方几千年的一个哲学观和审美观。女装的造型也是奉行这一标准的。中国女装以宽松方正的平面造型为主,比较而言,西方女装则重视立体的空间造型。李当岐对此有精到的评述:“前者(中国服装)是‘一气呵成’的,充分保持布料原貌,结构十分单纯,是‘非构筑式的’;后者(西方服装)则根据人的体形把衣服‘解体’,分成若干个独立的部件,分别完成这些部件的造型后再组装起来,结构复杂,是‘构筑式的’。前者充分尊重人的存在,衣服造型依赖于人体才能完成其最终的造型,成型程度较低,多属于‘半成型类’;而后者则往往无视人的存在,衣服本身就是一种‘人形’的‘壳’,许多时候是强迫人去适应这个人造的‘壳’,其成型程度较高,多属于‘成型类’。”[10]这无疑是对中西文化两大体系的继承和发扬。
进入20世纪以后,中西两种文化被交集在一个共同的现代环境中,现代女装成为全世界女性们追求的标准。显然,在现代女装中,“平面”和“立体”虽然性质不同,但在造型上的力量是等齐的。现代女装,自始就在造型上无限扩展,以突出服装与人体的亲和度为其首,同时倾向于艺术化的表现手法。以《啼笑因缘》为例,张恨水在小说中描写了“一件蓝竹布褂,束着黑布短裙”的学生装,该样式取材于“文明新装”,在西洋技术的渗透下,收腰合体,改围裹裙为直筒裙,这种“立体”造型的技术与“平面”已经混融在一起,很难一一分清。这时期的西方女装更表现出类似的情况。在向来以人的体形型为基本造型的女装中,突然经历了短暂的平直造型时代,“过时”的“构筑式”女服被摩登的“非构筑式”时装取代。以上都能形象地说明了:“平面”和“立体”不再是中西方女装的表现中心,双方共同向着自然显形的现代女装迈进。
1.3形态上“自然”和“人工”从对立到统一
中国传统的设计美学是“重自然、抑人工”,它的表层意义是“舍形而悦影”,深层内核则是“天人合一”的文化意境。“自然”虽合乎意境,但尚须借助人的智慧和双手,才能做到“意念的表现”。在各种技艺中,中国女装对拼接和缝制的技艺最为看重。受国产面料门幅窄的限制,排版时面料都要作拼接。常见的拼接部位有前后中缝、袖中、腋下和下摆,通常都很隐蔽,不易看出。在针法上,用回针加固拼接的位置,用扎针专缝贴花边装饰,而套结针则用来固定开衩顶端。归拔是改良旗袍的关键工艺,通过归拔,拔开胸量,斜拉腹量,归拢前腰,收紧后身,拔出臀量,归拢肩缝,圆顺袖窿,使衣片与体形进一步吻合。如果缺少这一工艺,仅靠省道就难以实现合体,旗袍的风雅韵味自然无法完美展现。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为何旗袍较少直白使用省道的原因了。因此,中西服饰文化融合,即“自然”和“人工”也可相提并论。
西方服装从繁到简的过程也类似于“人工”向“自然”趋同的过程。文艺复兴以来,服装朝着华丽的人工美发展,洛可可时期达到顶峰,这是最典型的衣为主、人为辅的例子,直到“20世纪初,女装尺寸开始逐渐减小,这样就使男装和女装在所占空间上趋于统一,致使女装在人工装饰方面也向现代男装靠拢。”战争时,“许多女子实际上已经开始穿上某种简单的民用制服”,以便从事工作,这是向“自然”趋势发展的契机。“以往女士们的姿势往往因为服装的宽松或紧密而导致了挺立和威严,而如今则允许有了随意轻松和懒散的样子——这是女士服装现代化的另一个明显不可逆转的标志。”[11]意思是漫不经心的“自然”感觉在起作用。这是现代女装的一个显著特点。安妮·霍兰德还认为:“20年代女士们的服装发生了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变化。那时的时装开始直接以女性的体型特征表现她们的性别特征,并以此代替过去间接暗示的表现方式。”[11]无疑,她在赞扬女性“自然”的肉体形态。这不是出自“人工”的主观能动作用,而是来自对“自然”的崇拜和再现。回归“自然”,使“自然”的人体和“人工”的服装相和谐(见图2)。
总之,在中、西方交汇的20世纪20年代,双方在裁制、造型理念和形态上的对立开始被等同起来,彻底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二分法,已体见出辩证统一的观念。这与其说是表现出服饰的进步色彩,不如说是现代女装日益显现出它的双重本质。
2 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
《现代服装的演变》序言中说道:“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间,女性服装逐渐找到了与传统相区别的现代理想。”换言之,20世纪20年代是古今服饰的分水岭。在探求传统与现代的交锋时,首先可以充分估量这样一个基本前提:“现代”既善于打破旧传统,又善于建立新秩序。由此可见,女装在新旧交锋时刻的三大支撑点:① 功能意识的转变;② 着装观念的形成;③ 女装变迁的方向。
2.1服装功能意识的转变
从传统的角度分析,中国人非常重视服装的社会伦理功能,这是历代君主出于为确立他们的统治合法性制造舆论的目的。帝王冕服,从先秦的“十二章”衮衣到后世的龙袍,对纹样、色彩、材质和结构都有一一对应的规定,就是极好的佐证。西方服饰发挥的主要不是社会功能,而是物质炫耀和财富价值。以巴洛克时代的男装为例,盛行使用大量的缎带和复杂的花边,男子的一件内衣甚至需要100多米长的缎带装饰,这是将奢华推向极至,无怪乎现在的西方高级定制业如此发达。17世纪法国画家里戈的《路易十四肖像》以这种装饰过重的盛装体现帝王的物质财富和权利威严。一方面表达了对拥有财富的赞美;另一方面把它延伸成了一种审美认识。这些社会文化功能有意识地与服装最初始的实用功能拉开了距离。
现代女装有一个原始的出发点,就是回归实用。其设计也是围绕解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而生。过去的传统重装束缚了四肢活动,装饰上故弄玄虚,这种“无用”设计脱离了实际。阿道夫·洛斯曾说过:“装饰就是罪恶。”此话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在设计之初,现代女装就对实用性非常关注,把日常生活中不被人留意,或被人有意讥贬的方便、轻巧、行动自由、感觉舒适的实用功能提升到“时髦、优雅”的高度,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夏奈尔偏爱自由舒适,把内衣的针织面料和便服的机能性提炼出来,用在时装中。让穿者感觉舒适的同时,又不妨碍穿者的活动自由。此后,女装的设计重心都转向了实用(见图3)。
当然,现代女装的实用思想并非如此单纯划一。虽然它减少了与实用无关的装饰,但并非就此摧毁了传统的社会功能和美学原则。女装同样在标识和审美上表现出惊人的作用。因此,现代服装的功能意识是全方位的。
实用与经济是现代设计体系的两大互为参照的尺度。现代女装也很重视经济节省,对繁琐形式造成的浪费和延续下来的奢靡之风持批判态度。的确,贵重工艺和装饰,只适宜于富有阶层,不适宜于社会大众。当实用性被突出强调时,实用与经济的关系逐渐鲜明起来,服装的朴素简单必然节省了人力和材料。在实践中,设计师们曾用“少即多”、“形式随功能”、“为大众需要而设计”等主张完成了许多绝妙的设计。
2.2现代着装观念的形成
人的价值观和整个社会风气关系到着装行为的养成。中国以儒道为哲学基础,在服饰上重视尊祖,追求精神寓意。传统服装形制单纯鲜明,几千年来都很稳定。款式上既不显露形体,更不裸露肌肤。西方哲学以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为中心,崇尚人体美,服饰上显露形体,甚至夸张形体。
从西方的传统观念中产生现代服饰文化有其必然性。西方文化重自我意识,重个性表达,重创新精神。文艺复兴以来,个体意识逐步强化,但被理性制约。现代社会揭开了理性的面纱,让自我意识裸露。西方现代文明产生了新的着装意识。因此,自我表现、注重个性、标新立异就是现代服饰发展一贯遵循的原则。
西方的人本意识在20世纪初激发了设计师,针对如何改变“人形的壳”,波烈等人先从改革内衣开始。一战后,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变了。女性对服装的要求不再以适应男性眼光为原则,而首先要满足自己的舒适和便捷,这也是女权映照下女性表现自信和自强的一面。夏奈尔等人的设计在充分考虑功能性的同时,还尽量表现强调自我的个人意趣。由此可以看出,现代女装体现了人本主义这一哲学思想。
20世纪初,中国女装的设计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以人为本”。这自然是传统“人物相丽”观念的继承,不同之处在于,传统“人物相丽”思想的提出主要是作为对不逾礼制的干预,而民国时则完全出自以人为贵的人文主义情怀。民国时期设计的新式旗袍,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开省收腰,表现体态”。这一符合生理机制的设计原则,与现代人体工程学相呼应。张竞生也认为:“美的服装不是表示在衣服上,而是能够衬托出穿者美丽的身材。”[12]
现代服装带给女性一种新的观念:典雅不再是唯一的风范,青春气为女性增添了新的时代面貌。在人文精神的影响下,人们获得了着装的自由。从服装形式来看,权贵和礼法的印迹褪去,人们求新求异的心理需求,有意突破创新,设计师的地位自然也被凸显出来,这是人本思想营造个性化的结果。
2.3现代女装变迁的方向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服装史的发展基本依赖于历史的传承,发展脉络主要由宫廷贵族来书写。民国伊始,中国开始了与西方的横向交流。这次交流的影响关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大众的热情参与方面,横向交流弥补了纵向传承的不足,促使全社会更快地形成类似西方的现代化风尚。
中国服装打破了纵向的历史传承之后,与西方的横向交流密切,“中西合璧”成了常见的设计。1926年《良友》总第8期上刊登了张令涛的图说“妇女秋服新装”,传统的“上袄下裤”都换上了由搭门和扣眼组成的西式门襟。《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全集》内“中西合璧”的婚服照片(见图4),整体虽保留了传统的袄褂形制、喜庆红色和盘金绣花,但西式对襟和西服戗驳领的添加,就充分体现了服装横向交流的结果;文中还提到新式旗袍的设计,也因为敢于变古法为新制,故赢得广大的受众。以上海、天津为代表的开埠口岸,崇洋之风更浓,服装的时尚节拍加快,一度紧跟西方的流行趋势。这些交流带给女装兼收并蓄的多样发展,成为中国女装快速现代化的不竭源泉。
西洋服装史的发展基本依靠传播来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横向交流一直进行着。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其服饰;同时,它也受到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异文化的影响,形成了风格独特的新艺术运动和装饰艺术运动。现代女装同样围绕着这些文化艺术的思想核心而展开。
透过现代女装的理论和实践分析可以得出:现代女装设计的宗旨,就是不脱离实用目的,依据个人意趣,充分调动自我主观能动性,体现创新精神,全方位地设计服装,进而决定服饰的美学效果。
3 结语
现代女装的形成,使得20世纪20年代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它具有古今中外“十里坐标”的时代意义,既是中国与西方的交汇点,也是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中西方女性在审美趣味上进入一个全新的探索阶段,现代审美观确立。当今的时装设计,无论如何变化,最终都会归入20世纪20年代的服饰类型中。这些变化,均是对现代服饰文化的发展。研究现代女装,认识其原型,有助于今天的设计师宏观地审视设计对象,勇于推陈出新,增强自己的设计发展意识。
[1]林语堂.论西装[J].论语杂志,1934,4(39):4.
LIN Yutang.Research suit[J].The Analects Magazing,1934,4(39):4. (in Chinese)
[2] 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集[M].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1996:97.
[3] 黄能馥,李当岐,臧迎春,等.中外服装史[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176.
[4] 叶立诚.中西服装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228-230.
[5] 华梅.灵动衣裾——华梅眼中的服饰文化:序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6] 汤献斌.立体与平面:中西服饰文化比较[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49-51.
[7] 李当岐.西洋服装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10.
[8] 张竞琼,蔡毅.中外服装史对览[M].上海: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2003:130-134.
[9] 李当岐.服装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73.
[10] 李当岐.中西方服饰文化比较[J].装饰,2005(10):24.
LI Dangqi.A comparison of dress adorn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J]. Art and Design,2005(10):24.(in Chinese)
[11] Hollander A.性别与服饰[M].魏如明,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46.
[12] 张竞生,张培忠.美的人生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85.
(责任编辑:邢宝妹)
Comparative Study of Women's Wear in China and the West in 1920s
LI Nan
(The Art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24,China)
Starting from the background of 1920s era,this article uses parallel and cross-culture comparative methods,Through the research on liberation of women's bodies,the transition from "heavy-type" wear to "light-type" wear and the exclusion of the social difference of women's wear,we got the conclusion that in 1920s,the western women's wear realized the modernization; meanwhile,Chinese women's wear started its modernization.
modern women's wear,1920s,China and the West,comparison
2016-03-07;
2016-04-17。
中国传媒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工程项目(041005)。
李楠(1980—),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服装设计历史与理论。Email:linanplay@sina.com
J 523.5;TS 941.717
A
2096-1928(2016)03-032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