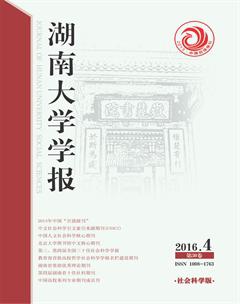读鞫与乞鞫新探
[摘要] 通过分析《后汉书》张俊案,指出读鞫是指官吏在行刑之前宣读罪状。梳理和解读三条家人乞鞫的记载,认为乞鞫是司法官吏向罪囚及其家属宣读罪状以后,罪囚及家属可选择的一种回应。三条记载都不涉及废除家人乞鞫制度。读鞫与乞鞫之间关系密切。
[关键词] 读鞫;乞鞫;秦汉法制
[中图分类号] H1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4—0018—05
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Zhang Jun case recorded in Houhanshu, Duju means justice officials read aloudcriminal facts before they execute criminal punishments. Through the car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ree records involving family Qiju, this paper claims that Qiju made by suspects and their family are permitted after justice officials read aloud criminal facts before them. All these records involving family Qiju do not mean that family Qiju is rescind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ju and Qiju is quite close .
Key words:Duju; Qiju; legal system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随着秦汉律令文献与司法案例文献的陆续出土与整理出版,学界对秦汉法制的探讨日益升温,“读鞫”、“乞鞫”是热议已久的问题,诸多前辈学者发表的相关成果为我们理解“读鞫”、“乞鞫”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文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读鞫”、“乞鞫”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求教于方家。
一从张俊案解析读鞫
传世文献所见汉代“读鞫”实例较少,我们以《后汉书》所见“张俊案”为材料对“读鞫”制度进行解读。
《后汉书·律历志下》:“蔡邕戍边上章曰:……顾念元初中故尚书郎张俊,坐漏泄事,当伏重刑,已出谷门,复听读鞠,诏书驰救,减罪一等,输作左校。俊上书谢恩,遂以转徙。”
《后汉书·袁张韩周列传第三十五》:“俊自狱中占狱吏上书自讼,书奏而俊狱已报,廷尉将出谷门,临行刑,邓太后诏驰骑以减死论。俊假名上书谢曰:臣孤恩负义,自陷重刑,情断意讫,无所复望。廷尉鞠遣,欧刀在前,棺絮在后,魂魄飞扬,形容已枯。陛下圣泽,以臣尝在近密,谓为尚书郎,识其状貌,伤其眼目,留心曲虑,特加遍覆。丧车复还,白骨更肉,披棺发椁,起见白日。”
可以看出两则材料有三种对张俊减罪情景的描述,一是蔡邕上章;二是《列传》中的描述;三是张俊上书。列表对比如下:
材料来源描述《律历志下》蔡邕上章已出谷门,复听读鞠《后汉书·袁张韩周列传
第三十五》史笔廷尉将出谷门,临行刑《后汉书·袁张韩周列传
第三十五》张俊上书廷尉鞠遣,欧刀在前
这一场景发生于谷门外的刑场,廷尉负责死罪执行。“临行刑”的关头,“廷尉鞠遣”,即廷尉读鞫并论遣,这里“遣”指论罪,而张俊“听读鞠”时“魂魄飞扬”。可以确认,“读鞫”是刑罚执行前的固定的必经程序,这一点汉代注释家已有提到。
传世文献“读鞫”见《周礼·秋官·小司寇》注疏,《小司寇》:“至于旬,乃弊之,读书则用法”,郑注:“郑司农云:读书则用法,如今时读鞫已乃论之。”贾疏:“鞫谓劾囚之要辞,行刑之时,读已乃论其罪也。”郑司农以汉代“读鞫”类比《小司寇》“读书”。“今时读鞫已乃论之”,指汉代司法官吏对罪囚读鞫之后对其执行刑罚,正对应前引《后汉书》“廷尉鞠遣”,“鞫”、“遣”并称,一指“读鞫”一指“论”,可以明确。
另一则提到“鞫”与“读鞫”的文献是《礼记·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则磬于甸人。其刑罪,则纤剸,亦告于甸人。”郑玄注:“告读为鞠,读书用法曰鞠。”郑玄注“读书用法曰鞠”化用前引郑司农《周礼·小司寇》注。对“读鞫”的分析,应以《后汉书》张俊案与郑司农《周礼·小司寇》注为主要材料。“读书用法曰鞠”语含省略,不宜作为主要材料。
汉代司法官吏于读鞫之后论罪,可见读鞫不等于论罪。这涉及对一个相关辞例的理解。
《史记·酷吏列传》:“传爰书,讯鞫论报。”《史记集解》:“张晏曰:传,考证验也。爰书,自证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讯考三日复问之,知与前辞同不也。鞫,一吏为读状,论其报行也。”
标点据《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第3810页。
张晏此注分析列表如下: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6年第4期欧扬:读鞫与乞鞫新探
张晏注“论报”:“论,其报行也。”意为:“论刑,是报复罪囚的犯罪行为。”这里“论”意为执行刑罚,“其”是句首发语词。此句从报应观念解释“论报”,不是对“鞫”的解释。张晏注“鞫”:“鞫,一吏为读状。”以读鞫制度来解“讯鞫论报”之“鞫”。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张晏注:“鞫,一吏为读状,论其报行也。”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江苏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67页。段将这两句连读来解释“鞫”,不妥。连读的理解是将“论其报行也”作为对“读状”的解读。然而“读状”是宣读罪状,罪状的内容是案件的事实,并没有涉及定罪论刑,或者说罪状文书并不等于论罪文书,因此无法将“论其报刑也”作为对“读状”的解读。
国内外学者对“读鞫”的性质多有论述。
陈晓枫指出,“读鞫”并不是很多学者认为的是指宣读判决书。
陈晓枫:《两汉“鞫狱”正释》,载于《法学评论》1987年第5期。
张建国注意到文献记载的“读鞫”和《奏谳书》中的“鞫”存在关系,进而阐释。他指出,“鞫”文书的内容是对犯罪事实的总结。在“鞫”程序结束后,程序中的“读鞫”是面对罪囚宣读“鞫”文书,也就是说“读鞫”程序紧跟着“鞫”程序后,并没有到行刑的阶段。张明确指出贾公彦解释“读鞫”为“行刑之时”宣读罪状是错误的。张指出,贾公彦将“鞫”与“读鞫”混为一谈是望文生义的结果。
张建国:《帝制时代的中国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311页。
宫宅洁明确区分“鞫”程序和“读鞫”程序,对后者,他认为“为了对确认的事实援引律令,还要经过一个‘读鞫程序,即向被告宣读确认的事实。”
宫宅洁:《秦汉时期的审判制度》,载杨一凡、寺田浩明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11页。他也认为“读鞫”是宣读“鞫”文书,对象是“被告”。
闫晓君引用了《中国法律通史》第二卷战国秦汉部分的内容:“案件审讯后,作出判决,并‘读鞫。鞫,是审讯的意思。……读鞫,就是宣读判决书。宣读后,当事人如果服罪,则照判决执行。”闫指出,这个观点不完全准确,将“读鞫”解释为宣判,是对汉人郑司农注的误解。
闫晓君:《秦汉法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87页。
综上,“读鞫”时间上在行刑之前,程序上独立于论罪,内容上是宣读罪状,其基础是司法官吏的“鞫狱”工作,性质上不能说是宣判。如果一定要类比当下刑事司法程序,那“读鞫”可以类比为当代的宣读法庭查明案件事实,而判决书不仅包括案件事实,还有定罪量刑部分。
二从家人乞鞫探查乞鞫
杨振红《秦汉“乞鞫”制度补遗》是最近发表的专题研究乞鞫制度的一篇重要论文。
杨振红:《秦汉“乞鞫”制度补遗》,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99页至509页。下文简称“杨文”。其论述家人乞鞫制度的部分使用了三条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关制度的传世文献记载,下文在杨文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些记载的内容与意义。
《晋书·刑法志》:“二岁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烦狱也。……斯皆魏世所改。”
另见杨文所引沈家本《汉律摭遗》卷六《囚律·鞫狱》“家人乞鞫”条:
《晋志》:“二岁刑以上,除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烦狱也。魏世所改。”
按:家人乞鞫,汉制也,魏世除之。《唐律》狱结竟取服辩条《疏议》曰:“其家人亲属唯止告示罪名,不须问其服否,囚若不服,听其自理。”
(清)沈家本著,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三,第1493页。转引自杨振红:《秦汉“乞鞫”制度补遗》,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09页。
第一,曹魏除“二岁刑以上”的“以家人乞鞫之制”,从字面上理解,并不是完全废除此制,一岁刑以下仍然允许家人乞鞫。沈家本统而言之“魏世除之”,不是很妥当。第二,废除“二岁刑以上”的“以家人乞鞫之制”,目的是省却繁难的狱事。然而这一目的与“二岁刑以上”之间存在矛盾。从常理分析,轻刑案件较多而较重刑罚案件较少,轻刑的错案昭雪以后产生的后遗症较小,而较重刑罚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一旦产生冤假错案,则较难补救。如果要省却繁难狱事又不至于产生大量的难以补救的冤案,立法者应该选择废除轻刑案件的家人乞鞫制度,而非较重刑罚案件。本文据此推测《晋书·刑法志》的“二岁刑以上”是“二岁刑以下”的传抄讹误,曹魏为了省狱事而废除了“二岁刑以下”轻刑案件的家人乞鞫制,保留了较重刑罚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的家人乞鞫制。这可得到《唐律》的证明,见杨文所引沈家本《汉律摭遗》卷六《囚律·鞫狱》“故乞鞫”条:
《史记·夏侯婴传》集解:“邓展曰:律有故乞鞫。高祖自告不伤人。”索隐:“案《晋令》云,狱结竟,呼囚鞠语罪状,囚若称枉欲乞鞠者,许之也。”
按:《唐律》,诸狱结竟,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仍取囚服辩,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详审。此即乞鞠之法。索隐引晋令,汉法亦当如是。
(清)沈家本著,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三,第1493页。转引自杨振红:《秦汉“乞鞫”制度补遗》,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00页。
沈家本引唐律:“诸狱结竟,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仍取囚服辩,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详审。”唐律的五刑从轻到重分别是笞、杖、徒、流、死。“徒以上”指徒刑以上的较重刑罚案件,这些案件的囚及其家属有听司法官吏“具告(罪状)”并提起不服的权利。而笞、杖案件刑罚轻而数量多,应该是已经废除了乞鞫制度以省狱事。这可以联系《晋书·刑法志》记载曹魏为“省所烦狱”而废除部分案件的家人乞鞫制,很可能《唐律》此处沿袭曹魏之制,可证《晋书·刑法志》“二岁刑以上”应作“二岁刑以下”。
《唐律》“诸狱结竟徒以上各呼囚”条,可得其它文献之证。
《汉书·万石卫直周张传》:“张敺……上具狱事,有可却,却之;不可者,不得已,为涕泣,面而封之。其爱人如此。”
晋灼曰:“面对囚读而封之,使其闻见,死而无恨也。”
沈钦韩:《史记》作“面对而封之”。按:面囚封上其奏,使知当死。必面封者,恐囚有冤也。《周礼·小司寇》“读书则用法”,郑司农云:“若今时读鞫已,乃论之。”《唐书·百官志》:“大理寺丞,徒以上囚,则呼与家属告罪,问其服否。”晋说是。
沈钦韩《汉书疏证》相关内容转引自(清)王先谦:《汉书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609、3610、3611页。
沈钦韩所引《唐书》内容见《新唐书·百官志》:“大理寺……丞六人,从六品上。掌分判寺事,正刑之轻重。徒以上囚,则呼与家属告罪,问其服否。”
《宋书·蔡廓传》:“宋台建,为侍中,建议以为: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自今但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便足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朝议咸以为允,从之。”
蔡廓建议的大意是:“官吏在进行鞫狱工作时,不宜命令罪囚的子孙下辞明言父亲或祖父的罪状,伤害礼教和人情,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请示自今(立这条法令):只令家人与罪囚相见,如果家人没有提乞鞫之诉,就足以证明服罪,不须强迫家人下辞(服罪)。”
第一,蔡廓建议前,家人乞鞫制度,是由司法官吏对罪囚家人表述罪状,家人被迫在两种行为中择一而行,一是对罪状不服并提起乞鞫之诉,另一种是“下辞”表示服罪,而这种“下辞”有固定格式,其内容必然明言罪状。司法官吏会强迫家人作出选择。第二,蔡廓建议的内容提供了家人的第三种选择,也就是不提乞鞫也不“下辞”服罪,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官吏不得强迫家人“下辞”,可以视为家人已经服罪。第三,蔡廓建议被立为律令条文的同时,并没有废除家人乞鞫制度。
这条源于蔡廓建议的律令得到唐律继承,可见前文的杨文所引沈家本《汉律摭遗》引《唐律疏议》:“其家人亲属唯止告示罪名,不须问其服否”,即司法官吏对罪囚的家人亲属只告知罪名,不须问其是否服罪。这正源于蔡廓建议:“但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便足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不仅内容对应,“不须”的相同用法可窥见其传承。
杨文认为:“直至晋末仍允许家人乞鞫,蔡廓因考虑到家人乞鞫时必然要谈论父祖等罪行,于孝道礼教不合,故建议禁止,得到朝议赞同。”
杨振红:《秦汉“乞鞫”制度补遗》,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08页。本文不赞同此观点,引文没有废除家人乞鞫制度的记载,也没有证据可以推定这一点。
《隋书·刑法志》:“(梁武帝天监)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对鞫辞云,母实行此。是时法官虞僧虬启称:‘案子之事亲,有隐无犯,直躬证父,仲尼为非。景慈素无防闲之道,死有明目之据,陷亲极刑,伤和损俗。凡乞鞫不审,降罪一等,岂得避五岁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诏流于交州。至是复有流徒之罪。”
大意是:“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引诱人口罪,当死罪。她的儿子景慈对鞫下辞,说:母亲确实有此犯罪行为。是时此案法官虞僧虬启称:案,子女服侍父母双亲,有隐无犯,直躬证父,孔子认为不妥。景慈一向没有防闲之道,而对母亲的死罪却提供有明目之证据,将母亲陷于死刑,伤人和损风俗。(律令规定)凡(家人)乞鞫不审,处以罪囚刑罚低一等的刑罚。(死罪低一等是五岁刑),岂能为避免五岁刑,而疏忽死罪母亲的命!景慈应该被执行(五岁刑)刑罚。诏书将景慈流放交州。从此以后又设置了称为流徒的刑罚。”
如果景慈既不下辞服罪也不乞鞫,按照源于蔡廓建议的律令规定,尚能使自己免受刑罚和伦理责难,然而景慈下辞服罪,成为母亲死罪案的证人,因此遭受法官谴责。
引文“其子景慈对鞫辞”正对应《宋书·蔡廓传》所见“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不须责家人下辞”,因此“景慈对鞫辞”,即景慈对“鞫”下辞服罪。可见罪囚家人是面对“鞫”而选择下辞服罪或提起乞鞫的。而向罪囚家人宣读和解释“鞫”,是司法官吏职责。可以推定司法官吏必须用口头的方式对罪囚家人宣读并解释“鞫”。这一程序采用口头而不采用书面的方式,因为无论是秦汉还是南朝,识字人口的比例都不是很高,而且阅读司法文书需要一定专业能力,所以是由司法官吏宣读“鞫”并进行解释,然后要求罪囚家人选择下辞服罪或乞鞫,并记录下来。这种司法官吏与罪囚及其家属进行口头的交流,然后司法官吏将相关情况载于书面的模式,可参见睡虎地秦简《封诊式》的《讯狱》条:
“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各展其辞,虽智(知)其訑,勿庸辄诘。其辞已尽书而毋(无)解,乃以诘者诘之。诘之有(又)尽听书其解辞,有(又)视其它毋(无)解者以复诘之。诘之极而数訑,更言不服,其律当治(笞)谅(掠)者,乃治(笞)谅(掠)。治(笞)谅(掠)之必书曰:爰书:以某数更言,毋(无)解辞,治(笞)讯某。”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48页。
杨文指出,“任提女被判死刑,其子景慈‘对鞫辞,这应处于《唐律疏议》所说‘诸狱结竟,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仍取囚服辩阶段。当时制度仍然允许家人乞鞫”。此处与《唐律疏议》联系,是可信服的。然而杨文认为家人乞鞫制度在“梁武帝天监三年(540)始作为制度废除,并延续下来。”
杨振红:《秦汉“乞鞫”制度补遗》,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08页。引文涉及的家人乞鞫案件导致南梁增设了称为“流徒”的刑罚,上下文没有提到废除家人乞鞫制度。而《唐律疏议》所见的与家人乞鞫制度功能相同规定的存在,证实了从秦汉到唐代,在律令及司法实践中家人乞鞫制度从未被彻底废除。
三读鞫与乞鞫关系
《为狱等状四种》案例一二“田與市和奸案”存在读鞫引发乞鞫的记载,如下:
辤(辞)丞袑谒更治,袑不许。……袑曰:“论坐田,田谒更治。袑谓:‘巳(已)服仁(认)奸,今狱夬(决)乃曰不奸。田尝□毋智,令转□,且有(又)为(?)辠(罪)。田即受令(命)。”它如爨等。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6月,第205、208、209页。
此事发生在县丞袑“论”田之时,这里“论”是执行刑罚之意,《为狱等状四种》多见的“论令”是其完整形式,因此田接受刑罚即称“受令”。执行刑罚之前,可推定县丞袑按照律令“读鞫”即宣读田的罪状,田对“鞫”内容不服,“辞丞袑谒更治”,即下辞丞袑请求重新治狱,此处“谒更治”就相当于乞鞫。这里的治狱相当于秦汉简常见的“鞫狱”,指案件事实的侦查工作。最后,田被袑说服接受了刑罚。这一段引文,“读鞫”具有的救济功能得以彰显,不像张俊案那样徒留形式。而田“谒更治”是针对“读鞫”,这种请求再次调查案件事实的权利符合乞鞫的概念。“谒更治”在“狱决”之后,符合秦律令规定的乞鞫提起的时间,见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以乞鞫及为人乞鞫者,狱已断乃听,且未断犹听殹(也)?狱断乃听之。”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20页。“狱决”即“狱断”。
读鞫与乞鞫关系紧密。
第一,读鞫与乞鞫制度都含有司法官吏宣读鞫文书即罪状的程序。读鞫是司法官吏宣读鞫文书,宫宅洁、张建国等海内外多位学者均持此说。而乞鞫之启动,是在司法官吏宣读罪状之后,见前引《史记索隐》引《晋令》:“狱结竟,呼囚鞠语罪状,囚若称枉欲乞鞠者”。罪囚及其家属如任提女案的景慈“对鞫辞”,也就是面对司法官吏宣读的鞫文书来选择是乞鞫还是下辞服罪。
第二,“读鞫”、“乞鞫”的功能都是避免冤假错案。“乞鞫”为避免冤案,不必赘述。“读鞫”见前引《汉书·万石卫直周张传》“面而封之”的晋灼注:“面对囚读而封之,使其闻见,死而无恨也。”宣读罪状使囚听到,避免司法官吏暗箱操作,提供给罪囚一个要求重新调查案件事实的机会,如前引《为狱等状四种》案例一二的罪囚田一度“谒更治”。
第三,读鞫与乞鞫的时间不完全对应。读鞫是在司法官吏执行刑罚之际,如《后汉书》张俊案与《周礼·小司寇》郑司农注“今时读鞫已乃论之”。而乞鞫的时间则相对来说较为灵活,在各个时代有所不同,大致说来,在案件定罪量刑之后,即可提起乞鞫。已被执行刑罚的人员也可提起乞鞫,《为狱等状四种》、《奏谳书》所见三个乞鞫案例都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