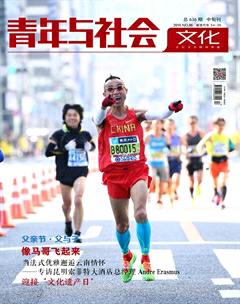陈忠实的葬礼
吊唁

“大多数作家的葬礼看上去都悄无声息,他的葬礼像是一次例外。”
贾平凹穿着深蓝色的衬衣,站在悼念人群第一排靠左的地方。身旁都是深色着装的人。他们神情凝重地看着前方。陈忠实巨大的画像悬挂在黑色的幕布里,仿佛陷入浓重的夜色。画像里的陈忠实身着蓝色的衬衣,同样望着前方,面目安详。他的遗体躺在画像下的白色花丛中,稀疏而整齐的花白头发枕着一本《白鹿原》,身上覆盖着党旗。
陈忠实活了74岁。他是在50岁的时候,有了用来垫棺材的枕头。1992年完成《白鹿原》后,他再没有出版过长篇小说。在中国文坛,尤其在陕西,作为《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有着足以与之匹配的身份。陕西在1980和90年代出现了一批享誉全国的作家,尤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代表。这个春天过后,只剩下贾平凹。
在西安凤栖原的殡仪馆里,许多人料想着贾平凹会上台念悼词,就像路遥去世的时候,陈忠实致悼词那样。1992年的路遥追悼会上,陈忠实念道:“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无论这个事实多么残酷以至至今仍不能被理智所接纳,这就是:一颗璀璨的星从中国文学的天宇陨落了。”
此时,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梁桂走上台去念悼词:“优秀的共产党员……”遗体的一侧,依次排列着国家领导人所送的花圈。
5月5日这个早晨之前,陕西省作协大院里,为陈忠实搭建的灵堂已经接待前来悼念的人士近一个星期。大多数时候,院子里是寂静的,麻雀在院子中间的喷水池上汲水。天气燥热,各种纸质的纪念物纹丝不动,并没有什么风。
陈忠实看上去并不喜欢待在这个院子里。2001年春节刚过,他在西安城里买了二十多袋无烟煤和食物,回到西蒋村祖居的老屋。
这些天,在西蒋村,有许多前来追寻陈忠实足迹的人。包括这个立着“陈忠实旧居”的院子。院子看上去是寥落的。当年陈忠实回到原下,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抽着雪茄。“原坡上漫下来寒冷的风。从未有过的空旷。从未有过的空落。从未有过的空洞。”
白鹿原
春末的一个下午,我通过手机定位,找到了电子地图上那个标着白鹿原的红点。这恰好是一片麦地,青色的麦穗直直地立在塬上,麦地里散落着几处墓碑,看上去有不少年月。天气很热,但过早到来的夏天里,并没有虫子的鸣叫。
一位姓韩的大娘独自走过白鹿原,她是附近的村民。
“《白鹿原》这本书?”韩大娘感到疑惑,“没有读过。”
“白鹿原的景色好得很。”她补充了一句。
从这片麦子地往东北方向走上几里地,经过白鹿超市,白鹿饭店……有一个刚开业不久的白鹿原民俗文化村。村口立着门楼,“仁义白鹿村”的旗帜高高地挑着,厕所的男女标识上分别写着“黑娃”和“小娥”。这里有陕西和各地的小吃。秦腔在仿古的舞台上唱着。
在这有些魔幻的场景里,我想起一位作家说过的话:强烈的想象能成为现实。白鹿原是陈忠实给陕西创立的logo。肖云儒认为,陈忠实就是一个logo。
“作为一个优秀作家能够成为文学的logo,已经很不简单了。如果你不但能够成为文学和文学史上的一个标志,而且能够成为一块土地、文化的标志,这就更进一步了。”肖云儒说。
陈忠实有一张手夹雪茄的照片非常出名。“西部大开发”刚提出来的时候,肖云儒跟他说,这张照片可以做广告:你要了解西部吗?请看我的脸。“他的脸上不是沟壑纵横吗?就像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一样。”
那张手夹雪茄的照片出现在许多地方,包括陕西省作协院子里。
演出的华阴老腔就是春晚上和谭维维合作的那一群人,也是在人艺版话剧《白鹿原》里出现的那一群人。他们敲打着板凳,急速地拨动琴弦,用喉咙涌出的声音唱着那曲经典的《将令》。“将令一声震山川,人披衣甲马上鞍,大小儿郎齐呐喊,催动人马到阵前……”
“我刚才觉得自己没法唱下去了。”张喜民在作协食堂的桌上收拾乐器的时候,低声地说。华阴老腔如今被许多人知道,陈忠实用了很多心。这几位华阴的农民刚才是流着泪走过来的。这是院子里那几天最激越的时刻,却透出更为深沉的悲伤。
“习焉不察、见惯不惯的惯性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它可以摧毁人对事物的惊讶、新奇,也可以摧毁人的激动、痛苦、欢乐、幸福,甚至使人变得迟钝、麻木、冷漠、冷酷。我对陈忠实就是这样的。”文学评论家李星在多年前写一篇关于陈忠实的文字时,感到难以下笔。
在李星眼里,陈忠实不光是一个能坐冷板凳的有沉静之气的作家,而且是一个能冷静地把握环境的作家。柳青曾说,他最讨厌身上有“烧布布味”的作家。陕西话说一个人有“烧布布味”,指的是这个人慌里慌张,静不下来,稍遇挫折就灰心丧气,稍有所得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陈忠实身上丝毫没有这样的气味,这是一种性格。”
农民
作协的灵堂和追悼会现场,贾平凹的一举一动都被相机所捕捉。在这期间,他很少说话,要说的话,也很短。纪念陈忠实的文章,他写得也短,只有283个字。这让他备受质疑甚至攻击。大家设想着他与陈忠实之间的关系。甚至贾平凹的新书《极花》在此时也招来了许多负面评论。
谢勇强是《华商报》跑了多年文化口的记者,他把这些事看在眼里。“这些几十年都在一起竞争、成长的老弟兄之间,感情是复杂,也是真挚的。李星对我说,贾平凹在他家里吃搅团,作协的人都来要字,从门房到年轻的作家,贾平凹趴在地下写了一上午。陈忠实也在他家吃搅团,一吃就是两大碗。如今吃搅团的老弟兄少了一个,贾老师的寂寞,岂是那些等着看热闹的人所能懂得。”
肖云儒看了贾平凹《怀念陈忠实》一文,他认为贾是受到了佛家与道家思想的影响,在这个年龄对于生死问题也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文中的那句“水流原在海,月落不离天”,来自《哭僧》,全诗为:“道力自超然,身亡同坐禅。水流元在海,月落不离天。溪白葬时雪,风香焚处烟。世人频下泪,不见我师玄。”
“有些人炒作平凹和忠实怎么样,都是小人之心。”肖云儒说,“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都是‘炸油条的,都飙着一股劲,这是正常的,飙着一股劲并不是横向地毁坏别人,这是往前走,看谁走得快,是一种良性竞争。”
陕西省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个文学社团就有陈忠实、贾平凹,肖云儒也是其中一员。肖云儒算年龄大的,四十多岁,其他人都是二三十岁。要给社团起名字,贾平凹想了个名字叫“群木”。“树林里的木头不要打横岔,不要闹不团结。你要往上长迎接阳光,迎接风。我们这个社团就是大家争着往上。所以,我觉得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的关系就是在文学的道路上良性的、积极的、向上的竞争。这种劲儿正是陕西汉子的劲儿。”
路遥得茅盾文学奖那天,大家在新闻出版局开一个会,陈忠实、路遥在,贾平凹可能不在,肖云儒在,好多人都在。“我们都还不知道路遥得奖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结果出版社有个人就过来了:路遥,祝贺你啊,你得茅盾文学奖了!陈忠实那个表情就是愣一下,像是被电击了一下,两秒钟以后才反应过来:祝贺你!他下决心就要回去写小说。平凹也有这样的心情,你想《平凡的世界》那么早得了奖,《白鹿原》也得了奖,他得了很多国外的奖,但从来没有得过茅盾文学奖,他就非常着急。我就和他开玩笑:平凹,你不要着急,你的写作状态就和你的一本长篇小说一样,有点儿浮躁。为啥?着急啊。最后他得上了。这些都是好事。文学陕军多少能成一点气候,就跟这股劲儿有关系。跑在第一圈的人都在追赶。不服气的人是在事业上不服气,陕西作家、评论家之间,没有搞小动作的,都拿作品说话。”
往事
这几天,在解放路西安图书大厦的三楼,陈忠实的作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和他的书放在一起的是陕西的几位作家,紧紧挨着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几部作品。《白鹿原》的第一个句子:“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明显是受了《百年孤独》的影响。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潮在1980年代曾经横扫中国文坛。
再往前走几个书架,可以看到柳青的女儿写的《柳青传》。邢小利在做了一段陈忠实研究后认为,如果要理解陈忠实和理解这个时代,很多东西要往前延伸。“我们的很多文化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的,陈忠实的一个师傅就是柳青。”
柳青是1916年出生,1938年5月就到了延安。那时国共还在合作,抗日战争刚刚开始,延安整风还没拉开帷幕。
邢小利是柳青文学研究会的副会长。“柳青这个人是很复杂的,很有价值。通过我们了解这个柳青,应该把那一段历史很多东西都弄清楚。柳青后来对历史进行了很深刻的反思。”
柳青早年顺风顺水,待遇都特别好,到了1966年,被打倒,受到很多折磨。“他的妻子自杀,他自己也自杀过,没死成,他怎么会不反思呢?”
“文革”开始之前的1966年2月12日,作为“民请教师”的陈忠实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
1967年初,春寒料峭,陈忠实从乡下进西安城,为学校养的几头猪买麸皮饲料,走着走着,他看到自己崇拜的柳青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被押在卡车上一路游街。他几乎绝望了:柳青这样的作家都被打倒了,自己还能在文学上弄啥?
那时候,大家都在绝望中支撑。年轻的肖云儒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肖云儒在描述这一段经历时,特别提到一点。“我跟你讲个事情,那时候在报社,我们站一排,都是要挨批斗的,前面是主任、编辑,最后是我,我是‘苗子。介绍到我的时候,我就看到两个女学生很惊异地笑:她们还不知道有这么个头衔。我觉得特别温馨,这个世界还是有穿越政治术语背后的同情和理解。女生的眼光我就一辈子记住了,我一下子就有了信心。”
2012年9月11日,邢小利陪同陈忠实一起去北京参加《白鹿原》出版20周年纪念活动。坐火车,晚上睡不着,闲聊起来。话题说到了“文革”,此时,陈忠实突然激动地说:“那个时代就是那个样子,当时谁都不觉得那是不正常。‘文革中人都疯了,我也疯了。”说到这里,他睁大双眼,把头猛地向后仰。
“他当时曾努力跟上时代的脚步,企望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其实就是紧跟当时的政治形势,并和当时的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他以为这样做就是‘进步的。主观上他不是要做一个紧跟形势的跟风派,但他的思想认识,在当时,缺乏更为宏阔的文化的、精神的和价值的参照坐标,他只看到了当时的历史现实,只受到了当时的影响。”邢小利说,“这种关于文学的认识,在当时,不仅仅是陈忠实一个人的理解,简直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意志。”
1982年11月,40岁的陈忠实调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也就是后来的陕西省作家协会),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从中国文化和精神的谱系上看,陈忠实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也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的经历,他所受的教育,以及由经历和教育所形成的生活观念和思想观念,都更接近于中国农民的生活观念和思想观念。”邢小利说,他还是偏儒家。他对儒家的思想文化的东西读得也不是很多,但这块土地就是儒家的。那个文化是骨子里头的。他一生下来,他妈他爸他村子里所有的人都是受这种观念影响。”
有一句评论陈忠实的话是:“告别权威历史、政治化历史和政治化文学崇拜的同时,陈忠实走向了文学的新的构建。”
1980年代,中国在转型,陈忠实也在转型。
功成
1991年腊月,妻子王翠英到西蒋村给陈忠实送面条和蒸馍。临走,送妻子出小院时,陈忠实说:“你不用再送了,这些面条和蒸馍吃完,就写完了。”王翠英问:“要是发表不了咋办?”陈忠实没有任何迟疑地说:“我就去养鸡。”
在当时的环境里,《白鹿原》能不能出版确实是个问题。而他已经50岁了。前面的路怎么走,他不得不考虑。灞桥就在前面,那是一个自古以来送人远行的地方。是把自己送走呢,还是把文学送走?
陈忠实出生在灞河边上。他在小说《白鹿原》中,称灞河为“滋水”,称浐河为“润水”,意为滋润大地之水。
1992年,完成《白鹿原》之后,他填了一首《青玉案·滋水》:涌出石门归无路,反向西,倒着流。杨柳列岸风香透。鹿原峙左,骊山踞右,夹得一线瘦。倒着走便倒着走,独开水道也风流。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一拂袖。
这一年,他在1992年3月底在广播里听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新闻。当时,《白鹿原》稿子已经被被专程前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两位编辑高贤均和洪清波拿走了。
听了广播大约20天之后,他回到城里的家中。进门后,按往常的习惯随意问妻子,外边寄来的信件在哪儿放着。他看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的信。他回忆过:“待我匆匆读完信,早已按捺不住,从沙发上跃了起来,大叫一声,又跌爬在沙发上。”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说自己叫了三声。不管是几声,总之是人生难得的兴奋。
《白鹿原》将在《当代》杂志上连载,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将会出版。
陈忠实在平静下来之后,对妻子王翠英说:“可以不用去养鸡了。”
版本
在凤栖原的殡仪馆门口,有读者拿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版的《白鹿原》前来悼念。而陕西省作协副主席红柯则拿来了当年的《当代》,这更为少见。
5月4日的晚上,陈忠实追悼会的头一天晚上,西安外事学院版话剧《白鹿原》在钟楼附近的人民剧场演出。我坐在剧院中,并没有回到两个多月前在北京中国剧院里看陕西人艺版《白鹿原》时的那种感受。北京的那场演出后,现场是如雷的掌声,许多看过那场话剧的人,觉得更为接近原著。
在凤栖原的殡仪馆咸宁厅里。许多人在等待着追悼会的开始。最后边的位置站着演员张铁林,他的身边是编剧芦苇。
“《白鹿原》的各个版本的话剧都不太好。”芦苇对我说,“太过于注重形式。”
张嘉译站在人群当中。他是电视剧《白鹿原》里白嘉轩的扮演者。不出意外的话,电视剧《白鹿原》将在2016年底上映。
“电影能在两三个小时里把《白鹿原》的故事讲好吗?”我问芦苇。
“完全可以。”芦苇自信地说。芦苇正在策划《白鹿原》的新电影。他对于自己的剧本没被很好地拍摄心有不甘。
心结
陈忠实的愿望实现了,《白鹿原》成了他棺材里的枕头。许多年过去,陈忠实落后于时代了吗?《白鹿原》讲述的历史截止于50年代,之后的中国呢?
大多数作家的葬礼看上去都悄无声息,陈忠实的葬礼像是一次例外。作协的大多数人都未曾为一次葬礼这么忙碌。
殡仪馆里,贾平凹站在悼念的人群中,显得有些疲惫,站在他旁边的是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彦。他见证了陈忠实生命的最后3天。当载着陈忠实遗体的灵车缓缓通过医院大厅、医院走廊、医院车库、医院大门时,他想起海明威墓志上的那句话:“恕我不起来了!”
“在《白鹿原》之后,他几乎再没有创作‘大东西,如果以长度来说的话,也的确如此。但他在进行着另一种‘长度、‘宽度、‘厚度的创作,那就是扶持人,一个个扶持,一点点扶持,参加各种作品研讨会,为作者新出的作品写评论,写‘腰封,为青年作家搞推介活动‘站台,总之,他是在为他人活着,尤其是为成长中的文学新人们活着。”陈彦说,“在西安的大街小巷,偶然能看到一个挎着破旧皮包的老人,永远是那身灰灰的衣服,走起路来不紧不慢。”
几个月前,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出版,拿到样书后,想送陈忠实一本,可他知道陈忠实的病情,即使是去看望,也没好意思拿书。可有一天,陈忠实给他打来电话:“《装台》我拿到了,祝贺!都听说了,有可能了,我再写点文字。”在医院里,陈忠实送给陈彦一本《生命对我足够深情》,这是他的最后一本书。“我感觉他那时候心里已经非常清楚自己的状况了。书上印着‘感恩阳光,感恩苦难。他认为他是苦难的,他的确是受了很多折磨。而那时,他已经准备好了。”陈彦说。
菊花
陈忠实去世第二天,杨则纬去往省作协,经过那个水池,给灵堂的遗像献上了一束菊花。 从口音里听不出杨则纬出生在西安。而老一辈的作家,几乎都更习惯于说陕西话。
杨则纬卖得最好的小说是《躲在星巴克的猫》。在鼓楼和钟楼之间,有一个大玻璃房,那是一家星巴克咖啡馆,像是嵌入了现代的传统西安。这启发了她的写作灵感。2006年,刚上大一的杨则纬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编辑把她的稿子给陈忠实看了,请他为其写一个评论或者推荐语。
“那天我太激动了,一位文学青年见到文学巨匠的画面请你们想象一下……”她的父母也跟着一起见了陈忠实。陈忠实夸奖了她的作品,并且询问她是否愿意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我的少女时代,常常在深夜里梦想,或者我真的可以成为一名作家。”
2016年4月29日晚上9点半,杨则纬走进一家远离省作协的花店,想为陈忠实买一束花,准备第二天早上去祭奠。
“你好,订花,想要什么样的?”
“嗯,你好,我……我想要菊花。”
“菊花?哦,是给陈忠实的吗?”
“你怎么知道?很多人来买吗?”
“因为我知道他今天去世了。”
那一刻,杨则纬心情复杂,惊讶,哀伤,又隐约感到文学复生的力量。她站在那,说不出话,眼泪快要掉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