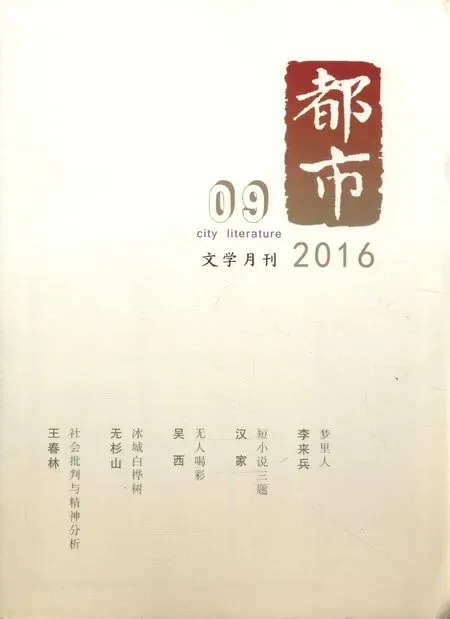社会批判与精神分析
——关于孙频《我看过草叶葳蕤》
王春林
社会批判与精神分析
——关于孙频《我看过草叶葳蕤》
王春林
近些年来,以中篇小说创作而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位女性作家,是80的孙频。不仅每年都会有大量作品发表问世,而且其中一些作品往往还会在诸如《收获》《钟山》《花城》等大刊去掠得头阵。《我看过草叶葳蕤》(载《收获》杂志2016年第3期),便是近期内难得一见的一篇佳作。如同孙频的其他很多作品一样,这篇小说的叙事切入点,依然是男女之间的畸形情感问题。男主人公李天星是一个身世颇为坎坷畸零的流浪画家,依靠在湖边摆画摊替别人画像而勉强谋生。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便不幸丧生于交城当年一场曾经轰动一时的铜矿事故。从此,外婆就成为他的根本依仗:“他从小和外婆相依为命,只有摸着这两只乳房,他才会觉得自己没有被这世界遗弃,这乳房便是他的家。”遗憾的是,到了他十岁的时候,相依为命的外婆也死了:“外婆顺便带走了那两只干瘪的老乳房,也就带走了他的家。”如此一种孤苦无依的少年经历,就从根本上奠定了李天星很难融入到某种群体中的孤独精神底色。好在外婆临死前坚持让舅舅答应一定要继续供他上学,这才有了李天星十九岁时到省城太原的一所中专学校学习美术的可能。四年的中专学习时间并不算长,但却从根本上影响到了他未来的人生道路。因为有过这四年的省城生活,李天星便不再安心仅仅在一座县城的小学里度过自己的人生:“他想,他怎么可能在这个地方结婚,在这结婚了就意味着永远被钉在这里了。他可是要成为画家的。”一方面与他的少年经历有关,另一方面则缘于他要离开交城这样一个小县城去往远方的生活梦想,那个时候的李天星在别人的心目中变成了一个难以理喻的怪物。与李天星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相伴生的,是一种难以抵御的孤独与恐惧。但也正是在他拼力抵御孤独与恐惧的过程中,他在县百货公司邂逅了命中注定要彼此缠绕一生的一个售货员杨国红。
认识杨国红的那一年,是公元一九九六年。那一年,李天星年仅二十岁,而杨国红却要比他大了整整十三岁,时年三十三岁。那时的杨国红虽然已经结婚多年,但却不仅没有孩子,而且夫妻感情还非常糟糕。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和我丈夫已经好几年没有性生活了。”如此一对男女相遇的结果,自然就是干柴烈火一般地碰撞与燃烧:“现在他明白他们的身份了,一个背着丈夫偷情的女人和一个需要女人的单身男人。原来她确实是有丈夫的,只是,她和他才更像是栖息在同一个星球上的居民。他们都是被抛弃的人。”在李天星的感觉中,他和杨国红之间的偷情关系,既带给他一种强烈的罪恶感,也带给他一种对危险的亲近感。男女主人公两位的萍水相逢,马上就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千古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与此同时,孙频的人物设计,也还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很多年前黄子平一篇著名的论文《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在这篇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论文中,黄子平有效借鉴西方的原型批评方法,前后跨越千年时间,把古典文学中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现代文学中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与当代文学中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绿化树》联系在一起展开讨论。黄子平把这样三部作品放在一起进行讨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这三部作品都有着一个中国传统所谓公子落难小姐多情的故事原型。《琵琶行》中是被贬的江州司马遇上了浔阳江头卖唱的琵琶女,《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是落魄漂泊的穷知识分子“我”遇上了烟厂女工陈二妹,《绿化树》中是下放劳改的知识分子章永麟在劳改地遇上了劳动妇女马樱花。然而,虽然存在着共同的故事原型,但由于出现的时代以及写作主体的不同,三部作品各自的思想内涵其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琵琶行》旨在借曾经红极一时的琵琶女后来的不幸遭遇抒发被贬谪为江州司马的诗人自身强烈的怀才不遇愤愤不平之意。出现于五四时期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启蒙思想背景,一方面表达对于底层女工的一种人道主义同情,另一方面也表现着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相濡以沫。创作于“文革”结束后的《绿化树》,在充分关注表达畸形政治时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遭际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着知识分子的自我忏悔意识。孙频的小说之所以能够让我们联想到黄子平这篇《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的论文,根本原因在于,她的人物关系设定也暗合于中国传统所谓公子落难小姐多情的故事原型。后来在杨国红的强力推动下上了大学的李天星,自然是落难公子,而下岗后自谋生路的杨国红,则可以被看作是多情的小姐。关键在于,虽然故事原型相同,但由于故事发生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孙频在其中注入的,显然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时代内容与思想内涵了。
李天星一九九六年初识杨国红,时间仅仅过去了一年,伴随着下岗潮在交城县的蔓延,杨国红就已经被迫下岗了。对于始料未及的下岗,毫无精神准备的杨国红无论如何都难以理解和接受:“我二十岁进了这单位,只以为生是这里的人,死是这里的鬼了,没想到三十多岁的时候就下岗了,就忽然没有工作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国营单位里居然会下岗,这让人怎么活?国家说让你没工作就没工作,说让你死就让你死。我到现在才知道了什么叫小老百姓。”是啊,国家是什么呢?其实,从理念上说,杨国红根本就不可能搞明白国家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庞然大物,却毫无理由地剥夺了她工作的权利,让她成为一个失业的下岗者。然而,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下岗是一种不可更改的事实。下岗了,怎么办?人总得想办法活着。于是,刚刚与丈夫离婚不久的杨国红,就只能够开了个小商店以维持生计了。正是面对着杨国红以及她的同类们拥上街头变身小贩的不幸遭际,多年之后的李天星方才恍然大悟:“从没有过投票权的人们其实节日更多,什么都可以成为节日。下岗是节日,万民变成小贩拥上街头抢食也是节日。它们都是节日。再后来李天星渐渐想明白了,节日不是庆贺,节日是匮乏,是补偿,所以,人人都渴望节日。”事实上,杨国红们的下岗,对于李天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夹在人群中的李天星在这个九十年代末的春天里第一次闻到了那种类似于各种菌类混杂在一起的腐烂的味道。他再次惊恐地感觉到,他厌恶这里,他必须逃离这个小县城。”关键在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从交城这个小县城逃出去的李天星,他自己的命运遭际也很是不堪。先是连着三年的高考相继败北,好不容易第四次高考成功,终于考上了一所远在杭州的美术学院,但等到他大学毕业,企图通过大学毕业证改变命运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这张毕业证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他突然惊恐地发现大学已经什么都不是了,读完大学可能只是一个失业的开始。”混杂在四处求职的大学生中,李天星目睹了大学生一种集体“献祭”的场景:“虔诚的,急切的,恐惧的,每个人都前所未有地端庄、恭敬和谄媚,都前所未有地伶牙俐齿,都前所未有地害怕被遗弃出这集体的节日。”就这样,李天星再一次赶上了一个盛大的节日:“这是属于大学生们的节日。盛大的、隆重的、无一人可以幸免的节日……他想起了多年前的下岗工人们集体拥上街头抢食的场面。他忽然明白了,确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节日。他只是,碰巧把两代人的节日都赶上了。”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方才明白,“节日”一词被频繁使用在孙频的这篇小说中,其实带有鲜明的反讽色彩。正如同叙事者曾经强调过的“节日是匮乏,是补偿”一样,究其根本,“节日”在这个小说文本中更多地带有人生劫难的意味。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思考追问的一个问题是,杨国红与李天星们的以“节日”的方式呈现的人生劫难是谁造成的?究竟是谁才应该为他们不幸的人生遭际承担责任?细细想来,不管是杨国红,还是李天星,他们个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毫无过错可言。无论所谓的国企改革或者大学生的自主择业从执政者的角度看有多少合理的依据,对于杨国红与李天星这样的个体来说,他们事实上都只能是历史的祭品或者牺牲品。从这个角度来说,孙频的这篇《我看过草叶葳蕤》其实潜隐着极鲜明的社会批判色彩,其批判矛头尖锐犀利地直指不合理的社会政治运行机制。
然而,孙频的《我看过草叶葳蕤》却并不仅仅只是一部社会批判小说,社会政治批判的思想内涵之外,作品还拥有另外一层不容忽略的深层精神分析内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精神分析内涵是通过孙频带有突出“冒犯”意味的情色描写而表达出来的。实际上,只要充分尊重文本事实,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对于性的描写在这篇小说中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就此而言,一个切合事实的结论就是,《我看过草叶葳蕤》既是一部社会批判小说,也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情色小说。但千万请注意,虽然孙频在小说中有大量性行为与性场景的描写,但这所有的描写都不具有一般所谓色情描写的暗示与挑逗意味。与暗示和挑逗恰恰相反,孙频的相关描写,只能让我们感觉到在很多时候性甚至干脆就变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精神苦役,令人倍感厌恶。比如,就在李天星万般无奈地成为流浪地摊画家之后,曾经遇到过一位心理畸形变态的成衣厂裁缝女工。这位女工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需要不断地和男人做爱:“和我做爱吧,好吗,我喜欢做爱,只有在和男人做爱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这世上所有的痛苦都被溶解了,只有在那一瞬间里,我才觉得我和这个人融为一体了,我太想要那种融为一体的感觉了。”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女性强迫男性的场景出现了:“她已经不顾一切了,他恐惧地感到,她要强迫他。”“他再一次闻到了那种似曾相识的血腥气,他背上有点不寒而栗,然而他的下面已经脱离了他的身体,蜷在她手中无耻地硬起来了。”“这让他愈加难受愈加痛苦,他只觉得被眼前这个女人强奸了。汗腥味、泪水味和一种越来越尖锐的刺痛搅在一起,围剿在周围的空气里。”这哪里是在写性爱,这简直就是在真切展示一种处于残酷现实围剿状态中的精神的痛苦与无奈。当然,说到借助于性爱描写凸显人的内在精神困境,小说中最精彩的一处,恐怕还是对于杨国红年老色衰后为了讨好李天星身穿镂空睡衣跳舞那个残酷场景的描写:“她站在那里,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蕾丝镂空睡衣。因为睡衣是镂空的,透过睡衣他看到了里面蠢蠢欲动的两只乳房,不惟是乳房,连小腹上层层叠叠的赘肉和松松垮垮的臀部也一览无余。”但就是如此一个衰老不堪的躯体,居然还要扭来扭去地要拼命讨好李天星:“她忽然冲着他撩起了睡衣的下摆,对着他露出了自己那松弛而苍老的臀部。紧接着,她又随着音乐的节拍扭了几扭那苍老肥白的臀部。”面对着杨国红如此一种不堪的努力,李天星终于忍无可忍地大叫制止。一方面,杨国红比李天星大十多岁,另一方面,她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下岗多年仅仅靠开一个小商店勉强度日,但即使如此,为了尽可能地讨好回交城过春节的李天星,她却还是要做出如此一种没有丝毫自知之明的努力,其精神深处的那种种隐忍、自卑、焦虑以及猥琐,细细想来,真的是几欲催人泪下。
相比较而言,更能够从情色描写中见出精神分析深度的,恐怕还是作品中关于李天星与那位在公司里位高权重的艺术总监之间性关系的相关段落。首先,只有在面对着自己必须以身体去小心翼翼地加以伺奉的顶头上司的时候,李天星才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其实早已失去了自由:“在这个夜晚他忽然明白过来,这么多年里,他看似自由,孑然一身,其实身心都不是自己的。其实他从来就没有过自由。”于性关系中发现不自由,孙频此处难能可贵的一点,实际上是一种对于禁忌与自由之间关系的洞悉与书写。其次,也正是在与艺术总监的对话中,孙频不无犀利地一语道破了当下时代情欲泛滥的精神实质:“也没有什么奇怪吧,现在的人都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去做什么该去想什么,或者说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相信的时候,人们就会开始向情欲靠拢吧,纵欲成了一个社会必然的需要。要不然做什么?大脑简单,心灵空虚的人们……大约也只有靠情欲,所有人才会觉得暂时总有点事做了,不必有那么多的痛苦,也不必再思考那么多无用的东西。我们只是一个最渺小的个体,不随波逐流,我们能做什么?”是啊,作为普通不过的中国人,身处现行社会政治运行机制之中,除了近乎于虚无地随波逐流,真的什么都做不了。第三,或许正是因为受到艺术总监洞见启发影响的缘故,李天星于一刹那间发现了同样的偷情行为在时隔十年之后的意义变化。十年前:“他和杨国红站在漆黑的煤屑里不顾一切地做爱。那时候他觉得自己是整个时代的叛徒,是独一无二的,他和杨国红做的是当时别人都不敢做的事情,他敢去挑衅整个庞大的社会秩序。那时候无论别人怎么看他怎么说他,他都觉得自己和杨国红不仅仅是在偷情,还有点像英雄在追求什么。”但十年之后呢?“而现在,情境与十年前如此相似,质地却完全不同。他不仅仅是在和一个女人偷情,更是在被一条巨大的深不见底的河流裹挟着向前走,他不过是河谷中的一粒石子,和其他所有的石子没有任何不同。他再不出奇,再没有英雄色彩,更不用说叛逆。他单单只是在和一个女人为了情欲而偷情,而且,这种偷情居然是服从秩序的,是顺流而下的,是合理的。”就这样,同样的偷情行为,在时隔十年之后完全变了味儿。十年前的偷情,是带有英雄色彩的反叛行为,到了十年后,却变成了一种丝毫没有英雄色彩的对秩序的认同行为。这哪里仅仅是在进行性行为的描写,这简直就是一种格外精妙的关于性行为的社会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深度分析。
说实在话,能够把一部情色小说悉心经营到具有如此一种精神分析深度,具有如此一种高妙艺术境界的地步,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从其中见出的,也就只能是孙频的下笔之“狠”,透视社会与人性之犀利,以及她内心深处一种简直就是在普度众生的悲悯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