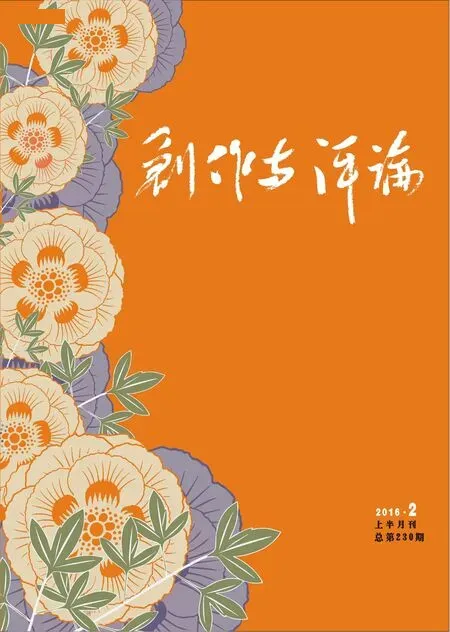弃绝者的自言自语——丁东亚小说一瞥
○谢尚发
弃绝者的自言自语——丁东亚小说一瞥
○谢尚发
初读丁东亚的小说,一种来自俗世生活中不为人知的陌生感油然而生,那些被压抑的声音如同在午夜发出的呜咽悲鸣,带着阅读者投入到似真似幻的梦境之中,疲于奔命地寻找自我的真实存在及其意义和价值。陌生感的获得并非仅仅只是梦的不真实与突兀,更来自于它对当下生活的强行介入,更是一方“内在的外来者”的角色争相展示自我的舞台,从而上演了一幕幕“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好戏。也恰恰是这种阅读上陌生感的获得,丁东亚的小说书写以迥异的风格区别于其他80后作家的创作——当一批批80后作家醉心于现实生活中无奈、压抑与恣意放纵、自我哀怜等的描写的时候,丁东亚已经将他的笔触伸向了心灵深处最幽暗的场所,进而试图揭示被埋在海水之中的冰山的真面目,让稀松平常的生活变得五彩斑斓,且毋庸置疑。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丁东亚的小说可以称之为是“弃绝者的自言自语”:一个由疯癫者、痴傻者、自闭症、忧郁症、妄想症等患者组成的世界,他们靠着梦、谎言、欺骗来维持着彼此的生活。然后在各自的相遇中,撕扯着他们的肉体和灵魂,一同坠入虚无之中。丁东亚的弃绝者形象很明显地和现代文学的传统是接续的,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祝福》,郁达夫的《沉沦》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这类弃绝者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丰富的谱系,深究他们弃绝背后的历史,或许能够得出一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史”。但是对于丁东亚小说中的弃绝者而言,他们没有拯救的希望,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何为拯救,拯救之所从来。而实际上,他们根本无需外在的拯救之力量的到来,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他们的拯救之希望,他们所构成的世界就是他们的完美天堂。
一、梦的书写者
翻开丁东亚的小说,一个最为基本的核心要素便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梦。无处不在的梦几乎构成了他小说的全部,从而在阅读的感官中,很难弄清楚丁东亚所写的到底是现实的生活,还是他自己的一个糊里糊涂的梦。在这些小说中,任何一个随时出现的人物都是伟大的造梦师,他们借由自己丰富的想象构造出亦真亦幻的梦的世界,不但要自己沉醉于其中,还要将之昭示为整个世界的存在。他们俨然是一群现实世界的思想者,沉思着人世间不为人知的、最为隐秘的存在,哪怕是一片落叶之于他们也是伟大的奇异世界。所以,充斥于小说之中的,就是一种孤绝而独立的感觉,一种被弃绝之后无奈又感伤的境地,且在这种感觉中夹杂着恐惧、欢欣与疯狂的热爱。“我感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诡异虚渺的梦境。”“或许是天气的诱使,这些日子,我开始在梦中迷失。”他们宁愿沉浸在梦中也不愿意醒来,哪怕那梦是空虚无边的深渊,他们也愿意堕落在那深渊中。由此出发,他们可以想象出一个比现实世界更为斑斓的所在,“我在梦里总是看到一顶火红的轿子在空中飘来荡去。”“我在梦里看见你妻子夜晚时候站在我们床前,看着赤裸裸的我们。”于是对于他们而言,梦直接就是现实生活,或者说现实生活只不过是梦境的重现而已。所以在他们看来,生活往往在梦中已经被提前预演了,所谓的活着只不过是证明梦真的存在过。“其实每个人都像是活在一个梦里,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我在梦中竟看到了她死去的样子。”“其实我知道他不过也是一场梦,而在梦醒之前,我还是想要在他构筑的这场无终的梦里活着,直到有天他感到厌倦,先于我醒来后离开。”现实生活与梦境一而二、二而一的交融状态,最终让我们看到了丁东亚写作的高明之处——在那些已经被写烂了、写俗了的生活之中,发现那些从不曾被触碰的东西,因为它们早已经被一种称之为是“正常”的东西给掩盖住了。丁东亚借助梦的形式,给我们揭示了日常生活中被“话语的权利”所压抑的存在,并以此来纠正俗世的偏见与执念。或许丁东亚并没有“纠偏”的野心,但是他的小说的的确确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平静水面之下,有着多少激流和险滩,对于我们进一步地认识我们的生活,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虽然有些反讽,却也有一种透心凉的觉醒。
与梦相关,丁东亚的小说注重对生活中的谎言、欺骗等进行揭示,仿佛任何一个人都只是故事的一种讲述方式而已。并且在这种讲述中,掺杂着大量的虚构、任性和不负责任的添油加醋,以至于我们越是看到了某一个人丰富多彩的生活有多么热烈刺激,就越是能够体会到这种生活的表面之下是拥有着多么复杂而又幼稚的自我想象与欺骗在其中。他们不但将自身的真实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来进行架空,并且还试图将这种被架空了的想象当做一种真实来强加给别一个人。而实际上,这或许只不过是他们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已,因为非如此不可,否则难以窥探到生活世界的真实存在。在《隐秘盛开》中,那个心理咨询医生韦多林,正是被精神病患者萧童拉进她的世界中的一个“正常人”的代表。或许他们都是生活的“冷静的旁观者”,只是一个被贴上了病人的标签,一个被贴上了疗救者的标签。这两个看似对立面的存在,只不过是生活的一体两面罢了,是不可分离的那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而已。实际上,在丁东亚的小说中,确认生活是梦境,不仅仅是通过做梦,还通过记忆、编故事等方式来试图证明生活就是梦的真理。在《风行无址》中,第一人称的交替叙事方式,呈现了一个狭小的格局中,双线结构的精致存在形态,当“我”向“她”诉说“她”就是“我”多年前失散的妹妹的时候,“她”其实早就明白,“其实我知道你根本就没有一个被理发师带走的妹妹,那不过是你编造的一个故事而已。”最终连“我”自己也承认,“我出生、长大的那个坐落西北之地的偏远小镇尽管流传着许多离奇诡异的故事,却根本不存在一条叫‘九道’的街道和那个将孩子送人的习俗,更没有过一个挑着火炉走街串巷的剃头匠。”当然同时,为了刺激“我”,“她”同样在虚构着故事,一个和男人邂逅的故事。“其实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个叫A的男人,他不过是向我索要电话号码的其中一人而已。”丁东亚只是用了一种较为荒诞的形式,给我们揭示了庸庸碌碌生活之中,隐藏着的那些人尽皆知又谁都不知的秘密——我们不正是在许多时候,靠着谎言来过日子的吗?在我们随口说出的话中,有多少是真实的呢?这也正是那些弃绝者之所以成为弃绝者的原因,因为对于谎言来说,他们是真正的真实,他们代表了震撼人心的真诚。所以他们不可能容于谎言的世界之中,终将成为弃绝者。
使用怪诞的形式来揭示生活谎言的本质,是丁东亚常用的手段之一,这在他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另外一个牵涉着梦的便是黑夜,因为丁东亚很少让白日梦窜进他的小说中,所以黑夜就占据着绝对的位置。梦多半发生于黑夜之中,唯其在黑夜中发生,才让弃绝者真正地看清生活的可弃绝之处。梦同时又是温暖明亮的,以其独特的存在映照了黑夜的不堪,那么弃绝者完全可以以一个更为清晰且明确的理由,将黑夜置之于自己的身后,轻飘飘地翩跹飞翔,一直飞到他们渴望已久的神圣天国——那里,阳光明媚、繁花似锦,草长莺飞、纸鸢乱空,那里同样有森林的幽深却寂静的属性,也有田野的广袤与安闲之相。然而梦毕竟是与黑夜相连的,因此本应该明亮温暖的梦总带着黑暗的阴影,幽灵一般徘徊在做梦者的周围,所以他们作为弃绝者,又不免落入到黑夜之中,唯独通过做梦,来安慰一己的灵魂。“我确信是我把自己放逐在了黑夜。”只有放逐在黑暗中的人,才能够独享梦的美妙时刻,才能够在梦的残忍或温馨中窥探到生活的实质。尤其是在小说《请你将梦带出黑夜》,对于黑夜、梦,以及对于记忆的刻骨铭心的体验,提请任何一个阅读者,黑夜之漫长恰是美梦之延续的最佳时刻,而那些美梦或许只不过是过往的记忆累积而成的一段故事,只是以梦的方式被讲述出来罢了。所以可以说,弃绝者是一群喜欢暗夜的人们,他们奔跑在黑夜中,那么轻盈又那么实在——他们轻盈,是因为他们总是在梦中生活着;他们实在,是因为他们的梦又总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二、以虚无之名:弃绝者和他的肉体与灵魂
丁东亚在对梦的强调中,牵连着谎言、欺骗、黑夜、记忆等,在在宣告了一个真实可触的世界之虚无的本质。我们所熟悉的可能只是我们记忆中所保留下来的东西,而记忆又是那么的不牢靠,正如梦的不真实一般。在一个如此难分真假的世界中,以虚无之名,丁东亚让一群弃绝者,讲述着他们弃绝和弃绝他们的故事,以一种突兀生硬的感觉将自我与世界拉开一段距离,唯独此,才能冷眼旁观热闹的凡俗人世。所以这一群弃绝者都是迥异于常人的人,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弃绝的故事”。
在这个群体中,病人是最常见的。然而他们的疾病并非来自于他们的身体,而是来自于他们的灵魂。这一点使丁东亚的创作接续了鲁迅的《狂人日记》的传统。在丁东亚的小说中,这一群弃绝者所患疾病都是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自闭症、忧郁症、妄想症等是他们病历中常出现的字眼,从而他们也必定会被俗常的人世所弃绝,被关在了远离都市文明的乡下——被称为“精神疗养院”的地方。于是他们得以用自己独特的身份,甩开现代城市的文明病,他们不用再以虚伪、谎言、欺骗大行其道于都市的角角落落,他们终于可以赤裸裸地将自己的灵魂展露出来,大步流星地行走于天地间,正直而狂傲,真诚而狷介。因此,在读丁东亚的小说之时,我始终有一种期待已久的感觉,因为太多80后的小说因其取材的单一性导致了大规模的雷同现象,所以当有一个小说径直关注生活中那些“不正常”的领域的时候,我以为丁东亚的小说其价值和意义是超乎了同时代人的,给予我们以深刻又独到的观看生活的智慧。那些患病者不异于福柯书中所分析的那些被权力压抑的人,他们很难掌握话语的权力,只能被驱赶上“愚人船”,贴上病人的标签。
同样地,在这一群弃绝者中,还包括精神障碍者,疯子、傻子、癫狂者等,甚至包括私生子、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沉溺酒缸中的“酒鬼”和能够通神的“巫婆”。与正常的生活相对立,这是一群被以各种理由赶出正常生活的弃绝者——他们之称为“弃绝者”,就是正常的生活世界将他们永远地遗弃,而他们也自觉地弃绝了那个宣称自己是正常的“生活世界”。《风行无址》中互相以编造故事和瞎话的方式来折磨自己并进而折磨他人的一群;《如是我闻》中杀人者长柱以死亡来宣告自我的存在和弃绝、酒鬼长胜以酒精的麻醉来获得飞升的感觉、吴能迷醉于乳房而不能自拔并最终死在对乳房的痴迷上、没有名字的人更是以自己的存在宣告了自己的不存在、那个做着发财美梦的空心人和他的疯子媳妇儿与儿子们,直到最后,一把火将所有的弃绝者全部烧毁,连那个可怜的从火堆中幸存下来的傻子也最终被处以火刑——这不禁让人想到因为宣扬真理而被判处火刑的先知布鲁诺,以及因为天体运行学说而受到鞭尸的哥白尼等人。在丁东亚的小说中,几乎都是以弃绝者作为核心人物,来编排他们的生活和故事,从而传达了不为人知却实实在在存在的真理。或者丁东亚就是要用一种让人感觉到膈应的方式,来提醒那些沉醉于谎言和欺骗中的人们,他们所过的生活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生活罢了,所谓的正常生活,就是隐藏起自己真实的面目和初心,而以虚假和伪装示人,并径直将虚假和伪装作为存在的真实。
当一个世界不以真实为真实,而是以虚假为真实的时候,他们就跳入到了生存的水深火热之中,互相间的倾轧、杀戮、战争,以至于日常生活中的争风吃醋、煽风点火等等,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他们是一群“正常的”身体和智慧的消耗者,以他们的聪明才智消耗着他们的智慧,干出毫无价值却自认为价值满满的事情来,宣称自我的成就。这一切都在弃绝者的世界里轰然倒塌,他们以他们的疯癫、痴傻、病体一语中的地直指现代生活的文明病。从他们的视角看去,现代生活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装”而已,那一整套自欺欺人的把戏只不过是可笑的自我掩饰罢了。所以那些精神病患者必然是要走到遥远的乡下,他们疗养的地方都是远离城市的净土。这也是弃绝者拯救自我的地方,既是从身体上远离现代文明的污染,也是在精神上、灵魂上给自己找寻一块诗意的栖居之地。
但仅仅只是拥有这么一块远离现代文明的野地还远远不够,以虚无之名,弃绝者还要找寻心灵上的解脱。如何在污浊的人世用了痴傻、疯癫和患病者的形象来戳破普遍的谎言之后,安慰一己的灵魂不至于在孤绝中陨落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是弃绝者,就注定了他们是孤独者。孤独者前行的路上伴随他们的拯救之所来,正是丁东亚给现代生活开出的一剂救命良方。在弃绝者的追问中,拯救之所来有四个方向。其一,是佛陀的世界,包括瑜伽的静思与佛经的启迪。在小说的书写中,来自佛陀世界的梵音袅袅代表了一种庄严清净地的神圣和崇高,奔着这样一个清洁的世界,弃绝者寻找到了安防一己灵魂的神龛,并将之虔诚地供奉在那里,作为顶礼膜拜的日常功课。丁东亚不但要让弃绝者沉醉在瑜伽世界中,借以修身养性,更是在小说中多处直接饮用佛经经典,《金刚经》是其中引用最多的一部。弃绝者正是用了这样的方式,来点化迷途中的现代人,一语惊醒或者循循善诱。只有勘破红尘的种种虚妄与不真实处,才能领悟大智慧,才能得到大解脱。其二,是古中国的诗意世界,那来自遥远时代里的喃喃细语。这几乎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远离,正如荒野是对现代都市的空间上的远离一样,久远的古中国的形象正是现代中国的时间上的对立面,是那个沉迷于声色犬马、灯红酒绿,日日纸醉金迷的现代生活的古典对应,更是缺乏诗意和诗情的现代世界的绝佳的讽刺者和挖苦者。所以古中国的诗意经典《诗经》,成为弃绝者的拯救之来源,也是弃绝者借以敲醒现代人的最好的锤子。正如小说中的叙述那样,“可是那晚她熟睡之后,我还是用绳子将她绑在了床上,生气地用木棍敲破了她的头。”但弃绝者是不会敲破谁的头颅的,他们只能在虚无中敲破智慧的大门,敞开永恒而光辉的世界。其三,是古代的医学典籍,它们仿佛成为医治现代文明病的最佳药方,径直成为丁东亚书写的一个核心焦点。我私下里猜测,丁东亚应该掌握了不少医学知识,尤其是中医药学的相关知识。他如此着迷于对疾病的描写,又如此着迷于对疾病的治疗,我想应该是他发达的医学知识促使他不得不如此。在小说中,弃绝者径直成为书斋里的饱学之士,看不到他奔波忙碌于现代都市的货币哲学,反而总是看到他在自己父亲死后留下的书房里拼命阅读的情形(《请你将梦带出黑夜》)。《本草纲目》也时不时地站出来,对现代疾病指手画脚。可以想象,来自古老时代的中医药智慧,最终能否在弃绝者的使用中拯救现代文明不可避免的衰败,是完全有理由值得期待的。其四,是古典音乐,尤其是带着宁静、悠长有明亮色调的莫扎特、李斯特等名家的曲子。以音乐拯救灵魂,是弃绝者开出的最符合现代生活的药方,因为它完全符合了现代人虚伪的一面——以艺术之名附庸风雅。倘若他们的虚伪中真的能够带给他们一丝古典音乐的教养,拯救之可能便会最终发生。哪怕是虚伪的,这种用音乐来疗救现代文明病痛的方式,也是值得一用的,纵然作为尝试。从这里,可以看出丁东亚的别有用心,也可以看出他的款款深情,以及他焦虑的内心。毕竟,他就是这“正常的”生活世界的一员,那些弃绝者与其说是在努力地说明自己从而来拯救他人,不如说他们首先要拯救的就是丁东亚本人,通过丁东亚来实现最初的拯救目的。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作为弃绝者的书写者,丁东亚早已经被这些拯救过了,是经过佛陀世界、古中国的诗意世界、中医智慧和音乐精神清洁过的灵魂,所以他才大胆地尝试用弃绝者的形象,来以虚无之名拯救他人于现代生活世界的深渊之中。
无论如何,丁东亚笔下的弃绝者仿佛永远是虚无的存在,他们不真实,他们也不相信真实,他们宁愿在自己虚构的故事中存活,也不愿意在青天白日下庸常的现代生活世界里存活。然而虚无或许恰恰只是他们的假借之名,实际上他们以虚无的名头,直指现代生活的病入膏肓,以自戕的形式来唤醒沉睡的人们——他们在做梦,也在歌唱,却唯独看不见最真实的存在。
三、惆怅的诗意
丁东亚的小说,使用的是一种略显生涩又别扭而实则是韵味悠长的欧化长句子式的语言,这和他的弃绝者形象一起,给阅读者带来了极其怪异的陌生化效果,也从而将自己与其他80后写作者区别了开来。这种欧化长句子的形式看似是一种幼稚的模仿和套用,背地里却显示出了丁东亚的别有用心。用这种略显别扭又稚嫩的方式,丁东亚在小说中营造了一种“惆怅的诗意”的感觉,独特的属于南方小城的生存意境。在一个缺乏诗意的年代里,丁东亚执着地用异域的语言方式来塑造属于自我生活的诗意氛围。如果用海德格尔的言说方式,我们可以追问,“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丁东亚用弃绝者的形象和欧化的句式给出的回答是:贫瘠时代里,更应该营造诗意,哪怕这诗意中充满了惆怅的思绪。说来也奇怪,丁东亚非要用一种东西杂糅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诗意语言:明显的来自古中国的那些言语要素,被强行地塞进了欧化的句式之中,在不伦不类里显示出一种语言的张力,让人迷醉在这样的诗意世界中。语言构成要素的中国性与句式构成的欧化特点,让人在别扭的阅读体验中,觉察出一丝丝魅惑的气息。
此时,萧童已回到先前抱膝沉思的坐姿。那顶飞旋空中的红轿子的暗影犹似一束火焰闪过韦多林的脑海时,萧童突然大笑起来,秋日的浮躁在她干净而怅惘的笑声中瞬即膨胀起来。他转过身惶恐地看着她。(《隐秘盛开》)
夜风裹挟微弱的声音穿过梦境从遥远的无名之地吹来叩响那扇紧闭的房门,造梦师从黑暗中醒来。之后他将你唤醒,告诉你你又一次在夹竹桃盛开的季节于他缔造的世界死去。多年以来,这个你梦中眉目疏朗、性情温和且寡言的情人,冷峻面孔下深藏着他者无法猜测的哀伤。甚至一次次在他温暖的怀抱醒来之际,你渴望他成为你真实且永不背弃的丈夫。我知道他早已成为你生命幻象空间不可缺失的一员。你说你曾在一个飘渺浑沌的午后睡梦里问他为何如此凄伤,他只是看着你,问你是否听到了那吵人的花开声。
(《请你将梦带出黑夜》)
这样的例子在丁东亚的小说中比比皆是。一方面是古典的忧愁意象,一方面则是别扭的欧化长句子,在阅读体验中,那些鲜明又略带忧愁的意象仿佛是要撑破整个句子的容量,从而满溢出来,流淌一地——那不是语言的饱满之爆炸,而是诗意的自然之流露。丁东亚近乎偏执地想要在现代俗语的世界中寻找到古典的诗意之端庄,又偏偏不使用明清小说里的那种近代白话的方式,而是借用来欧化的句式装载古典的文化意象,确实奇哉怪也。也恰是这奇哉怪也,带来的审美体验是经久不息的。
在阅读丁东亚的小说之时,你会感觉到他的小说中,意境的营造往往大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其说是他是在讲述一个优美绝伦的故事,不如说他是在书写一种难以忘怀的人间处境——那来自生活深处常常被忽略的一部分,以及那深埋在我们内心之中的奇异感觉与不知不觉中构筑起来的奇思妙想,甚至是虚无缥缈的梦境一样的悠远遐想。这种遐想连接着古中国的风习,在古代诗词的世界里早已存在了百年千年,竟然以幽灵的方式重又出现在现代的世界中。秋风、秋叶、雨水、树林、菊花、夹竹桃、蓖麻等是常见的意象,一种素净、典雅又略带忧愁的感觉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作为灵魂的韵贴,萦绕在阅读者的心间,久久不能忘怀。其中,菊花意象的一再出现,不得不让人想起古中国的诗歌世界中,由那些风流雅士们所赋予它的种种附加的意义。尤为重要的一点便是,菊花作为四君子之一的气节,恰好符合了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弃绝者的形象之设定与假想——奔忙于现代性的器物世界中逐渐迷失了自我,又在迷失之中努力寻找拯救之所来,便犹如一朵菊花一般,虽然遭遇繁霜的打击而凋零,却宁愿抱着枝头老死空中,也不愿意坠落红尘成为粗鄙的人世间的一种俗常的代表与象征。而在弃绝者的口中,菊花又带着满满的忧愁和伤感,“你知道我最是偏爱菊花的。若是我死了,你一定要照顾好那片菊花,像照顾我一样,每年清明时节,采那最美的一束放到我坟前,告诉我你没有将我忘却。”一种死的暮色气息,加上菊花的典雅芬芳,构成了丁东亚小说中独特的诗意境界,我们可以称之为是“惆怅的诗意”。所以丁东亚在诗意贫瘠的年代里,努力地践行着他“惆怅的诗学”的观念,书写着弃绝者的故事,淡淡哀愁里寄托着浓浓的相思和惦念。
但是另一方面,丁东亚的成绩恰恰和对他的担忧是成正比例的。在这一类关于弃绝者的小说中,《如是我闻》算是一个小小的高峰了——完全可以说,其他的小说几乎都是为了《如是我闻》所做的铺垫与准备,那些要素在这篇小说中以较为集中的方式呈现了出来。我们不禁要问,这之后呢?丁东亚该怎么办?在小小的书写世界中,已经有了自我重复的迹象,那么他漫长的创作生涯难道就要在重复之中耗费殆尽吗?我以为,丁东亚的书写可以朝着两个方向前进:其一,宽广的一面——以弃绝者为核心,扩展到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以清醒和冷静的笔调观察我们的时代和社会、生活,在宽阔的领域中继续书写他“惆怅的诗意”。其二,深刻的一面——抛开对弃绝者表面的展示,而是深入到他们的内在世界,挖掘他们更为深刻的东西,不是匆匆的赶路人,而是长居此处的扎根者,他或许可能挖掘到更为丰富的矿藏。题材的有限性是任何一个写作者都会面临的问题,关键是看他如何调整自己,甚至是他的语言方式。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对丁东亚的创作有着更为久远的期待,我深信在未来的时代里,丁东亚会创作出更多特异而实在的作品,给80后写作带来更扎实的作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本栏目责任编辑张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