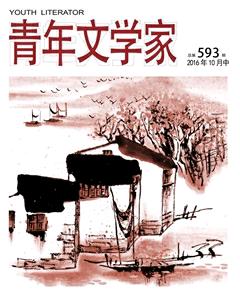《接骨师之女》中的人物原型分析
赵楠楠+李辉+池丽霞
摘 要:谭恩美是华裔美国著名女作家,母女关系是她主要关注的主题之。本文旨在运用大母神和回头浪子两个原型对宝姨和茹灵、茹灵和露丝这两对母女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谭恩美对母女关系的看法,即母女之间因不解造成的隔膜,可以通过女儿对母亲过去的回忆消解。
关键词:大母神;原型分析;回头的浪子;《接骨师之女》
作者简介:赵楠楠,吉林大学英语语言学硕士研究生,防灾科技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李辉,西安理工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防灾科技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法及英美文化;池丽霞,中国矿业大学硕士研究生,防灾科技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9-0-03
《接骨师之女》是谭恩美继《喜福会》、《灶神之妻》和《百种秘密知觉》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与前三部小说一样《接骨师之女》同样是围绕华裔移民母女间的矛盾与和解展开。《纽约时报》书评人南希·维拉德盛赞本书结构,将它比喻成精细雕刻的象牙球,一层镂空里面还有一层,如此层层不穷,构造非常精巧。国内的文学批评也是呈现多种多样。陈爱敏教授主要针对其母女关系的这一主题,人物中国母亲和美国女儿两代间的冲突可以用过分享母亲的回忆来消解;胡亚敏则从后殖民主义分析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建构;而庄恩平教授认为谭恩美对多元文化的看法是解读小说的关键。除了这些学术论文外,还有许多关于《接骨师之女》的硕士论文,由于篇幅受限不一一列举。而本文主要从大母神和回头的浪子对祖孙三代女性中两对母女关系形象进行分析,揭示母亲对女儿矛盾的爱以及女儿对母亲的态度从叛逆到理解的转变过程。
一、 大母神和回头的浪子原型
用原型解读文学作品是在原型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结构主义的方法,“对整个文学经验和批评做原创性的分类对比,寻求文学的本质属性。”[1]原型(archetype)一词来自希腊文,由arche(原初)和typo(形式)合成。原型批评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荣格和弗莱。在《试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中,荣格称原型是反复发生的领悟的典型模式,是种族代代相传的基本原型意象。他认为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是原型或原型意象,并把人的头脑中继承下来的祖先经验称作“种族记忆”、“原始意象”,或“原型”。因此有的批评家把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称为“原型心理学”。“原型批评家认为,最基本的文学原型是神话,各种不同的文学只不过是神话的延续和演变。”[2]因而,原型批评又被称为“神话原型批评。”
分析心理学中的大母神原始意象或原型“并非是存在空间和时间之中的任何具体形象,而是在人类心理中起作用的一种内在意象。” [3]它是原始女神崇拜的最初形态,是伟大母亲的象征。在人类神话和艺术作品的各种大女神(The Great Goddess)形象里都可以发现这种心理表达。大母神这一说法是近代以来才有的,由于原始模型的是正负属性的融合,具有对立统一和二重矛盾性,大母神“具有三种形式:善良的,恐怖的,既善又恶的,” [4]因此大母神可能表现为恐怖母神(如美杜莎),也可能是善良母神(如雅典娜),还有可能是两者的结合。根据埃·诺伊曼,女性的基本特征是大圆、大容器,包容万物,因而大母神积极的一面表现为母性的慈爱、关怀和养育,她消极的一面则为秘密、黑暗、诱惑和恐怖。简而言之,大母神既是创造也是毁灭的化身。浪子回头原型源于《圣经》,是《新约圣经》中《路加福音》15章第11-32节记载的一个耶稣的比喻。回头的浪子是一个犹太年轻人在挥霍浪费了从父亲继承的财富以后又回到家中,幡然悔悟,开始脚踏实地的生活,成为父亲“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儿子。现在浪子回头多指做了坏事或不务正业的人改过自新或是迷途知返的人。在西方文学史中,回头的浪子是历经一丢失自我、又寻回自我的形象,一直深受文人墨客们钟爱。
二、大母神宝姨和回头浪子茹灵
《接骨师之女》中的大母神宝姨既代表了亲属关系和中国血统,又代表了统治和占有欲。宝姨是著名的谷接骨师的独生女,相貌出众,“生着蜜桃般水润光洁的额头,大大的眼睛,丰满的脸颊,中间嵌着小巧而轻盈的鼻子。” [5]她从小就接受教育,很有才气,充满智慧,与当时闺阁中的女子不同,她可以随意出门。大方的性格使她有自己的主见选择自己的婚姻,并大胆地在婚前与未婚夫偷吃禁果。她婚礼当天受奸人所害,丈夫和父亲都丢了性命,痛心疾首之中她想要了结性命,却自杀未遂,但容貌已毁声音已失。为腹中的孩子,她在婆婆家当起了保姆,隐姓埋名,受尽他人鄙夷和冷眼。尽管她不能一名母亲的身份照顾茹灵,但她人全身心地给予茹灵无限的关怀,教她读书写字,嘘寒问暖,极尽所能。童年时期的茹灵在她的保护和照顾下生活安稳满足,尽管她不知道宝姨就是妈妈,还认为宝姨的一切关怀是理所当然,宝姨依然默默守护她的孩子。当然茹灵也是爱她的,她不觉得宝姨丑,甚至还觉得宝姨的嘴是个谜。宝姨善良慈爱的一面是大母神性格中积极包容的一面。
然而尽管宝姨为人智慧,心地善良,但是她性格中消极的一面也因茹灵的不感激、不理解而触发、激化。首先,宝姨的面容可怖,她“右边脸颊里面硬邦邦的有如皮革,左边却湿润柔软。部分牙龈也烧坏了,牙齿都掉了。她的舌头好像一段烧焦的树根。” [6]面容的可怖让人产生厌恶、恐惧的感觉,使宝姨遭到嫌弃。随着茹灵长大,比起来自宝姨的爱,她更期望得到名义上的母亲的关注。宝姨在家中地位低下,受人鄙夷,在他人的影响下长大后的茹灵对待她的态度也变得矛盾起来。小说开篇就对宝姨进行了描写“她不能说话,只能发出喘息声和吁气的声音,犹如寒风的啸声,” [7]由此可见宝姨给人的感觉都是消极的意象。茹灵既热爱、敬重宝姨,同时又嫌弃她,看不起她,甚至有时讨厌她,对宝姨公然反抗。一次茹灵说要取回龙骨,情急之下的宝姨歇斯底里地摇着她的肩膀,打手势说道“你还嫌我为你遭的罪不够多么”。[8]“她捶胸顿足,拼命挥手,比划着说,这姓张的不是东西,就是他杀了我父亲,害死虎森,她拼命发出一种很怪的声音,仿佛恨不得把喉咙掏出来。” [9]失语的宝姨是如何的绝望、无助。当茹灵不顾宝姨的极力反对要嫁给仇人的儿子时,宝姨动手打了茹灵。当这一切都无法阻止茹灵,走投无路的宝姨决心以死来阻止悲剧的发生。自杀后的宝姨化成鬼魂到茹灵的继父在北京的笔墨店,使茹灵的继父在惊恐中打翻了油灯,笔墨店被毁于一旦。“负面基本特征来源于内在的经验,原型女性表现的痛苦、恐怖和对危险的恐惧。” [10]由此可以看出,在仇人心怀鬼胎的危机面前,在自己的女儿不理会自己忠告的情况下,宝姨只能走极端,以狰狞的形象面对所有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的痛苦的人。她的声嘶力竭与死亡、魔鬼等意象联系在一起,这些正与大母神的消极一面对应。
宝姨身上有明与暗的双重特征。以大母神为原型,谭恩美笔下的宝姨形象清晰地跃然纸上,让读者喜爱她的善良,同情她的遭遇,理解她所有黑暗的一面是不公的命运造成的。她的慈爱与极端充分体现了大母神这一原型意象。
作为女儿的茹灵,她对母亲宝姨的态度经历了鄙夷忽视到理解感悟,寻求原谅的过程,这一轨迹恰好符合回头浪子这一原型意象。正如上文提及的,小时候的茹灵不谙世事,跟宝姨很亲,也很听话,但长大后的茹灵,意识到宝姨在自己家中只是个保姆,从内心渴望“母亲”认可的茹灵,开始对宝姨的悉心关怀不理不睬,无动于衷,甚至也开始像其他人一样瞧不起她,对宝姨“尽是怜悯之情,就像怜悯那些乞丐,却不敢直视他们的眼睛。” [11]固执的茹灵不愿意听从宝姨的忠告,执意要嫁给张老板的儿子。宝姨将自己是茹灵母亲和张老板是自己家仇人的事实写下来,让茹灵看,但茹灵认为这是宝姨想要阻止自己追求幸福的诡计,没有读完宝姨的信。最终,茹灵对宝姨的种种警告不理不睬,把宝姨逼上了自杀之路。宝姨的死终于让茹灵醒悟,过去的种种都拼接在一起,悲伤的茹灵去穷途末路找宝姨的尸体,任凭自己被树枝刮伤也抵不上失去宝姨的痛苦和对自己的悔恨。她甚至感觉“一部分的我自己,永远遗失在了穷途末路。” [12]之后,茹灵在各种艰难险阻和生活悲惨遭遇面前都顽强的活下来,但她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想得到宝姨的原谅。最终,茹灵在女儿露丝的沙字中获得母亲的原谅。
三、大母神茹灵和回头浪子露丝
来到美国的茹灵有了女儿露丝,在第二任丈夫也就是露丝的父亲在车祸中去世后,一个承担起照顾女儿的责任,她尽可能给女儿最好的生活,也极力地想保护女儿,不受美国文化的腐蚀。茹灵对露丝的爱是深沉的。一次露丝为了故意气自己的母亲从滑梯摔下去,导致骨折,茹灵非常心疼女儿,恨不得是自己掉几颗牙齿,替女儿承受疼痛,她“并没有生气,她忧心憧憧,满怀爱意。露丝惊讶之余,竟忘记了身上的疼痛。” [13]对女儿的关心让她包容女儿的恶作剧,也没有进行责备。像宝姨教茹灵知识一样,茹灵也教露丝汉字,她不愿女儿舍弃她的中国传统,宝姨留给她的东西她也要传给自己的女儿。大母神中的善良母神可以是“基本特征占优势,也可以显露出恐怖女神的特点,具有变形特征优势。” [14]茹灵身上也有一些恐怖女神的特征。例如,她总是偷看女儿的日记,“母女两人根本不能互相信任。背叛和不忠就是从这种小事情开始的,并非什么惊天大谎言,而是这些生活中的小秘密。” [15]她对女儿的任何行为都加以干涉,指手画脚,甚至在露丝选择和亚特同居后,她还不停地追问什么时候结婚,让露丝觉得自己的母亲简直是不可理喻,造成母女间的隔阂。露丝甚至故意在“日记本里写道:‘我恨她!再找不到像她这么糟的母亲了。她不爱我,不听我说话,根本不理解我,只会挑剔我,发神经,让我更难受。” [16]此外,茹灵对任何事物的解读都和鬼魂有关系,如“打碎了碗,狗叫个不停,电话接起来没有声音,或者听筒里传来沉重的呼吸声,都是鬼魂作祟。” [17]就连露丝都觉得母亲总是盯着她,“她的后脑生着一双魔眼。” [18]在茹灵的精神世界,一切都显得令人胆战心惊。由此可见,茹灵是一位具有恐怖女神变性特征的善良女神。
第三代女儿露丝作为一名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移民,生长在美国土地上的露丝对于自己的中国母亲茹灵一直采取叛逆的态度。中美文化之间的巨大差距,让母女俩不能进行充分的交流。深谙美国价值观的露丝认为母亲是种约束,阻止她做一个真真正正的美国人,她无法理解母亲中国式的好意,也不懂得母亲传给她得中国文化传统有何种意义。母女俩不断地争吵,不断地互相伤害对方会。露丝甚至认为母亲蹩脚的英语和在公共场合大声讲汉语的习惯是她的羞耻。对母亲的疏离、不理解的结果是露丝成年后选择和亚特同居,离开母亲。露丝的这一举动是为了努力融合到美国生活,融入白人生活,斩断她所有的中国根基。可是当茹灵别诊断出为老年痴呆时,亚特的反应很冷漠让露丝既震惊又失望,同居十年,却依然不能在困难时刻互相搀扶。但随着母亲的健康每况愈下,露丝已顾不得自己的个人生活,开始全身心照顾母亲。与此同时,她开始反思自己的华裔身份。“听妈妈讲述自己的故事,陪她回顾生命中经历的种种曲折,听妈妈解释一个汉字的多重涵义,传译母亲的心声,尽量了解母亲的思绪。” [19]她找人翻译母亲的手稿,认真读母亲的回忆录,感受的她的中国血统,了解家族史。渐渐地她认同母亲所给与她的中国传统,迫切地想知道代表着祖母宝姨身份的名字。最后从高灵那得知宝姨的名字是“谷鎏信”后,露丝不禁落泪,因为她终于在这么多年后找回了自己丢失的身份:“宝姨有她的姓氏家族,茹灵也属于这个家族,露丝也是” [20]。通过找到自己的身份,每年三月就会失声的露丝也找回了自己声音,更正了她和亚特的关系,步入婚姻的殿堂。最终,母女俩来得及原谅了对方。露丝终于理解到“这些都是祖上传下来的警示,不是为了吓唬她,而是提醒她不要犯她们当年犯的错误。” [21]从此她不再为别人执刀,她开始为自己、为母亲、为外婆写作。正如一名回头的浪子,露丝最后接受了她的华裔身份,而这也让她找到了完整的自我。
结语:
通过解读大母神和回头的浪子这两个原型,分析宝姨——茹灵和茹灵——露丝两对母女的关系,不难看出谭恩美笔下的母女关系中的爱与憎分明,都是互相爱着对方,但由于不了解造成的不理解,母女甚至会互相伤害,但正如陈爱敏教授认为的那样,母女之间的矛盾冲突可以通过母女共同品读母亲对于过去的记忆来消解。茹灵通过宝姨的信理解了她又慈爱又绝望的种种举动;露丝通过茹灵的回忆录接受了母亲给她的中国身份。外婆、母亲和露丝三代人终于消除了矛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注释:
[1][2]张中载. 原型批评[J].外国文学.2003.No.1:69、71.
[3][4][10][14]埃·诺伊曼,李以洪译.《大母神:原型分析》.东方出版社.1998:3、22、148、37.
[5][6][7][8][9][11][12][13][15][16][17][18][19][20][21]谭恩美著,张坤译.《接骨师之女》.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2、2、2、171、173、181、202、69、37、137、138、9、68、146、331、333.
参考文献:
[1]陈爱敏.论谭恩美新作《接骨师之女》中的母女关系[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
[2]陈爱敏.母女关系主题再回首——谭恩美的新作《接骨师之女》解读[J].外国文学.
[3]周梅香.以沉默的方式打破沉默——解读《接骨师之女》中的沉默与自我伸张[D].南昌:南昌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