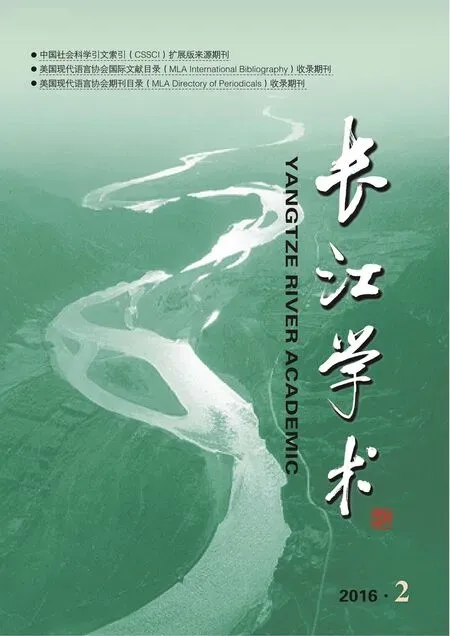“临界处境”启示录
——论科马克·麦卡锡的《路》中之末日恐惧景观
刘堃
(武汉大学 外语学院英文系,湖北 武汉 430072)
“临界处境”启示录
——论科马克·麦卡锡的《路》中之末日恐惧景观
刘堃
(武汉大学 外语学院英文系,湖北 武汉 430072)
2007年的普利策获奖作品《路》人物模糊、情节淡化、故事性弱,丰富的末日景观书写却凸显为文本重心。此乃科马克·麦卡锡实现创作意图的策略。他使人物符号化、情节退隐化,以聚焦末日“恐惧景观”,极致营造作品的启示录效应。从自然、社会和心灵这三个层面创设、展陈的“临界处境”恐惧景观,言说着人与自然、人与同类以及人与自我的失谐。在恐惧景观的背后,爱的“火种”长存,引领人类超越“临界处境”。
临界处境恐惧景观 《路》 科马克·麦卡锡
在当代美国文坛上,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 cCarthy,1933—)声名显赫、风头日盛,近年来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强劲人选。文学批评巨擘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将其与托马斯·品钦(ThomasPynchon)、唐·德里罗(Don DeLillo)及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一起,列为美国当代小说“正典”的四大盟主,认为他是美国文豪麦尔维尔和福克纳的“杰出信徒”①Harold Bloom,Introduction,Bloom’sModern CriticalViews:Cormac M cCarthy,New Edition,ed.Harold Bloom(Infobase Publishing,2009),1.。《路》(TheRoad)是麦卡锡的第十部小说,问世于2006年,荣获2007年普利策文学奖,2009年被搬上银幕。同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路》的中文译本,这是继上海译文出版社于世纪之初首次引进其“边境三部曲”之后,国内对麦卡锡的持续追踪。显然,中国学界对这位美国当代小说巨匠的译介、研究目前还正在“路”上②陈爱华:《科马克·麦卡锡国内外研究评析》,《山东外语教学》2011年第1期。。
《路》被认为是一部“残酷的诗学”,有着启示录一般的冷峻和庄重③科马克·麦卡锡:《路》,杨博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故事开启之际,世界已成一片废墟,寥寥无几的仅存的人类“等待着终结”。一对父子在这种时刻显现于废墟中:寒冬迫近,衣衫褴褛的父子饥寒交迫,仅剩两粒子弹,推着捡来的手推车装着可怜的“装备”,踽踽前行,向南方跋涉。饱经磨难、历尽艰辛,父亲最终生命耗尽,死在了途中;前面长路漫漫,年幼的儿子孑然一人,求存的挣扎依然在继续,至此,故事戛然而止。纵观全书,传统的小说要素都不甚了了甚或阙如。如其一贯文风,麦卡锡对小说情节似乎丝毫没有兴趣。他的情节零碎,既无高潮,也无结局④Donoghue,Denis.“Dream Work”,New York TimesReview of Books,(24 June 1993)6—10.。此等创作特色在《路》中表现尤其突出。《路》的故事性极弱,几乎没有情节。沉默、孤寂、惊恐交加,父子朝着不可知的前方和明天无尽地跋涉、跋涉……,这便是所谓的贯穿整部小说的全部情节;时间、地点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此外,小说中出场人物也屈指可数,主角父与子始终无名无姓,身份只是“他”和“孩子”。对于父与子的外貌读者也自始至终模糊一片、无从想象,对此作者几乎只字未提、惜墨如金。同时,传统的塑造小说人物的重要手段—对话和心理活动,也遭到了最大限度的压缩。文中对话简洁至极。然而,与这般淡化情节、模糊人物、缩减对话等技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者不吝笔墨篇幅、倾力呈现了父子一路所见的一幕又一幕似乎无法穷尽的、令读者过目难忘的恐惧景观。这些景观特写细致精微、栩栩如生,成为撑起整个文本叙事的主体。
作者何以要如此独运匠心,倾尽笔力将景观书写处理为这本小说的重心?
本文认为,刻意淡化故事情节、隐去人物姓名、略去外貌描写、压缩人物对话,诸般手段正是麦卡锡彰显其艺术诉求的创新策略。他刻意使情节退隐化、人物符号化,从而集中笔力、凸显末日“恐惧景观”(landscapesof fear),以便创设想象人类在雅斯贝尔斯所谓的“临界处境”(Grenzsituationen)下的生存,从而震撼读者,收获小说文本极致的“末日启示”之功效。大自然、人类社会以及个体心灵在“临界处境”所呈现的“恐惧景观”,深刻言说了人和自然、人和同类以及人与自身的失谐。在这些恐惧景观背后,爱的“火种”代代不息,成为在“天路历程”上跋涉的人类超越临界处境的唯一救赎。
“临界处境”下的生存
美国麦卡锡研究专家指出,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为2006年麦卡锡创作《路》这部小说提供了深层契机①Luce,DianneC.“Beyond the Border:CormacM cCarthy in theNew M illenium.”TheRoad Home:CormacM cCarthy’s Imaginative Return to the South.Ed.(ChrisWalsh.Knoxville:U of Tennessee New found P 2007),9.。硝烟四起的建筑废墟、惨不忍睹的尸体、恍若世界末日的恐怖图景,震撼了一切有良知的灵魂。人类的自相残杀、生命的脆弱以及绝境中的生存,毫无疑问,引发了作者深邃的思考。显然,极端境遇下的人的生存,人类集体的命运将走向何方,对始终坚持认为死亡才是这个世界之主要问题的②科马克·麦卡锡:《路》,杨博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科马克·麦卡锡来讲,是文学无法回避的的残酷现实,有着极为特殊的书写价值。在他看来,文学本身最应关注探讨的就是生与死。人都是必死无疑的,人的生存始终摆脱不了绝境的压迫,但正是这种绝境压顶的境遇赋予了生存以更深的启示。因而,麦卡锡对不关心生死问题的作家历来不屑一顾③科马克·麦卡锡:《路》,杨博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他只读陀思妥耶夫斯基、麦尔维尔、乔伊斯和福克纳这些热衷探讨生死大问的泰斗的作品。自然,这也成为他最喜爱的创作主题。想象向死而生的人类在极端境遇下的生存图景,探索人类在死亡的阴影下获知的启示,相比精美的情节,当然更为麦卡锡所青睐。当然,《路》的直接创作契机,源于麦卡锡与儿子的一次旅行中的断想:若果世界崩塌,仅剩这旅程中跋涉的父子,他们的生存将会怎样。
在“荒原”中跋涉的父与子,这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中,本就是一个饱含启示的意象。上帝与其子耶稣历尽艰辛寻求希望和出路,以期救赎罪孽深重的人类。这种启示联想,或许正是麦卡锡只设定主角“他”和“孩子”、不予其以名姓的深层缘由。如此一来,人物被典型符号化,其普世性代表功能因而大增。同时,男孩的“母亲”临乱自戕,母性角色的缺失显然被刻意安排,暗示着与之密切相关的形上形下的家园都已荡然无存。一无所有的父子俩挣扎在荒野上,时刻经受着饥饿、寒冷、悲伤,还有随时被别人吃掉的恐惧和地震带来的死亡威胁。显然,麦卡锡已经将这对父子置于了其精心创设的“临界处境”中了。绝境之中求生存,置之死地而后生,麦卡锡所热衷的创作主题,本就具备生存论上的意义,这是人类永恒面对的哲学问题。
所谓“临界处境”,就是指那种人类生存根本无法逃脱或改变的境遇。在《世界观的心理学》中雅斯贝尔斯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这是人生存的一个宿命。他特别提到了四种临界境遇,即死亡、痛苦、斗争、罪责④Alan M.Olson,MetaphysicalGuilt,Existenz 3(1)(Spring 2008):11.。任何人都无法摆脱死亡,在向死而生的历程中,人必须经受巨大的痛苦,竭尽所能地去抗争,才可能摆脱罪责。可见,死亡和痛苦,恰如海德格尔对雅斯贝尔斯的评价,成为“临界处境”的入门①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51页。。也就是说,“临界处境”最显著的标示就是死亡和痛苦。显然,这和麦卡锡以“文学之眼”对生死进行考量异曲同工。命定要死亡的人是无助的、弱小的,无从摆脱“临界处境”,这是人生存的前提。
父与子在末日的世界中经受种种痛苦和磨难,在“只有每个人都死了才好”②科马克·麦卡锡:《路》,杨博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的时刻,直面恐惧和死亡,挣扎求生,显然,是对“临界处境”中的人类生存的形象诠释。或许正是基于此种审视,《时代》杂志犀利地揭示道:《路》揭开了隐藏在悲伤和恐惧之下的黑色河床,灾难从未如此真实过,麦卡锡仿佛是这个即将消失于世界的最后幸存者,……他把未来发生的那个时刻提早展现给我们看③科马克·麦卡锡:《路》,杨博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将处于“临界处境”中的人类的生存图景以启示录的形式展陈于“后911”时代的人们眼前,这其实正是麦卡锡的创作意图。正是由于这种“临界处境”下的生存,人类身处险境,生命反倒被赋予更丰厚的价值,简单的东西变得宝贵起来。人们因而深刻接触到人类基本的价值观,从而被净化④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515页。,深刻感悟启示。
“临界处境”下的“恐惧景观”
恐惧或者害怕,大约是《路》中的“临界处境”无论是对读者抑或书中角色,所激起的最强烈的情感,成为贯穿文本始终的基调。“害怕”一词在文中频繁出现、由孩子之口直接呼告读者。跋涉路上,途径父亲儿时故居,父子俩短暂停留。儿时家园往往让人留恋,会唤起美好情感,然而一路上本来尽力坚强起来的孩子,内心却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惧,以至于从进门到出门这片刻的停留故园期间,他反复念叨,“我害怕”,“我害怕”,“我真得害怕”⑤科马克·麦卡锡:《路》,杨博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显然,一路历历在目的恐惧景观,是令孩子害怕的直接根源,这也正是最能震撼读者、产生启示录效应的景观呈现。相比曲折精致的情节、精细生动的人物刻画、寓意深刻的对话等传统小说技巧,麦卡锡,这位“文学史上所能发现的所有野蛮行径的集大成者,对暴力、屠杀、折磨、掠夺、谋杀的描写都很精彩”的作家⑥科马克·麦卡锡:《路》,杨博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显然更快意于书写这类触目惊心的恐惧景观,其作品因而也被赋予了更鲜明的启示录色彩。
那么,究竟什么是恐惧景观?文化地理学家段义孚如此作答:所谓恐惧景观,就是指混乱的、自然的和人为的力量近乎无限的展示。每个人类构造物,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是恐惧景观的一部分⑦段义孚:《无边的恐惧·序》,徐文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为便于分类探讨,本文将其通俗地理解为混乱失序状况在自然、社会和心灵三个维度上的无尽展示,并以此为路径来解读《路》中的恐惧景观、探求麦卡锡的创作意图。
首先,自然恐惧景观在《路》中的主要体现有二:一是自然界生机全无、已完全丧失孕育和承载生命的能力;二是尸横遍野,死寂无声,俨然阴森的乱葬场。在麦卡锡的笔下,自然永远破败荒凉,远非“我们对人不满时可以退回其中的纯真之地”。⑧段义孚:《无边的恐惧·序》,徐文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荒原是其作品里反复出现的意向,和诗人艾略特形成显性的互文指涉,这在《路》这部小说里,该意象尤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⑨John Cant,The Road,Bloom’sModern CriticalViews:Cormac M cCarthy,New Edition,Harold Bloom ed.(Infobase Publishing,2009),186.“幽暗的森林,冰冷的夜晚,他醒来时,总要探手摸向睡在身旁的孩子。”①科马克·麦卡锡:《路》,杨博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小说引用皆来自本书,下文只标页码。(1)这是小说的第一句话,乍一开头就已经给整个故事定下了阴冷怪异的基调:“荒芜、静寂、邪恶。”(2)这里,有“枯死的芦苇。”(3)“漆墨般的小溪,光秃秃烧焦的树干,灰尘在路面上翻滚,熏黑了的灯柱上耷拉下一截截废电线头在风中啜泣。”(5)这里,会有夜晚中就像地铁一样呼啸而来的地震。(23)这会给人带来怎样的一种恐惧?当大地本身都在颤抖时,我们会突然感到自己被剥夺了安全感的一个终极来源②段义孚:《无边的恐惧》,徐文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页。。自然再也不能孕育生命:“荒地上长出的每样东西都已烂入根茎。环绕着山腰的那些旧庄稼已经死去,沦为平地。荒芜的山脊上,黑色的裸露的枝丫浸在雨中。”(16)“曾经都是富饶的土地。再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186)更可怖的是失却生命孕育能力的荒原如同乱葬场,人类尸体随处可见,死亡气息笼罩一切。小男孩和父亲一路向南的跋涉过程就是一路见证各种死亡恐怖景观的过程。麦卡锡在文中以令人惊悚的笔触聚焦了大量尸横遍野的画面。在荒芜的乡间有“三具干瘪的尸体悬挂在房梁横木上,干瘪、污浊,映着灰莹的薄光”(13)。“遍地是木乃伊般的死尸。肌肤和骨骼分得一清二楚,韧带缩得又干又细,恰如绳索。死人干枯萎缩得如同现代版的沼泽林干尸,脸皮像煮过的床单,一排牙如同泛黄的栅栏。”(19)在浮动的灰烬中,这些尸首被封存在路上,冻结成块,永恒地挣扎着。(176)精心进行诸多类似的恐惧景观的大量特写,麦卡锡的良苦用心昭然若揭。
生机全无,死尸遍野,“这些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让我感到恐惧。”③帕斯卡尔:《思想录:论宗教和其他主题的思想》,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6页。《路》中的荒原景观所营造的正是这样的恐惧。人们长期以来熟悉的世界图景已经彻底消失,无尽的恐惧景观是无言的天启:自然已被彻底销毁,人与自然严重失谐。索尔·贝娄曾赞赏麦卡锡使用的是“关乎生死的句子”,是“对语言绝对的强势使用”,(13)显然,从文本中显而易见的作者想要启示读者的创作意图来讲,其评价颇有见地。
人与自然的失谐加剧着人与人之间的失谐。在《路》中,社会恐惧景观也与荒原的恐怖景观骇然并呈。这种恐怖景观主要呈现有三:第一,人人皆已无家可归;第二,吃人成为生存下去的途径。“吃或者被吃,这是个问题。”第三,人人感受着孤独的折磨,但却害怕与同类狭路相逢。社会,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体,已不复存在、被彻底摧毁。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自然也被“雨打风吹去”。如麦卡锡一贯的喜好,他小说中的人物多半没有家园,他们要么从家里逃离,要么已丧失了自己的家④Terr iWitek,“Reedsand Hides:Cormac McCarthy’sDomestic Spaces”,Harold Bloom edited,Bloom’s Modern CriticalViews:Cormac M cCarthy,(New Edition.Infobase Publishing,2009),23.,总之,无家可归、无处可去,生如浮萍。《路》中的父子俩始终在家园之外流浪。所有的村庄、街道、房屋都杳无人烟;所有的家园皆被摧毁,所有仅存的、苟延残喘的人类都已彻底去根。万物都失去了支撑,在灰蒙蒙的空气里无所依托。依靠一口气熬着,一口颤抖的、短暂的气。(8)显然,这种状况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典型的 unheim lich(陌生、非家、无家可归)。家园一旦散失,此在成为流浪者。人就会“感到无名恐惧而茫然失措”,即海德格尔所说的“畏”。世界面临终结,家庭和社区已被彻底摧毁。所剩无几的仅存者成为游荡在路上的活死人,家园成了永远无法企及的梦想。甚至拨一下家里的电话号码,尽管明知这是永远不可能接通的电话,也能多少慰藉一下流浪者的心灵。“他跨过去,走到桌前,停住了。继而拿起电话话筒,拨下父亲家的号码,那许久以前的号码。”(2)
作为文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位、个体生存的重要依托,家园承载着重要功用。一旦被摧毁,整个伴,他反复追问父亲:“他们在哪儿?他们躲起来了。他们在躲谁?”(169)“相互躲避。”父亲如此简单然而沉痛地回答了孩子。可见,人与人之间已彻底失谐。如此畸零的社会景观,和帕斯卡尔对人类曾有的设想如出一辙:“让我们想象有一大群人披枷带锁,都被判了死刑,他们之中天天有一些人在其余人的眼前被处决,那些活下来的人就从他们同伴的境况里看到了自身的境况,他们充满悲痛而又毫无希望地面面相觑,都在等待着轮到自己。这就是人类境况的缩影。”③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人人在离散的孤独中等着最后一刻的来临,而人与同类间的失谐加剧了这种时刻来临时的恐惧与痛苦。
自然的、社会的恐惧景观投射到个体心灵世界,导致信仰迷失、引起形而上的恐惧。《路》中人物心灵世界所呈现的恐惧景观也意味深长,麦卡锡对此也不遗余力地进行了揭示。父子俩“仿佛哪个神话故事中写到的朝圣者,让花岗岩怪兽吞进肚子里了,找不到出路。”(1)上帝死去,众神远离,父子迷茫困顿,再也找不到信靠。上帝本人的火龙,犹如火星冲起,又泯灭在黑暗无星的夜空。(25)“你在吗?他悄声问。我最后能见到你吗?你有脖子,好让我掐死吗?你有心吗?你这该被永世诅咒的,有灵魂吗?哦,上帝,他悄声道。哦,上帝呀。”(8)在这条路上,没有上帝派来的传讯人。他们都走了,留下我一个,他们带着这个世界一起离去。明天可没为我们作什么准备。明天都不知道我们会出现。衣衫槛褛的众神,无精打采地走过废墟。他们行走在干涸的海底,地面干裂破碎犹如碟子跌落成片。几路熊熊的烈火燃烧在于沙滩上。众神的身影渐渐消逝于远方。(44—45)父子俩偶遇的盲老头,干脆直接宣称,“上帝根本不存在,我们就是他的使者。”(158)在如此境遇中挣扎求存,这是一种怎样的恐惧!失去了最大的存在守护者的牧养,人经受着信仰迷失的痛苦,经受着与自身失谐的社会就基本失范,人类文明必将大大倒退。此时,人类的兽性开始泛滥。在食物缺少的极端境遇中,同类相食不是耸人听闻。《路》中最血腥恐怖的景观莫过于那些人吃人的场面。人被自己的同类圈养在地下室宰杀、烹食。吃不吃人成为善与恶的分水岭。“墙上倚靠着光身子的男男女女,他们都躲闪着,用手挡住了自己的脸。床垫上躺的是个男人,两条腿从屁股下面齐齐被截了去,剩下的腿根子黑糊糊的,烧焦了,发出一股恶臭。”(98)“烧得焦黑的木柴棒混杂着灰尘和骨头,陷在熔化的沥青地里。”(61)“烤焦的无头婴孩的身体,肠肚都掏空了,黑糊糊地粘在叉子上。”(183)“一路上只见尸骨和人皮堆压在石块下。肚肠摊了一地。”(62)麦卡锡倾尽笔力,也无法穷尽诸般骇人场景。吃人或者被人吃成了幸存者唯一的命运。“彼时,所有食物储备都已空竭,大地上到处都是谋杀。这世界忽地兴起一大帮眼睁睁当着你面就能吃掉你儿子、女儿的人。而各城中,结队而行的劫匪穿梭于各处废墟,踩踏在磨白的牙齿、炭色而模糊的眼珠上,用尼龙网裹着不知哪儿来的食物罐头行走着,就如来自地狱的采购买办。”(166)弗洛姆曾说,人类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类有超越本能的意识。我们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存在,意识到自己将要死去。人类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大自然,因此面临着动物所没有的不确定性。于是人类感到孤独、感到恐惧。除非实现与他人的结合,否则我们无法消除恐惧和孤寂感,并最终走向疯狂和毁灭①艾·弗洛姆:《爱的艺术》,李健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海德格尔认为,他人的在场保证了这个世界和人们自己的现实性,使得一个人得以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实现自己的最高本质。可见,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他的生存无法离开同类。然而,在《路》中,和他人的狭路相逢却成为孤独的人类最恐惧的经历,因为这就意味着被人烹食。人是我们安全感的最大来源,同时也是我们恐惧感的最大来源②段义孚:《无边的恐惧》,徐文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孤独的孩子渴求同恐惧。
帕斯卡尔曾说:“真正的恐惧来自信念;虚假的恐惧来自疑虑。真正的恐惧是伴随着希望的,因为它来源于信念,而且因为人们对自己所信仰的神怀着恐惧。前者怕失去神,后者怕找到神。”①詹姆士·里德:《基督的人生观》,蒋庆译,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如此看来,《路》中的恐惧正是这种真正的恐惧。对于“临界处境”中的人而言,无论是怀疑神的存在、还是恐惧于神对人的遗弃,信仰在这里成了生存的支柱和核心。因此,这种恐惧是伴随着巨大希望的恐惧。神必将眷顾不丧失希望的人。故事结尾时,孩子试着和上帝说话,正是对此的最好诠释。
恐惧景观的启示:超越“临界处境”
恐惧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可憎,也更难以忍受②蒙田:《蒙田随笔全集》(上),潘丽珍等译,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为了实现完满的人生,需要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获得控制恐惧的力量。”③詹姆士·里德:《基督的人生观》,蒋庆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可见,直面、控制和超越恐惧是个体生存的根本需求。恐惧,已不仅仅是一种情绪,它关涉着人类生存的哲学本源。麦卡锡在《路》中穷尽笔墨、展陈“临界处境”下的恐惧景观,绝不仅仅是为了激起读者的这种情感反应。正如上文所言,这里的恐惧和希望相连。在这些“临界处境”中的恐惧景观背后,人类逐渐逼近自身极限,在这样的进程中,感悟启示,逐渐走向超越。人不可避免要经受死亡,忍受诸种巨大的折磨。人无从逃避或改变这种宿命,但对这种无助境况的意识能使人们充分感悟自己的使命。雅斯贝尔斯说:“在临界状态中,人类要摆脱或者超越一切将要消失的世间存在,或者指向虚无,或者感觉到真实存在。”正是这些无助、沮丧和失败的经验,给人带来了超越的意识④李雪涛:《哲学的信仰——雅斯贝尔斯对佛教的认识》(上),《亚洲研究动态》第11页,2012年9月第18期,第9—18页。。为了改变当下自我的境遇,人才会努力寻求突破与超越,从而达到个人真实自我的实现。正是在临界处境中,才产生寻找关于真实存在的启示的根本冲动,从而接触到超越(Transzendenz),而通过这个接触,人得以实现自己的存在。
在“临界处境”中却会升起最强烈的生存意识,而后者就是关于某个绝对者的意识⑤参见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4页。。孩子由一开始看到死尸的恐惧,到不再回避、敢于正视;由一开始希望和妈妈一样死去从而免于恐惧之苦,到后来父亲病死路旁、自己接过那仅剩一粒子弹的枪,心中带着“那团火”独自无畏地走向前方,寻求生的希望,显然,孩子心智上日益成熟,开始走向成长。这正是雅斯贝尔斯所谓的人在临界状态之中的超越,这使得进而实现自身的存在成为可能。“他试着和上帝说话,但他最想做的却是跟父亲说话。他跟父亲说话了。他没有忘记。那个女人说这样很好,她说上帝的呼吸就是他爸爸的呼吸,虽然上帝的呼吸会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直至天荒地老。善会找到那个小男孩的。一直都这样。善会再次找到他。”(258)这意味着,孩子实现了“临界处境”的超越,找到了永恒的世界。“在这个永恒的世界中,基督发现了无畏的秘密。他知道不管是自然的灾害,还是人类的残酷,都不能触及到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永恒世界里面的事情。在这个永恒的世界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会受到水与火的威胁,因为水与火的威力永远也达不到这个领域。”⑥詹姆士·里德:《基督的人生观》,蒋庆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结论
“所有的文学作品,通过启发所有人类存在的自然本性,提出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生活?”⑦Love,Glen A.PracticalEcocriticism:Literature,B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3),66.这在“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精神发展、二者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的现当代”①,麦卡锡的《路》尤其显示出这种启示功用。他从人类9·11恐怖经历中,反思了人类的死亡、罪责以及超越等基本问题,尖锐地提出了质疑:人类应该如何生活?
麦卡锡一反传统小说的叙述套路,极力淡化时间、地点、人物和情节等要素在故事叙述中的作用。相反,将自然、社会和心灵世界呈现的恐怖景观视为写作焦点。这些景观营构出了人类所处的“临界处境”,言说着人与自然、人与同类以及人与自身的失谐。人类凭借“保持内心的火种”方可超越“临界处境”、超越恐惧,赢得新生。恐怖景观由而成为推动故事向前发展、深化启示主题的重要推手。
Apocalypto from“Grenzsituationen”: On the Landscape of Fear in Cormac McCarthy’s The Road
Liu Kun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The Road, written by Cormac McCarthy, was 2007 Pulitzer winner. This novel distinguishes itself by ignoring traditional fictional elements as characters, plots but overloading numerous landscape of fear, which is targeted as the focus of the narration. Such literary creation is just the very fulfilling of the author’s writing purpose: to maximize the fiction’s apocalyptical effect by highlighting the landscape of fear to visualize Grenzsituationen. The landscape of fear is dominantly displayed in the nature, society and inner world, as the exact indication of the mistermin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man and his fellows, and man and himself. Man can survive Grenzsituationen by“keeping the fire inside”.
Grenzsituationen; Landscapes of Fear; The Road; Cormac McCarthy
责任编辑:张箭飞
①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刘堃(1973—),女,湖北十堰人,武汉大学外语学院英文系讲师,主要从事美国现当代小说和美国思想史研究。